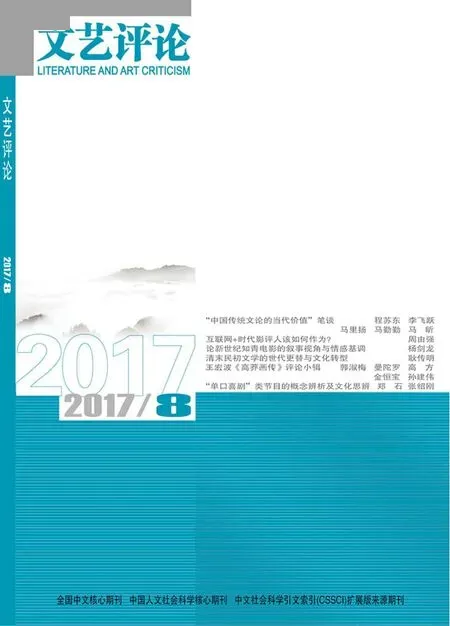孔子“诗教”思想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启示
○马 昕
孔子“诗教”思想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启示
○马 昕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与中和含蓄的审美意蕴。而与这两点同时相关的,首先就是儒家的“诗教”理论。“以诗为教”,成为儒家文艺思想的基本线索,不仅主导着两千多年来古典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而且对教育领域维持着长久而深度的渗透作用。在当代中国,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趋于边缘化,但教育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保障。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其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不再是塑造社会意识形态,而是充当一种教育资源。我们有必要从儒家“诗教”思想中汲取营养,但必须要明白一点:儒家“诗教”思想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必须要分清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不同面貌。
一、儒家“诗教”理论的两重面貌
宋人叶适说:“自文字以来,诗最先立教。”[1]而以诗立教,又起源于《诗经》。《礼记·经解》记载: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
这段话是“诗教”一词的最早出处,引述的又是孔子的话,似乎是最为可信的表述。但《经解》篇的写作时间最早也得在战国中期,[3]甚至有学者推到汉初。[4]这段话又是否真的出自孔子之口,也在疑信之间。我们以此作为儒家“诗教”理论的源头,会将战国时期以来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儒家思想与孔子的原始儒学相混淆,进而得出过于笼统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先将儒家“诗教”理论在孔子那里和在孔子之后的两重面貌分离开来。
所谓“诗教”,必然离不开教育问题。而教育的对象,或是周王庭与各邦国的贵族子弟,或是邦国内的所有臣民。《经解》篇这段话首先冠以“入其国”三字,针对的问题是“为人”,显然是指邦国臣民,这就将“教育”替换为“教化”,将贵族子弟的教育问题转移到社会治理和政治运行的领域。然而,在孔子更为可信的材料中,对《诗经》教育功能的揭示,重点却不在政治教化。《论语·阳货》云: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5]
这段话可以分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鸟兽草木之名”三个层次。最后一层显然与政治教化无关,更接近于对青少年贵族子弟的知识教育。“事父事君”这一层好像与政治有关,但细味语意,就发现远迩有别,其重点其实是“迩之事父”,是对少年人的亲情伦理塑造,而“远之事君”并非指亲疏远近,而是指时间距离——对少年人而言,眼前的任务是“事父”,未来的任务才是“事君”。看来,“事父事君”这一层也完全可以跟政治教化无关。最关键的是“兴观群怨”这一层。《论语注疏》解释为:
“《诗》,可以兴”者,又为说其学《诗》有益之理也。若能学《诗》,《诗》可以令人能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可以观”者,《诗》有诸国之风俗,盛衰可以观览知之也。“可以群”者,《诗》有“如切如磋”,可以群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诗》有“君政不善则风刺之”,“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6]
这段在解释“兴”和“群”的时候,是指向贵族子弟的教育;但解释“观”和“怨”的时候,就俨然是一套政治教化的原则规范。相并列的四个概念,却硬生生分化为两个层面,分属不同领域,这当然可疑。王启兴先生曾提出更为融通的解释:“兴”是指“提高道德修养”;“观”不是观政,而是观志;“群”是“培养人们在社交中符合礼义准则的思想言行”;“怨”是“表达内心的怨愁和不平”[7]。这四条都与个人道德、情感、气质的修炼、养成有关,是对少年人的人生指导,而与政治教化无关。笔者非常赞同此看法,而且愿意增添一些新的理由。
首先,探寻“可以兴”的含意,最直接的参照就是同样出自《论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8]。“兴”有“始”的意思,孔子说“兴于诗”,就是将诗教看作贵族教育的初始步骤,集中完成于成年之前;而“立”是指贵族子弟自成年起,要接受礼的约束,所谓“《礼》本《冠》《婚》”[9],就是强调礼教针对的是成年人,并且以作为成年标志的冠礼为起始;最终“成”于乐教,可见乐教是贵族教育的最终阶段。《论语·季氏》篇记载孔子对孔鲤少年时的教导: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10]
这里只及于学诗与学礼,不言学乐,恐怕也是因为诗教与礼教、乐教分属于贵族子弟人格培养的不同阶段,并以成年(冠礼)为界——乐教完成于成年之后,与政治伦理息息相关;礼教完成于成年前后,是为成年之后的社会生活所做的必要准备;诗教则完成于成年之前,不直接关乎政治,而是一种以锻炼性情、修养身心为主的启蒙教育。这也印证了礼教、乐教和政治有关,而诗教则与政治运作保持一定的距离,是相对纯洁的领地,而更接近教育的本质。
其次,王启兴认为“可以观”就是“观志”,是通过赋诗行为观察个人的思想意志。其证据主要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郑国七大夫赋诗言志之事,《左传》的表述是“武亦以观七子之志”[11],正体现了《诗经》的“观志”功能。这与个人修养有关,而与政治教化无关。此外,《庄子·天下》篇也有一段关于六经性质的著名论述: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2]
若将“可以观”解释为观览各国风俗,则与政治教化联系得比较紧密,是君主通过各国进献的诗作去观察臣民的精神面貌;而将“可以观”解释为观察个人意志,则与道德修养密切联系,更偏重于教育问题。《天下》篇中“《诗》以道志”的说法正好做实了后者。
这样,我们厘清了一个重要的差别:在孔子那里,《诗经》的教育功能只与贵族子弟的性情教育、伦理教育和知识教育有关,与政治的距离较远,属于启蒙教育的范畴;到战国时期的儒家后学那里,例如《经解》篇中,就发展成为针对普通臣民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直接服务于政治生活,属于政治教化的范畴。更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借助着《毛诗序》的影响,在后世发扬光大。
在《经解》篇中,“温柔敦厚”四字奠定了“诗教”的基本品格。这种品格在汉代人编纂的《毛诗序》中被发扬成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和“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些具体的表述,这就使政治教化的意味更加明确与强化。比如《毛诗序》说,《诗经》可以“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13]。如果说“用之乡人”还保留了一分贵族子弟启蒙教育的痕迹,那么“用之邦国”就完全蜕变成为对普遍臣民的政治教化。《诗经》中包蕴的价值理念,原本是对贵族子弟行为方式的约束与制衡,却在这一转变中成为了对普通百姓的思想统治。
《毛诗序》所做的“概念偷换”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使得后人对“诗教”的认识偏差越来越大。东汉末年,郑玄加强了《诗序》中就已萌芽的“美刺说”和“正变说”,并以《诗谱》和《毛诗笺》来系统阐发其观点。到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仍然肯定诗歌“藻辞谲喻,温柔在诵”[14],就是对《诗序》诗教观的发扬。唐代的《礼记正义》在对“温柔敦厚”所作的阐释中,也根本不去谈贵族子弟的教育问题,却提出了“以诗化民”“以诗教民”的主张,仍然在加强“诗教”理论中的政治色彩。这也正是“诗教”说在后世被附加上诸多内涵以至于遭到歪曲和误解的关键原因。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诗教”概念的一些负面评价,多是缘于其与礼教和政教的牵扯。例如闻一多就指出:“诗的女神善良得太久了……她受尽了侮辱和欺骗,而自己却天天在抱着‘温柔敦厚’的教条,做贤妻良母的梦……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15]徐复观也说:“《正义》的解释,乃由长期专制淫威下形成的苟全心理所逼出的无可奈何的解释。”[16]甚至到20世纪80—90年代,这类批评的口吻仍然没有停歇。著名的《诗经》研究专家赵沛霖先生就说:“封建时代说诗的另一个特点和局限性是将‘三百篇’政治伦理化。所谓政治伦理化是指将‘三百篇’奉为封建经典,以封建政治伦理阐说诗义……这种将‘三百篇’封建政治伦理(化)的后果,是使人们只‘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影响是非常恶劣的。”[17]这些说法都没能从儒家“诗教”理论中获得有益于文学教育的有益思想,非常可惜。
本文认为,儒家“诗教”理论实际上包括两重面貌:一是孔子本人的“诗教”观,二是孔子之后儒家后学的“诗教”观,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后者确实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是对孔子思想的偏离,虽然适应了战国以来的社会政治需要,但在现代社会逐渐丧失其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儒家后学的诗教观将“教育”偷换为“教化”,从根本上偏离了文学教育的主轴。而孔子本人的诗教思想则与政治教化没有太大关系,是一套比较务实的文学教育思想,当今的文学教育工作仍可从中获得有益借鉴。
二、孔子“诗教”思想的情感教育属性与当代文学教育
如上文所论,孔子对《诗经》教育功能的界定可分为三个层次——“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和“鸟兽草木之名”,它们分别对应为启蒙教育阶段中的性情教育、伦理教育和知识教育。这三个层面看似游离于不同的问题界面,实则贯穿以同一要义。
首 先,“兴 ”“观 ”“ 群 ”“ 怨 ”都 指 向人的 情感,而以诗歌文本的独特形式来实现情感的生成、表达与沟通,需要一个培养和训练的过程。人在青少年时期,情感最为敏锐,心思最为单纯,在此阶段完成性情教育,当然最为合宜。
其次,一切的伦理建设都难以摆脱情感的基础,在培养情感能力的同时,个人伦理观念的搭建也应展开。《诗经》中的情感,无论是父母之爱、君臣之义、兄弟之亲、男女之情、朋友之谊,这些基本的人伦关系都以情感为纽带。“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基础必然是所兴、所观、所群、所怨之情。
最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虽然属于知识教育的范畴,却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一门指引着年轻人去亲近大自然的学问。《文心雕龙·物色》篇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18]大自然的一切变化,都可能引发人类情感的悸动。而《诗经》中俯拾即是的比兴手法正是最佳的自然读本。因此,与其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一种知识教育,还不如说这是一种自然教育。这也使我们顺便去反思:当今我们对青少年的知识教育本身是否太远离自然了呢?
概而言之,这三个层面都由情感来联结。这意味着:诗歌教育基本上就是一种情感教育。这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教育意义重大。
2017年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之所以引发全民性的关注和追捧,除了新颖有趣的节目形式,恐怕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节目激发了人们内心中丰富的情感。每期节目开场时主持人热情洋溢的演讲,以及点评嘉宾就某一个诗句所作的饱含深情的讲解,都没有使诗歌停留在简单的知识层面。“诗词大会”这类节目考查选手对古诗词的记忆能力,其实最容易堕入对记忆本身的炫耀和对简单知识的迷恋。但这档节目从其设计的细节来看,显然意不在此。
与此互为对比的却是,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中小学教师,对青少年时期诗歌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简单知识的层次上。甚至有很多教育者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缺乏对诗词内涵的理解能力,因此让他们多发挥青少年在记忆上的生理优势,多记多背,囫囵吞枣,就可以了;至于对诗歌内涵的理解,可以留到长大之后性情较为成熟的时候再去进行。但这陷入了一种悖论当中:如果青少年对诗歌只追求记忆,又如何去培养出体悟情感的能力;如果他们行尸走肉般的活过了少年时代,又让他们如何去在长大之后重新回忆起那些已经沦为简单知识的诗歌文本?即便再次回忆起来,又有多少情感能被他们主动地发掘出来,感知得到呢?青少年的诗歌教育,实质就是情感教育。因此,不能等到人的情感萎缩与麻木之后,再去跟他们侈谈诗歌。
目前的中小学写作教育,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主要培养叙事能力,在高中阶段主要培养议论能力,唯独缺少抒情能力这一环节。这使我们担忧,诗教作为一种情感的教育,还能否延续其几千年来的传统,惠及当代中国的年轻人?笔者曾有机会与高中生接触,惊讶地发现:他们对童年时代背诵过的诗篇其实从来就缺少敏感。例如孟浩然的《春晓》这首诗,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诗人为什么会“不觉晓”,为什么会听得到“夜来风雨声”,诗人在面对“花落”场景时内心又该有何种感受?学生们虽然在长大之后仍能流畅地背出这首诗,却无法做到与诗人感同身受,无法进入文学现场,自然也就无法感受到孟浩然青年时期隐居鹿门山时的敏感与闲愁。
从孔子的告诫中可以确信一点:今天的文学教育(尤其是诗歌教育),应当着重培养青少年的情感感知能力(“兴观群怨”),从而增进其与社会(“事父事君”)、与自然(“鸟兽草木之名”)的联络。要呵护他们那颗足够敏感的内心,让他们牢牢记住的不是诗篇中的具体字句或某些“知识点”,而是他们在孩提时期对鸟兽草木的满腔好奇,和他们对父母兄弟的温情与牵挂。
三、孔子“诗教”思想的贵族教育属性与当代文学教育
孔子所坚持的“诗教”,除了具有情感教育的本质属性,还具有贵族教育的特征,这一维度也应引起我们重视。在本文第一节里,我们反复强调过,孔子的“诗教”是针对贵族子弟的教育行为,实际上沿袭了西周以来的贵族教育体系。而孔子毕生的贡献,正是将周王庭官学普及到平凡士人当中。虽然孔子的弟子中多有寒窘之士,但孔子在对他们的教导和培养中,并未改变贵族教育的基本品格。孔子的教育,无论怎样主张“有教无类”,都不是平民教育,而是将贵族教育下移到平民身上,使平民成为具有士人风范的新贵族。
众所周知,《诗经》中有一些富于平民色彩的作品,其中甚至包含一些语近淫亵的诗句。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平民歌唱,羼入了一些直接而又天然的诉求,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但是,当这些带有泥土气息的作品被呈入王庭并收入贵族教本之后,就要被赋予全新的阐释。这虽然势必要偏离诗歌的本来内涵,却非常必要。因为《诗》三百篇首先不是文学选集,也不是展开社会学调查和民间文学研究的田野资料,而是贵族教本。对于如何解读《诗经》、如何学习《诗经》,孔子提出过一个很好的教学建议:“《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9]“思无邪”三个字,正是将平民作品转化为贵族教本的关键方法。
说到“思无邪”,必然要联想到一个与之近似实则不同的概念——“温柔敦厚”。《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这一表述被后人加以过度发挥,认为是理解《诗经》的钥匙,甚至是惟一的钥匙。但其实,深入到《经解》篇的语境中,就发现《经解》作者对六经教化作用的看法都只是一般的描述,并不是对各自本质属性的限定。这就好比,“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句话,也不意味着《春秋》只能教人“属辞比事”,其实也可以跟《尚书》一样使人“疏通知远”。明白这一点,就会知道:《经解》篇说《诗经》可以使人“温柔敦厚”,并不意味着《诗经》就不可以收录“温柔敦厚”之外其他风格的作品。而且,就算《经解》篇真认为“温柔敦厚”就是《诗经》的唯一风格,也不意味着孔子是这么看的,因为《经解》篇只是战国儒学的一个片段,与孔子本人的“诗教”思想仍有差距。历来的研究者,经常不假思索地将“思无邪”与“温柔敦厚”相等同。他们竟然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温柔敦厚”是肯定句式,是对某一特定风格的界定;而“思无邪”是否定句式,只是对负面极端情况的排除。在“思无邪”的规则下,“温柔敦厚”只是众多“无邪”风格中的一种而已。只要不沦落到“邪”的地步,诗的风格与品位当然可以多元。
“思无邪”三个字,对读诗的人虽然有一定约束,但并没有灭绝掉诗歌创作与阐释的多元性。从约束性的角度讲,“思无邪”规定了贵族文学教育的基本品质,使受教育者摆脱了低级趣味,维护了一个贵族该有的矜持;而从多元性的角度讲,“思无邪”也没有泯灭活泼的人性,不至于使受教育者被框定在统一的模板中。而这两方面也正是孔子“诗教”思想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另一重启示。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他将抒情归为“国民文学”(实即“平民文学”)的特质,而将“贵族文学”僵化地理解为雕琢与阿谀这单一的品位。我们今天主张文学教育的贵族追求,并不是要彻底推翻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而只是想提醒当今的教育者们,“贵族”不是对地位与阶层的界定,而是对人格与情操的描述。在孔子的时代,具备一种贵族化的人格,是对纷纷乱乱、丧失底线的时代浊流的一种反击;而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也面对着生活中的种种浊流吗?当我们的青少年沉迷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让他们明白,高贵的品格比金钱与享乐来得更为实在;是不是该让他们懂得,“思无邪”是一种既矜持又包容的眼界与气度?如果说当代中国的文化局面与孔子所面对的“礼坏乐崩”有某些相同之处,那么我们在对下一代展开文学教育时,是否也应依靠着一种“贵族化”的精神操守与文化坚持,开出一条有益的道路?
首先,我们也需要坚持多元性,不能泯灭青少年多样化的人格情操和精神风貌。有的孩子沉醉于“求之不得”的爱情,有的孩子更喜欢“与子同仇”的豪迈,《诗经》中容纳了多种多样的主题,每个人都能从中各取所需。甚至同样写爱情,《诗经》中的爱情诗篇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类型,满足了青少年对爱情各种各样的想象。只要不堕入“邪”的陷阱,《诗经》呈现给我们的是充分的自由。不仅《诗经》如此,整个文学世界也都是如此。
其次,“思无邪”还意味着一种贵族化的坚持,要让孩子们明白,我们需要终其一生地与这滚滚红尘展开一场持久战,以维护一个君子该有的尊严和节操。例如,孔子说《关雎》这首诗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少年人读到它的时候,应该明白:当我们陷入爱情之时,纵然“寤寐思服”,纵然“辗转反侧”,也要保持君子般的风度,对那“窈窕淑女”,可以“琴瑟友之”,可以“钟鼓乐之”,但不可以像《野有死麕》中的男人那样动手动脚,连狗都会惊觉。我们不希望青少年把《诗经》乃至整个文学世界当作成人影片,这在文学的领域里或许是“迂腐”的,但在教育的话语中却是多么的必要啊!当今中国的文学教育者们,对孔子的“诗教”思想,应尽量放下那些尖酸的指责,而葆有一份尊重和坚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叶适《叶适集》卷一二《黄文叔诗说序》[A],《丛书集成续编》第129册[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12页。
[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五(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8页。
[3]王锷《礼记成书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4-209页。
[4][16]参见徐复观《释诗的温柔敦厚》[A],《徐复观全集·中国文学论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页,第405页;杨天宇《礼记译注》(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49页。
[5][6]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一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第237页。
[7]王启兴《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J],《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
[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9]班固《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第10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40页。
[10]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一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1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八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3页。
[12]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67页。
[1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4]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68页。
[15]闻一多《诗与批评》[A],朱自清等编辑《闻一多全集》,第 3册[M],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 231—232页。
[17]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8]《文心雕龙义证》下册[M],第 1728 页。
[19]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三家《诗》辑佚史研究”(14CZW0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