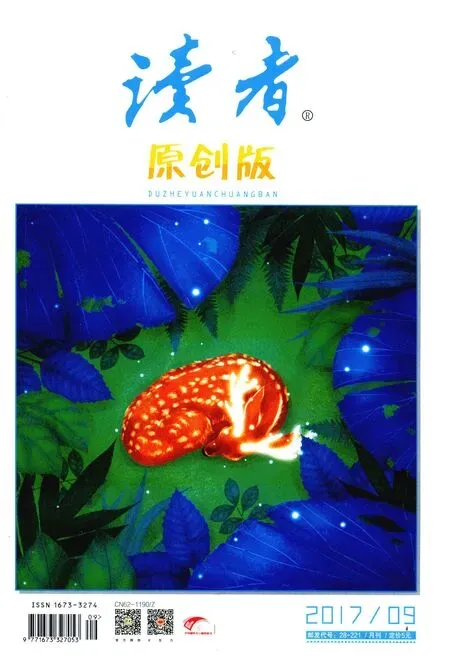手艺人的小酒局
文|寇 研
手艺人的小酒局
文|寇 研

2010年9月一个细雨迷蒙的日子,我买了张机票,拎了一只包,来到西安。本打算回学校继续读书的,听了几堂课后,我骨子里不安分的“坏学生”因子被激发出来,然后是永久性缺课,继续捣鼓我的文字去了,但从此也就留在了这里。来西安的第四年,我组建了自己的一个小团队,我称之为“喝酒三人组”。
三个人第一次碰面,是在晗的服装工作室。她个子娇小,年过四十,脸上却没有这个年龄的女性常有的疲惫和焦虑。晗从小热爱缝纫,用她的话说,一辈子都侍弄针线,能靠一技之长在这个城市立足,是她一直的梦想。她做到了。
那一次,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木桌周围,我对面的凌子,一面自如地喝着茶杯里的酒,一面与我们谈笑风生,根本不把高度的二锅头当回事。这使我这种平时总馋酒,可一喝烈酒就退缩的人,顿时对她无限崇拜起来。
喝酒的人自然知道,能不能一块儿喝酒,第一次酒局就能互相感知。第一次之后,我们三个人继续约酒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有人负责带酒,有人负责准备下酒菜,似乎有一种久已存在的默契。
不久,凌子的瑜伽工作室完工,我们的约酒地点便转移到她会客用的榻榻米房间。凌子是一个性格温和又非常独立、有主见的陕西女孩,她本来是学机械的,在日本留学期间鬼使神差地迷上了瑜伽,从此开始疯狂研读相关书籍,四处拜师学艺,回国短暂休憩后便开办了瑜伽工作室。从刷墙到铺地板、量榻榻米尺寸、裁窗帘,都是自己一手拾掇,用她的话说,她就是喜欢做手工活,难得有机会实践一把。
记不清多少次了,我们仨各据一方,盘腿坐在矮桌前,就着茶和酒,就着花生米、蔬果沙拉和一些小零食,慢慢说话,慢慢喝酒,从日落之前,一直坐到夜灯初上。窗外,城市高楼隐身在霓虹灯的氤氲中,落地窗涌进丝绒般的夜色,房内光线逐渐暗淡,只有眼睛里有光在闪耀。等夜色再沉下去一些,凌子才会打开墙角的梨形落地灯。
有时窗外起风了,盛夏傍晚突然袭来的狂风,从高楼中间呼啸而过,雨滴击打着树冠,间或斜射在窗玻璃上,噼里啪啦,一阵热闹。我们偎着落地灯一点昏黄的光,看着窗外的树在风雨的裹挟中呈现各种妖娆的怪姿,静悄悄地不说话。说不上岁月静好,只是觉得无比幸运。晗做服装工作室,凌子开瑜伽工作室,我自由撰稿,三个手艺人各凭自己的一技之长谋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终在这个城市立足,能在外面风大雨大的时候安坐室内,喝酒喝茶……
我们绝少喝醉,微醺即止,成年人的自制以及酒局结束打车安全回家的要求,都让我们适可而止。唯有一次例外,晗离婚了。20年的婚姻,积累了诸多的不满和不舍,最后走向分手,令人心痛。那晚我们都喝多了,各自拥着毯子,胡乱躺在榻榻米上。那是唯一一次,三个人越喝越沉默。算起来,三个人的年龄都不小了,都早过了所谓的“适婚”年龄,连最小的凌子也已过而立之年。人们总说人生无常,许多人一生的风光、低谷或重生,无不辗转于爱情与婚姻之中。
但又一次约酒时,我们谁也没有提这件事,不是刻意回避,而是那一阵感喟情绪过去,又实在不觉得男朋友、婚姻、家庭是一件那么重要、需要时刻拿出来讨论的大事。再说,那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吗?我们偶尔也会试探对方:“哦,上次我看见与你一起的那个男人……”“那位啊,只是普通朋友啦。”对话不过如此,被询问者想说就说,不说也不会有人追问,更不会有“我有一个朋友还不错,介绍给你”这样尴尬的提议。
我更中意这种成人间浓淡相宜的友情。也许中国人过日子就喜欢热闹,热衷于参与别人的生活,以朋友或闺密的身份全面介入对方的隐私,各种调查、各种建议、各种苦口婆心的劝阻,美其名曰“为朋友两肋插刀”,可其实不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的城市版本吗?
大约这也是我分外喜欢待在这个陌生城市、分外享受我们三人小酒局的原因。我们随身携带着各自的职业印记,同时对彼此的技艺心存敬畏,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今的环境中,我们各自在为把结婚生子变成“人生的一个选项”而付出。我们不是单身贵族,但也不是悲惨的“单身汪”,更不是独身主义者,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活着—努力工作,磨炼自己的手艺,过自己的小日子,喝自己的小酒。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探索人生诸多的可能性。
我毫不怀疑,有一天,我们中间有人会结婚,也许还会有孩子,那一定是她遇到了合适的人,而不是迫于某种压力。我也知道,我们的小酒局兴许在某一天会悄然终止,因为友情跟爱情一样,当节奏不能保持一致时,便会各自散去。但这正是人生的精彩之处,遇到,同行,渐行渐远,遇到新的人。无比幸运的仍是,外面风大雨大,我们曾同坐一处,喝酒饮茶,看风看雨。然后酒局结束,各自打车回家,进门那一刻,发一条信息互相告知:已安全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