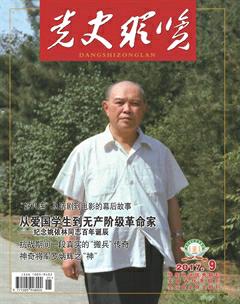“好八连”:从话剧到电影的幕后故事
王梦悦
20世纪60年代,由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创作的大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一经公演,便引起巨大轰动……一条普通的马路,造就了一个天下闻名的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曾是几代人的经典记忆。
没有硝烟的战场
1949年春夏之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在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攻入大上海,他们严守军纪,风餐露宿,接管了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特务团三营第八连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进驻到俗称大马路的南京路执行警卫任务。
解放前的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位于市中心的南京路更是繁华,这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解放之初,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派出潜伏特务,采用“腐蚀拉拢加破坏暗杀”等手段实行骚扰,并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解放军红的进来,不出3个月,就让他们黑的出去。”
那时,八连的任务是在市中心站岗巡逻。受环境影响,有些战士经不起灯红酒绿的诱惑,思想产生了动摇。有的去饭店开“洋荤”;有的不惜花钱到高级理发厅理发;有的不抽老烟叶子了,去买一块多钱一包的雪茄;个别战士花光津贴费还要向别人借钱逛“大世界”。战士童新根甚至向班长提出,白天不上岗,要求与别人调换,改站夜班岗。起初班长感到奇怪,夜里站岗不是更辛苦吗?童新根说:“站夜班岗比看一场电影还刺激。”因为每当夜幕降临,都可以看到那些衣着时髦的男女们相互挽搂着进出舞厅电影院,站在哨位上的他总会禁不住朝丽人瞟上几眼、嗅闻飘逸的玫瑰香,艳羡不已:“南京路上的风都是香的。”连里还有一个排长,开始嫌弃老家的妻子太土,闹起了离婚……作为連队首任指导员,善于观察的张成志发现有些干部战士受环境影响露出了不太正常的苗头,感到在南京路上不能仅仅是简单地站岗巡逻。他开始苦苦思索,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部队怎样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呢?
针对连队出现的不良现象,张成志在党支部会上指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他组织全连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领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并豪迈地提出了这样口号——“革命战士穿草鞋,香风臭气脚下踩!”
连队炊事班有一口在淮海战场上用过的行军锅,老班长背着它过了长江,一直背到南京路。当时不少人劝他:“到大上海了,铁锅钢精锅有的是,你就扔掉它吧。”老班长说:“行军锅不能丢,我们能用尽量用,还要艰苦奋斗。”
每天,八连指战员脚穿草鞋,肩扛铁锹,豪迈地喊着口号,走过大光明电影院前的南京路,步行去郊区拓荒种菜。每到盛夏,街头赤豆棒冰只卖4分钱一根。而八连的每个战士却都背着水壶,天再热,也舍不得花钱去买棒冰吃。在常人看来这样似乎太寒酸了,但是战士们把省下来的钱存起来,作为“爱国储蓄”。连队有个小银行,给每个战士一张小存折。战士们每个月都要从6块钱津贴费中,拿出一点钱放到小存折里存着,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这些小故事后来被一个有心人一件一件都记在了本子上,最后升华成影响整整几代人的大文章。这个人叫吕兴臣,是八连所在团机关俱乐部主任兼通讯员。他时常挎着照相机在几个连队里巡走,把驻守在南京路上的几个连队比来比去,总觉得八连训练成绩突出,完成任务也比较出色。一天,吕兴臣对八连第二任指导员刘仁福说:“你给我介绍你们连几个动人的故事吧?”刘仁福摇摇头说:“没有什么事,你不用报道。”吕兴臣还是不甘心,他把包里的照相机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将一分钱带掉了出来。看到这一分钱,刘仁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我们八连就有一分钱的故事。”随后,刘仁福慢慢地讲起了一分钱的故事……
1957年,吕兴臣前后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篇通讯,并把稿子送到了解放日报社。报社总编看到稿子后,顿觉眼前一亮,敌人曾预言上海是个黑色大染缸,现在快10年了,八连红旗不倒,宣传出去一定会产生很好的政治影响。很快,《解放日报》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 人们称赞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为题,率先报道了八连的事迹。1958年3月23日,《解放军报》以同样的标题刊出吕兴臣的报道。此后,吕兴臣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针线包》《行军锅》和《一分钱》等一系列反映八连官兵优良作风的小故事。1959年2月,解放日报社领导建议把八连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用“艰苦奋斗”这根主线统领全文。于是,吕兴臣写出1.7万字的初稿,几经修改,刊登在《解放日报》7月23日头版头条,同时报社还配发了社论。这篇8500字的长篇通讯题目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好八连”的美名就这样传开了。
“毒草”起死回生
1960年,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带领军区机关部长以上干部到浙江沿海巡视,返回时路过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接待了他们。席间,王必成对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沈西蒙说:“西蒙啊,你知道吗?上海有个好八连。你是文化部长,写了不少戏,也为好八连写个戏吧!”
新四军出身的剧作家沈西蒙曾写过《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等优秀作品。他当即回答:“好啊,但是我有个要求,我要到八连当兵去,亲身下去蹲一段时间,亲自体验生活。”
于是,沈西蒙和导演漠雁都“剃了光头,背上背包,登上草鞋”,下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
这段在八连的生活让漠雁终身难忘,他后来在《温馨的回忆生活、创作与纪实》一文中写道:“1961年春节刚过,遵照部队首长关于部队的作家要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去熟悉生活,熟悉战士,写出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的指示,沈西蒙同志率先带头,剃了光头,背上背包,登上草鞋,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当了一个月的兵。步他后尘,同年3月17日,我也剃了光头,背上背包,登上草鞋,由吕兴臣同志引荐,来到好八连,向连长张继宝、指导员刘仁福敬礼报到。”
沈西蒙也在《创作回顾》中写道:“和‘好八连战士生活的过程,就是接受教育、改造思想、理解生活、解剖典型、搜集材料的过程。吸吮了生活的乳汁,获得了丰富的营养,产下的‘婴儿才不会先天不足。”endprint
除此之外,前线话剧团的主要演员在接受任务后也住到八连体验生活。由于连队没有女兵和女眷宿舍,当时的指导员王经文和连长就把他俩住的一间房腾出来,给女演员陶玉玲住。为了照顾女性,就没让她站岗开荒,而是分配她在炊事班里帮助洗菜、摘菜、做炊事等后勤工作。
最初的话剧剧本取名为《南京路进行曲》,后又先后改名为《霓虹灯下遭遇战》《霓虹灯下的奇兵》,前线话剧团在排演中正式将这部戏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
《霓虹灯下的哨兵》如今可谓家喻户晓,而这部在我军文艺史上享有辉煌声誉的作品,却曾被认为是“毒草”,差点遭到扼杀。
该剧在排练初期就遇到了麻烦。有些人指责说:“这是一株毒草!”并列举出了许多理由,比如,戏中的新战士童阿男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林媛媛谈情说爱;排长陈喜经不起“香风”熏染,丢掉了老家带来的土布袜子,与乡下妻子春妮分手;老战士赵大大不安心在南京路站岗,申请去前方;尤其是童阿男为受伤的罗克文输血,是无产阶级战士的血输进了资产阶级的血管,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在当时,这些情节被认为是给我军抹黑,给好八连抹黑!
面对种种责难,沈西蒙等人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关键时刻,远在北京的《剧本》杂志主编张颖为他们解了围。张颖将该剧所面临的责难和即将遭到扼杀的困境反映给了周恩来,引起了周恩来高度重视。而正是因为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可,这部话剧才得以起死回生,重登艺术舞台。
从此,《霓虹灯下的哨兵》像一股旋风,红遍了大江南北……
从话剧到电影,“哨兵们”走进千家万户
1963年初,南京军区党委把八连作为重大典型,上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看了八连的材料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又对八连的具体情况作了进一步了解,他决定把八连作为保持艰苦奋斗革命本色的一面红旗树立起来。一个多月后,《解放军报》用4个整版的篇幅介绍宣传了八连的事迹,同时发表了《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社论,随后又陆续对八连进行深入宣传报道。4月,国防部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后,八连代表刘仁福、王经文一行去北京向总部机关及驻京军事院校等单位报告连队事迹,萧华在家里用江西菜招待了他们。萧华高度评价了八连的工作,他说:“好八连的事迹和雷锋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雷锋和好八连都是对部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活教材,在一定意义上讲,好八连就是集体的雷锋。”
4月12日,周恩来接见刘仁福,勉励他说:八连的工作做得很好。希望八连的同志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学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建军路线建设连队,继承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荣誉称号,“好八连”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典范。5月8日,《人民日报》专门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命名发表社论,同时还发表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长篇通讯。随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热潮,许多单位、团体、个人给八连官兵写信,表达敬意,表明学习八连的决心。“好八连”被国防部命名后的一个月内,朱德、邓小平、陈云、陈毅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都纷纷为其题词。
1963年8月1日凌晨,毛泽东欣然挥就了诗篇《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紀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1963年11月29日晚,中南海怀仁堂上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当演到童阿男把军装一脱要离开连队时,坐在观众席里的毛泽东十分着急,喃喃自语道:“童阿男,你可不能走啊!走要犯错误。”当童阿男重新回到连队时,毛泽东面露笑容,微微点着头,说:“回来就好,改了就好。”演出一结束,毛泽东便走上舞台同演员一一握手,边走边说:“连长、赵大大,还有老班长,演得好。”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美名远扬,为了让全国亿万观众都能欣赏到这部经典剧目,拍摄一部电影无疑是好的选择。
据在话剧和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老班长洪满堂的扮演者刘鸿声回忆,话剧改编成电影主要还是周恩来拍的板,他说:“1963年前线话剧团进京演出期间,有一天,周总理在西花厅宴请剧组成员,陪客包括陈毅夫妇、夏衍等人。宴请结束时,大家又一起谈起这部话剧,总理提出一定要把这部红色经典搬上银幕,并且特别关照说:拍电影用演话剧的原套人马,最好一句台词不要改,一个演员不要换。由于是部队题材,总理还点名要八一厂的王苹来执导。为了方便拍摄,总理还指定由好八连所在地的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来摄制完成。”
1964年初,由王苹任导演,沈西蒙任编剧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南京路实地完成拍摄,并在全国公映。随着影片的公映,“哨兵们”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部脍炙人口的电影成为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生活中的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虽然在今天看来,话剧和电影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有着很大区别,原汁原味地把一部话剧搬上银幕,在摄影和制作技术上不好处理。但是,无论是话剧还是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都从根本上表现出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因此,至今看来仍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吴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