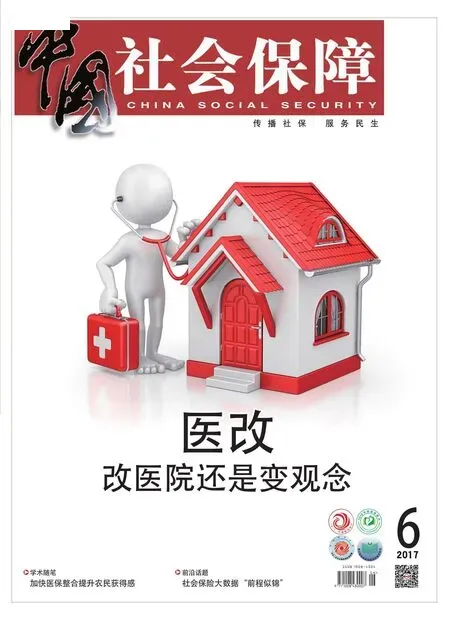医改裂变,医保支付改革是制度性促因
■文/顾昕
医改裂变,医保支付改革是制度性促因
■文/顾昕
促进分级诊疗的发展在2016—2017年成为新医改的重中之重。其实,如何让基层医疗机构以及各级中小型医院在医疗服务领域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从而改变大医院人满为患、中小医院门可罗雀的局面,让既有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这是自新医改启动以来,甚至是在新医改启动之前,就早已提上政策议事日程的老大难问题。
无需赘言,促进分级诊疗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落实这一改革工作的政策路线图直到2017年才逐渐清晰起来。在国办发〔2017〕37号文件所列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中,第17项为“探索对纵向合作的医疗联合体等分工协作模式实行医保总额付费等多种方式”。此项工作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局、财政部负责实施。这一改变与罗湖医改的成功启示不无关联。
在2017年之前,促进分级诊疗的政策举措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密集,但林林总总的政策,其特征可以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行政化”。这些政策多由卫生行政部门所主导,政策工具都具有命令与控制的特征,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向基层倾斜,以图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命令更高层级的医疗机构调动优质人力资源到基层去展开帮扶工作。
卫生行政部门的命令型政策,从医疗卫生专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参照初级卫生保健的全球性发展,还是顺应整合医疗发展的大趋势,都是正确的。然而,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正确的命令却没有达成政策本身设定的目标,以致命令者必须采取其他行政手段,不断加以控制试图使命令得以执行,但结果依然是不尽如人意。

行政化之举的效果不理想,其关键在于利益关系没有厘清。命令之后还要施加控制,这本身就说明命令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被命令者的利益,于是命令者被迫需要施加控制以迫使被命令者去执行不利于自己的命令。这些年来,政府不断命令社区卫生机构为民众提供“六位一体”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试图扭转这些机构专注于医疗服务的倾向;政府不断地敦促高层级医疗机构下基层去帮扶,继而通过“拉郎配”的方式推动医联体建设。这些行政化之举尽管花样百出,但都不大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高举公益性的大旗而避谈利益,这在儒家中国有着上千年的传统,其结果就是有损公益性的行为在中国大行其道,而那些践行公益性行为的人都变成了仁人志士,至少是“有情怀”的人,成为众人敬仰的对象。新医改的理据貌似与儒家不相干,但这种只言“义”不谈“利”的传统思维方式,弥漫在这些年医改大政方针的决策与执行之中,也弥漫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强基层、医联体建设、分级诊疗促进(小病进社区)等具体改革举措之中。
无论何种行为具有多大的公益性,要想推而广之,使之成为相关人员的日常之举,而不是什么理想、情怀甚或“感动中国”的行止,要旨就在于让行此之举的人从中获得应得的利益。这就需要我们打破行政化的思维与政策窠臼,另辟蹊径,探寻一条新的改革之道和改革之路,即市场化和去行政化。实际上,这种改革之道和改革之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早已行之并有成功的经验,而且在中国新医改的进程中,也早已载入了执政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文件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市场机制的运行在各个行业之间有不少共同的特征,但不同行业中市场机制运行是否良好,还有不少差异性。换言之,市场治理模式具有某些行业性的专属属性。就医疗行业而言,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关键在于公共契约模式的建立,即政府主导的公共医保体系与多元化的医疗机构建立医药服务集团购买的契约关系。简言之,首先,政府主导推动全民医保;继而,医保机构力行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代表参保者就各种类型的医疗服务与医疗机构签订各种类型的“打包付费”的支付契约;再次,医疗供给侧形成多元办医的格局,通过为民众(参保者)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竞取来自医保机构的支付。
具体而言,从医学角度而言,初级卫生保健和整合医疗的发展有利于民众,因此具有公益性。要想推动其发展,关键在于让其践行者从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很显然,如果付费者按项目付费,且政府管制者按项目定价,那么绝大多数服务提供者就没有长久的积极性去提供初级卫生保健中那些不大可能收费但却对民众有好处的服务,他们也不会有多大积极性去关心从预防到医疗再到康复的全链条整合。在按项目付费主导的付费体系中,服务提供者获取自己赢得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多收病人、多提供医疗服务,甚至出现供方诱导医疗服务的情形,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在这样的体系中,医疗供给侧的管理者们也没有多大积极性进行成本控制,例如将医学检验、放射影像、消毒供应、社康管理、健康管理和物流配送等业务整合起来,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进行共享,更没有积极性对药品的性价比进行分析以遏制药价虚高。在按项目付费和按项目定价所框定的利益格局中,即便促进初级卫生保健、发展整合医疗、遏制过度医疗的公益性是众所周知的,命令与控制的行政之举在短期内只能是事倍功半,从长期来看也只能是劳而无功。
罗湖医改的宝贵经验就在于公立医保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通过谈判协商建立了全新的公共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的要害在于医保机构采用了总额预算制或按人头服务的新支付体系。根据罗湖医院集团所吸引到的参保者人数,深圳市医保机构实行签约参保人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总额管理、结余奖励”。
总额预算制(global budget)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医保支付方式,即医保机构在预算年度内向医疗机构支付一整笔费用,医疗机构必须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面向参保者完成协议规定的医疗保健服务,超支自理,结余归己。如果总额预算的测算依据是医保机构签约的参保者,总额预算制就变成了按人头付费(capitation)。简言之,人头费乘以签约参保者人数就成为医保机构向医疗机构支付的年度医疗费用总额。
人头费的核定是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双方谈判的产物,但其测算也是有据可依的。如果人群规模足够大,那么人均年度医疗费用就可权做人头费。更为精细的测算依据是将人群分组,例如按年龄分组、按性别分组、按慢性病分组,不同组别的人头费有一定的加权,权重测定在医疗保险专业中被称为“风险均等化”(risk equalization)。
无论是依据粗犷还是精细的测算,医保和医疗机构谈判商定的第一个重要事项就是签约参保者的年度医保支付总额。深圳市医保机构给予参保者充分的就医选择权,这意味着所有同罗湖医院集团签约的参保者,其部分医保覆盖的医疗费用发生在罗湖医院集团之外。医保机构在年终结算时将外部发生的费用从双方商定的总额中扣除,剩下的余额全部支付给罗湖医院集团。
由此,罗湖医院集团为了保证运营顺利并提高所有医务人员和其他员工的待遇,必定会想方设法至少做好如下几件事情。
第一,尽可能地吸引参保者与集团签约,对其健康管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第二,全力开展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和其他健康管理,自动让“六位一体”从卫生行政部门的纸面要求变成医疗机构的日常业务,从而让签约参保者们尽量少去医疗机构,无论是集团内部还是外部的医疗机构。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者的专业“情怀”瞬间可以变成现实。
集团不仅会如报道中所提到的为老年人签约家庭免费安装扶手,而且一定会积极为签约民众选择最好的疫苗。那两位仰赖贩售劣质疫苗而大发横财的山东母女在罗湖区根本不可能找到客户,而当地的疾控监管者也无需对疫苗的生产、流通和使用进行全方位、全环节、全天候的监管了。
第三,集团所属的医疗机构会大力激励医务人员,一方面提升医术,另一方面加强医疗服务的人文性,尽量让签约参保者在集团内部完成必要的医疗服务。即便做不到这一点,也会扮演好医疗咨询师的角色,合理转诊,让签约参保者在他处获得性价比高的医疗服务。否则,签约参保人在其他地方的花费越多,集团的收益下降就会愈加严重。
第四,集团会大力控制非人力成本,医疗资源的共享就是其中的办法之一,另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压缩采购成本。由此,即便政府不实施药品采购零加成和“两票制”,药价虚高也会不治而愈。
由此可见,分级诊疗也好,与分级诊疗有关的医联体建设也罢,其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行政举措多么繁多、多么强悍,而在于利益格局的重构和激励机制的重建。这其中,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