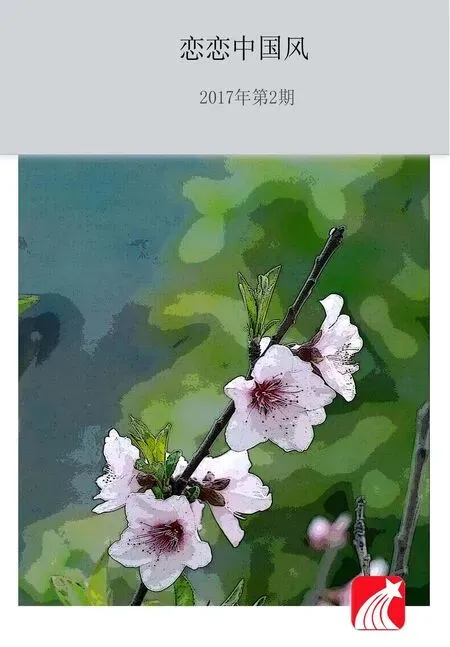墨色里走来,把寂寞采摘
◎绥 曳
墨色里走来,把寂寞采摘
◎绥 曳

他身上有说不尽的故事,让岁月如同纸幅上的墨点,由单薄变得厚重。世人皆说,徐渭徐文长一生风流落拓,狷介疏狂。可被他描摹过的山石草木都知道,他的内心那样温柔,却又藏着深入骨髓的寂寞。
就像所有波折都曾有过美好的开端,徐渭也曾是惊才绝艳的少年。他当时不过十多岁的年纪,仿照扬雄纵横捭阖的《解嘲》作出一篇语惊四座的《释毁》,名动城郭。面对铺陈的白宣,他提笔蘸墨,洋洋洒洒便是诗词文章。那蜿蜒的笔画随着墨痕舒展,仿佛在勾勒一个顺遂光明的前途。
待年岁稍长,他研究王阳明的学说,也叩问禅道精髓。那些烛光掩映下翻阅过的书卷,还有静心聆听过的教诲,都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但并非所有学说都能托起鸿鹄志向,彼时唯有科举才能给予士子扬名立万的可能。
九岁的他便能写出求取功名的文字,十多年过去,却早已荒废八股。虽思及仕途之时对所学庞杂偶有悔意,但当他读到他仰慕的古人文章时,床榻周围遍布卷轴图谱,沉思之际早已忘却晨昏。他的思维挣脱了缰绳,在广阔的原野上驰骋,再难束缚。
屡试不第,从前的赞誉变作嘲弄,纵然他可以充耳不闻,却无法对心中家国天下的理想视而不见。壮志难酬,是多少士子心中之痛,不是为与朱门相隔而惆怅,而是因拳拳赤诚无处安放生出连绵憾恨。徐渭亦害怕斐然才思在岁月的罅隙里流失殆尽,从此变得碌碌庸常。
所以,即便身为一介布衣,他亦忧国忧民。彼时东南边境难安,倭寇侵扰之下百姓流离失所。他换上短褐,随大明将士奔赴前线,于金戈铁马中细察局势,写就一篇篇见解独到的方略呈至官邸。而城中掩面而泣的妇孺,沙场上泛着寒光的铠甲,都在徐渭心底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那些直抒胸臆的诗文,皆是最真挚的动容。
这份默默坚持为他带来了一展韬略的机缘,年近不惑的徐渭得到直浙总督胡宗宪的青眼,入其幕府执掌文书。徐渭没有辜负胡宗宪的赏识,为报知遇之恩,他代笔而作《进白鹿表》,得到天子赞许,为胡宗宪在政治上扭转格局。后来擒徐海、诱汪直的抗倭谋略,亦有徐渭的功劳。
身为幕僚的六年,是他人生中最光辉的日子。他并不仰慕泼天富贵,而是需要一份笃定的认同,胡宗宪恰好给了他不可多得的信任和礼遇。这位杀伐决断的总督,统领边兵威震东南,寻常将吏皆对其匍匐恭谨。唯徐渭葛衣乌巾,拱手一礼便相对而坐,口若悬河纵谈天下之事,于府中亦来去自如。他天性中的直率不羁被妥善包容,经世之才可以无所顾忌地施展。
可风云诡谲的朝堂不会恒久不变,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被参劾罢官,徐渭的幕僚之名也随之隐去。他不是没想过重寻出路,但再无一人能如胡宗宪那般给予他礼遇与宽容。当胡宗宪死于狱中,他想起往昔那个威风凛凛的男子,有不可一世的豪迈,亦有礼贤下士的谦和,不由痛心疾首。
信仰倏忽碎成尘痕,坍塌的不只是前路,还牵引出过往的哀伤。胡府许多幕客受到牵连让他惊惧忐忑,何况他骨子里深埋着不安。虽在官宦人家,他的生母却身份低微,他十岁时生母便被嫡母赶出家门,这段幼年经历在他心底烙下深刻的痕迹;后来入赘潘家,受尽冷眼,结发之妻又不久亡故,亦成为他悲恸的记忆。
这些情绪仿佛翻涌不息的海浪,撞击着他故作镇定的从容。于是他病了,对人生厌倦,对现世不满,取下斑驳的旧笔,回顾毕生岁月,为自己写下墓志铭。墨痕尚未干透,他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以寻了结。反反复复,他九次寻死,却终究九死一生。在他极度崩溃之时,甚至质疑起枕畔人的忠贞,将其杀死,由此入狱。
徐渭的狷介之名由此而来,可被他描摹过的草木知道,他的内心柔软干净。他笔尖的兰有幽谷清芬,纸幅上的牡丹亦不献媚,那些冰冷的山石也有了风骨。墨韵流转间可见挥洒不羁,枝叶的舒展却分明那样温柔,那些写意的水墨,毫无保留地呈现出一颗澄澈的心。所以他曾设法惩治酒楼里不肯留钱的军士,亦看不惯倚仗钱财而肆意妄为的和尚。
狱中的光景是寂寞的,他却仿佛得到了沉淀和安宁。在独身为囚的方寸之地,他背倚冰冷的高墙,不安的情绪逐渐消退。在这里,他远离权谋纷争,亦不必担忧温饱,而今已是孑然一身,无所牵挂。时光好像回到了很久以前,他重新拾起书卷,潜心思索,高墙外朝夕更替,高墙内灯烛长燃。
有真心相交的友人为他四方奔走,几经周旋,徐渭终于在七年后重见天日。虽不再是鲜衣怒马的少年,他鬓发染霜亦要游历天下。他看遍江南湖光山色,吟诗作画,以文结友,在朦胧烟雨里饮下浓酒清茶。他亦纵观北地边城要塞,御马迎风,在草原黄沙间描摹民俗风物。
有一种友人不适合朝夕相伴,却未必不能地老天荒,徐渭恰是如此。曾为徐渭奔走周旋的友人中,便有张岱的曾祖父,翰林编修张元忭。花甲之龄的徐渭应其所邀前往北京,前有至交之情,后有营救之谊,自当更为亲厚。但他生性放纵疏狂,与恪守礼教的张元忭性情大异。张元忭尽力包容他的狂士性情,徐渭却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如坐针毡,最终两人不欢而散。后来除却张元忭去世之时前往吊唁,他终日闭门不出,再不管人间悲欢。
究竟怎样才可称是风流名士,怎样才可算是落拓疏狂?他善画,便以泼墨写意开创一代画风,齐白石亦为其折服;他喜文,便以诗词文章名扬后世,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他爱戏,便著成《南词叙录》,汤显祖也推崇他所写剧目。他的书法行云流水,他能弹琴晓音律,他博学综杂通晓古今。他不仅是才华横溢的文人,于兵法谋略亦有造诣。他不愿写青词,不攀附权贵,手头略微宽裕便不再作画。可他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曾以画换蟹满足口腹之欲。从家国之志到闭门索居,他的人生活色生香,他的寂寞五味杂陈。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暮年时他穷困潦倒,以字画维持温饱,藏书散尽,家徒四壁,至临终时亦不过一犬相伴。一生凝成一语,已是万千不易。
铺开一卷牡丹图,墨色天然,淡雅清绝。那些属于他的久远故事,也仿佛穿越寂静的光阴,不疾不徐地走来。
祖硎山陡峭雄伟,四周都是常青松柏。萧子良登临远眺,黑暗中看不大真切前方景致。风卷起地上尘土,遮蔽了人的眼,竟无端让人觉得害怕。这里是他为自己选择的葬身之地。在另一个时空里,有至亲相伴,他定不会再孤独。
不知过了多久,当太阳初升的光芒渐渐驱走夜的黑暗时,身旁小童忍不住寒气侵扰,犹疑许久,终于上前提醒萧子良该回去了。
回去?他咀嚼着这两个字,凝神思量。他心中一阵纳罕,回哪里去,王府吗?可纵然是朱甍碧瓦,富丽繁华,又何尝是他真正的家?这里才该是他的长眠之所。他轻轻说了声“走吧”。小童看不懂他神情中蕴藏的无限苦涩,真正懂得萧子良的,只有他自己。
萧子良19岁那年,便随祖父一起夺了刘宋江山。一朝踏入金銮宝殿,这天下终于为他们萧家所有。可他的心从此却再难安宁。他自幼喜好文学,有过目不忘之能。可祖父却在他十岁时把他带入军中,亲自教授他行军布阵之法。祖父常说,此子禀赋极高,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萧子良没有令祖父失望,短短几年就已战功赫赫。
刘宋皇帝不仁,取而代之本是顺理成章。只是以杀戮对抗杀戮,以鲜血对抗鲜血,这代价未免太过惨痛。萧子良不禁摇了摇头,他的手紧紧地握成拳,又慢慢松开。天下既定,这双手终于不用再拿起刀剑了。他抬头,望着天边那朵火红的云,终于绽开一丝笑容。
三年后祖父驾崩,依制将皇位传给了他的父亲。萧子良受封竟陵王,领丹阳刺史。在丹阳的日子是那般浓墨重彩,令他终生念念不忘。他减免百姓赋税,与民休养生息,并在当地推行佛学,教人向善。因为上过战场,经历过从生到死的绝望,所以他愈发懂得珍惜生命的意义。他很想用心去对待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谁,有着怎样的过去。
丹阳百姓都很喜欢这个年轻的刺史,以至于他离开那天,百姓们无不自发地到城门口相送。萧子良心头不禁泛起一阵阵酸楚。百姓就是这般淳朴,只要他用一分真挚的心对待他们,他们必定会用十分敬爱的心去回报。萧子良策马飞奔,他怕再回头看一眼,就会再舍不得离去。
他不愿回去,却不得不回去。他的长兄文惠太子病逝,皇帝急需人帮忙料理朝中琐事。他和兄长一母同胞,自幼感情深厚,兄长留下的担子,自该由他去扛。哪怕他所愿从来都不在这庙堂之上。他所求的,不过心安而已。
可这样的心思落入旁人眼中却是别有用心。太子过世后,皇帝便立刻加封萧子良为司徒,行宰相之权。和年少且资质平平的皇孙萧昭业相比,人们宁愿相信,皇帝想将皇位传给这个儿子。谋士们想让萧子良假意辞去官职,以退为进,逼皇帝下最后的决心。可萧子良总不置可否。他们跟了他那么久,却始终看不透他想要的是什么。终于有一日,在谋士们又一次的恳求下,萧子良淡淡地说了一句,就在这几日了。
开始他们都不懂他的意思,可就在此后三日,皇帝正式诏告天下,将已故太子的长子萧昭业立为储君。父死子继,本无可厚非,可谋士们依旧替萧子良不平。萧子良却明白,大齐新立,讲究的就是名正言顺,皇帝不能让别人挑出他一丝错来。所以尽管萧昭业有诸多不好,他依旧是唯一的储君人选。萧子良长长地舒了口气,不属于他的东西,就算失去了,他也不会觉得失落。
然而就算如此,萧子良对朝政之事也一刻未曾懈怠。人们以为他不甘,想要用这种方式换得皇帝的重新考量。无数恶意的揣度袭来,萧子良依旧不发一言。直到有日,皇帝在寝殿之内对他说,自己年岁既长,恐不久于人世,昭业庸碌,希望他能做好辅弼之臣。
皇帝面孔日渐苍老,投向他的眼神中也有了混沌之色。萧子良的心不由深深沉了下去,那句将要冲口而出拒绝的话被他生生咽了下去。谋士们不懂他,皇帝也不懂他,唯有他自己知道,他并不适合这个云谲波诡的朝堂,也应付不了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