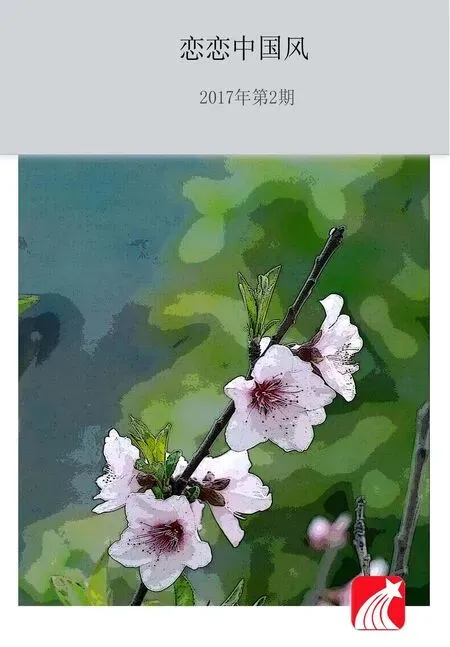衣妆清淡,难系他眉眼
◎糖炒栗子
衣妆清淡,难系他眉眼
◎糖炒栗子

图/星光
文帝十二年春,日光明媚,马车中的薄氏忍不住撩起帘子,阳光潮水似的涌进来,晃得她闭上了眼睛。待再睁开眼时,她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景象—柳垂金线,桃吐丹霞,高阁凌云,层楼耀目,这些和阳光一样,富丽堂皇到咄咄逼人的地步。
这便是长安了。
马车摇晃一阵后,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终点—东宫。侍女上前打起帘子,扶着薄氏下了马车。尽管文帝崇尚简朴,可东宫那直抵青天的重檐,还是压得薄氏喘不过气来。她不由垂下头,谦卑得好似一个侍女,而不是高贵的太子妃。
太子刘启打量着眼前这个低眉顺目的女子,不禁皱起眉头,继而苦笑一声,这便是薄太后为自己挑选的妻子吗?就算将她放到一堆宫女中间,也是最不出挑的那个,遑论母仪天下。倘若真要在她身上寻出一点贵胄气息的话,便是她的长相与祖母薄太后有几分相似吧。可刘启厌恶祖母不考虑自己的意见,便将她的远房孙女嫁与自己。然而他不能违逆,所以只好将怨气撒在眼前这个无辜女子身上。
薄氏,还真像她的姓氏一样,单薄得好似一阵轻风就能吹走。刘启看了她一眼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此时薄氏才敢抬起头来,望一眼夫婿。他步履稳健,身姿挺拔,恰如她想象中的一般,血气方刚又不失稳重。只那一眼,他的背影便永远印在了她眼中。
因他转嫁于她的厌恶,因她谦卑隐忍的爱恋,她的失败从一开始便已注定。
薄氏第一次见到栗姬时,心下便凉了几分。这个姿容绝艳的女子,即使不施粉黛,也称得上国色。薄氏之于她,正如星辰之于朗月。只一瞬间,她那本就不灿烂的光华便愈加黯淡下去。她有预感,这个女子定会享专房之宠。
她没有猜错,刘启果然独宠栗姬,他们很快便有了儿子。薄氏纵然良顺,此刻也不免生出妒意。她与刘启不过担了个夫妻的虚名,连相敬如宾都没有—他甚至不愿敷衍她。
然而她到底是善良的,自听见婴孩第一声啼哭时,妒忌之意就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慈母的一片怜子之心。身为东宫女主人,未能为太子诞下麟儿,她深感内疚,因此便将栗姬的孩子视若己出。
文帝驾崩后,刘启继位为帝,是为汉景帝。薄氏自然也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一个无子无宠的皇后。行册封礼时,她严妆丽服,饰金佩玉,用端庄的笑容,郑重掩去一切不堪与外人说的凄凉心事。
妃嫔媵妾们盈盈向她拜倒施礼,恭维之辞不绝于耳。她知道,眼前每一张妩媚的笑脸下都隐藏着一颗磨刀霍霍的争宠野心。她们都是风华绝代的美人,也难怪他总是流连其间。心中苦涩到极点,反而蔓生出一丝堪破世事的超脱。也罢,她给不了他的,就交予别人吧。
一众丽人迤逦离去,偌大的椒房殿顿时冷寂下去。椒房殿以椒和泥涂墙,本是取其暖而多子之意。薄氏苦笑,如今就连这宫室的名字,也充满嘲讽的意味。画阁漏频催,反复难成寐,从前在东宫如此,如今住进椒房殿后怕也要如此。
刘启难得来椒房殿坐坐,她却一副木讷的模样。成为皇后后,她更加拘谨,刘启彻底失望了,例行寒暄后便迫不及待地离开,只留给薄氏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背影。
寒风掠过,珠帘响动,薄氏的鼻子有些发酸。寂寞的滋味,她已反复咀嚼了近二十年。有时她不禁问自己,为何他连一丝怜悯也不肯施予自己?是因为他还对祖母怀恨在心吗?还是因为自己形貌卑陋更兼不解风情?或是因为她未曾为他诞下子嗣?薄氏不解原因,只能将此归结于自己福薄。她原是个聪慧女子,倘不是自卑至此,便不会寡宠至斯。人已远去,门又重掩,掩住寂寥池馆、花样年华,也一并掩住了那颗破碎的心。
前元二年,薄太皇太后病逝。消息传到椒房殿时,薄氏几近昏厥,这宫中唯一真心待她的人,走了。阖宫上下为太皇太后哭灵,却显得无比做作,唯薄氏悲哀到极点,反而流不出泪来。她只怔怔地跪着,想着如果当年祖母没有将她从吴郡带到长安,她的人生会怎样。平凡如她,该有一个同样平凡的夫君吧,但却真心待她,会在吴地软醉的春风里携着她的手踏青,也会因柴米油盐的琐事对她大发脾气……可世间没有如果。
她牵起衣袖悄悄拭了一把泪,是哭祖母,也是哭自己。因为她知道,祖母一死,她皇后的位置也要坐到头了。
此后,她不再过问后宫琐事。刘启的几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她也算尽到了嫡母的责任。栗姬的儿子刘荣被封为太子,栗姬在宫中风头一时无二。她听到也只是淡淡一哂。又过两年,刘启正式下旨废黜薄氏的后位,令她迁居别宫。尽管她早就预料到会有这天,还是心如刀绞。
刘启亲自来送她,算是给她一点颜面。两人还是相对无言,他看着眼前的女子,衣色清浅,脂粉单薄,一如往昔。他不愿久留,将要走时,她却一反常态,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声音颤抖,一字一句问道:“陛下,你对嫔妾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心动?”
他愣住了,未曾想到一向柔顺的薄氏竟敢这样逼问他,如此直白明了,不留半分回旋委蛇的余地。他不发一语,阴沉着脸转身离去。
二十多年的光阴是一面镜子,映出两人之间的萧索往事。在刘启转身的那一刻,镜子碎裂在薄氏脚下,钻心的疼痛也从足底蔓延至心间。末了,他留给她的,依旧是那个永远触碰不到的背影。
午夜梦回,她常忆起年少时光。那年花开,她和金郎携手花下游遍芳丛,金郎伸手将一枝含苞的桃花摘下,簪入她鬓角;后来花落,她却再也寻不见刻骨铭心的从前,也握不住轻许的诺言。
她名翠翠,他唤金定。一金一碧,自此交错成彼此生命里最璀璨的色彩。
初次相遇,是在学堂。翠翠自幼聪颖好读,父母将她当作男儿教养,送入私塾读书。入学时,桃花树下眼波一转,她就从活泼学童中寻见了那名少年。他一身朴素麻衣,难掩风华。虽只是个与她同岁的孩子,却已有了不流于俗的气度。
入学后,村里孩童总是依照淮安旧俗取笑她:“同年生者当为夫妻。”她虽笑着打骂,可心中却暗暗生了希冀。金定亦是如此。有时两双眸子在不经意间相遇,眼中便都开满桃花,两人遂将此时的心意付诸诗篇,赠予对方。
及笄已过,父母本欲为她择一位家世相当的夫婿,不料翠翠执意以金定为夫,不惜以命相争。父母拗不过女儿,许下了婚约。成亲那天,一束红绸牵着彼此,雀跃不已的心将欣喜的悸动不断传递给对方。当晚,灯下的翠翠眉笼翠雾,唇点朱砂,怯怯地向身着红袍的金定道一声“夫君”。在此后的羁旅岁月里,这份牵绊化为他心中最深的挂念。
婚后翠翠常与金定诗词唱和,以绿水鸳鸯自比,夫唱妇随,不胜和美。那年韶华正好,一切都处在最好的时节,天心月圆,花枝春满。
可战乱来得猝不及防,一年后,元末农民军领袖张士诚兄弟在高邮举起反旗,枝头花叶转眼离散,各自东西。过往种种似水东流,再无法捡拾。
漂泊得久了,翠翠总会疑心,过往岁月是否仅为一梦。时日渐长,她想忘了金定,却总是忘不掉他的模样,忘不掉他们曾有一诺,誓同生死。愈念愈痛,愈痛愈念。
她样貌出众,文辞飞扬,即便身在乱世,亦是极为鲜明的幽夜明珠,很快被一名将军看重,收为姬妾。曾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嫡妻,如今却成了逢迎鬻笑的妾室。其间差别,恍若云泥。一夜夜无望的等待吹凉了她心头的热血,吹散了她的梦。最后,她不再希冀。只有在午夜梦回之时,才会梦见鲜花缭绕的当年。
她并不知晓,在她沦落街头时,金定亦费尽心血来找她。任凭星霜屡移,辗转千里,箪瓢屡空,亦甘之如饴。终于,他来到了她所在的湖州。
相隔了无数个日夜,终于又同处一片星空下。即将相逢的期待牵动了他心中那一点残留的幸福,他却从别人口中得知他深爱的妻已成了将军的妾。谁忍将那场年少欢情以薄凉相待,可等到这最后的结局时,他却来迟了一步。
怀着一重希冀,他在将军府外徘徊,终于被将军看入眼中,询问他的来意。惶惑之下,他谎称翠翠为他的妹妹,他此番是千里寻亲。将军许他们相见。重逢之日,听得那一句妹妹,翠翠不由低下头,笑出了敛藏在眸中的清泪。
在踏入将军府之前,她曾设想过破镜重圆,自此相互扶携至永远,却不想再度重逢,却是如此荒谬的场景。昔日恩爱夫妻,如今谎称兄妹。那一声声呼唤,直令她心头滴血。
口无言,心有恨,她默默转身背对着他。之后金定成了将军府中的一名文书,她极少出门,更少与他相见,只因这相逢再无喜悦,唯有伤悲与难堪。然而那一夜,洗衣的侍女抱回来晾干的衣物。她细心翻检,竟从一件衣裳领口中拾起一枚纸片,正是金定苦心传递。只见纸上写着一首小诗:“好花移入玉阑干,春色无缘再得看,乐处岂知愁处苦,别时容易见时难!何年塞上重归马?此夜庭中独舞鸾!雾阁云窗深几许?可怜辜负月团圆!”
她本以为,经过岁月的熬煎,她早已无泪,却不想读完诗句,却是泪落如雨。那晚翠翠倚在窗前,泪久久不干。她想金定终究还是有情的,不像她,在离了他之后渐渐冷了下去。一夜刻骨惆怅,令她心碎情迷,她回了一首小诗:“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长使德言藏破镜,终教子建赋游龙。绿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谁知也到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