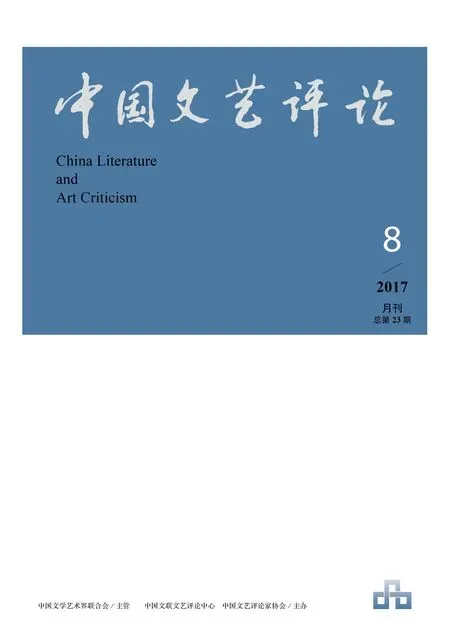“微弱的叙述”与“不确定”的力量
——访文学史家洪子诚
采访人:杨 宸
“微弱的叙述”与“不确定”的力量——访文学史家洪子诚
采访人:杨 宸

洪子诚简介 1939年4月生,广东揭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文写作、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等方面的教学、研究。1991至1993年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2009年至2014年,先后担任台湾的彰化师大国文系、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初版,2016修订版)以文学-社会的历史分析方式,将文学历史变迁、文学规范确立过程的冲突、作家存在方式等文学“外部”因素,与作品的形态、经典的构造等文学“内部”因素有机结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很大影响,他提出的“一体化”等观点至今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论题。这部文学史除了被众多高校采用为当代文学教材外,还在国外出版了英、日、俄等文本。其他代表著作有:《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2016年出版新著《材料与注释》。
一
杨宸(以下简称“杨”):您在2016年出版了新作《材料与注释》虽然采用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但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学术总结,涉及到了您此前治学生涯中的许多研究主题。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您的治学经历吗?
洪子诚(以下简称“洪”):我在北大念大二、大三时,正赶上“大跃进”,毛主席号召说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我们就积极响应,投入到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批判中,除此之外,也开始集体编写教材。这或许可以看作我学术生涯的开端吧。当年我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古代戏曲史两部教材的集体科研,和谢冕、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等合作,编写“新诗发展概况”。除了“新诗发展概要”部分章节在《诗刊》刊载外,其他的都没有正式出版。这些成果,学术上都简单粗糙,甚至粗暴,学术水准谈不上。但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还是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
1961年大学毕业到“文革”发生之前,我留校当写作课教师。这个时期没有做什么专题性研究,但读了很多书,包括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俄国和中国现代的文学作品,《鲁迅全集》也是这个时期通读的。没有很明确目的性的阅读其实有很大好处。“文革”结束后,写作课取消。张钟、谢冕两位先生在北大中文系筹建当代文学教研室,就把我招募进去,我就以“当代文学”为业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创新、突破的热点层出不穷,大家都被现状吸引。但是我缺乏敏感,反应迟钝,就选择从现实问题出发回顾历史的路子。这表现在我《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那本书中。加上上世纪70年代末我参加集体编写当代文学史教材积累的材料和经验,我后来的研究便沿着文学史(包括新诗史)的方向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很多。我从事这个工作,如果不想做无效劳动,就要让自己的研究和已经出现的论著有所不同,要进入还没有被人深入的领域。90年代末我独立编写的当代文学史,以及后来的《问题与方法》等著作,一方面是侧重现当代文学之间的转折研究,另外是清理当代文学的概念、范畴的内涵、来源,还有就是当代文学产生的制度问题。其中我最想弄清楚的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在当代转化为“社会主义文学”之后的状况,它的合理性和衰败的命运的根源。
杨:在您的诸多学术观点中,传播最为广泛且引起最多讨论的就是“一体化”了。在经过这么多年后,如今您怎么看待“一体化”这一观点?
洪:“一体化”现在好像很多人在用,我自己最早使用它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讲课的时候,正式把它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提出来是在1996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里面,后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书里面也有更为具体的说明。“一体化”简单来说,就是指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一体化”的时期。首先,它是指“左翼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如何“演化”、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其次,它还用于概括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方式的特征,比如文艺管理机构、文学报刊出版、经典评定等,也就是出现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最后,它还是这个时期文学形态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题材、主题、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趋同。当然,“一体化”这个概念有它的使用限度,开始阐述上也有瑕疵,对此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质疑、批评,我也针对一些提法进行了回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体化”是一个过程,而且我也不认为内部就没有异质的东西存在:正是这些不同性质的异质成分,使当代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充满激烈的争斗、冲突。
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您参加了很多社会劳动,这类生活体验对您之后的人生,尤其是学术生涯具有怎样的意义?
洪:我上大学时和现在很不相同,下乡下厂劳动是家常便饭,插秧(那时北大周边都是稻田)、麦收、深翻土地、修水库……经常去的是平谷,还有就是密云。1959年末到1960年初,我们年级在平谷韩庄公社参加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整社运动”,春节都是在乡下度过的。同年级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因为发表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言论,经不起批判自戕身亡,这件事作为“时代背景”写在《我的阅读史》读契诃夫一篇的开头。后来当教师,我还和学生参加过半年多的农村“四清运动”,“文革”期间多次的开门办学,去过门头沟煤矿、房山的炼油厂、朝阳区的纺织厂、地震之后的唐山……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劳动对学习当然有很大影响,许多课我们都没有好好上,这造成我的知识结构很不合理,有点支离破碎的,后来想自己补课,但因为工作关系总是不如人意。
不过对我来说,这些经历也不只有负面意义,它们让我不仅从理论,而且从实践和情感上意识到,在我生活、工作的狭小世界之外,还存在另外的、我所不完全了解的世界,存在和我那个世界也许相通,但时常相异的“事实”和道理。1969年到1971年,我们在江西宜春一位老农的指导下完整地种了三季水稻,也经历了南方夏天农村的“双抢”,这对我来说都是财富。这里不可能详述那些深刻触动我的细节,但总而言之,我在和“另一世界”的相遇中,常常会在对比中看到我这样的读书人苍白、缺乏谋生技能、夸夸其谈却经常背离常识的一面,在时势更易面前,好像也容易动摇,不能坚定维持必要的尊严。这种感觉对我影响很大,最直接的是,让我知道有另外的看事物的角度和方法,帮助我抑制经常发生的自得,让我与“自恋”多少保持距离。
杨:您在《我的阅读史》中勾勒出的郭小川、契诃夫等人复杂多面的形象、温和“怀疑”的立场,每每让我想到您对自己“悬浮的位置”“犹疑的性格”等的表述,而这种渗透在您文字中的怀疑与不确定,也常常为读者称道。请问这种性格或写作姿态,如何影响了您的文学史研究?
洪:人文研究,即使是再“客观”的论著,也不可能没有研究者“影子”的投射。研究者、研究对象,以及研究主体和对象之间建立什么关系,这是从事这项工作要面对的问题。但这里面还是有些分别,有的研究者可能更多抑制“主体”影子的投入,有的则正相反,对象可能更多成为个体表达的载体。这里不能简单谈论高下优劣。举个例子,虽然是强调“客观性”的文学史写作,林庚先生“美丽”的《中国文学简史》就更具个体性的色彩,获得很高评价。另外方面,也跟不同的文体性质有关系。像《我的阅读史》,当然就是要呈现写作者的声音、影子、性格,“客观性”倒是其次的。这方面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我的当代文学史确实比较节制,尽量避免自己感情过度投入,在一些问题上回避明确判断。这既是退却,但是某种“不确定”,也拥有自身的力量。
二
杨:您在《材料与注释》中收入了此前的一篇文章《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这篇文章既道出了《材料与注释》中所用材料的来源,也涉及了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与编写《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及其他大批判写作的一段经历。如今在新书写作中回顾这段经历,您有怎样的感受?
洪: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的大批判写作,也就是《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这篇文章里提到的那些了,有的是自己主动去写的,有的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材料与注释》临近出版时,我请1967年一同参加编写《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两位同事回忆当时的情况,他们对这件事都记不清了,很茫然,勉强回忆才有一些依稀的影子。这让我很感慨。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我经历的事情相对要少,参加社会活动不多,生活单纯而且单调,因此它在我这里就被当作“重要”事件记取。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记忆的磨损、消失是很容易的事情。写这篇文章时,我曾探访当年在那里住了一两个月的中国作协宿舍,也就是王府井灯市西口的黄土岗胡同6号,想看看那个院落、门前的大榆树、偏院里的枣树,以及后面角落里陈敬容先生的住所。谁知却踪迹全无——在城市的大规模改造中,那里已面目全非。今年回老家想去看看我读书的真理小学、中学,发现前几年还保留的最后一栋教学楼也拆除了,校门口那两株高大的木棉树当然也不见踪影。记忆和实物之间再也不能取得任何关联,这也是我这样的老年人(不是那种“与时俱进”,而是跟不上时代的一类)经常感到伤感,有时也感到恐慌的事情。
杨:您在1977年至1978年参与编写《当代文学概观》时,《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在这两个文本的编写之间,您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种转变又如何在《当代文学概观》的编写过程中,影响了对《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使用?
洪:思想的变化其实在“文革”期间已经发生,特别是1968年夏秋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之后。这个思想变化有一个过程,因此编写《当代文学概观》的时候,并没有情感观念断裂、转折的情况发生,但有一种当时许多人都有的“解放感”。我在一篇谈音乐的短文里讲到听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不止一人流下眼泪的情景,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是一种“解冻”的春天来到了的奇妙感觉。回过头去看,这种对时代的感觉也许幼稚、理想化,却值得珍惜,往后我好像“成熟”了一点,激情却减弱了,“怀疑主义”般的有点冷漠起来。
《当代文学概观》是刚成立的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集体写作成果,由张钟老师主持。因为觉得文艺思想斗争问题当时还不能讲得清楚,所以主要以体裁作为主轴和结构方式。这种方式,在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中不多见。集体可能也有一些讨论,体例什么的,但各个部分基本都是独立完成,分给我的是诗歌和短篇小说两个部分,我最后还承担了戏剧、长中篇小说部分的统稿工作,主要是平衡篇幅和叙述方式。当时我的思想文学理念,基本是“新启蒙”的一类,但也警惕不要把文学史当作意识形态性的批评工具,尽量从“文学史”自身去讨论问题。因此,对《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使用,主要是从史实线索的方面,毕竟当年是花了很多时间整理的。观点虽然更易,但有些基本事实还必须尊重。
杨:《材料与注释》一书借助对历史材料的某种“原生态”式呈现,“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同时通过抹除或隐藏写作/叙述的“踪迹”,实现一种切近历史情境的体认,从而展现历史本身的多面与复杂。您为何会采用这样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另一方面,作为写作者,您并不置身于“情境”之外,相反,“情境”恰恰是经由写作者对材料的编排、注释构造出来的。那么,在“材料”对叙述性的隐藏和“注释”对叙述性的彰显之间便形成了某种张力。您如何看待在这种文学史叙述方式中存在的张力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如何把握文学史书写中历史对象的客观性和写作者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洪:我对“原生态”这个词,包括“原汁原味”等通常的那种解释都不大信任: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比喻性说法吧。上世纪50年代上高中和大学时,我也一度入迷意大利的“新写实”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点钟》等),1972年看过安东尼奥尼的有点类乎“新写实”的纪录片《中国》——罗兰·巴特说它是“现象学”式的,说他自己的《中国行日记》也是现象学式的记录——所以明白“原生态”不是自明的,而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概念。
假设可以把《材料与注释》看作是一种另类的,或“亚”文学史叙述的话,既然是“叙述”,就不可能没有勾勒趋势、没有提供判断和结论。“材料”不可能自动呈现。对材料的选取、编排、注释,都是写作者“支配性”的处理。说起来,当初使用这种方法的最重要动机,是手头有一些特殊材料需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处理。“特殊”的地方是,它们大多是特定时代、特定情境下(反右、“文革”等)的产物。对那些检讨书的作者来说,他们的写作、陈述,是在人身、表达的自由受到压制、剥夺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们固然可以让我们了解在这样的“时刻”,受害者和加害者(加害者在材料中往往隐匿,或不以个体的身份出现)的个别处境、心态,但材料是否具有文学史的“史实”意义,或在文学史研究中是否可以作为“史料”加以征引,就不好说了。对这些材料做注释的最初动机,就是要提供支持、证明:确实性或疑点,以及相异的叙述等等。因此,注释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背景性的,另一个就是尽可能寻找另外的作为支持或驳诘的材料。
虽然是一种叙述,但确实是尽量隐蔽(或避免过分暴露作者的评述观点)、“尽量让材料自身说话”的写法。这首先是基于“文体”上的考虑:本来就是要呈现“材料”。其次是材料本身的阐释存在着多向度的可能性,因而不想做太多强制规范。还有就是自己也时常拿不定主意,这种情况下不妨让判断搁置。当然,也有属于“自娱自乐”的一些表达上的“小伎俩”。
我想,“当代人”写“当代史”可能经常会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写作者意识到“亲历”的经验性优势,会加强评述的强度;另一种是感知到“当代人”与“历史”在时间上的重叠,写作者的经验、情感与“历史”的无法剥离的纠缠,会失去“旁观者”的视角,因而宁愿采取一种收缩的姿态。不能简单化地判断哪种方法更好、更值得提出。由于历史观、性格、知识等方面的限制,我似乎更愿意采取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一种“微弱的叙述”。
杨:在《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您通过会议记录、检讨书等多种材料涉及了作协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文学评价机制、批判运动开展的模式等等,可以说,这是对“当代”文学生产体制的一次“微观解剖”。通过这种对作协的“微观解剖”,您想要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又如何看待作协、文联等组织在今天的作用?
洪:虽说我是较早将作协等制度性因素引入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之一,不过,我对作协制度本身其实没有深入研究,我也不是作协会员,对它的构成、运作方法等,不是特别清楚。不过在《材料与注释》中,确实可以略微窥见作协在“十七年”中具体而微的运作方式、它在当代文学权力运作机制中的位置和作用。这些材料有不同的角度,比如林默涵、张光年等对周扬的回忆性检讨书,从里面可以清理出运作的基本线索。而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62年的大连会议和1962年《人民日报》社论的写作,这从一次重要斗争(牵涉权力重组)、一个重要文学会议(文学写作的现实困境)和一篇重要理论文章(重新制定纲领、路线)三个方面,将组织、运行的情景具体化,也就是“当代文学”中政治权力的控制的具体实施方法、步骤,遇到的问题等等。
换一个更具体的角度观察,这些材料也在显现通过反右斗争和1957年党组扩大会议,周扬等人如何取得文艺界最高权力,建立了文学/文化的领导核心,以及这一核心在50年代末到“文革”发生前的几年中,如何雄心勃勃地实施他们的文学/文化抱负,和这一抱负、计划遭遇到的挫折,经历了怎样的溃败……这是当代文学中一个尚有继续讲述空间的“故事”。对于周扬,目前关于他的评价分歧很大。有些学者的研究侧重于文学理论方面,有的因为他在“十七年”中整了不少作家,特别是在丁玲的问题上,即使1980年代他多次道歉也不原谅。与他亲近的、有好感的人,对待他的严重问题在论著中则或略去、或轻描淡写。还有的人对他1960年代初期采取的大胆变革措施没有给予重视。总之,这是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当然,这些材料还可以引申出更多问题。举个例子,在1962年大连会议(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半个月的讨论中,占据最多时间的是当时的农村生产、生活状况、农村政策、农民的情绪、心态等等。邵荃麟和周扬的长篇报告中,也用很大篇幅谈农村情况和农村政策调整等问题,周扬甚至详细介绍他所了解的当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村状况(遗憾的是,邵荃麟和周扬的报告、讲话收入邵荃麟文学评论集和《周扬文集》时,有关农村状况的分析不少被删去,大概编者认为它们与文学无关)。在我们这里,大概对这个情况习以为常。但是在另一语境下,人们会疑惑,文学会议居然主要不是谈想象力、文体、语言、虚构、形式等问题,谈的都是“现实”和政策,是有点怪异。前些日子上海师大的光启读书会讨论《材料与注释》时,一位学者说,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不是反映论的,文学就是现实。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当然,如果细加分析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周扬等,倒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政治、现实与文学之间,试图努力加重“真实性”、语言、虚构等的“中介”,以削弱政治对文学的那种强势挤压。但他们的努力没能奏效。
至于对作协的看法,前面说过,我没有深入考察、研究,难以有根据的意见。在《材料与注释》中,也收入多年前接受《南方周末》电话访谈的关于作协答问的一篇,也只是浮光掠影的。印象里,作协的规模比“十七年”要扩充、庞大许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省、直辖市的分会是逐渐成立的,现在,包括地级市、县都有文联、作协。不能说这样的机构设置没有好处,将基层文学爱好者组织起来,阅读和写作,无论如何不能说不好,但也出现了行政化、机关化现象。
杨:在进行注释时,您谈到了在这些运动中,有的人有不断翻覆转向的表现。一方面,您特别强调“这虽属于个人品格,但一定意义上,也是某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您又补充指出“不应将一切推到外部环境,认为个人无需担责”。这两种看起来比较矛盾的表达,暗示了您怎样的态度?
洪:《材料与注释》的一些部分,确实和当代作家、知识分子的道德问题有关,特别是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那一部分。另外,书中还有一篇专门谈道德问题的文章。从体例上说,这一篇其实不属于“材料与注释”的范围,我曾想改为合乎这本书的体例,但文章已经发表过,改动工作量也太大,就放弃了。在对当代所作的历史反思中,与诸如告密、揭发、伪证、见风转舵等联系在一起的道德,在人们心目中要比什么理论、路线分歧来得严重得多。这是一个经常提起、引发争论的棘手问题。而且,它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在仍不断发生、上演的现实问题。其实,在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以及他去世后大家讨论他提出的“讲真话”的命题时,这个有关道德的问题就让我相当困惑。更早些时候,在1956年斯大林问题揭发,就连带引起我对有关理想、信仰、真理性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因为涉及人的道德素养、品质,也涉及“泛政治化”的当代的道德话语、修辞的问题,以及权力和道德的关系等问题,我自觉没有能力处理,在《材料与注释》中,其实是将这个复杂问题限定、缩减为文艺批评上的范围。我的基本看法是,一个时代的道德状况的形成有更大的、复杂的原因,但个体的道德、人性品格问题,绝对不能消失在“大历史”的借口下。我看到相似的情境下,“人与人确有不同”。不过,人对自身的反思其实很难,我自己就常常有意无意回避,或避重就轻,或寻找开脱的理由——经常的方法就是让“环境”来承担一切,而卸去自身的责任。不过,从整体、从重要性而言,我也不愿意离开语境来抽象谈论道德问题。我更加关注的是探索当代政治、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因为我确实清晰地看到,道德问题的“指控者与受辱者位置的错动甚至互换,是当代史的奇观。当受辱者被推上‘不老实’‘两面派’的审判台的时候,指控者自然获得了道德优势,一旦他们权力地位失去,立于‘道德制高点’上的就是另一些人。”这是当代我经常看到的不断演出的“戏剧”——悲剧或喜剧,或悲喜剧。
杨:您的“材料与注释”式写作从2010年就开始了,后来您却对这种写作方式产生了怀疑?
洪:本来设想的比现在出版的这本书的规模要大许多,设想选择一组有代表性的材料:文章,讲话,宣言,某一期的刊物,某一作品……它们不限于“十七年”和“文革”,也包括1980年代以后,这些“材料”能在一个方面涉及当代文学重要现象、问题,这样来具体描述“当代文学”的具体面貌。它们可能是正规的文学史的一种更侧重“感性”的补充。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和孟繁华共同主编的《当代文学关键词》也是试图从概念词语的角度提供“当代文学”的另一种补充性质的梳理方法。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模仿雷蒙德·威廉斯,是不得要领的“东施效颦”。其实我们没有那样的胆量:那时根本没有读过威廉斯的《关键词》,也不知道有台湾廖炳惠的《关键词200》,只是觉得批评界为一些概念争得不可开交(如“现实主义”“真实性”“日常生活”等),却对这些概念的历史内涵所知无多,理解和使用上也各行其是。
对通过注释若干有价值的材料来处理文学史问题,这个想法让我“自我激动”起来,后来我却觉得根本难以实施:一方面,材料的选取就很费思量,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做这样的处理。另一方面是精力越来越差,再像过去那样收集查找相关资料,已经难以做到。再就是,我有一个致命缺陷——从不把“学术”看得那么重要。一个新鲜想法冒出来,维持一段时间后又兴味索然,提不起精神来。这种情绪低落的周期,大概是两到三年。我受制于这难以超越的高涨、低落的周期的摆布,真的没有办法。
有幸能够较为系统就地拜观画家客岁金秋在西德首都波恩以及名城科隆几处展出的大批作品,如行山阴道中,目不暇接,眼福委实匪浅。尽管我对画家相当熟悉,却从未一次观赏过如此全面而又自成体系之作,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无怪对素有艺术修养的德国人民,为此掀起一股热潮,当属意料中事。
三
杨:近年来,您的学术研究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阅读”。2016年您发表了多篇“读作品记”,这是《我的阅读史》的延续吗?您在“读作品记”中重读了一些上世纪80年代颇有影响力的作品,可否将其也理解为一种“重返八十年代”的尝试?
洪:“读作品记”是近几年写的一组文章,最早应该是2012年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爸爸爸〉:丙崽生长记》。这些文章大部分写在2016年,其实很多是我在台湾的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上课的讲稿整理的。我2009年到台湾彰化师大国文系给研究生上课,还有2012年在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讲课都主要以归纳一组问题的方式进行,这些问题都很大,备课花了很多时间,而由于台湾学生大部分对中国大陆当代历史、文学情况了解甚少,虽然听课认真,但效果甚微。我自己也为了重新写讲稿,看材料,累得够呛。回到北京,讲到这些尴尬情况,就受到过去的学生的批评,如陈顺馨、贺桂梅、周瓒、冷霜他们,都不赞同我这样的讲课方式,说不切实际,吃力不讨好,也不符合教学规律。他们劝我改为选择具体作品,与学生一起阅读讨论的办法。所以,2014年在新竹的清华中文系,就改为读作品的方法,当时那门课叫“大陆八十年代文学”,挑选的作品都是这个时段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异禀》《北方的河》《绿化树》《动物凶猛》,还有北岛、顾城、多多的诗……但我并不是要“重返八十年代”。人大程光炜老师带他的学生已经很有成效地重返过,贺桂梅老师对1980年代文化/文学问题的研究也相当深入,我再接着做就是狗尾续貂了。也有一些不是1980年代作品,如1960年代“黄皮书”《“娘子谷”及其他》、爱伦堡1950年代的文章《司汤达的教训》、1960年代法国作家阿拉贡的文章,以及伏尔科夫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等。
表面看来,“读作品记”好像是《我的阅读史》的延续,其实有很大不同。虽然也是读具体作家作品,但“读作品记”并不特别强调个人阅读在时间、在不同人生阶段和不同境遇里发生的变化,也不重视个人阅读感受留下的时间痕迹。如果总按照“阅读史”的思路那样写,一个问题很容易重复,为了敷衍成篇,也容易将一时的零星感触想象式放大,造成“回忆尽在不实之中”的情况——这是需要警惕的。所以,“读作品记”将重点转移到通过作品解读,引出一些我关心的思想、文学问题。本来想更侧重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的分析,但是积习难改,写着写着就离题,就转到一些思想、文学史方面的问题上去。这些问题有当代苦难记忆和文学的苦难书写,20世纪政治诗的命运,1950年代斯大林事件发生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信仰危机……计划中还有另外一些题目,但也是前面说的情绪上的虎头蛇尾,没有坚持力而放弃了。因为想保留一些资料,所以这些文章都写得很长,有的真是拖沓,但是也不想修改,就这样吧。这本书在2017年夏秋之间应该能出来。相对于《材料与注释》,它的好处大概是不那么枯燥难读。
杨:您常常被问到最喜欢哪位作家,但每次都语焉不详,这次我想换种提问方式:在当代中国,您比较欣赏哪位作家?另外,以前中国作家总是受到外国文学的滋养,如今中国作家也走向世界,获得了许多国际性奖项,您对此怎么看?
洪:又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相信不同民族、时代,在文学评价上总有共通点,存在某种共识。但是个人的爱好又是千差万别,这牵涉到作为读者的处境、文化素养、性格、趣味等等问题。喜欢当代哪些作家?如果我列举起来,可能是一个颇长的名单,而且不同时期,我的爱好也有变化,有时变化还很大。读中学、大学的时候我曾喜欢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现在却弄不明白那时为什么喜欢。如果偷换概念,我就会有具体回答。比如,我喜欢《我在霞村的时候》胜过《在医院中》,喜欢《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胜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喜欢赵树理胜过喜欢柳青,喜欢《异禀》胜过《受戒》,喜欢《北方的河》胜过《黑骏马》,我觉得王蒙最好的小说是《杂色》,而莫言最好的小说是《透明的红萝卜》,喜欢《归去来》胜过《爸爸爸》,喜欢《乌托邦诗篇》胜过《小鲍庄》,喜欢《棋王》的前面三分之二胜过后面的三分之一,喜欢1980年代以来的许多诗胜过许多小说……由于知识、视野的局限,我不知道中国文学是否已经走向世界,而且我觉得是否走向世界并非那么重要。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诗人,确实受到外国文学(古典的,现代的)的许多“滋养”,可以肯定今后也还是这样;至于外国作家是否需要中国文学滋养,由他们自己决定吧,我们管不着。
杨:您是否对当前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有所关注,比如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在原有的文学生产体制已被市场和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所改变的情况下,您对将来的文学史书写持有怎样的态度?
洪:文学发生很大变化,这是真实的情景。我因为精力、年龄的关系,已经没有力量去关注,包括网络、科幻等等,这些新现象自然十分重要,也可能改变原有的文学生态、格局,这需要认真考察、研究,但这是年富力强的人,特别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业。按照1934年出生的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著名学者木山英雄先生的说法,我们都属即将“消灭的一代”,因而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做出有根据的判断的。
初览学术门庭时,有一本书我时常翻阅,因为它的叙述总是吸引着我往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纵深处窥探,每每阅毕都有种“原来文学史还可以这样写”之感,这本书便是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没想到若干年后竟有机会访问洪老师,出于对学识的不自信,我重读了洪老师的著作集。这次,除了对过去那种激荡之情的再体验,我更多感受到的是洪老师学术研究乃至性格中犹疑、不确定的那一面。在我看来,它源于洪老师常年钻研和遍阅世事后形成的温和怀疑的立场,这种立场使洪老师总会有意无意地柔化其叙述的棱角。但显然,在温和表面包裹下的怀疑目光仍然有着直达问题本质的力量。这一印象也在我对洪老师的访问中得到了印证。
因为洪老师在此前多次采访中对一些重要论题都有所回应,这次的访谈重点之一就放在了他2016年出版的新书《材料与注释》上。在这本书中,洪老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他称之为“微弱的叙述”。这里的“微弱”让我联想到洪老师对契诃夫的论述:“契诃夫的独特,在于坚持以艺术感性的复杂和‘怀疑’的智慧,来在已深入人心的象征方式和思维逻辑中,争取一个‘微弱’的空间。”这两处“微弱”的意思虽然不同,拼凑起来却可以得出一个关于洪老师研究的大致完整的表述:看起来是充满克制、收缩的叙述,内里却有着坚硬、强韧的支撑物。“在复杂事物面前保持手足无措的虔敬态度”,却始终不改温和之中那份质疑的“锋芒”。我想,这大概就是洪老师所说的“不确定”的力量,也是我们面对这个愈加变动不定的社会时,值得借鉴的一种学术姿态与“人生方法”。
杨 宸: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史静怡)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27-1036室
邮编:100050 电话:010-65978917
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