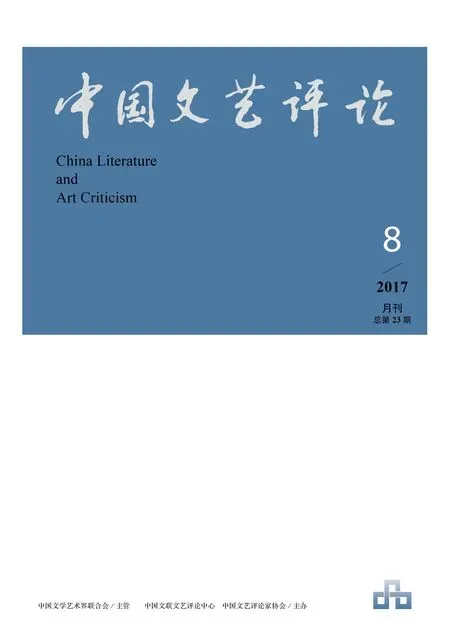越剧男班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廖 亮
越剧男班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廖 亮
在越剧史研究中,相较于女子越剧研究的繁荣而言,早期的男班时代无疑是被“冷落”的。从越剧艺术的角度看,男班的演出确实是粗糙和不成熟的,但从剧种发展的角度看,女班的发生、发展,以及女班之立足上海等,都与男班有着重要和必然的逻辑关联。目前的研究对于男班对越剧剧种发展的历史性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本文通过细读早期男班历史、还原男班演出状态,厘清越剧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探讨男班在女班兴起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越剧史 男班 女子越剧
越剧史研究中,对早期男班时代的历史考察大多侧重在对其闯入上海的时间,初进上海的人员,初进上海的剧种改造,改名绍兴文戏等史实的认定,但男班在上海的具体演出情况并没有得到详细还原。从越剧艺术的角度来看,男班的演出确实是粗糙和不成熟的;但从剧种发展的角度来看,女班的发生、发展,乃至女班之立足上海等,都与男班有着重要和必然的逻辑关联。笔者认为要厘清越剧剧种发展的历史脉络,必须从男班的历史研究入手。
一、升平歌舞台的出现是越剧男班立足上海市场的直接证据
初入沪的越剧男班,在当时被称为“小歌班”。第一副小歌班入沪是在1917年5月13日,演出于新化园(十六铺新舞台原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同年6月9日),第二副小歌班也来到上海,在河南路观音阁码头的镜花戏园与绍兴大班一同演出。不过这两次向上海市场的冲击皆以失败告终。
第二年,总结失败教训后的艺人再次入沪,此后尽管班社有进出、人员有变动,但越剧从此时起便不曾离开上海。“到1919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四),以卫梅朵、费翠棠为首的男班演出于民兴茶园;以琴素娥、紫金香、白玉梅、沈桂芳、王永春等组成的男班于2月9日起,演出于第一戏院。小歌班在上海开始了两副班子竞演的局面。”越剧史研究者卢时俊因此认为“男班小歌班从1918年4月起,已在上海站住脚了。”这一结论本身值得挑剔的地方并不多,不过从“小歌班”入沪前五年的演出数据来看,升平歌舞台——这个越剧专属场地的出现,或许是该剧种在上海市场立足的一个更为直接和有力的证据。

表1 “小歌班”入沪前5年演出信息汇总[2]根据《上海越剧演出广告》(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编)相关信息整理制作。
从“演出场地”“实际演出时间”“全天演出比例”这几项指标来看,“小歌班”入沪前五年是一个稳步成长的过程:演出场地从两个增长到四个,再提升到七个;实际演出时间从1917年的167天,到1919年的478天,再到1921年的771天,基本上两年是一个增长周期;全天演出比例也从1917年的85.6%上升到了1919年的99.4%,此后数十年间除了遇到战乱等特殊情况外,基本都保持在95%以上的全天演出率。
“小歌班”演出日盛,上海升平歌舞台因此开张,这是越剧在上海的第一家专属演出场地。通过对当年演出信息的分析,我们还看到了在升平歌舞台出现后,随之而来的越剧演出市场竞争、兼并、垄断行为的发生。例如,在1921年时有三副班社在沪上演出:以王永春、卫梅朵、马阿顺为主的班社和以马潮水为主的班社分散在升平歌舞台和新群仙茶园,支维永、紫金香为主的班社在绮云茶园演出。其后升平歌舞台将马潮水班也吸收进来,通过这种强强联合,新群仙实际上被挤出了当时的越剧市场。在其后的两年中,升平歌舞台始终占据上海越剧演出市场最大份额,每年都保持了全年的演出量(1922年演出336天,1923年演出334天);而在这两年中男班在上海的整体演出也是趋向成熟的(1922年上海越剧演出场地四个,全年演出772天;1923年越剧演出场地六个,全年演出626天)。
从流动性演出到有了专门的演出场地,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竞争、兼并、垄断行为的发生,都足以说明彼时的越剧在上海已经有了固定的观众群体。这一群体表现出一定的观看需求,并形成了基本的欣赏习惯,故此才能吸引商人的投资,建设演出场地。可以说,升平歌舞台的出现和对市场的稳定占有,是男班立足上海演出市场的一个直接和有力的证据。
二、女班出现与男班第一次衰落之间的历史关联
越剧史一般将1921年至1922年间,男班艺人相继将剧种改称为“绍兴文戏”之后,至1937年前的时间称为“绍兴文戏时期”,并认为是男班的鼎盛时期。通过对当年演出状况的梳理和还原,可以发现人们普遍忽略了这一时期越剧男班经历的第一次衰落,以及女班之创立、入沪与此之间可能存在的历史关联。
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在经历了数年的稳步提升后,1924年越剧的全年演出时间突然急剧减少为185天,几乎只是1923年的五分之一。升平歌舞台从1924年5月1日起就改演常锡戏了,直到10月底才恢复越剧演出。这一年中,除了升平歌舞台的越剧演出量锐减外,其他六个越剧演出场地绝大部分仅保有半个月的演出量。可以说当时整个上海的越剧演出市场都陷入低迷。虽然,其后男班找到了游乐场这个暂时的存身之地,但1924年演出市场的低迷,确实给男班艺人带来了生存考验,正是在此背景下,女班出现了。
一般认为越剧第一副女班是1923年7月9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由王金水在施家岙创办的。关于兴办女班的想法,历来认为是受当时京戏髦儿戏的影响,第一副女班的入沪演出广告中也确实借用了“髦儿戏”的称呼,称为“髦儿小歌班”。当时的上海戏曲市场上,女性演员结班演出是一种流行趋势。王金水以商人的敏感,赶女班之时髦,目的当然是获取经济利益。从这一目的出发,女班的仓促入沪就显得有些不合情理。施家岙女班在三个月后即“串红台”,在农村短暂演出后,王金水便于1924年初匆匆将女班带进了上海,1月14日在升平歌舞台第一次亮相。可以说,当年的施家岙女班几乎是“跃进式”地一头闯进了上海,这种违背地方小戏层级式累进的发展规律的做法,很容易招致失败。其时的女班,演技幼稚,行头粗糙,缺乏演出经验,女声唱男调又无法悦耳,很快便由于观众稀少被迫退到茶楼,几个月后离开上海。
反观男班进入上海市场的历程:从1906年到1916年,“小歌班”用了十年的时间,在其发源地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并在其诞生的四年后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中等城市,作好了向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挺进的准备。这种层级式的累进对于戏曲艺人来说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他们在乡村、市镇、城市一步步获得经验的积累,然后输入到上海这个当时最成熟的市场。层级式累进几乎是地方小戏发展的必经之路,一旦违背这种发展规律,很容易招致失败。
那么,作为前台老板的王金水应当明白以女班当时的演出水平,如此冒进上海市场可能会存在风险,但他为什么依然甘愿冒这样的风险呢?联系王金水的身份以及上文所述1924年的演出数据,笔者发现了这样几条线索:
1. 女班首进上海选择了升平歌舞台;2. 女班进上海的1924年,男班在上海的演出突然由盛转衰;3. 女班的创始人王金水正是升平歌舞台的前台老板(即参与投资开设剧场)。将这三条线索连贯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如果说创办女班是顺应市场潮流之举,那么女班仓促入沪的举动则有可能是为了救市。
1924年整个上海的越剧演出市场都很低迷,升平歌舞台这个当时最大的越剧场所受冲击无疑是最大的。上海的越剧演出市场直到1927年游乐场中开始大量演出后才逐渐恢复。毫无疑问,1924至1926年在越剧发展史上是一个低落时期,正是在这个男班由盛而衰的当口,女班入沪了,而女班之兴办者又恰恰是升平歌舞台这个当年最大的越剧演出场地的老板。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在这个当年最热的场子里,老板和演员才最深切地感受到,甚至预见到了男班的危机。以女班之新鲜来挽救越剧演出市场可以预见的衰退,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在整个行业全面衰落的局面下,仅仅一服“髦儿小歌班”的尝鲜“药方”,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为一剂救市的“强心针”的。好在游乐场的演出形态给了男班复苏以缓冲的时间,女班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回到农村、城镇,重走了一遍那条不可逾越的“层级式累进”道路。
三、游乐场演出对越剧男班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
1924年至1926年的三年间,是男班演出的第一次衰落期,在此期间女班开始创立,但并未迅速占领上海市场。机缘巧合,男班则借游乐场演出获得复苏,并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三年间,越剧男班在上海的生存形态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演出场地数量虽在减少,但游乐场类场地的比例却在提高。游乐场的演出从1924年前的零星,到1925年的断断续续,发展到1926年的隔日演出,到1927年起便开始能够保证每天日夜两场的连续演出了。此后游乐场演出一路上升,30年代更全面进入了上海南京路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的游乐场。甚至大新公司1936年刚开设游乐场,当年男班便进驻演出。可以说当时的城市娱乐潮流中无论是高端还是中端的游乐场场地,越剧都占领了。至1937年,当年广告中共出现了18个演出场地,从演出量上看,较为主要的是新世界、大世界、福安游乐场、永乐戏院、老闸大戏院、先施乐园六家,其中四家为游乐场。考虑到由于当时大部分游乐场都有自己的报纸,而《上海越剧演出广告》中仅收录了《申报》和《新闻报》上的广告信息,我们可以由此推测,游乐场的演出应当比这些数据中所表现出来的更为兴盛。
男班不仅在这些游乐场演出的年数长,而且演出时间也比在其他类型的场地要多。一般游乐场演出往往每年能保持200至300多天的演出量,而其他场地大多数演出通常只在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可以说,正是游乐场演出挽救了越剧男班在上海的第一次市场危机,并形成了以游乐场演出为支撑,戏院(剧场)演出为辅助的演出形态。这实际上是作为地方小戏的越剧对上海演出市场的适应结果。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正规剧场演出主要是被京剧和新剧两个剧种占领。从剧场运作来看,不够成熟的地方小戏由于观众面的狭窄以及演出水平的不稳定,会带来较大的票房风险,剧场老板自然不会倾向于它们。这种情势下,倒是游乐场的经营模式为越剧的逐步成熟,提供了宝贵和充分的时间。
首先,游乐场巨大的客流量为越剧男班提供了拓展观众的可能性。例如,永安公司的游乐场每天就可以卖出2000到3000张门票,而30年代“鼎盛时期,大世界,每日进出的游客达两三万人,节日更达到五万人。摊点就有77个。”来来往往的游客,虽不一定特为越剧而来,但进场后各种游艺、表演项目循环上演且不再单独收费,进去看一看越剧表演,又何乐而不为呢?偶尔接触之下,很有可能会引来一部分人的喜爱,并进而形成消费习惯。
其次,与专业性剧场追求票房不同,游乐场的经营压力在客流量,不在各个剧场的单独票房。也正因此,越剧这样的地方小戏在“票房解压”的情况下,赢得了积累观众数量的时间。于是,在1921年首入小世界后,随着1922年大世界的第二次扩建,以王永春为主的越剧男班艺人开始进入了这个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游乐场(在楼下新厅演出)。1924年,经历了第一次衰落后,越剧男班演出的主要阵地开始明显地向游乐场转移,并逐步获得了稳定发展。正是通过游乐场的长期演出,男班逐渐适应了城市观众的观赏习惯,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观众,也才有可能拓展游乐场之外的演出空间。
但游乐场的演出形态也同时为如越剧这样的地方小戏的发展带来了局限。首先,游乐场实行的是一票制,游客购买门票进入后,场内各种游艺项目不再另行收取费用。游客购票进场并不单纯为看戏而来,而是可以有如照哈哈镜、坐电梯、看影戏、放烟火等诸多选择。以低廉的消费获得更多的游乐项目和更长的娱乐时间,是游乐场吸引人的地方,而不似专业型剧场,以演出质量为生命线。既然游乐场观众的观看心理并不以追求演出质量为第一需求,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越剧男班在剧种艺术发展上的惰性。
其次,游乐场的经营模式决定了其在演出成本方面必然受到严格控制。游乐场收入主要来自门票,且票价相比电影院和独立剧场来说始终低廉,因此“演艺节目的数量、质量的控制以及带来的成本控制是各游乐场最大的问题,也是竞争胜败的关键。”为了控制成本,游乐场必须选择那些相对并不够成熟、稳定的剧种,这样才能把包银砍到最低。对于如越剧这样入沪不久的地方小戏来说,尽管包银制度使他们从独立剧场的票房压力中暂时解脱出来,但较低的包银和严格的成本控制,也使剧种在艺术创新所必须的经济投入中显得捉襟见肘。
可见,游乐场演出对于越剧男班而言,实在是一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双刃剑。但若从剧种发展的角度来看,1938年以后女子越剧在上海的崛起正可看作是二三十年代男班游乐场演出的又一次层级式累进的结果。正是男班在游乐场的多年经营,为越剧完成了观众群的培养积累和演出水平的长足进步,也才令女子越剧具备了冲击专业性剧场的实力。
四、男班艺人对女班的着力培养促成女班的同时加速了自身的衰退
起步阶段的女子班社在组建和培养上都得益于一群优秀和热情的男班艺人。相较男班的速成培训而言,女班从建立之初,就采用相对正规科学的培养方式。以1924年王金水开办的第一副女班为例。教戏师傅就以男班大面(花脸)演员,有着17年舞台经验的金荣水为主,此外还有著名唱书艺人相金堂的徒弟任阿裘,苍岩小京班的武生王和铨为武戏师傅,同时有主胡、笃鼓等组成的四人乐队。无论从科班性质、管理方式,还是从教戏师傅和乐队构成等来看,女子科班都比男班要正规和完整。同时,女子科班由金荣水等人建立的口授“赋子”和“单片”的“赋子教戏法”,从小戏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进入大戏教学则更为科学;当时几乎所有女子科班入科开始便都有严格的训练日程,角色行当也是由师傅根据艺徒的特点进行分配的,金荣水还提出了女小歌班分行当的表演程式,俞传海(一说喻传海)则在高升舞台时对各种行当进行了细致的区分,要求艺徒把角色的内在感情与身段动作统一起来;鲍金龙在“四季春班”则采取“以功促戏,以戏带功”的方法,对艺徒的基本功训练有新的发展。在这些男班艺人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女班艺人的技艺提高自然比“速成”的男艺人要迅速得多。此外,与个体培训相比,科班是行当齐全的演出团体,可以在不断的演出实践中培养默契、提高技艺。女子科班人数大多在20人左右,有的甚至达到40至50人;但男班除了个体拜师外,科班人数一般只在十人左右,规模小,行当不全的问题便会出现。例如最初与女班合演的陈素娥班就是“因为班内演员太少演不了大戏,就将全班人马并入以赵瑞花、屠杏花为首的女子小歌班”。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男班艺人在女子科班的组建和培养上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的投入为女班的大规模兴起打下了基础,接下去便是男班艺人干脆以给女班传艺为生,在促进女班成长的同时,实际上也加速了男班的萎缩。
五、结语
还原男班在上海的演出状况,笔者认为女班的出现并不仅是“赶时髦”,而更可能是越剧——即当时的演出主体“男班”——要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生存下去的一种商业策略。此后,男班对女子班社的着意培养则在事实上造成了女班的发展、形成,同时也带来了自己的衰落。而男班在游乐场的多年演出经营,则为女班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男班在音乐上始终无法很好地解决男女声同台演唱的问题时,随着男调的衰落和女调的成熟、丰富,男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可见,男班与女班之间与其说是此起彼伏的“替代”关系,倒不如说是承前启后的“继承”关系。没有男班的探索,就不会有女班;没有男班艺人的悉心传授,就不会有女班的成功;没有男班的积累,就不会有女班的崛起。
*本文为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文化生态场的数字化挑战对上海戏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PJC036)阶段性成果。
廖 亮:上海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