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萍:诗,写着就是全部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陆萍:诗,写着就是全部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作为一名从1970年就开始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处女作的诗人,这将近半个世纪以来,陆萍的名字在诗坛时而响亮,时而余音悠长,但她在今年忽然就抛出了两本诗集来,很是让老读者和文友们吃了一惊——惊喜的“惊”。以至于评论家毛时安在给她写的序文中第一句就感慨万千:“像沉寂了多年的火山,再度喷发出烈焰火光岩浆,诗人陆萍在远离诗坛多少年后,居然在同期内推出了两本诗集《玫瑰兀自绽放》《生活过成诗》。那么强烈,那么耀眼!”但我拿到这两本诗集时却是真有点惊奇的:两本同期出版的诗集,一个封面十分现代,灰色底,有抽象的云霞和飞鸟,简而雅,是目前比较常见的设计风格;另一本则浓墨重彩,墨绿色底色上是手绘风格的爱心,爱心中半张粉色的少女侧脸,设计风格朴实却又有几分古典——这两本书的封面可以说是相当不统一了。问陆萍其中可有缘由,她果然娓娓道来:“其实这张画是我先生35年前的一次心情留迹,当时他在得知我处女诗集《梦乡的小站》喜获出版时,为我开心,就信手画了这张小图送我,其实也只是私下庆贺。”结果这一次两本书同时出版,出版社找的封面设计一个过了一个没通过,大家都有些着急,责编就请陆萍也发些自己喜欢的图片或图书封面过去给他们参考,陆萍于是就在书房里翻找开来,忽然这张画就从旧书中飘落出来。“是巧合,也是缘分吧。”女诗人总是敏锐而感性的,陆萍的眼睛亮晶晶的:“我那第二本诗集的名字就是《玫瑰兀自绽放》,一看到这张旧画,我心里就知道是它了。”
这一次陆萍出版两本诗集,很多人都觉得“想不到”,毕竟一个曾经活跃而耀眼的女诗人“沉静”了几十年后,忽然又“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中间总该有点故事?于是我问她,为什么中间会停下来?她有点莫名,我便更直白一些:“在这两本诗集之前,你的上一本诗集出版于1995年,中间这二十年你为什么不写诗了?”“没有不写啊,我一直都在写,从来没停下来,只是不发表而已,”陆萍的回答坦然而真诚,“我一直认定,写着就是全部。诗,让我寄托放飞、让我释怀透风、让我宣泄收藏,让我卸却也让我获有。一切喜怒哀乐、所有七情六欲,包括这之间的过渡、映照、渐变,五味杂陈的情怀,只要走过我的身心,都会有诗留下痕迹。诗走生活,或者说把生活过成诗,几乎成了我的一种生命方式。”原来,在主流文学离诗歌越来越远的这些年,陆萍却从未曾远离一步,只是写诗于她早已“得其意而忘其形”,发表不发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心不改。当然,陆萍也并不只是寂寞地埋头写作,之所以并不在意发表与否,一来是她本心如此,认定写诗的意义只在“考量灵魂”而非“追逐名利”;二来也是她找到了一个更大更纯粹的心灵花园——博客。“自从世界上发明了博客,我真是喜从中来。在那儿我可寄托灵魂置放情感。她像个神盒,不管我在北欧还是南非,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都伸手可及,可取可写可读可发。来我博客做推广的人,我一律将其关进黑名单。我不需要来自外力的推广,哪怕我的万千诗情,全然是自生自灭,个中乐趣也足够我享受足够我快乐了。”
就这样,在博客这片“自留地”上,陆萍笔耕不辍,时而有新的读者和文友留言,更结交了一两个真正知心的诗友,她很为这样的状态怡然自得。“去年夏初,我博客上忽然来了个陌生的ID‘老陈评诗’,神秘的老陈与我素昧平生,却每每通过一篇三四千字的文字就可以洞察我的昨天和今天。文中那份深刻独到,切我诗句,潜我心魂,瞬间让我从另种视角,看到陌生的自己。文学生涯中再没有什么比收到这样的大礼更让一个作者感动兴奋。”随着“老陈”的留言越来越多,陆萍愈加将这位素未谋面的“网友”看做知音,于是在此次决定出版诗集的时候,特地留言邀请他参与。这边厢陆萍略有忐忑地给老陈留了言:“如果出版社允许,我想在书的某处,有名有姓地推出你,请问该用如何的文字介绍?”那边厢老陈倒是回复的飞快:“我的初衷就是和你交流学习诗歌,这样就够了,有心得,彼此意会,各有快意,夫复何求?”这一瞬,陆萍觉得仿佛诗神在前——诗的神圣,莫过于此;诗的最高形式,莫过于此;诗的殿堂模样,莫过于此。友人如镜,陆萍时常跟随着老陈的文字重新审阅自己的诗作,而在这个过程中,她忽然动念,想把这几十年来写下的诗汇编成集——不是想要出版,也不是想要总结,“就像铁圈滚出去时,路上碰到什么改变了方向一样,我就是觉得要汇编一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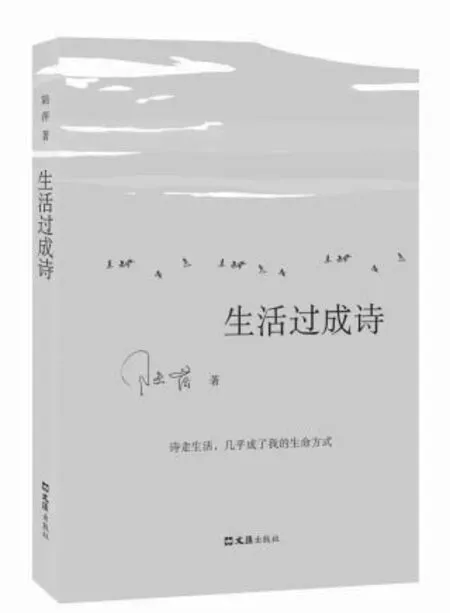

想到便去做了,于是在那个夏天,陆萍在酷热中把自己这十几年来存在电脑里从未寄出去投稿的作品翻翻看看,增增删删,心里生出些许满足,却并不知道这些诗稿在两个多月后将遭遇幸运。她把写在2010年之前的诗汇成一册,命名为《玫瑰兀自绽放》;把2010年之后写的则命名为《生活过成诗》。“其实,成功就是一件事情的句号,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而有滋有味的过程体验,才是成功本身的内涵。”当然,很多时候命运如齿轮滚滚,很多看起来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情,暗处未必没有严丝密合的相交。当时的陆萍只是从心而行在整理作品,却在某一天翻寻资料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一张自己去台湾参加诗会时与哲思诗人梦蝶的合影。见到照片便勾起回忆,于是陆萍顺理成章地去翻看了他的作品和纪录片《化城再来人》,这才得知他的第一本诗集《孤独国》竟是自费出版的,顿时觉得自己也该去尝试一下。“我之前总觉得出版这种事情应该由出版社主动邀约,方才证明自己是有实力的,但看了梦蝶的例子,我忽然醒悟,何为‘为文学守夜’?坚持写作是一种,靠一已之力出版,也是一种。都是为诗尽了自己的一份绵力。有何不可?”
思想一动,方案即刻出来,陆萍决定自己设计版芯、排版、插图,由着自己性子,“主动”出一本自己的诗集。“那些天里的电子排版真是日以继夜,我四处求教,却怀着兴奋,欣喜自己遇上了新时代——早几十年,想要任性一下自己‘出版’一本书,哪有可能?”怀着一腔热血,陆萍就这么在电脑前忙了一夜又一夜,辛苦归辛苦,但想到自己用专业软件“飞腾4.1”排好的书,那淡雅渐变上色的页面,那自己选的插图、照片……女诗人化身“一个人的出版社”,感觉充满了成就。这时,陆萍的诗友、“桂冠诗人”王小龙知道了这件事,惊叹之余给陆萍指点了一条新路。“他说,陆萍,你为什么不去申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项目?我认为你完全够格。”命运的齿轮环环相扣,短短几个月内,陆萍就从“动念整理一下旧作”不知不觉走到了“申请基金出版诗集”这一步,并且很快得到了上海文化基金的回复,申请通过了。之后的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陆萍自己都还有点云里雾里的恍惚,更多的却是欣喜——不是为自己,却是为诗:“能够得到文化基金的支持,在眼下市场经济统领,文学萧条的今天,我很意外,但也倍感幸运。感谢诗歌,在我将近半世纪生命行走的过程中,是一条严厉的鞭子,让灵魂不曾倦怠。也感谢诗集后面这坚实有力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托将,让我感受欣慰也感受一种强大。”
细读两本诗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组总题为《刻在一块河石上的诗》的诗篇。众所周知,陆萍早年蜚声于文坛,1970年就发表了处女作,1972年写的歌词《纺织工人学大庆》在全国海选中胜出,由上海交响乐团灌制而唱遍神州大地。而她早年最有名的那首让她飞出国界的诗《冰着的》——我的痛苦是一块绝望的冰/因为绝望,才冷得透明……朋友,你如看见它,可千万别碰/世界上最怕的就是你的手温/我不愿让它轻轻融化/只因在绝望中冰着我最初的纯真——则是于晶莹剔透中真切地透露出冰冷的绝望,让人感同身受。1988年3月,陆萍因这首由《中国文学》译成英文法文的诗而被亚洲诗歌中心盛情邀请,赴印度博帕尔出席亚洲诗会,她在开幕式上亲自朗诵了这首诗,掀起了一阵“冰”的旋风。而很多年后,我们又从这组诗中重新感觉到了那种痛苦和绝望,原来,这是她为了悼念去世的先生所做。陆萍的先生是一位从事航天事业的科学家,2004年5月5日倒下的那刻,他口袋里还装着为“神五”奔波的机票。“人类向宇宙索取,宇宙自要人类付出代价”,这是陆萍在她先生的墓碑上刻下的二行诗,而其中隐忍不发的痛苦,却转眼在自己的诗篇里倾泻而出:在“血肉淋漓的深处”,“深沉的碎裂尖利地呼啸着/我痛成一个黑洞”,那洞是灵魂无法攀爬的无底的深渊,“灵魂有个对穿的洞/洞被血被泪洗过/光洁得不可思议”;“泪就这么悬着/堰塞湖般险恶/等我失足”;“箱里随便扯个残线断丝/都会活生生拖出一大段岁月”;“不知这口井有多深/落石三年才传来回声……我在井底望着飞鸟/不相信自己有过的曾经/坚固的守候被一枪打穿/手里捏着岁月而指间却流走了灵魂”……
这一字字,一句句,如泣如诉,如玫瑰兀自绽放,那红却是泣血染成。无怪乎今年已95岁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屠岸读毕这一组诗,便“按捺不住”,立即在“离你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北方”给陆萍写来长信表达心中的激越:“我读你的这一组诗,特别是其中的《让我的疼痛流出来》《深层的碎裂尖利地呼啸着》《痛断肝肠之后我为自己疗伤》《落暮时分》《不知这口井有多深》等,不只是使人印象深刻,真是深深触痛了读者的灵魂!这些诗句,这些诗篇中所营造的意象,道前人所未道,是一种空前的创造,但又不是刻意而为的形与意,而是从内心深处流溢而出的血与泪,出于感情的自然,却又经过了诗的过滤和净化,成为一种情绪的具象和精神的折射。没有亲身经历的悲情,写不出;没有诗的蓄势,写不出;没有构建语言张力的勇气和爆发力,写不出。这些,是诗。但,也不是诗——或者说不仅是诗,是生命!是生命的沉潜、升腾、濒灭和复活!这样的诗,是“做”不出来的。这样的诗,古诗中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诗,后人无缘模仿。不知道你自己意识到没有?而我,决不吝惜形容词。”
在屠岸看来,中国诗史上有过著名的“悼亡诗”,都是诗人悼念亡妻的。“悼亡”由于潘岳的诗题而专指悼念亡妻。元稹的《遣悲怀》,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此类诗词中的佼佼者。英国华兹华斯的《露西抒情诗》则是悼念早夭的恋人的杰作。但这些名作都是丈夫悼念妻子或者男性诗人悼念所恋女孩。“妻子悼念丈夫的有没有?我没有见到。”但陆萍的这组诗无疑填补了这个空缺,她把刻骨铭心的痛抒写得淋漓尽致。究其原因,正是陆萍用了“心”去调遣指挥语言文字,使它们为“心”服役,才能成就。对此,陆萍的文友毛时安亦深以为然——诗人陆萍以源于天性又出乎自然的才情,凭着对人类永恒主题的坚守挖掘及对人性与生命最幽暗无意识的探究,她的诗歌,便具有了广泛地激起人类共鸣的力量,也使陆萍完全能毫无愧色地跻身于当代最优秀抒情诗人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