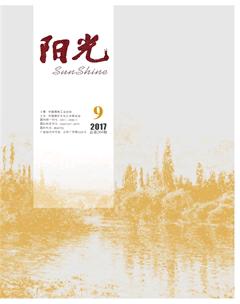矿工的女人
一
八月的天燥热燥热的,中午时分。一个十六七岁、身材瘦弱的男孩掂着饭盒下了运煤公路,拐进了一条通往矸石山的小路。
男孩踩着长满车前草的小路来到矸石山下。这座五十年代中期投产的煤矿,经过四十多年的开采,排出的矸石形成了高高的山岭。男孩朝最高处的一座山岭凝望,半山腰上,七八个女人正在扒捡着煤核。
妈……
妈……男孩把手握成喇叭状,朝着矸石山呼喊。
矸石山陡峭而险峻。一辆矿车刚刚倒过碴,黑烟还没有散去,躲在两边的女人便像甲虫似地迅速聚拢过来,在灰色的烟雾中拼命地扒捡。
冬梅踩松了矸石,她感觉脚下一沉,随着矸石仰面向下滑去,大小石块哗哗滚动,滑出去两丈多远,她被一块大石块挡住了。好险哪!她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呯呯乱跳,这个时候,她看见了山下的儿子,儿子一手掂着饭盒,一手握成喇叭状,正朝她叫喊呢。她朝儿子摆了摆手,意思让儿子先放那,等捡满一袋煤核再下去。
她站起身,用手摸摸屁股,火辣辣地疼,她听到上面传来“咯咯咯”的笑声。
梅嫂,屁股呲叉没有?乌眉皂眼的玉萍问。
呲叉了看俺秋水哥咋办?莲香接着说。矸石山上响起女人们哈哈的大笑声。
梅嫂,那不是侄儿给你送饭来了?玉萍指了指山下说。
日他娘,不让他送,他偏送,我早上带的几个馍还没吃完哩!
梅嫂,鹏飞该开学了吧?莲香问。
可不是,再有一个星期就该去北京上学啦!冬梅颇为自豪地说。
梅嫂,你多有福,娃子考上了北京大学,咱邻居都跟着沾光哩!玉萍说。
还享福哩,我给你哥整天愁得睡不着觉,光学费就得三四千,吃住哩?冬梅叹息道。
日头愈加毒辣了,冬梅的汗缕缕往下淌,肚子也咕噜咕噜叫唤起来,她感觉有点饿了。她扔掉抓钩,用手扒了起来。她那十个手指尽管早已磨得粗糙而皴裂,手指肚烂肉似地殷殷往外渗血,但扒起煤来依然是那样的麻利。黑东西抓在手里托一托,便知道是真假家伙,她有點为自己高超的鉴别力而自豪。
山上女人都下去了,再没人做伴了,她才把两半袋煤合成满满一袋。扎紧口,猛地往下一推,圆鼓鼓的蛇皮袋子便打着滚儿往山下滚去。
她踩着乱石密布的山坡,小心翼翼地下了山。弯腰扛起煤袋,趔趔趄趄往前走。
妈、妈、你放下,我扛!鹏飞飞奔着跑过来,抢着要接母亲肩上的煤袋子。
甭、甭、你身子还嫩!冬梅用手拦着,脚步放得更快了,简直跟小跑一样。她穿过一个个煤堆,终于来到一座小山似的煤堆前,啪地一声,把蛇皮袋子重重地摔在煤堆上。
我哩娘哎,累死我了!她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汗水,从她那沾满煤灰的鬓发间浸出,把她那张乌黑的脸冲出一道道小溪。
妈,我给你说,不让你捡了,你偏要捡!儿子噘着嘴,嘟哝着。
咦,你以为我想捡呀!母亲有些生气地望着儿子。你姊妹俩都上学,我不慌咋弄,你爸工资又开不下来,我不捡咋弄?
莲香端着碗过来了。梅嫂,还不吃饭呀?
你看我手脏的,咋端碗呀!冬梅说着,掂起一个塑料袋跑下了芦苇丛生的小河。清澈的河水映照着蓝天、白云,也映照着梅嫂那张乌鬼似的花脸。她捧起水,朝脸上哗哗地撩水,用肥皂使劲打了几遍,终于把煤灰洗掉了,她站起身时,感觉眼前金星乱窜,她晃了晃,“咕嗵”一声栽倒在水草丰盛的水边。
孩子一声惊叫扑了过去。
二
冬梅是十八年前嫁到榆树镇的。丈夫叫梁秋水,是个矿工。在八十年代的农村,能嫁给一个煤矿工人当老婆,是多少乡下姑娘的梦想呀!
和丈夫结婚后,两人一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儿子鹏飞小的时候,她每天回到家里还有人说说话。可自从三年前,丈夫把正上初中的儿子带到矿上上学后,她更加孤单了。平时下地,人家两口子扛着锄肩并肩有说有笑地走着,而她形单影只,只有自己和影子相伴行走在家里和地里之间。有一年麦收季节,遇上连阴雨,成熟的麦子都泡在了雨里,她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硬是把三亩麦子从雨肚里捞了回来。
那个时候,她就盼望着,啥时候能和丈夫团聚,日日夜夜厮守在一起,那该多好呀!
终于有好消息来了,丈夫在井下工作了十五年,按照国家政策,给家属办理了农转非。
冬梅三年前和丈夫来到玉女山煤矿。
刚来到煤矿时,冬梅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结束了多年的两地分居,两人像新婚燕尔那样快乐。工休日,丈夫带着她爬山摘野果子,到水库边嬉戏、钓鱼。他们还拿着傻瓜相机,让别人帮忙拍合影照。依偎在丈夫怀里,她感觉是那样幸福,两个酒窝里漾满了甜蜜的琼浆。
后来,丈夫又在大食堂给她找了一份工作。虽说是临时工,可每月除了管三顿饭,还发一百五十元的工资,在乡下上哪找这份工作?多少个温馨的夜晚,两口子憧憬着,好好干上几年,把儿子供养成大学生,再在矿上买套房,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然而,幸福的日子还没有过两年,煤炭市场风云突变,彻底打乱了他们美好的计划。
那天初冬的傍晚,冬梅正在案板上切菜。门开了,她扭头一看,丈夫回来了。丈夫没有像往常那样回来先拥抱她一下,而是垂头丧气地坐在床边,一声不吭。
她惊讶地问:秋水,你咋啦?哪儿不舒服?
哪都不舒服。丈夫有气无力地说。
那是咋啦?
丈夫告诉她,矿上发不出工资了。这月的工资应该在每月十五号发,可直到月底还发不成。矿上头头说,煤有的是,问题是卖不出去,卖出去的一部分钱又收不回来。前几个月的工资都是从银行贷款发的,现在国家紧缩银根,所有贷款项目一律暂时冻结,矿上实在是一筹莫展了。听说今天下午矿上已经开会研究,准备精简人员。冬梅说,我哩娘哎,这可咋办呀!
十一月底,矿上精简人员工作开始了,冬梅作为临时工,被第一批精简下来了。冬梅哭得一塌糊涂,丈夫一边用毛巾给她擦泪,一边劝她:梅,有我呢,你怕啥!你好好在家歇着,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还能养活不住一家人?
北边的寒流扑过来了,大风刮得树梢子哗哗地响,风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硬邦邦的,沟里河里都结了冰。半夜,又下起了大雪。韩冬梅看到窗外有些晃眼,以为天亮了,揉眼的工夫却闻见了浓重的雪气,才知道下雪了。她对丈夫说下雪了。丈夫说知道。原来丈夫比她醒得还早。已经临近年底了,矿上还是没有发工资的迹象。过罢春节,又该交孩子的学费了,怎么办呢?丈夫擦着一根火,点上烟。明灭的光线里,冬梅看见丈夫的眉头皱成“川”字,听到丈夫一声接一声地叹息。
一天晚上,韩冬梅从外面回来,看见屋里坐着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韩冬梅认识,是玉女山镇有名的煤老板钱二孩。
韩冬梅听见钱二孩对丈夫说:梁师傅,你好好考虑考虑,给我回个话。说着就告辞走了。
掩上门,韩冬梅问,这人找你干啥?
丈夫犹豫了一下说,他想叫我到他矿上干。
韩冬梅说,你咋想起来上他那儿干呢?去年拴柱要不是上他那儿干还不会丢性命哩!
丈夫叹口气说:那是他运气差。
咋,你想到他那儿干?
唉,矿上大半年没有开工资了,我着急呀!他说了,一个月一千八块,急用钱还可以随时支取。
屋子里一阵沉默。停一会儿,韩冬梅抬起头问,你不是没答应他?
还没有。
叫我说,你就好好在咱矿上干算了。矿上虽然眼下困难,那只是暂时的,形势总有好的那一天。再说,你在矿上干十几年,矿上也没有亏待咱呀!咱家里五间大瓦房,买的自行车、缝纫机,孩子上学,一家人吃穿花费,不都是矿上给的。前年矿上又给咱办理了农转非,一家人都吃上了商品粮,矿上对咱的恩情啥时候也报答不完呀。如今,矿上遇到难处了,你拍屁股走人,咱良心上过不去呀!
见丈夫不说话,冬梅又说:你到那个矿上干,要是有了三长两短,你叫我和孩子咋办呀!
冬梅仿佛又看到拴柱那拍成肉饼似的血肉模糊的身子,她的眼圈红了,用手帕揩起了淚水。
丈夫低下了头,叹了口气,又叹了口气,一拍大腿说,不去了!
三
过罢年,矿上想了一个办法,给职工发煤票,煤价八十元一吨,谁卖了就顶谁的工资。
动员会开过几天了,也没见有多少人行动。聚在一起时,大家都唉声叹气说,现在煤到处堆积如山,上哪里去卖呀?有的人把煤票以每吨六十元,甚至五十元的价格卖给了二道贩子。
丈夫也领了六十吨煤票,两口子商量着怎么办?是像其他人一样卖给二道贩子,还是自己卖?冬梅说:咱矿上的煤也不赖,咱老家在集上,我回去一趟看看。要是找到场地了,就拉回去一车试试。
三天后,冬梅坐着堂哥合兵的大货车来了。当天下午,就装了二十多吨煤,第二天就回到了三百公里外的老家榆树镇。
玉女山矿煤质好,价格适中,煤拉回家没几天就卖完了。冬梅信心大增,紧接着又拉了一车,不到十天又卖光了。
然而,拉第三车的时候,就没那么顺利了。一到家,就遇上了连阴雨天,雨一个劲儿下个不停。看着飘着煤油的煤沫被水白白冲走,冬梅着急上火,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老歪叔给她出主意说,你去找找大圈,他开着轮窑厂,你给他说说,拉给他,就不用发愁了。
冬梅不是没想过找大圈,高中时大圈曾疯狂地追她。可冬梅就是看不中大圈的德行。一次,两个女生在厕所解手,他从砖缝里偷窥,被老师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大圈怀恨在心,半夜时分,竟然把老师家的窗玻璃砸了个粉碎。校长一怒之下,坚决开除了这个害群之马。从此,冬梅和他彻底断绝了关系。后来,冬梅嫁给了矿工梁秋水,两人再也没有联系过。现在上门找他,还真有点难为情。可是,不找他,这一大车煤堆放在这里怎么办呢?总不能就这样在家熬下去呀!
思来想去,冬梅只好租了一辆三轮车,赶到了二十多里外的田楼轮窑厂。
大圈正翘着二郎腿,坐在办公桌后边一面悠闲地抽烟,一面观赏者雨中的情景。他那十八孔轮窑在潇潇春雨中像蒸笼一样散发着白色的雾气。他在心里盘算着,这一窑砖出来,又能赚个四五万块。一想到这儿,心里就像猫娃舔一样舒坦,他禁不住用手轻轻敲起了桌面。这个时候,一把红伞出现在门口,伞下是一个模样标致的女人。那女人问:黄厂长在屋吗?
大圈站起来,定睛一看:呀,这不是老同学韩冬梅吗!几年没见,冬梅还是那样白,身材还是那样圆润而饱满,眉眼还是那样妩媚动人。大圈忙迎上前去,激动得说话都有些颤抖了:哎呀,老同学,真……真没想到你……你会到咱、咱这寒舍来!
冬梅说明了来意,并把带来的样品让大圈看了一下。大圈略微踌躇了一下,前一阵子煤场刚进了七八车煤,货源充足,可昔日的恋人找上门来,他不能不要,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第六感觉告诉他,重温旧梦的机会来到了,一定要抓住,千万要抓住!他和冬梅谈好了价格,一百五拾元一吨,货到付款。
冬梅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坐在返回的大篷车上,尽管老天依然阴沉着脸,尽管外面雨声潇潇,但冬梅心里畅快极了。伴随着雨点敲击大篷车顶的嘭嘭声,她唱起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第二天,冬梅找了一辆四轮拖拉机,跑了五六趟,等把煤全部拉完了,已是傍晚时分。两人拉了一会家常,大圈又向冬梅问了一些煤矿和她的家庭情况。正说着,会计把钱送来了。大圈拆开一捆,从中抽出几十张简单数了数,递给冬梅说:你数数。冬梅数了一遍,多了五张;又数了一遍,还是多五张。她抽出多出的票子,递给大圈说:老同学,你数错了,多了五百。
大圈忙用手挡住说:多五百就多五百呗。
那不行,咱说好的价格,多一分我也不要。冬梅说着,又递给大圈。
大圈说:我的轮窑厂我当家,多给你三百五百算啥?再说,侄子上高中,正是花钱的时候,权当我给侄儿拿点学费吧。
看大圈一脸真挚和诚恳的样子,冬梅只好收下,可总感到心里欠着人家啥儿。
这时,屋门口出现了一个体态臃肿的中年女人。那女人看屋里坐着一个漂亮而陌生的女人,剜了冬梅一眼,有些变了调的声音问:你吃啥菜?
大圈脸上顿时显出不悦来:我晚上不在家吃。
那你上……上哪吃?女人陪着小心问。
大圈挥挥手,不难烦地说:你没看我正谈生意吗?
女人嘟嘟囔囔地走了。
又说了一会儿话,冬梅要走。大圈说:你走啥,老同学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你不叫我表现表现呀?我已在杜康酒楼订好了饭,咱这就去。
盛情难却,冬梅只好坐上大圈的小轿车。一路上,大圈尽说一些老婆的种种不是和对老婆的厌恶。言外之意,与老婆生活在一起简直就是受罪。说着话,就来到了榆树镇杜康酒楼,两人进了包间,大圈很快点齐了酒菜。他倒了两杯酒,要敬冬梅,冬梅说啥也不喝。大圈只好喊服务员拿了瓶红酒。他一边倒酒一边说:红酒没啥度数,还美容养颜。他给冬梅倒了一大杯。两人碰杯后又一边吃喝一边聊天。志得意满的黄大圈向冬梅说起了他的发家史,言语间不时炫耀出他的家产和财富,并向冬梅透露出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打算再投资建一座轮窑厂,目标是当全镇的首富。末了,大圈感叹说:冬梅呀,论说这些年我没少挣钱,可就是娶了个老婆让我不满意呀!
大圈身子靠近冬梅,直勾勾地看着她说:老同学,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冬梅问:是什么?
是没把你娶到手!
冬梅脸刷地红了。她说:我有什么好的?
你漂亮、贤惠、能干,还善解人意。比我家那熊女人强一千倍!大圈说着又靠近冬梅一些,用试探的口气说:梅,你离开秋水跟着我行不行?
冬梅说:老同学你是不是喝醉了?
大圈说:没醉。你跟了我,我不会让你吃一点苦,受一点罪,让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冬梅笑了:你的好意我领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辈子既然嫁给了秋水,是苦是甜我都会跟他一辈子!
大圈说:佩服!佩服!来,再碰一杯!
冬梅本以为红酒没啥度数,谁知道几杯酒下去,她的头晕乎乎的,脸一片酡红。她赶紧用双手托住了头。
大圈抱起冬梅就要往沙发上拖。
冬梅睁开眼,看见大圈嘴脸已谗得不成样子,她的酒醒了大半,她从提包里拿出大圈之前多给的五百元钱,“啪”地摔在他面前,然后扬长而去。
四
七月中旬,矿上召开职工大会,说为了扩大煤炭销路,决定在淮河岸边的刘湾码头建一个煤炭中转站,动员每个职工集资八千元。丈夫和她商量时,冬梅没有丝毫的犹豫,就说咱也拿八千元。
丈夫犹豫说:这下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就不够了。
冬梅说:没事,我到矸石山捡煤核去!
丈夫一把把她抱在怀里,哽咽着说,集资是自愿,这钱留作孩子的学费吧,我不让你去捡煤核了。
俩人紧紧搂抱在一起,冬梅的泪水流了出来,她说:煤矿是咱的根,是咱的家呀。煤矿要是不行了,甭说捡煤核,喝水也找不着地方呀!
韩冬梅来到了矸石山。儿子开学的日子愈来愈近了,冬梅加班加点地干。天麻麻亮,她第一个赶到这里;天黑透,最后一个离开。每天晚饭后,别人休息了,她又来到矸石山,打着矿灯捡一阵子。这个时候捡煤核的人少,只捡小半夜就比一天捡的还要多。
五
站在煤堆旁等候母亲的鹏飞迟迟不见母亲上来,有些着急了。他忐忑不安地走到河岸边,喊道:妈——,妈——,没有回应。一种不祥的预感倏地升上心头,他跳进芦苇丛,跌跌绊绊地冲到水边,他看到了倒在水边的母亲。
妈,妈他摇晃着母亲,没有应声。他哭喊着,抱起瘦弱的母亲,吃力地爬上岸。捡煤核的女人们跑过来,众人七手八脚把梅嫂抬到架子车上。鹏飞拉起架子车,莲香、玉萍在两边扶着,三人一路飞奔,把梅嫂送到了矿医院,抬进急诊室,梅嫂醒来了。
梅嫂睁开眼,左右看了看,惊诧地说:我,我咋在这儿?
妈……儿子叫了一声,泪水汹涌而下。
梅嫂,你吓死俺了!玉萍还没说完,莲香抢着说:你四脚拉叉,往那一躺一声也不吭,俺几个慌着把你拉来了。
医生摸摸病人的脈搏,又用听诊器听了听,放下说:你这属于低血糖,劳累过度,输几瓶水就好了。
得多少钱?梅嫂坐起来问。
大概百十块吧。
我不输,我没事。她说着,就要下床。
医生说: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身体垮了咋还去挣钱?
妈,输两瓶水吧,输点水就好了。鹏飞擦了擦眼泪劝道。
梅嫂叹了口气,极不情愿地躺了下去。
妈,你等着,我回家拿钱去。鹏飞说着,跨出急诊室,向家中奔去。
鹏飞取出钱,刚下楼,就看见穿着一身工作衣、满脸煤尘的父亲从井口方向跑来。看见儿子,他焦急地问:你妈咋啦?
医生说低血糖,得输水。
父子俩大步流星往医院走去。走进急诊室,里面空无一人。
哎,人呢?两人四处寻找。一个护士说:她说出去买点东西,谁知出去这么长时间还不见上来。
父子两在医院内外寻找个遍,哪还有冬梅的身影?
是不是又去矸石山了?鹏飞说。
父亲想了想说:走,去看看。父子俩沿着通往矸石山的矿车道急急走去。
一辆矿车蜗牛似地爬上矸石山顶,一个鹞子翻身,哐当一声,矸石煤沫飞沙走石般倾泻而下,一路荡起腾腾黑雾。
黑雾刚刚散去,一群黑黑的女人又蜂涌似地向山顶爬去。父子俩仔细辨认着,突然鹏飞一指:爸,前面那个不就是俺妈吗?
高高的矸石山上,一个戴红纱巾的女人背着蛇皮袋子,躬着腰,踩着崎岖而险峻的山路,艰难而又执着地一步步向上攀登……
李庆伟:河南沈丘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已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阳光》《牡丹》等刊物发表小说70多万字,作品先后获第二届老舍散文奖,全国职工文学大赛一等奖,新世纪报告文学奖等。
——旧诗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