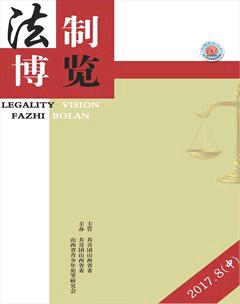转换性使用制度的国外困境
邹艳琴
摘要:“转换性使用”起源于美国司法实践,是一种著作权侵权的抗辩制度,近年来频频出现在我国学者对合理使用的个案研究当中。本文阐述了转换性使用的渊源与内涵变迁,分析了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最后从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价值出发,对转换性使用制度的本土化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转换性使用;合理使用;目的性转换;内容性转换
中图分类号:D971.2;D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23-0182-02
一、转换性使用的提出与内涵
“转换性使用”首次出现于美国最高法院是在一例著作权侵权案件——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案中①,当时法官将其作为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的首要因素。此举直接对美国产生了冲击,一方面,大量的使用行为被免于侵权,创作环境极度宽松带来了音乐、美术、文学等各个产业的繁荣;另一方面,传统的合理使用判断方法发生了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市场影响”因素逐渐被淡化,甚至在地方法院,不少法官将其等直接同于“合理使用”,许多错判一直被诟病至今。
至于具體内涵,在早年的判决当中,法官一致将其定义为形式、内容上的变更,但在近些年的判决中,改变目的的精确复制行为也被认为属于转换性使用,因而就出现了“内容性转换”与“目的性转换”的分野,且后者却越来越凸显出其地位,轰动一时的数字图书馆案便属于此类。
二、转换性使用认定的困境
(一)内容性转换认定的困境
内容性转换属于选择性复制,其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判断复制内容的多寡,但这一传统路径在新兴的挪用艺术领域愈发暴露出了不足,2014年Cariou V Prince案便是例证。原告Cariou是一位摄影师,被告Prince在创作作品《运河区》时使用了原告作品集《Yes Rasta》中的三十张肖像照片,但只使用了图像的一小部分,并且通过着色或者其他方式将原来的人物面部特征遮蔽;法院最终认定其中的二十五张图片具有转换性而剩余五张构成侵权。
此案之后,舆论哗然,因为从法官的判决当中,人们无法知悉何种程度的美学变化才能构成实质的转换。显然,常人对艺术的敏感远远不及专业视角,何况早在Campbell案中,最高院法官就提醒过,将美学价值交由法官判断绝对是不可取的,若无法对转换程度做出合理解释,就将导致内容转换与原作作品演绎权的界限模糊。
(二)目的性转换认定的困境
如前文所述,目的性转换的力量在于,即便精确复制也可能成立合理使用。但事实上,“不同的目的”并非安全界限。应当注意到,原作版权所有人创作意图也许是单一的,但其衍生市场却会随着时代发展延伸,版权法赋予版权人的多项专有财产权正是通过衍生市场而得以保障的。目的性转换中的难题,恰恰就在于如何确保使用行为与原作的衍生市场不相冲突,如果衍生市场并不明确,此时就必定涉及到作者专有权利与合理使用行为的划分。如何解释衍生市场的范围,应当将其限定在特定范围之内还是随时代发展相应地进行适当扩张,这一问题尚值得深思。
三、转换性使用的本土构建
不同于美国版权法中四因素的判断方法,我国的立法模式是明文列举十二种合理使用行为,因而缺乏一定弹性;而转换性使用的引进便可化解这一难题,为当下挪用艺术、电子游戏直播等诸多著作权案件提供分析路径。但鉴于美国司法实践中的误区与现存困境,在我国的法制背景中如何构建转换性使用制度,笔者认为应当把握以下重点:
(一)避免过度强调转换性
如前所述,转换性使用在美国合理使用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合理使用四因素与转换性使用之间本身存在交叉重叠,过度强调转换性导致美国司法实践中出现许多错判。我国学者应当吸取前车之鉴,避免将合理使用与转换性使用混为一谈。合理使用四因素中历来最受重视的“市场影响”因素同样是我国著作权侵权审判中的重要考量内容,因而不能因为使用行为的转换性就对市场影响避而不谈;由于我国的合理使用标准相较于美国而言更为严格,对转换性和市场影响进行双向分析则更符合我国国情。
(二)适当适用内容性转换
传统的转换性使用案例多数均因内容性转换而得以成立,而挪用艺术市场在国内外的繁荣更暗示了内容性转换在当今存在的价值。尽管目的性转换更有利于转换性使用的成立,但仍应为内容性转换留出一定空间,否则挪用艺术家将难以预计其侵权的风险。类比文学作品或专利侵权,美术作品中改变程度也并非不可识别,但适格的判断主体可以选择艺术专家,以其专业视角做出合理的判断。
(三)以立法价值为根基适用目的性转换
目的性转换被国内学者提及最多,但在认定目的性转换时不能绕开原作衍生市场的界限。笔者认为,衍生市场的划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涉及立法价值的考量,也即更偏向于保护公共利益还是著作权人。
不同于英美法系,在我国的立法价值之下,版权乃天然的财产权,合理使用只应当限于个别领域,且应紧紧围绕公共利益开展。因而我国对于目的性转换应当审慎适用,避免过度扩张。不过在个别领域,也应当结合时代背景下的产业政策而做出突破,如当下在文学、音乐及电影领域,消费者普遍热衷于挪用式创作,于是许多著作权人主张“版权作品使用共识”,呼吁跳出偏执的版权保护意识,对消费者的使用行为表现出宽容的态度。版权产业自发形成的这一类“版权共识”为未来的“转换性使用”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从产业环境到司法态度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因势利导,将更有利于转换性使用的移植。
四、结语
美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为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诸多经验,曾经出现的误区应当成为前车之鉴,而当前面临的困境也应当被我国学者所重视。审慎对待这些误区与困境,避免其转换性使用地位与内涵的过度扩张,才是制度最佳的本土化方式。
[注释]
①法官评述.adds something new,with a further purpose or different character,altering the first with new expression,meaning,or message.
[参考文献]
[1]阮开欣.美国版权法新发展:美国数字图书馆构成合理使用[J].中国版权,2016(1).
[2]王迁.电子游戏直播的著作权问题研究[J].电子知识产权,2016(2).
[3]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27-231.
[4]尤杰.“版权作品使用共识”与参与式文化的版权政策环境[J].上海大学学报,2016,33(1).
[5]Ashten Kimbrough.Transformative use VS Market Impact:Why The Fourth Fair Use Factor Should Not Be Supplanted By Transformative Use A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in A Fair Use Analysis[J].Ala.L.Rev,2012.
[6]Edward E.Weiman,Transforming Use:The Google Books Cases Have Created A New Area of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Transforming Use Defense to Copyright Infringement,LOS ANGELES LAWYER,2014.
[7]Nell Weinstock Netanel.Make Sense of Fair Use.Lewis&Clark Law Review,2011,15(3):715-771.
[8]Pierre N.Leval.Toward a Fair Use Standard[J].HARV.L.REV,1990,103(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