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为农村书写病历
三秋树
黄灯,为农村书写病历
三秋树
读黄灯的书《大地上的亲人》,犹如万箭穿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黄灯原本可以对这些苦难选择性失明,可她选择跳下打造精英的流水线,坚持自己的底层立场。
读书改变命运
2002年之前,黄灯走的是读书改变命运的路线。她1974年生于湖南汨罗的凤形村,自幼喜爱读书,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会走出乡村。1995年,黄灯从湖南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到岳阳一家苎麻纺织印染厂做文秘。
1997年,国企改革,要求干部到基层当工人,黄灯调到车间做挡车工。在短纺车间,她学会了梳棉和并条两个工种,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三班倒。变故接连发生,1998年,受香港金融危机影响,工厂效益变差,连体力活也没得做。1998年年底,24岁的黄灯下岗了。
此刻,黄灯切身体验了什么叫“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什么叫“改革阵痛”。那意味着每个月不到80元的工资,一个大学毕业生突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也意味着同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养不起家了。
她要再一次靠考学改变命运。1999年,黄灯考入武汉大学现代文学专业。象牙塔内,读书、写作、听音乐,那些不堪过往似乎从未发生。周围同学谈论最多的,是如何拿到经费、课题,怎么取得导师的青睐及出国等等精英通道。
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令黄灯感到可悲。在选择论题时,看到同学幼稚而天真的纸上谈兵,作为“下岗女工”的她忍不住驳斥,就连导师都暗示她要平和。而黄灯知道,她不是愤世嫉俗,她只是知道生活的另一面。
读研的三年,是黄灯思考的起点。
一场拜访令她跳下精英快车
2002年,黄灯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博士。那年中秋,在广州打工的堂弟带着一盒精致的月饼和一箱国产牛奶,敲开了黄灯宿舍的门。
堂弟不肯跟黄灯去食堂吃饭,就匆匆赶回工地。黄灯知道有很多亲戚在广州打工,可所谓精英路线的其中一条,不就是告别农村并与老家的亲戚减少交集吗?堂弟的拜访让黄灯对自己的冷漠产生了严重质疑——知识不应该稀释感情与人性。
而这个印象中一直很可怜、没得到过爱的弟弟,依然懂得关心亲人,依然保存了悲悯和爱的能力。这不能不让黄灯反思:“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进而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图景中,悄然放弃了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
这成为黄灯与亲人联系的起点,也是她选择写作方向的起点——学术应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读书并不完全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此后,每逢传统节日,黄灯跟着堂弟,一次次穿过广州城中村的街道,见识了什么叫“一线天”“握手楼”“蜗居”,见识了什么叫暗的生活。而在这些地方,黄灯通常是礼遇的对象,接受同乡们腊鱼腊肉的招待,“改善生活”。
一位亲戚住在两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用五瓦的灯泡,很得意:“用这种灯,电表根本不会转。”她奉行“赚不到钱就尽量不花钱”的生存原则,在阴暗、逼仄的出租屋里一住十几年,只为凑齐孩子的学费。而堂弟在母亲早逝、父亲不顾家的家庭长大,初中没毕业就到了广州,靠打零工维生,15岁时因没办暂住证被关过收容所。
2006年,博士毕业后,黄灯留在广东金融学校任教。业余时间,她探访了一批在广州、东莞打工的亲人。他们打工的艰难和无奈刺痛了作为旁观者的黄灯,她打算写一本书作为记录。
代际的贫穷开始轮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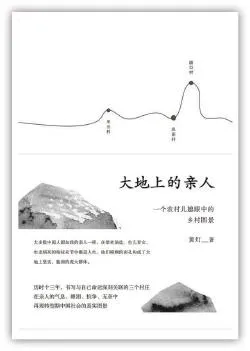
2004年,因为一篇《今夜我回到工厂》,黄灯与同在中山大学读博的杨胜刚相识。黄灯在文章里叙述了几位国营工厂工人下岗后的艰难处境。杨胜刚被其中的真实打动,“从没见身边的人写过这些。”他给黄灯写邮件,讲起农民的苦难:“极度的贫困使他们只能紧贴着地面卑微地生活。”
杨胜刚来自湖北丰三村,家里兄弟姐妹七个,他是举全家之力,走出乡村的读书人,也是那个大家庭唯一的希望。随后,两人相识相恋,并在同一所学校任教。
2005年,黄灯跟杨胜刚去了他的老家。虽然同样出身农村,可那样的贫穷还是给了黄灯欲罢不能的“我要跟你共担”的疼惜。
可等到他们真正走进婚姻,黄灯才知道,有时候,这种承担是多么的杯水车薪,又是多么无力。从1993年到2009年,杨胜刚的大哥杨敦武跟着四妹夫在北京做活十六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工资存在妹夫那里。那十几万元是大哥一家改变命运的全部希望。为了这个希望,大哥大嫂不得不将一双儿女留在农村,在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奋斗了十六年。可由于开发商突然消失,作为包工头的四妹夫一夜之间破了产,四妹夫为躲债而有家不能回。
已经步入晚年的大哥大嫂不再是城市的壮劳力了,他们不得不一无所有地回到老家。打了水漂的工钱和一身伤病,是城市留给他们最深的伤痕。
一年又一年,黄灯每年春节都先跟杨胜刚回老家,然后再一起回自己的老家。一年又一年,她目睹了亲人们生活的真相:妹妹出家了,外甥女因此辍学,越来越内向封闭;破产的四妹夫住在北京城中村,靠着四妹做洗碗工和两个女儿当导游维持家用;在体力最好时,哥嫂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嫂像当年的公婆一样,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去外省务工,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攒一万多元,运气不好,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20岁出头的他,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婆婆去世了,维系大家族最牢固的纽带断了,而老人生前最大的遗憾是家里有两顶博士帽,却不如一个当官的。在老人看来,只有出一个当官的,才可以彻底改变家族的命运。
为农村书写病历
因为体验至深,黄灯也越来越了解丈夫的沉默与压力,甚至是压抑。和大部分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杨胜刚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教书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可与他亲人深重的苦难相比,他觉得自己的这些快乐都是带罪的。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让他无法对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他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他从未有过回绝的念头。
2016年,黄灯和老公一起在老家度过了没有婆婆的春节。返乡后,黄灯写了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里的乡村图景》,阅读量超过了100万人次。
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黄灯一直心生警惕,但她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儿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
这种发声引来关注与共鸣,但也遭到质疑,质疑声中最大的声音是:“农村真的像你书写的那么悲催吗?”在很多人的眼里,乡村是田园牧歌,是诗与远方。这样的质疑让黄灯更加坚定自己的底层立场,除了教书,她持续写作,将亲人们的故事逐一写下。于是,就有了《大地上的亲人》这本书,刷新着大家对中国当下乡村的印象,也令大家对这片土地上三十年来的发生,有了重新的审视。
《大地上的亲人》一共三章,黄灯老公跳过第一章,看了后两章。因为第一章是写他的家人的事情,那些他再熟悉不过,却最不忍心直视。后两章是写黄灯家和外婆家。
作为一个老师,黄灯很关注班里那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她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心灵上的包袱,也理解他们对身世的回避。尽管这是一个太大的命题,可是,记录、发声,她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她不是医生。她会坚持为农村做记录,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在这样一个狂奔的时代,她要慢下来,继续关注、思考与记录。
(编辑 张秀格gegeprett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