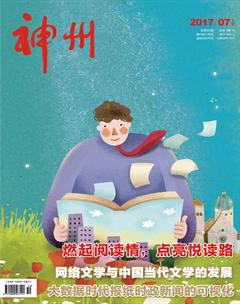八大山人的绘画意境

摘要:中国写意画发展到明清时期,以“四僧”和“扬州八怪”为代表,将写意画推向一种新的高度。尤其是“四僧”,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皆一生寄情于书画中,游离于法度外。其中以石涛和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本文主要浅谈八大山人作品的绘画意境,本人才疏学浅,敬请各位老师、同行批评指正!
关键词:八大山人;趣味;笔墨;痛;意境
八大山人原名朱耷,为明宗室后代,是明宁王朱权后裔,受封辅国中尉。明亡后,为避政治迫害保全自己,二十出头的他便装聋作哑,遁入空门,削发为僧过上了住山讲经,吟诗作画的日子。后建道院,其名为“青云谱”,晚年自筑陋室“寤歌草堂”于南昌城效,后八大基本在此终老,享年八十。有一首诗描述了八大晚年在“寤歌草堂”的生活状况:“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丛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
想要解读八大山人的画必须要先从其遗留下来的作品提款诗作中寻找线索。八大山人曾在一幅《古梅图》上题诗道:“分付梅花吴道人,幽幽翟翟莫相亲。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尘。”,其中“-”字被人抹去,后人解读此字应该为“胡”或者“虏”,意为“扫胡尘”或“扫虏尘”。此诗表明了八大山人反清复明,意将满清统治者“扫”出“南北”的态度思想。还有一首诗写道:“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诗中所说的“思思肖”是指怀念郑思肖,他本是元初遗民画家,其身在元却心念旧宋,画兰花露根不画坡土,人问何故,他回答说:“土地都被人抢夺去了,你难道不知吗?”,八大借用典故表明自己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态度。这两首诗足以证明其心念朱明王朝,深怀国破家亡之恨。可以说这种痛恨一直伴随着八大一生,他一生大多作品皆和这种心境密不可分,这也成就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我暂且称他的绘画艺术为“痛”的艺术,因为他作品所呈现给我的震撼是一种悲痛的震撼,其所传达出的悲痛的力量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谈到八大的绘画艺术,不得不说其笔下的兽鸟鱼虫,多白眼向上或闭眼沉思,老干枯枝多东倒西歪,凄凉荒冷,似乎正是他的“化身”,把对满清统治者和他对这个世界的“高冷”的反叛的态度用一种象征意义上夸张、变形的趣味,尽乎完美的呈现在绘画作品中;可以说是非常之巧妙,而他却很擅长这种“游戏”,可体现在八大山人这个名字的由来:朱耷,可拆分为“牛,八,大,耳”,“牛耳”在古代多指权利,其取“八大”而舍“牛耳”正是指如今失去“国家”的自己,其弟朱道明改名牛石慧,兄弟二人一“八”一“牛”正好是“朱”字,可见其用心良苦。到此并没有结束,他在画作上经常把“八大山人”连笔写成“哭之”“笑之”的模样,其中也暗含着自己哭笑不得的无奈,和悲痛的心境。在身处“他世”的情况下,八大也不得不玩这些“游戏”,只能将自己的情绪暗藏在这些意境里。而八大在笔墨上则表现的很直观,其笔墨极其简练、孤独,近乎“癫狂”却又能收放自如,画面几乎没有文人画的安静、雅致,多粗乱生冷,正应证了他“墨点不多泪点多”的感叹。他的构图也很有特点,从自然的角度看,总是觉得他的画面少了一些“内容”,在他画了不少的独鸟孤鱼,无水无草的“空洞”的意境中有所体现,这种“空洞”的意境也直指“不完整”的自己,及无力回天的复国之梦。可见八大山人心中“亡国”之恨有多深,心中有多苦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八大的繪画艺术就是其“痛”的艺术。
八大山人的绘画和他的“亡国”之痛如出一辙,他的绘画意境主要表现在通过各种隐含的趣味表达他的痛苦和悲伤,而他独特的身世和经历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貌,他这种“痛”的艺术形成的那种“带刺的美”,足以让人触动心弦!
作者简介:王旭明,1994年出生于甘肃省陇南市,汉族,现就读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endprint
——评朱良志先生《八大山人研究》(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