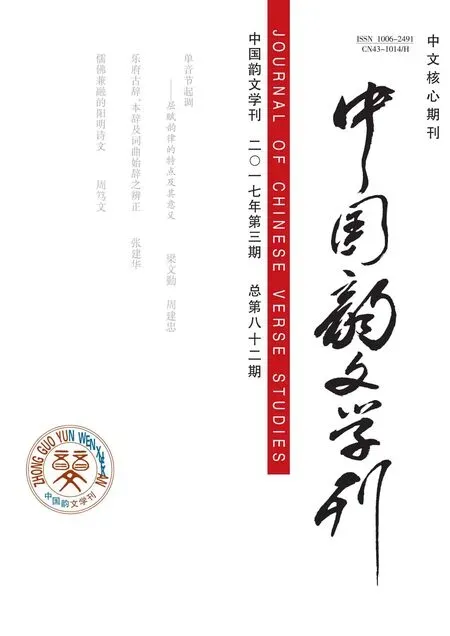乐府古辞、本辞及词曲始辞之辨正
张建华
(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乐府古辞、本辞及词曲始辞之辨正
张建华
(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时,除沿用沈约《宋书·乐志》“古辞”之概念外,另引入“本辞”概念。从《乐府诗集》编排体例可知,古辞与本辞具有确乎不同之所指。与本辞概念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是,在词曲研究领域中则多见“始辞”之用。这三个概念同中有异,其间有联系亦有区别,目前学界尚无成说定论。本文认为,本辞为同一曲题乐府诗创作的本源参照,它是汉乐府处于民歌或俚歌阶段的状态,古辞是将本辞进行音乐加工后,可入于汉魏晋宫廷音乐歌唱的汉代乐府歌诗,始辞则是指为词曲牌调名所主之曲调填配的初始之辞作。
古辞;古乐府;本辞;始辞
北宋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时,首次引入“本辞”之概念,但郭氏并未对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界定,仅在相关曲题之下列出10首本辞。郭书同时还沿用沈约《宋书·乐志》“古辞”之概念。但本辞究为何指、何意、何用,学界尚诸说不一。因本辞与古辞具有密切之关系,所以,探究本辞含义必自古辞而始。
一 关于“古辞”
1.古辞界定诸说
“古辞”亦称“古词”。关于古辞最早之说法见诸《宋书·乐志》,其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宋书》依此标准,共收古词16首,皆在“相和”一类。《晋书·乐志》有相似之表述,当是撮录《宋书》而略有不同。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卷二《乐府第七》:“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减之,明贵约也。”左延年为魏国协律郎,活跃于黄初(220—226)、太和(227—232)年间,所谓“增损古辞”实际是他将汉乐府歌辞进行拼接分割,奏入乐章。《隋书·音乐志》:“《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既然古辞是汉以来旧曲所配的歌辞,它即为汉世所创无疑。唐李善《文选注》卷二十七“古辞”下注曰:“言古诗不知姓名,他皆类此。”又唐李延济注曰:“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散採齐、楚、赵、魏之声以入乐府也,名字磨灭不知其作者,故称古辞。”是李善等认为,梁萧统等所选古辞,皆是汉世搜集的无主名之歌诗。逮及宋世,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明确标注“古辞”者有72首(实收古辞73首,另1首未标注者《宋书》列为16首古辞之一),此为研究古辞最为重要之资料。元左克明《古乐府》将古辞又细勒为“古辞”“汉古辞”“宋古辞”(《艾如张》曲题之下,无题1首)三种共96首,实已与以上诸说颇异。左氏是唯一将“古辞”再加细分者,其成书距郭书不远,亦有相当之价值。明冯惟讷《古诗纪》是迄今所见搜罗古辞最多的诗歌总集,收古辞160余首。明梅鼎祚《古乐苑》则收古辞46首,大体因循郭书而略有删汰。梅书仅将“汉铙歌”18首中《朱鹭》1首列为“古辞”,其余17首则弃而不录,不知所据。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曰:“乐府之体,古今凡三变:汉魏古词,一变也;唐人绝句,一变也;宋元词曲,一变也。”胡氏认为汉魏古辞,可作为乐府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有清一代,对古辞讨论者不多,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两汉古辞”下注曰:“皆无名氏。”似乎是遥承唐李善、李延济等注家的说法。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认为:“凡《宋志》中所谓‘古词’,决为汉人作品”,“‘古辞’之名,起于《宋志》,后之录乐府者皆袭之。《宋志》定‘古辞’界说,谓‘并汉世街陌谣讴’,惟《乐府诗集》所录古辞,多于《宋志》一两倍,未必尽出汉代。”梁先生是第一个对郭书所录古辞的真伪提出质疑者。陆侃如《乐府古辞考》是近代学者对乐府古辞进行专题研究的首倡之作。陆先生认为《宋书》对“古词”之界定原指“相和歌辞”而言,“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便把范围扩大起”,“就大体看来,他大概限于汉代无名氏的作品,《西洲曲》及《灵芝歌》可算做偶然的例外”。他认为古辞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创制的;(二)入乐的。”因此,其所谓古辞之范围就史无前例之大,囊括“郊庙歌”“燕射歌”“舞曲”“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曲”“清商曲”“杂曲”八大类,约330首。但该书并未收录歌辞,仅于每一曲题之下列出歌诗题名,并作简要梳理考证。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则认为:“《乐府诗集》列《相和歌辞》一类,其中‘古辞’即为汉世民间之作。”萧先生只是就相和歌辞而论,认为古词为汉世民间之作。罗根泽《乐府文学史》指出,古辞之名,“盖创始沈约《宋书》,后世各史《乐志》及乐府书因之”,“《宋志》所载古辞,皆沈约认为汉世之歌”,“然《通志乐略》、《乐府诗集》所录古辞,视《宋志》几增一倍,是否尽为汉讴,又有问题”,“无名氏古辞每嫁名汉人”,“推原其故,盖偶或失名,或为甲为乙,不能断定,即题为古辞”。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第二篇在论述“清商三调”时也点出:“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平调’七曲,‘清调’六曲等,是汉代所传的曲名,其歌辞一部分传到六朝,被称为‘古辞’。”古辞既然是汉曲所传之辞,则必为汉世作品无疑。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前言》说:“现在乐府古辞中假如某一篇失去了当时合乐的标题,无所归类,则我们也不得不泛称之为古诗。”马先生的意见大概是说,古辞与古诗有时可以混同而称。逯钦立《汉诗别录》也认为:“古诗与古辞相当,故常有互混之例。”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专辟“乐府古辞”二卷,辖“相和歌辞”“舞曲歌辞”“杂曲歌辞”三类,共收古辞87首(含残篇,见汉诗卷九、十,魏诗卷十二),这一数目比《乐府诗集》所收古辞多出14首。曹道衡先生在其著述中也多次提及古辞,其观点与马、逯二先生的有点类似,如其云:“其实《相和歌》的曲辞,凡属古辞,都是取诗中几个字为名的,如《乌生》《平陵东》《东光》等”,“所谓‘古辞’,当指这一乐曲最原始的歌辞”,“《文选》所谓‘古辞’,只能是‘古诗’的同义语,非指乐曲原辞”,“我认为《文选》所谓‘古辞’,其实与‘古诗’是同义语”。刘德铃《乐府古辞之原型与流变——以汉至唐为断限》(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认为:“汉代乐府古辞的判定除了符合时代条件,也必须具有民间文学的特质。”刘博士将古辞分为“鼓吹曲辞”“相和曲辞”“杂曲歌辞”三类共计51首。
以上诸家观点,虽各说纷纭,但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古辞为汉世无名氏创作的乐府歌诗,另外古辞的特点在于其篇题和曲题保留着紧密关系,二者在指称上具有共一性,同时,二者与歌诗的内容或本事也具有一定关联性。这只是对古辞的初步印象,关于古辞的具体而微的含义,留待下文论及古辞与本辞关系时再作进一步发掘。
这里尚需辨明的是,“古辞”之同名异义词。如《碧鸡漫志》卷一“古音古辞亡缺”条引元结语:“呜呼!乐声自太古始,自世之后,尽亡古音。乐歌自太古始,自世之后,遂亡古辞。”这里的“古辞”是太古谣歌或乐歌的歌辞,“古”为“太古”。又比如,明万历茅刊本《花间集》温博叙:“如《清平调》《欸乃曲》《杨柳枝》《竹枝词》,即七言绝句,而实古词。”这里的“古词”是指古代的词作,其“古词”之“词”乃是文体之一种,即“诗词曲”之“词”。我们讨论乐府古辞,必须将这些同名异义的词汇剥离开来,以免引起思维混乱。
2.古辞与古乐府关系
乐府古辞与古乐府辞是两个密切关联而又截然不同的概念,但学界诸君或有不分者,往往混一而用。因此,有必要略申二者之关系,以进一步凸显古辞之特性。
古乐府较古辞之概念更为宽泛,它具有广狭二义。就狭义而言,专指汉乐府或汉魏乐府。之所以将魏乐府也连带而及,主要是因曹魏去汉不远,魏氏父子所作乐府,皆援古题、依古调、多可歌,即事名篇、赋题作诗,汉乐府之古风犹存,可以说大致延续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就广义而言,又有三层含义:一曰“沿袭古题”或“寓意古题”,更有或者,乃是从汉魏乐府诗句中派生出乐府新题,这类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意承袭汉魏乐府;二曰后世称前世之拟乐府;三曰可以入乐。后二层含义又渐不被提起,但至少需满足第一层含义。
先看狭义之古乐府。
假名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其卷一云“古乐府诗六首”,下列《日出东南隅行》《相逢狭路间》《陇西行》《艳歌行》《皑如山上雪》《双白鹄》六首诗,均为汉乐府歌诗,而且均为古辞。不过,此并非古乐府最早之文献出处。“古乐府”之称,最早见诸《宋书》,其列传第十一《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及《子义庆》附《鲍照》曰:“鲍照,字明远,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鲍照长沈约二十余岁,沈约却称比他稍早的鲍照所作之乐府诗为“古乐府”,可见,古乐府也不能简单地视作一个时间概念,认为前世之乐府较当世之乐府而言即为古乐府。也就是说,古乐府之“古”,非仅指古今之“古”。“晋宋之际诗歌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复为变、由复转变”,鲍照正处于宋齐梁诗歌裂变的时代,其乐府诗既远绍汉魏乐府传统,纪实写事、寄意古调,又浸润建安风骨,慷慨悲凉、辞气高古,同时也深受齐梁文人拟乐府和柔靡铺彩之诗风的影响。然而,鲍照乐府诗的总体风貌仍是汉魏遗韵,与当时齐梁诗风别具一格,故与之相较,可称之为古乐府。
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人怕失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所谓乐府中的“泛声”,即乐府诗合乐歌唱时的虚声或散声;填一个实字,即是在虚声处填一个表声之字。古乐府中间添许多泛声的情况,多存于汉乐府,尤其是汉乐府声辞杂写的时代。又如明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一“谈艺”云:“予尝见一江南士人拟古乐府,有‘妃来呼豨豨知之’之句。”“妃呼豨”正是汉乐府《有所思》声辞杂写所致,故江南士人所拟之“古乐府”,也当是指汉乐府。刘燕勋跋《人境庐诗草》曰:“读君诗,无体不备,而五七古尤擅胜场。其音节之古,色泽之浓,气格之高,非将《离骚》、汉魏古乐府诸作,咬出汁浆、灌入肺腑,不能有此古艳……”这里明确说“汉魏古乐府”,可见,直到晚清人,仍视汉魏乐府为“古乐府”。
再看广义之古乐府。
《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题解曰:“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郭茂倩为北宋末人,其称唐代乐府为新乐府而非古乐府,主要乃因其“未尝被于声”。不过,后世乐府诗绝大部分不曾入乐,故入乐与否,便不再有实际意义。如果在郭书中,除去“新乐府辞”“近代曲辞”等与“古乐府”具有相对而言的乐府歌辞外,剩下的可视为“古乐府辞”,那么,在《乐府诗集》所体现的观念中,古乐府之范围则明显扩大,已涵盖汉魏六朝甚至隋之乐府诗,此观念已将后世文人拟作也囊括在其中。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歌词之变”条曰:“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尠矣。”王灼把唐中叶的古乐府与西汉魏晋的古乐府视作一脉相承,所不同者,唐中叶的古乐府唯不入乐,此与郭茂倩的观点颇似,不过,他认为入乐与否,已不妨碍其乐府是否属之为古乐府。《新唐书》卷一六七《韦渠牟传》曰:“韦渠牟,京兆万年人,工部侍郎述从子也。少警悟,工为诗,李白异之,授以古乐府。”李白为盛唐时人,他对汉魏乐府的本事相当熟悉,常借吟咏汉魏乐府古题的本事以抒发个人怀抱,这也是其乐府诗被称为古乐府的重要原因。随着时代变迁,汉魏乐府之曲调泯灭殆尽,其音乐殊不可考,而其本事或有文献可征,后之追步者,唯可于此大加发挥。又如南宋范晞文《对床夜话》卷二云:“古乐府当学王建,如《凉州行》《刺促词》《古钗行》《精卫词》《老妇叹镜》《短歌行》《渡辽水》等篇,反覆致意,有古作者之风,一失于俗则俚矣。”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亦云:“古乐府命题,俱有主意,后之作者,直当因其事用其题始得。”可见,后世“古乐府”之称,主要在于其所创或所拟之乐府诗与古乐府之本事有一定关联,或者在风格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径直采古乐府之旧题赋诗,至于音乐上的形制,已然渺不可稽。这一观念,自中唐而下,未曾大变。
通过对古乐府的简略考察,可以大致区分古辞与古乐府,即前者为后者的源头和创作的范式,后者的含义则更为宽泛,将前者包括在内。所以,“乐府古辞”绝不等同于“古乐府辞”。
二 关于“本辞”
1.本辞解读诸说
《乐府古题要解》卷下云:“以上乐府杂题……自《君子有所思行》已下,又无本辞。”则据此可以推知,唐时吴兢所见本辞唯8首,那么,唐时所见本辞数量已不多。细读题解可知,这8首诗皆出自汉世。《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提要》)对《乐府诗集》作题解云:“(郭书)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得以考知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孰为增字、减字。”郭氏的编纂体例,正可以显出同一曲题之下,乐府诗之发展源流。徐嘉瑞则主要从入乐与否的角度区别本辞与非本辞,其《中古文学概论》第二编说:“汉代乐府每一篇有两种。其中的文辞,多少长短不一。用于音乐的一篇,分做数解,以便歌奏。其中字句为‘不整齐体’和‘重复体’。全篇结构比本辞长。本辞一篇,大半无解。因为不施之于音乐,所以无分解的必要。其中字句为‘整齐体’,很少重复。全篇结构,比较乐辞少短。”刘永济说:“郭《集》,每以协律之辞与本辞并载,其本辞皆五言古诗也。”其意在于“乐奏辞”协律,本辞皆五言古诗,未必协律入乐。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一《古代诗史》之篇四《乐府时代》云:“《乐府诗集》载汉《清商》古辞时,常载两首,一为‘晋乐所奏’,一为‘本辞’。……所谓‘本辞’,大约是未经晋乐工修改者。”其意谓“本辞”与“乐奏辞”的区别在于是否经过“晋乐工修改”,并且把“本辞”和“乐奏辞”皆称为“古辞”。逯钦立《汉诗别录》说:“郭氏作晋乐所奏者,据《宋书·乐志》也,作本辞者,则本之《文选》及《玉台》等集也。”其意谓“乐奏辞”与“本辞”有歌诗文献来源上的区别。阴法鲁在《学习整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小记》一文中说:“现存相和大曲中有《陌上桑》(《艳歌何尝行》),是‘魏晋乐所奏’,本辞不传。本辞当是汉代作品,而大曲形式的歌词大概是经过魏晋时代的乐人加工扩充而形成的。”可见,阴法鲁先生认为本辞是汉代作品,而且是有别于魏晋乐所奏辞的。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说:“汉代传辞为《白头吟》之本辞,晋乐所奏为后世拟作。其中增改字句,为了便于入唱,可能乐谱如此。末二句‘今日相对乐,延年万岁期’,与本辞文义无涉,属于乐工外加之乐府套语。”施先生肯定本辞是汉代歌辞,与入晋乐歌辞有较大差别。萧涤非认为:“沈约在《宋书·乐志》里把汉代无名氏的民歌和晋乐所奏的汉民歌,统统称为‘古词’,郭茂倩为了把这两者区别开来,他一方面沿用了‘古词’这个旧名称,一方面又添造了一个新名称‘本词’。所谓‘本词’,顾名思义,就是指的未经晋乐府加工过的汉代本来的歌词。或者说是货真价实的‘古词’……王先生(王季思)对这一区别似未注意,把‘本词’也称为‘古词’了。”可见,萧先生是反对把“本词”称为“古词”的,他同时也认为,沈约《宋书》中的“古辞”概念,实际包括汉代无名氏民歌和晋乐所奏的“乐奏辞”两类,郭茂倩引入“本辞”的概念则是为将二者区分开来。崔炼农教授的观点与萧先生的观点有些相似,他认为:“‘本辞’与乐奏辞相对而设的文献价值无可怀疑”,“乐奏辞具有曾经入乐的明显痕迹,相对而言,‘本辞’则是最初(或前次)入乐之辞;二者的分判本是歌辞文本记录的传统,是配乐歌辞历史发展脉络的片面显现”。崔教授前既说“‘本辞’与乐辞相对而设”,下又云“‘本辞’则是最初(或前次)入乐之辞”,不知道“最初(或前次)入乐之辞”算不算“乐辞”,这种说法阐述得似乎还不够清晰。以上诸家都认为本辞与古辞存在着入乐与否、版本异同等方面的差异。另外,日本学者前野直彬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章也提到“本辞”:“乐府诗本来指的是伴随乐曲演奏而唱的歌,不久其范围被扩大,乐府的定义也就模糊了。也就是把原来唱的歌辞作为本辞,和原来一样的题名、一样的曲调,只改了歌辞的模仿作出现了。”这里的“本辞”显然是指同一曲题和曲调下的初始之作,与后来的拟乐府具有相对性。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晋乐所奏”》一文中支持法国汉学家桀溺从版本来源区分“本辞”与“晋乐所奏”的观点(桀文《驳郭茂倩:论若干汉诗和魏诗的两种版本》,载《法国汉学》第4辑,中华书局,1999年),并补充论证:“我们不知道是谁最先区分了‘本辞’和‘晋乐所奏’,但是这种分别判断只可能出现在学者们开始收集和对比不同版本之后。它看上去更像一个代表了价值观念的判断而非带有历史主义精神的判断”,并指出“所谓‘本辞’其实代表了对《宋书·乐志》中乐府歌辞进行规范、修整并且赋予连贯性的努力”。宇文教授的论述显然越来越偏离“本辞”的语境而不得要领。
王季思先生则认为:“如果说郭茂倩为了区别汉代无名氏民歌和晋乐所奏汉民歌的区别,在少数相和歌词里,在古词之外,另立本词一名。那么,从《乐府诗集》所引《乐府解题》的说明看,并没有这种区别。”王先生的判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因为“汉代无名氏的民歌”主要是指古辞。前文梳理古辞概念时,诸位学人基本认同其为汉代无名氏的民歌,另外从《乐府诗集》所录古辞看,其中绝大部分为汉代无名氏的民歌。而“晋乐所奏的汉代民歌”也包括古辞在内,这一点从《乐府诗集》收录的“魏、晋乐所奏”或“晋乐所奏”的14首标注“古辞”的乐府诗即可知。《乐府诗集》虽然引入本辞之概念,但其实整部书中收录的本辞并不多,总计有10首,请参下表:

《乐府诗集》本辞(10首)汇总表
此表按照《乐府诗集》的体例依次迻录,即每一曲题之下,先列古辞,次列乐奏辞,再次列本辞,最次列后世拟作。由此汇总表可知,在《乐府诗集》中所见的10首本辞中,仅5首前有古辞,其中4首古辞入晋乐,1首古辞未言是否入晋乐;而《乐府诗集》共收古辞有73首,其中14首为“魏、晋乐所奏”或“晋乐所奏”。可见,古辞并非不入魏晋乐,如果单以入晋乐与否来区分古辞和本辞显然不妥。
《乐府诗集》所载的10首本辞,均隶属于相和歌辞。朱自清在《中国歌谣·歌谣的起源与发展》中谈及“诗的歌谣化”时,说《乐府诗集·相和歌·瑟调曲》里,有《西门行》两首,一是“晋乐所奏”的“曲”,一是“本辞”。本辞就是徒歌。又说,“那首本辞是从古诗化出来的,而那首晋乐所奏的曲是参照古诗与本辞而定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朱先生的两点认识:一是本辞是徒歌,二是本辞是晋乐所奏曲的参照。王淑梅教授通过考察10首本辞的音乐特征,也认为:“所谓‘本辞’,即乐奏之本,就是荀勖‘撰旧辞’时用作底本的旧歌辞。”这一认识可视为对以上诸多观点的总结和深入,但其对本辞内涵的界定似乎还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必要。因为,“本辞”与“古辞”具有密切之关系,在未探明古辞之前,对本辞的阐释总归缺少一环。
2.本辞与古辞关系
《乐府诗集》载有本辞10首,而在同一曲题下,仅5首有古辞与之相对应,其中《怨诗行》1首笔者又怀疑其并非古辞,同时《乐府诗集》又未明言其是否为晋乐奏辞。为方便分析,笔者将其余4首古辞与本辞作一比勘,因而可以明显看出古辞和本辞均具有明显的入乐标志。
首先,古辞多分解,且有的古辞还有“趋”。如《满歌行》“饮酒”以下即为“趋”。
其次,古辞有援引他诗或添加成句的情况,如《西门行》中“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这四句显然源自汉乐府古辞《王子乔》,或化用《古诗十九首》之第十五首《生年不满百》中“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之句。这种援引或对辞句的改动、添加,当是乐工为协律、便于歌唱演奏而对歌辞进行的再加工,是由歌诗入乐的具体要求决定的。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晋人每增加本词,写令极畅,或汉晋乐律不同,故不能不有所增改。”萧先生所说仅反映晋乐的情况。而实际上,古辞与本辞之间这种因入乐要求而加以相应改动或增损的地方,汉魏乐亦如此。
再次,这四首古辞都明确标注“右一曲,晋乐所奏”。这是其入晋乐的铁证。
但就文本而言,歌诗入乐与否,只是其外现形式不同而已,并非古辞与本辞的特质区别,因为本辞也同样具备某些入乐的特点。
其一,本辞的诗句也具有明显的复沓叠句形式,《西门行》中“逮为乐,逮为乐,当及时”便是例证。罗根泽先生已注意到这一点,他曾提出质疑:“乐府所奏,多叠句以赴节,本辞叠句者极少,何以独叠‘待(逮)为乐’句?”崔炼农教授也指出:“‘逮为乐,逮为乐,当及时’为叠唱痕迹无疑,其辞乐对应关系当不至疏离太远。”
其二,本辞诗句具有明显的韵脚。如《白头吟》中的“雪”“绝”,“头”“流”,“啼”“离”“簁”“气”等,这种押韵作为诗歌内在的音乐特质,为其入乐提供了有利条件。本辞均具有明显的换韵现象,这种换韵,或是本辞歌唱时划分段落(或者说分章,也可能是乐句分拍)的音乐痕迹。
其三,本辞与古辞相较,虽然有个别字句更改或语义转述的差异,以及个别篇章援引或添加成句的现象,但大致风貌保持不变,尤其是《满歌行》一曲,只存在个别字句的更改和语义转述的差异。可见,古辞能入乐,本辞亦可入乐,应是不容置疑的。
需要明辨的是,古辞入乐和本辞入乐间的区别为何?我们所见的古辞,标注有“魏、晋乐所奏”或“晋乐所奏”,而“本辞”却未标注。采自四方的街陌谣讴之辞,有的经过加工可达“入乐”之地步,有的在筛选过程中删汰、散佚,也有的可能仅仅能够暂储于乐府机关,以备不时之需。这些事实说明,郭茂倩在编纂《乐府诗集》时,把这些经过汉魏晋乐工加工过的,得以运用到汉魏晋宫廷音乐(主要是宫廷俗乐)的汉世乐府歌诗,称为“古辞”,而将这些古辞的原貌,或那些不曾为乐工加工而写定的歌诗文本,又为后人模仿而进行拟作的歌诗,称之为“本辞”。
将《乐府诗集》10首“本辞”和14首乐奏“古辞”对比可知,其中只有5首重合。此即说明,“本辞”概念的引入,并非如王淑梅教授所说是郭茂倩与“荀氏入晋乐之辞作对比者”,因为至少仍有9首之多入晋乐的“古辞”,郭茂倩并没有列出与之相应的“本辞”以作对比;对照上文“本辞”10首汇总表,我们还会发现,魏武帝、魏文帝、曹植的诗作也经过荀勖加工而入晋乐,却同样也有与之相对应的“本辞”,而荀勖加工曹氏父子诗作以入乐,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以汉代歌诗当作底本的。
许多前辈学者认为,“本辞”是“货真价实的‘古词’”“未经晋乐府加工过的汉代本来的歌词”,这些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这说明,“本辞”具有某些与“古辞”相同的特质,而又与“古辞”具有名实之别。也就是说,“本辞”是魏晋以前(汉代)的歌诗。
根据以上探讨,并结合古辞与本辞相关诗作的比勘,我们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古辞”与“本辞”应是同源异流之关系。它们起初皆为汉世街陌谣讴,部分本辞在汉世被收入音乐机构后,由宫廷乐工依据其在民间传唱的俚歌音乐特征,对其进行合宫廷俗乐的加工,这些经过加工入乐的本辞,后人给予一个新的名称,即为古辞。《宋书·乐志》曾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清赵执信《声调谱·论例》云:“汉人歌谣之采入乐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罗敷行》之类,多言当世事。”《钝吟杂录》亦云:“魏、晋所奏乐府,如《艳歌行》、《长歌行》、《短歌行》之类,大略是汉时歌谣。”而那些未经乐工加工、只合汉世民间音乐系统歌唱的歌辞,当即后来载录古代歌诗者所编辑而为我们今天所见的本辞,所以本辞尚停留在俚歌阶段,古辞已进入到宫廷音乐的层面。魏晋时期,古乐亡佚殆尽,而作为歌辞文本的本辞和古辞却得以保存下来。其中的部分古辞,又经过魏晋乐工的再加工,成为“魏、晋乐所奏”或“晋乐所奏”辞。于此同时,本辞中的部分歌诗,也可能因为魏晋乐工的加工而入乐,转而演为所谓的“古辞”,这也可能是元代左克明将古辞再加细分为“古辞”“汉古辞”“宋古辞”的原因。
其二,“古辞”与“本辞”的主旨具有一致性。古辞,无论是入汉乐,还是入魏晋乐,都只是对本辞的个别字句的加工,并不影响本辞的主旨。即使有的本辞被乐工添加其他诗文、成句,但本辞的主旨亦基本保持不变。从上文提及的古辞与本辞的4首歌诗对照看,便可一目了然。造成古辞和本辞文字、诗句上的差异,并非皆因其源自不同的版本,更有可能是源自同一根系,经乐工加工后而发生了新的变化所致。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辞”和“古辞”实际为一脉传承,二者同源异流,既有统一性,又有交叉性、变更性,二者的结合,构成汉乐府歌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乐府歌诗最具经典性的部分。
3.本辞含义及功能
我们认为,起初,本辞乃原生态的“汉世街陌谣讴”,属汉民歌音乐系统,未配以特别繁复的器乐,它的音乐形态相对简单,它还处于俚歌阶段。还应有更多的本辞,未能被著录而逐渐失传。流传下来的本辞和古辞,即为后世汉乐府歌诗的经典作品,成为魏晋及以后乐府歌诗创作的模板。诸如魏晋援古题而创制的新辞,六朝和隋的拟作,唐朝的新乐府等,皆是在本辞和古辞基础上的创新。本辞与古辞存在文本对应的关系,而与非古辞的“魏、晋乐所奏”辞则无文本对应关系。因而,本辞之“本”,亦非单指“荀勖‘撰旧辞’时用作底本”的“底本”之意,而是“本源”之意。本辞是其所在曲题最初、最原始的歌诗。后世同曲题创作,都由此而派生衍变。
本辞之名,虽创自乐府,但却不唯独乐府使用。抛开入乐与否一层而论,在古人或后人拟作的歌谣或诗歌中,其被拟原辞,亦称“本辞”,不过此处之“本辞”已非《乐府诗集》之“本辞”,而是“原文之辞”的意思。比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曰:“晋乐府奏子建‘明月照高楼’诗,中四句云‘北风行萧萧,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陈王本辞所无,殊类魏武语也。”又《诗薮·内编》卷三曰:“古歌谣惟《皇泽》《白云》,典质雅淳,即非周穆本辞,亦非西京后语。《拾遗记》所载《皇娥》《白帝》等歌,浮丽纤弱,皆子年伪撰无疑。”这两处之“本辞”,皆是“原文”或“原作之辞”的意思,与《乐府诗集》之本辞又隔一层。
作为同根同源的本辞和古辞,与拟作间当然亦构成相应的对应关系。因此,后人在载录编辑时,自然就会将本辞和古辞列在同一曲题之前,将拟作列在其后。而从音乐文学的角度看,郭茂倩在几种文本并存的情况下,列古辞于前,次列乐奏辞,再列本辞和拟作的做法,显然是很合乎情理的。这可使人很清楚地知道它们间存在着的自然而然的逻辑关系。即前两者强调入乐,重在音乐要求;后两者强调歌辞,重在文本传承。这样编排的好处,亦如《提要》所说的优点,可使“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本辞和古辞对后世拟作的曲调特征和题名、主旨、本事、体式、风格等均有一定影响。
“本辞”提供的是最初的民歌声唱系统的参照,“古辞”提供的是歌辞最初合宫廷音乐系统(主要是宫廷俗乐)的参照。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八《诗文》曰:“古乐府之题,盖今之曲名也。其古词有与其题相涉者,有与其题绝不相涉者,则用其曲也,然其节奏不可考矣。后人拟之有二,有拟其曲而为之,而次不相蒙;有拟其题而为之,而曲不相中。大抵唐人多取题目字面为古歌行,而不用其曲节,则世变而音节异也。”又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一曰:“夫乐之义理,诗词是也,声歌犹后世之腔调也。两者俱偕,乃为大成。汉古乐府如《朱鹭》《君马黄》《雉子斑》等曲,其辞皆存而不可读,想当时自有节拍,短长高下,故可合于律吕。后来拟作者,但咏其名物,词虽有伦,恐非乐府之全也。”只不过,音乐节奏渐不可考,故已经失去实际意义。当本辞失传,或本辞与古辞的音乐系统得以转换以致其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古辞可以代替本辞,并体现本辞的作用,这就是为何部分曲题下仅有“古辞”而无“本辞”的原因之一。但当本辞与古辞的音乐系统相差较大或文本差异较大时,则有必要将本辞、古辞俱列同一曲题之下,以便比较。另外,还有部分曲题之下仅有本辞,而无古辞,或是因为这些歌诗起初并未被汉代音乐机构用来加工入乐,只是依靠民间传唱或后人载录而流传下来。
本辞与包括古辞在内的乐奏辞之间的关系,也可体现为音乐对比关系。正如《提要》所说“得以考知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至于“孰为增字、减字”乃是本辞和古辞间的文本对比关系。但本辞的民歌音乐形态和古辞的宫廷音乐形态已无从细考。
总之,就本辞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它主要体现为古辞的文本参照、乐奏辞和拟作的音乐、题名、主旨、本事、风格的参照,概而言之,即同一曲题乐府诗创作的本源参照,它是汉乐府处于民歌或俚歌阶段的状态。
三 关于“始辞”
1.始辞的基本认识
始辞,亦称始词,这一概念与本辞、古辞具有很大相似性,一些学者苦于三者界限不明,所以多有混用者。其实,三者侧重点不同,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根本上却各异。先看看当代学人对始辞的基本认识。
任中敏先生《唐声诗》下编论《轮台》(燕子山里食散)曰:“四句地方色彩甚浓,应是唐代原地所传始辞,不是邻邦拟作,甚可贵!”同书又论《木兰花》一调曰:“《教坊记》载曲名,曰《木兰花》,无‘令’字,创于开、天之间。故此曲与名,确曾存在,为不可掩之事实;特始辞不传,今所得见者,仅晚唐人作一首及五代人作五首而已。”另任先生在《唐声诗》上编二章指出:“所谓始辞,对拟辞言,于前代乐府与唐、五代声诗,同一重要。”任先生所谓始辞,强调其“地方色彩”和“原地所传”的特点,并且与后人的拟作相对而言。吴熊和先生在《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一文中说:“《踏莎行》是一种歌舞曲,其始词见于晏殊《珠玉集》及欧阳修《近体乐府》。”姚奠中先生《〈词谱范词注析〉前言》云:“唐宋文人填词时,一般只标调牌名,而不抄乐曲谱,如同今人用《绣金匾》(即《绣荷包》)的曲调写歌词,只按格式写,用不着抄乐谱一样,因为乐谱人人熟悉。但久而久之,曲调过时,无人演唱了,乐谱便逐渐失传,留下的就只有不能唱的词,既和原调牌的‘始词’无关,也和原乐曲的曲谱脱离,仅留调牌的名字,代表着这一形式而已。”从姚先生的表述中,可以推知,其所谓始辞是指依照一名词牌的曲调所填的最初一首歌辞。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认为:“所谓‘唐词多缘题’,与实际不尽相符。‘调下无题’,这是事实,但其所赋完全依照本题的原声始辞已极难寻见;晚唐五代诸家传本,调名之下,虽未附著作意,但其作意,真与本题之意相符合的,也并不太多。”施先生认为,始辞是与该词调原声相配之词,且多已经不存于世。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认为“唐词多缘题所赋”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并称“在现存的曲子辞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曲调所托的始辞了。”王先生意谓曲子辞的曲调所托之始辞多已失传。李昌集《中国散曲史》在引元初刘秉忠〔南吕·干荷叶〕8首散曲之后云:“第一、二首之内容属‘辞咏本题’(曲牌即题目)。‘干荷叶’,在金元土语中意指‘失偶’,其曲所咏,正合其意。故这两首散曲可视作〔干荷叶〕尚在俚歌阶段的原始面貌,文学史上通常称这类歌辞为‘始辞’。”李先生认为始辞乃曲调、曲题和曲辞内容相合,而且具有俚歌特点,同时他还认为,两首散曲均可视为同一曲题的始辞。龙晦先生《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图〉跋》云:“按《浪淘沙》为曲名,据万树的《词律》,它有两体,一是28字体,始词是皇甫松作,又一体即李后主之‘帘外雨潺潺’也。”王星琦《元明散曲史论》论及杨果(号西庵)的散曲〔越调·小桃红〕《采莲女》时说:“〔小桃红〕又名〔采莲曲〕,西庵此组首句都扣‘采莲湖上采莲人’,尚是始词的规模意蕴。另外八首〔小桃红〕,多未离开水和船,采莲、采芙蓉等,亦未尽脱始词的影子。”王先生并未确之凿凿称杨果这几首散曲为始辞,不过,他认为始辞的曲调、曲题与曲辞内容有紧密联系。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中云:“作者倚声所制的第一首歌辞为始辞。当有了始辞,懂诗律的人便可模仿始辞声韵字句而作词,于是形成了以词调为单位的独特的词律。”其观点与姚奠中先生的观点有点相似。王志清《晋宋乐府诗研究》云:“刘宋文人对乐府传统的认同与接续还体现在乐府创作的‘始辞’现象。笔者所言‘始辞’意为《乐府诗集》该曲题下收录的第一首作品。”王博士以《乐府诗集》该曲题下所收第一首作品为始辞则不太妥当,因为各曲之始辞未必皆能流传下来,郭茂倩也只能在同一曲题下选择较早的作品而已。张仲谋师《明代词学通论》说:“在词的调题合一或调即是题的时代,词调名就是词的题目,故词调名还是应与初始之词(即始词)的内容相统一。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李珣《巫山一段云》下注云:‘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事实上,‘缘题而赋’应该是稍晚的情状了,对于最初之‘始辞’而言,应该是因言仙事而名《临江仙》,因咏女道士而名《女冠子》,即先是‘因事主题’,而后才是‘缘题而赋’。”这一观点认为,始辞之于词,具有词调名、词题名和词作内容的统一性,三者紧密融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观点可谓是对以上诸观点的总结,也算是目前学界对“始辞”概念较为全面和清晰的论述。
由以上诸论我们可以总结出学界对始辞的初步认识,即它指为词曲牌调名所主之曲调填配的初始之辞作,其特点是牌调名与词曲题名二而一、一而二,同时与歌辞内容具有紧密联系,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曲题本事。吴相洲教授《乐府学概论》在论及乐府本事的文本由来时,也有类似的推断:“本事记录未必都是散文,在相关记录缺失情况下,始辞或较早歌辞就担负起保留本事的作用,后人得以据此追索本事。”不过,从其下文来看,吴教授又有将始辞与古辞相混而用的嫌疑。既然始辞是歌曲每一牌调配辞的初始之作,那么,每一牌调的始辞就只能有一首,而不能有多首。
2.本辞与始辞关系
始辞之概念虽多用于词曲,但却衍自乐府。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自汉至唐所存之曲”条,是目前所见始辞的最早文献。为方便分析,特将这段文字转录于此:
汉时雅郑参用,而郑为多。魏平荆州,获汉雅乐,古曲音辞存者四:曰《鹿鸣》、《驺虞》、《伐檀》、《文王》。而左延年之徒,以新声被宠,复改易音辞,止存《鹿鸣》一曲。晋初亦除之。又汉代短箫铙歌乐曲,三国时存者有《朱鹭》、《艾如张》、《上之回》、《战城南》、《巫山高》、《将进酒》之类,凡二十二曲。魏、吴称号,始各改其十二曲。晋兴,又尽改之。独《玄云》、《钓竿》二曲,名存而已。汉代鼙舞,三国时存者有《殿前生桂树》等五曲,其辞则亡。汉代胡角《摩诃兜勒》一曲,张骞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魏、晋时亦亡。晋以来新曲颇众,隋初尽归清乐。至唐武后时,旧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紵》、《子夜》、《团扇》、《懊侬》、《石城》、《莫愁》、《杨叛》、《乌夜啼》、《玉树后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叶,声辞存者又止三十七,有声无辞者七,今不复见。唐歌曲比前世益多,声行于今、辞见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尔。大抵先世乐府有其名者尚多,其义存者十之三,其始辞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则无传,势使然也。
因王灼对“始辞”未作界定而径自用之,所以我们认为这在当时(南宋初年)已是约定俗成的概念,只是我们暂未发现更早的文献出处而已。根据王灼上文历述汉至唐代歌曲的语境,可以推知,其所谓“乐府”指可以入乐歌唱的诗歌,是广义乐府之概念。所以,其所谓“始辞”的指称对象也应该包括乐府诗、近体诗、词等多种文体,但并未涉及到曲,因为南宋初年,曲还未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另外,王灼每论及一代歌曲,都很重视音乐(声)、篇题(名)和文辞(义)三个方面。他最后在总结时说,前代的歌曲,篇题保留下来的“尚多”,文辞保留下来的“十之三”,“始辞”保留下来的“十不得一”,音乐则“无传”。这几层含义与乐府诗中的篇题、古辞、本辞、音乐几个概念正好一一相对应,故可以推知,“始辞”之于狭义乐府,则相当于“本辞”。
由上文我们对乐府本辞含义的梳理,也可以延而推及近体诗、唐宋词以及汉唐宫廷音乐文学。因为乐府本辞是汉代口头传唱的最原始的民间乐府歌曲,乐工将它搜集起来进行再创造时,往往即以其篇题名作为曲题名。但口头传唱之歌曲偶或无篇题者,乐工即从其歌唱的歌辞中割取一句或一词,作为曲题。它起初被传唱的歌辞,因为要适应宫廷新音乐的新需求,会被删削增损。这种增损是因为,民间音乐里存在着丰富的微分音以及微节奏,准确地讲是不确定音高和不确定节奏,为使其符合宫廷音乐的五声音阶或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七声音阶,必须对其加工改造。不过这种改动并非大刀阔斧,而是“稍协律吕”,只是在其口头传唱的调式和调性的基础上,对歌辞结构和音乐形式稍作调整,总体上仍然保持原来的本事、主题和基本旋律,可以说其“义”尚存,而这种被加工过之后入乐歌唱的歌辞又有一个新名称,即“古辞”。一首本辞可能被不同乐工配以不同的音乐,所以,同一曲题之下可能有两首甚至更多的古辞,但本辞却始终唯一。这即是为何《乐府诗集》在部分曲题下收多首古辞,如《木兰诗》收同题二首古辞,《长歌行》收同题三首古辞。
这里需要思考的是,既然本辞与始辞具有对等性,为何至迟发展到南宋初年,时人又造出一个新名词“始辞”呢?这是因为音乐文学发展至唐后,辞与乐之关系已发生重要变化,音乐已由从属地位转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二者的关系已从“以辞传乐”转化为“以乐传辞”。刘尧民先生称之为“以乐从诗”和“以诗从乐”,他认为,“从唐代以来是‘依声填词’,先制好曲,然后跟着音乐的节拍来作诗”。这话还不够准确,隋唐五代还是采辞入乐与依调填辞并重,及至宋代,依调填辞渐渐占到上风。所以,本辞虽然与始辞具有对等性,但其强调的侧重点则不同,本辞强调辞的主导、乐的从属,本辞之“本”是本源之意;始辞强调乐的主导、辞的从属,始辞之“始”是初始之意。刘尧民先生将音乐文学之“音乐”分为内在的音乐和外在的音乐,内在的音乐指音乐文学的“字句之数”“声韵平仄”,外在的音乐指音乐体系的节奏、旋律、曲式等要素。本辞具有外在音乐参照的意义,始辞并不具有外在音乐参照的意义,但它具有创体或创调的意义。这就是为何本辞用之乐府,而始辞用之词曲的原因。任半塘《唐声诗》上编三章谓:“盖始辞主声,而拟辞主文,正不容忽耳。”此处之“声”,若主要指辞的“内在音乐”,即是词调的字句之数、声韵平仄,则或可通;若指外在音乐体系,则不可通,因为依调填辞的始辞,较音乐而言处于被动地位。
本辞、古辞、始辞三个概念虽极相似,但从根本上讲,其含义、所指、应用却各不相同。本辞为同一曲题乐府诗创作的本源参照,它是汉乐府处于民歌或俚歌阶段的状态,古辞是将本辞进行音乐加工后,可入于汉魏晋宫廷音乐歌唱的汉代乐府歌诗,始辞则是指为词曲牌调名所主之曲调填配的初始之辞作。
[1]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刘勰.文心雕龙义证[M].詹瑛,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萧统,李善,等.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6]章学诚,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8]陆侃如.乐府古辞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9]萧涤非,萧海川.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增补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0]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11]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M].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1975.
[12]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13]逯钦立.汉诗别录[M]//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14]曹道衡.《相和歌》与《清商三调》[M]//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曹道衡.论《文选》中乐府诗的几个问题[M]//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
[16]刘德玲.乐府古辞之原型及其流变——以汉至唐为断限[M].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
[17]王灼,岳珍.碧鸡漫志校正[M].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18]赵崇祚,李一氓.花间集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9]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0]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王士禛.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黄遵宪,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3]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4]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5]向回.从本事的掌握和运用看李白“古乐府之学”[J].中国诗歌研究,2010(第六辑).
[26]范晞文.对床夜语[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27]朱承爵.存余堂诗话[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28]吴兢.乐府古题要解[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29]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
[30]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M]//徐嘉瑞全集:第一卷.昆明:晨光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31]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2]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33]阴法鲁.学习整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小记[C]//阴法鲁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34]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5]萧涤非.《东门行》并不存在“校勘”问题——答王季思先生[M]//乐府诗词论薮.济南:齐鲁书社,1985.
[36]崔炼农.《乐府诗集》“本辞”考[J].文学遗产,2005(1).
[37]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骆玉明等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8]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M].胡秋蕾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
[39]王季思.《东门行》的校点和评价问题——答萧涤非先生[M]//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40]朱自清.中国歌谣[M]//朱自清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41]王淑梅.《乐府诗集》“本辞”索解[J].文献,2010(2).
[42]赵执信.声调谱[M]//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3]冯班.钝吟杂录[M]//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4]于慎行.谷山笔麈[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5]宋长白.柳亭诗话[M]//张寅彭.清诗话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6]任中敏.唐声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47]吴熊和.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M]//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48]姚奠中.《词谱范词注析》前言[M]//姚奠中论文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49]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0]李昌集.中国散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51]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图》跋[M]//龙晦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9.
[52]王星琦.元明散曲史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3]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4]王志清.晋宋乐府诗研究[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55]张仲谋.明代词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6]吴相洲.乐府学概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57]洛地.词乐曲唱[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58]刘尧民.词与音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赵成林
2016-12-01
2016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历代词话中的音乐史料研究》(项目编号:KYZZ2016_0477)
张建华(1984— ),男,河南方城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文学。
I207.2
A
1006-2491(2017)03-0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