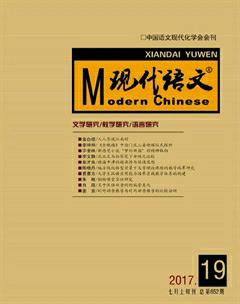《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嗅觉叙事
摘 要:《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关于气味的描写贯穿全文,其主要作用有诱发心理活动、强化时间记忆和丰富叙述效果。小说中的气味根据诱发的心理活动的不同类型,分为“香”“臭”及生理性气味三种。费尔米纳身体的香味被阿里萨逐渐审美对象化,成为了两人爱情的象征;而带有香味的爱情记忆,又在时空距离的扩大中不断得到强化。超乎常人的体味感知力不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一环,也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效果。
关键词:《霍乱时期的爱情》 嗅觉 叙事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马尔克斯获诺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是一部自我超越、颠覆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之作。但目前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的探讨上,在叙事策略方面尚有较大探讨空间,且鲜有研究谈及“气味”在该小说中的独特作用。关于“气味”的描写贯穿小说全文,有的表达如“花香”“老人体味”反复出现,且指向“爱情与死亡”的主题,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嗅觉诱发心理活动
(一)诱发常规联想的“香”与“臭”
气味贯穿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的心理活动产生无形的影响。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嗅觉叙事贯穿了三位主人公相识、相恋、相守衰老的过程,最常见的作用即诱发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根据诱发的心理活动的不同类型,气味可分为“香”“臭”和“体味”三种。
在以往的嗅觉文化中,“香”和“臭”是两种最基本的气味。人们通常把“臭”与罪恶、死亡相关联,把“香”与爱情、健康相联系。小说中“香”所诱发的心理活动,就基本围绕“爱情”这一中心展开,最典型的即贯穿费尔米纳和阿里萨恋爱过程的花香。两人感情如蜜时,不论是互诉衷肠的信件、情人的衣服还是费尔米纳本人都充斥着花香。主人公常由现实中的香味联想到爱情的甜蜜。这些描写都遵循了惯常的关于“香”的联想内容。
其次,文中出现了较多关于“臭”或“臭”变异气味的描写,如开篇暗示死亡的苦扁桃味、水中尸体的恶臭等。这些气味的出现常勾起主人公痛苦与恐惧的情感。氰化物的苦扁桃味,勾起了乌尔比诺医生有关情场失意结局的回忆;联系阿莫乌尔,他还感受到不幸爱情的幽怨与隐痛。浴室里的氨气味暗示了乌尔比诺衰老的事实、招来费尔米纳的抱怨,令人烦躁不安,勾起老人对死亡的恐惧。纯正的“臭”是“腐臭”,是霍乱与死亡的气味。阿里萨在与费尔米纳分手后,独自乘船远行。在这部分描写中,有晾在轮船杆上的肉的腐臭,有垃圾令人作呕的气味,这都让阿里萨感到恶心与疲倦。乌尔比诺随着轮船到达港口时,闻到了牲畜浮尸的恶臭。作為一位医生,他随即联想到了霍乱与自己故去的父亲。这些“香”“臭”及变异的“臭”味都基本上遵循了气味的隐喻惯例,是一种情感标记,分别指向小说中“爱情与死亡”这两大主题。
(二)特殊的生理性气味
除“香”与“臭”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气味贯穿全文,那就是人的体味。具体来说有两种,第一种是老人的体味,常诱发人不安、焦虑和悲伤的情绪。皮埃特在《气味:秘密的诱惑者》中谈及,疾病某时会带有某种独特的气味,例如糖尿病患者呼吸的气息可能带有丙酮的气味。随着人的衰老,人的体味也会产生变化。乌尔比诺医生嗅到自己和妻子的体味,意识到两人已进入老年期。费尔米纳在小说末尾登上游船后,向阿里萨表达了自己身上不再是他记忆中的花香,而是散发着老太婆的酸味的悲哀。作者通过对老人体味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人在面临衰老时的心理活动。这种气味甚至延续到死亡以后。医生去世后,费尔米纳独自嗅着床上残留的丈夫皮肤的气味,暗自怨恨、伤心、思念、流泪。
另一种则是健康女性的体味,常诱发人的性幻想。令阿里萨魂牵梦萦的“香味”不仅有费尔米纳身上的香水、花香,还包括她的体味。阿里萨从海上回来后,认为城中的一切都充斥着费尔米纳特有的气味,其实暗示了他对费尔米纳的性冲动。费尔米纳婚后曾和阿里萨偶遇,阿里萨静静地观看了费尔米纳进餐长达一个小时,其原因就是他能在餐厅嗅到费尔米纳的体味,以此缓解灵肉分离的痛苦。
二、嗅觉强化时间记忆
(一)香味的审美对象化过程
皮埃特·福龙认为,被气味唤起的记忆图像带有明显的情感标记。小说中让阿里萨魂牵梦萦的费尔米纳身上的花香尤为特殊。花香伴随着强烈的情感记忆,逐渐从实际存在的气味变成阿里萨脑海里的虚拟气味,成为了爱情的象征符号。
阿里萨与费尔米纳在苦扁桃树下第一次见面时,他闻到了费尔米纳身上的馨香。之后他们之间所有与爱情相关的东西,不论是信件、情人的衣服、费尔米纳本人,还是这段爱情记忆,都沾染上了这奇异的花香。前期香味多实际存在,如情书沾染的香味、费尔米纳身上的香水味。但后期,香味越发趋向于虚拟的存在,比如记忆。在两人交往中,实际存在的花香总是伴随着愉快的情感体验出现,这就造成了嗅觉记忆的强化。于是,阿里萨只要一回忆起那令人魂牵梦萦的香味,就能联想到自己与费尔米纳愉快的恋爱经历。
当阿里萨知道费尔米纳去巴黎后,他感到花香“不再经常出现、浓郁,仅留在白栀子花里”。阿里萨之所以感觉花香时浓时淡,是因为他产生了“移情”现象。审美心理学认为审美移情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1]。阿里萨记忆中的“花香”是对象化了的审美客体,也能随着嗅觉记忆者心理的起伏而显隐。这体现了“移情”现象中无情事物的有情化倾向,即阿里萨与花香达成了某种情感交融,物我两忘。在阿里萨陷入情场困境时,花香也随之淡去。而当阿里萨重获爱的激励时,花香又变得强烈。乌尔比诺医生去世后,阿里萨曾把费尔米纳拒绝他的信当作情书。他感受到这些信件有着“栀子花香”,并让他联想到少年时代两人热恋时的信件。这里的栀子花香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是阿里萨对象化了审美对象,花香成为虚拟的爱情象征符号。
(二)被强化的爱情记忆
现实中两人时空上的分离,并没有使阿里萨遗忘费尔米纳的香味,反而让他对香味更加敏感、疯狂。笔者认为正是时空距离的扩大带来的失落感强化了带有爱情象征性的“香味”记忆,并造成了阿里萨对爱情的偏执。
在阿里薩与费尔米纳第一次分开后,实际的“香味”在现实中就缺失了,但阿里萨不仅没有忘记这种香味,反而对香味更加狂热。阿里萨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吃母亲种在花坛里的栀子花;一是他将母亲的花露水翻了出来,喝到呕吐。小说写道“他正躺在一片散发着芳香气味的呕吐物中间。”他思念费尔米纳的香味,又求而不得,于是找到了栀子花、花露水作为替代品,进行疯狂的掠夺以满足心理的不平衡感。长达五十三年的分离也未能减弱主人公关于“香”的记忆。当费尔米纳约阿里萨见面时,阿里萨顿时觉得大街小巷都散发着茉莉花香。而审美的主体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则是审美体验的必要条件。[2]正是由于阿里萨与费尔米纳现实距离的扩大,两人不再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中,反而能更惬意地按照自己意愿审视这段恋情。另一个方面,时空的隔离也增加了嗅觉记忆被重复提取的可能。真正让阿里萨魂牵梦萦的不是真正的花香,甚至也不是他与费尔米纳之间真实发生过的爱情,而是阿里萨理想化了的爱情记忆。在第一次分开时,阿里萨疯狂地陷入了寻找香味替代物的行为中。此时,他对费尔米纳的“香”尚没有足够的了解,显得焦躁不安,做出喝香水的疯狂行为。此时,费尔米纳身上的“香”尚未审美对象化,还处在接近实际香味的层面,无法进入理想化的享受阶段。五十三年后阿里萨则表现得从容许多,费尔米纳的“香”已经审美对象化了,与阿里萨的情感融为一体。他用五十三年时间造就了一个最“平淡”的执念。
三、嗅觉丰富叙述效果
(一)推动情节发展
小说展现了费尔米纳超乎常人的嗅觉。费尔米纳在家时,通过鼻子就能闻出衣物是否需要清洗,哪里有脏物。也正是通过这种超乎常人的嗅觉,费尔米纳闻到了乌尔比诺医生衣服上陌生的体味,发现了医生的出轨行为。因此,嗅觉在这篇小说中不仅能引起人物心理活动、强化时间记忆,还有推动情节发展的效果。但这样的情节并非全然是故弄玄虚,也有一定的生理及心理基础。皮埃特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对亲人气味的嗅觉分辨力。它是一种嗅觉护照,既能帮助我们承认伴侣和孩子的关系,也能给我们以安全感、归属感。费尔米纳喜欢通过嗅觉去指导家务,习惯嗅孩子和丈夫的衣服,是一种寻求安全感与归属感的表现。费尔米纳与医生的结合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恋爱结婚,更像是先结合再相处。费尔米纳从巴黎回来后,与医生关系一度紧张,这也说明了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费尔米纳存在诸多烦恼。笔者认为通过嗅觉发现丈夫出轨这个情节,一定程度上是费尔米纳缺乏安全感的印证。
(二)增加人物宿命感
尽管女主人公拥有超乎常人的嗅觉感知力有一定科学依据,但文中确也增加了许多戏剧化的处理。在阿里萨从海上归来时,正巧赶上费尔米纳第一次获得独立采购权,在集市上闲逛。文中提到集市上气味混杂,有芒草味、胡椒气味、安息香等。阿里萨竟然能在人群混杂的集市里感知到费尔米纳衣服的气息,进而与费尔米纳有了一次改变两人命运的相逢。这样夸张的嗅觉感知力,很难说不是作者为了增加人物的宿命感而刻意为之。《霍乱时期的爱情》所展现的“爱与死亡”的主题,贯穿了人类发展始终,是人无法逃避的宿命。嗅觉贯穿人的一生,又与身体机能、文化、心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很适合用来表现“爱与死”这种不可名状的、令人敬畏的永恒主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气味”有诱发心理活动的作用。其中“香”“臭”分别指向“爱情”与“死亡”两大主题。老人的体味常诱发人不安、焦躁的情绪;健康女人的体味则常与性幻想有关。费尔米纳身上让主人公魂牵梦萦的香味,是阿里萨对象化了的审美客体。他发生了“移情”现象,香味逐渐虚化成爱情的象征符号。时空距离的扩大又强化了爱情记忆,最终造成了阿里萨的偏执。在叙事效果上,超乎常人的体味感知力一方面推动情节的发展,从侧面表现了费尔米纳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人物的宿命感。
注释:
[1]童庆炳:《童庆炳谈审美心理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2]童庆炳:《童庆炳谈审美心理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参考文献:
[1]杨玲译,[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
[2]童庆炳.童庆炳谈审美心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3]陈圣生、张彩霞译,[荷兰]皮埃特·福龙.气味:秘密的诱惑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朱景冬.别具一格的爱情小说——评《霍乱时期的爱情》[J].国外文学,1990,(1).
[5]张宁.爱、时间与死亡——读《霍乱时期的爱情》[J].郑州大学学报,1990,(5).
[6]张慧云.痴情?滥情?——以弗洛伊德的人格论分析《霍乱时期的爱情》[J].名作欣赏,2006,(22).
[7]张世君.意识流小说的嗅觉叙事[J].国外文学,2012,(2).
[8]王伟均.论《香水》中的嗅觉叙事[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5,(1).
[9]姚婧.情感的疾病化书写——解读《霍乱时期的爱情》[J].名作欣赏,2015,(17).
[10]陈风.《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爱情主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1]荣利.“滥情”的痴情者——论《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阿里萨形象[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杨丽莹 湖北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