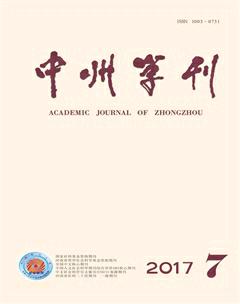圈子腐败现象及其治理路径透析
摘要:圈子腐败是一种特殊的腐败现象,其产生有多方面原因,利益共谋与交换是其基本动因。利益输送是圈子腐败中的核心问题,其中的利益主要以直观的物质形态和隐秘的情感形态表现出来。不管何种形态的利益输送,都是掩映在庇护关系中进行的。对于庇护者而言,其建构庇护关系是为了实现政治权益最大化、延续政治资源的利用时间;对于被庇护者而言,其寻求庇护主要是为了打通仕途升迁的通道和实现自我保护。圈子围绕利益而形成,这实际上预设了治理圈子腐败的路径:可以通过稀释圈子的利益聚集度,弱化其利益基础,降低其利益实现的可能性,最终分化圈子这一利益同盟。
关键词:圈子腐败;共谋;交换
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7-0013-05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深入推进,“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挖就是一串”的圈子腐败现象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破解诸多腐败问题的切入点。作为腐败的一种特殊形式,圈子腐败本质上是权力执掌者凭借对公权力和重要资源的支配,在其可控范围内编织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构建温情脉脉的交往结构,对特定关系人给予庇护和利益,并由此获得被效忠、利益反馈等回报的非制度化交往模式。圈子腐败现象与党的宗旨和人民的期待是格格不入的,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注意。目前,关于圈子腐败现象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在中国知网上以“圈子腐败”为题名进行搜索,仅有23篇文章,其中多数对圈子腐败的形态进行描述,没有涉及这一现象的产生机理和运作过程。这种研究状况与这个议题本身的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曾说,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职责在于对政治社会现象的运行及其背后的逻辑进行科学分析,发掘其中的隐秘。对于圈子腐败现象而言,研究的着力点也应是发掘其背后的诱因及其生成逻辑和运作过程,进而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
一、圈子腐败的“共谋与交换”特性
圈子,原本是指具有共同兴趣、爱好、阅历的人围绕某个目标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古有“竹林七贤”“兰亭盛会”,今有各种学会、协会,这些都是志同道合者所组成的圈子。但是,当权力、资源与不正当需求高度融合而又缺乏监督制约时,一种特殊的腐败形式——圈子腐败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客观地讲,官场圈子并不是现代政治的伴生物,而是古已有之。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现象就可以看作是官场圈子的雏形。到了现代社会,新的政治力量不断产生,但政治资源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跟不上这种变化,并且有限的政治资源往往还高度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便想方设法编织、挤入、运作各种圈子,以放大自己的非正当利益。于是,以权力为纽带、以关键人物为核心、以人际交往为载体、以结成利益同盟为目的的圈子腐败现象逐渐形成。从很多腐败案例来看,编织、经营各种圈子是一些腐败官员混迹官场的套路,在高压反腐态势下被揭露的“石油帮”“山西帮”等就是帮派腐败、团
收稿日期:2017-05-28
作者简介:陈朋,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政治学博士(南京210004)。
伙腐败的典型。
圈子腐败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利益共谋与交换是基本原因。所谓共谋,是指圈子成员具有共同利益,但依靠个体力量尚不足以实现共同利益,于是通力合作,为实现共同利益而一致行动;所谓交换,是指圈子成员各自拥有的权能不一样,其个体利益的实现需要与圈子中的其他人特别是关键人物进行利益交换。很多案例表明,共谋与交换是圈子腐败的内在逻辑和明显特性。大体而言,这种特性的形成与以下三个因素直接相关。
其一,政治资源的稀缺性。任何行动都离不开一定的资源,政治活动更是如此。罗伯特·达尔在讨论民主何以可能时就提出要重视政治资源的作用,他认为政治资源对政治活动有直接影响,“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因而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①。但是,与其他资源相比,政治资源是高度稀缺的。这种稀缺性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政治资源,但很多人又都需要政治资源。这就产生了矛盾。于是,一些人便通过结成圈子来达到争奪政治资源的目的。而一旦结成圈子,“内部资源配置又会不断强化这个小团体,使之成为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甚至是‘生死同盟,彼此间都坚守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原则”②。
其二,权力的碎片化。资源稀缺是圈子腐败现象的深层动因,而推动圈子腐败现象形成的直接因素是权力碎片化。政治结构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自身的惰性,再加上社会结构的日渐开放,会导致权力控制网络不断被肢解,以致出现权力碎片化。碎片化的权力被分割成彼此独立甚至封闭的单元,“它们除了在大的政治原则方面对上保持忠诚之外,在其他方面有相当大的‘自行其是的空间,而且它们有强大的动力扩充这种空间”③。权力碎片化必将阻碍一致性行动,一些人便“抱团”、结成圈子。在对碎片化的权力进行整合后形成的圈子,能让利益相关者在各种人情网、关系网中结成具有私人性、情感性、互惠性的利益团体,进行利益共谋与交换。
其三,人的逐利性。一些人追求不正当的互惠互利,这是圈子腐败形成的根本动因。斯科特关于庇护关系的论述对圈子腐败中的利益交换行为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在斯科特看来,庇护结构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客观场景,这种结构包含一种基于工具性友谊的特殊双边关系,“拥有较高政治、经济地位的个人(庇护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资源为地位较低者(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及恩惠,而被保护者则回报以一般性支持和服从”④。从这个判断中可以看出,基于角色链条而形成的庇护关系必然包含不同角色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各方通过友谊(工具性层面的)和利益纽带实现互动,控制彼此间的交往关系并实现各自的利益目的。维系圈子的就是蕴含这种互惠互利行为的庇护关系:一方提供另一方所需要的资源、收益、官位等,另一方则回报以忠诚、服务和馈赠,彼此以心照不宣的方式交换各自所需。
二、利益输送是圈子腐败中的核心问题
揭示圈子腐败的基本特性是共谋与交换之后,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圈子成员共谋与交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政治学上有一个基本原理为人们所熟知: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其利益密切相关。围绕各种诉求而结成的腐败圈子把圈子成员的趋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利益输送成为贯穿圈子腐败全过程的核心问题。這里的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货币、有价证券、古玩等,还包括情感层面的忠诚、依附、服务等非物质形态利益。
物质层面的利益输送是圈子腐败中常见的共谋与交换行为,主要有赤裸裸的行贿和较为隐蔽的送礼两种形式。前者在圈子腐败中很少有市场: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了解,一旦一方出事就很容易将另一方牵扯出来,交易存在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因而圈子成员不会如此直白地完成利益输送。相比较而言,圈子成员更愿意选择以送礼的形式来输送利益。“礼物交换一事貌似平常,其实是人类社会中相互交往的一个最重要模式,其给予—获取的双向选择维持、强化并创造着不同的合作、竞争、对抗的社会联系。”⑤但是,浸润着利益诉求的送礼与一般的礼尚往来具有不同的特征,前者与帮派主义的关系网紧密相连,“不断的送礼和帮忙的结果,不仅被视为是期望值,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表达和强化帮派主义态度的具体方式”⑥。在圈子里,送礼不仅是敲门砖,还是获得更大收益的砝码——送了礼,自然会获得回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雅贿就属于这种物质利益输送的范畴:在他担任不同领导职务期间,围绕他而形成的圈子中的人大多以玉石为礼送他,他“笑纳”之后回馈以矿产开采、房地产开发、道路修建等项目工程。实践中一些人利用其职权影响,隐秘地编织交际圈:先物色一些信得过且能力较强的商人或下属,给其创业或提拔创造条件甚至“开后门”,随后暗示其帮助自己的家人以商业经营的方式加入其企业或部门,再以分红或得干股的方式获取利益。诸多案件表明,掩盖在政商合作外衣下的利益输送是圈子腐败中的核心问题。
相对于比较直观的物质利益输送,情感层面的利益交换要隐秘得多。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一个社会人在生活中必然产生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对于圈子腐败的组织者(关键人物)而言,他所需要的不完全是物质层面的财富,更需要别人尤其是下属对他的依附,以及在关键时刻的信任——这种信任有时以投选票的形式表现出来。年终考核、民意测评是干部考评、选任提拔的必经程序,为了不在这些环节“出洋相”,一些官员便集结圈子,影响和带动圈子中的其他人给自己投票、打分,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对这些人给予回馈式关照。这就是掩盖在情感外衣下的资源交换和利益输送,只不过它的形态较为高级,形式较为隐蔽。如果说基于物质纽带的利益输送是维系圈子腐败的基础要件,那么基于忠诚的依附关系就是维系圈子腐败的情感纽带。在情感纽带驱动下,圈子成员之间会逐渐产生自豪感和责任感:自豪感不断强化圈子成员的身份,使其共同抵御外在力量对圈子的威胁;责任感约束圈子成员的言行举止,使其共同维护圈子的整体形象。
在圈子腐败中,典型的情感输送是关键人物与其身边人特别是其秘书之间的情感输送。“秘书通常是最接近领导的人,因而他们与领导关系的密切程度要超越于其他人与领导的关系。秘书对其领导的忠诚是毫无疑问的,领导对其的关照往往也是毫无保留的。”⑦一些官员热衷于编织各种圈子,但碍于情面和法律约束,不便亲自出面接受利益输送,而是交由其秘书等身边人负责管理;作为回馈,他会对秘书等身边人格外关照。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与其秘书秦裕的关系就是如此:彼此非常信任,互相交换利益。当然,这种特殊的结盟关系最终在反腐高压下土崩瓦解。
无论是直接的物质利益输送还是温情脉脉的情感传递,终究都是制度外交往方式。圈子成员为掩盖腐败行径,大多采取封闭、固化内部结构和做人做事上内外有别两种手段。就前者而言,圈子成员大多限于圈子核心人物所在的行业、部门、地区等较小的范围内,彼此之间要么是血缘、亲缘关系,要么是业缘、学缘关系,要么是政商勾结、互相利用关系。相对固化的圈子结构使圈外人很难进入其中,因而极易形成相互支持、庇护、依附的“利益共同体”。正是因为内部结构较为封闭、固化,有的圈子几乎演化成一种非法组织:核心人物拥有家长式的利益分配权和矛盾调处权,在成员落马、腐败行径败露之际极力隐蔽圈子、保护其他成员。就后者而言,为了遮人耳目、逃避查处,一些人在编织、挤入各种腐败圈子的同时,在与圈外人相处中行事低调、做事谨慎。如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九三管理局原局长张桂香就善于作秀,她在公开场合被罩以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等光环,实际上利欲熏心、大肆贪腐。在这些人看来,那种明目张胆索贿受贿的腐败招数早已过时、风险太大,要做到既捞钱又降低风险,就必须采取圈内圈外区别对待、“打深井、放长线”的手法,给自己和圈子中的其他人涂上一层保护色。但是,不管怎样变换招数,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利益输送。
三、掩映在庇护关系中的共谋与交换:
圈子腐败的运作逻辑无论何种形式的共谋与交换行为都不会赤裸裸地进行,否则就没必要形成圈子。那么,是什么因素使物质形态和情感形态的利益交换行为得以秘密而又稳妥地进行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厘清隐藏在圈子腐败中的庇护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关系安排,庇护关系的形成和维系在于互惠互利的利益交换性和彼此之间信任和忠诚的感情融入。”⑧在庇护关系的掩映下,形成了圈子腐败中共谋与交换行为的基本逻辑。
“庇护”原本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指经济社会地位高、掌控资源丰沛的人利用权力或通过其他途径向经济社会地位低、资源匮乏的人施以恩惠或给予保护,作为回馈,接受恩赐和保护的人回报以忠诚、信任乃至依附、服务。著名人类学家沃尔夫在描述传统乡村社会场景时谈到,作为庇护者的地主“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和保护以反对来自政府的合法或非法的汲取”⑨,而作为被庇护者的农民回报以“尊重”或提供其他服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既具有情感性,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工具性。情感性是指庇护关系能让卷入其中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能让由此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更加稳定、牢固;工具性是指庇护关系能给卷入其中的人带来互惠等好处。
“庇护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同样与政治资源的匮乏、政治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有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拥有权力者向特定人群或团体分配选择性利益以交换政治支持,而被庇护者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获取一定的利益也需要帮助。”⑩这就是庇护关系的生成逻辑。对于被庇护者而言,挤入圈子并参与利益共谋与交换主要是为了打通仕途升迁的通道和寻求自我保護。所谓仕途升迁,简言之,就是官员职级和岗位的向上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选任日渐步入制度化轨道,什么样的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考察要求等都有相关制度予以规定。这些制度规则本来是规范官员调整事宜的,但被一些人不当利用,借以形成圈子内部的庇护关系。干部选任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往往受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双重影响。比如,虽然干部选任制度明确了某个职位的具体条件(个人资历、从政经历、工作业绩、群众基础等),但一般情况下,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很多,谁能得到提拔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有些人坚持认为,基于利益、情感而形成的庇护关系对其职务升迁会有较大影响,于是就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编织、运营各种圈子。庇护关系得以形成并进一步强化的过程中包含一系列连锁反应:挤入圈子,通过利益交换而获得关照、提拔—被提拔者投桃报李予以回馈式利益输送—庇护关系变得更牢固—被提拔者得到进一步关心和再次提拔,并再次进行利益回馈。这种连锁反应使庇护关系不断被复制、庇护范围不断扩充,直至酿成圈子腐败。庇护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保护,根本发挥不了真正的保护作用。但是,这种扭曲的保护具有污染性:损害正常的政治生态,给整个政治生态带来重重雾霾。
与传统庇护关系结构中庇护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施以恩赐不同,现代庇护关系结构中不仅有恩赐关系,还包含交换关系。除了前述通过施以庇护而获得选票、在考评中获得高分,庇护者注重建构“相互帮助”的圈子还与其试图延续政治资源的使用时间密切相关。有的官员为避免“人走茶凉”,就在其位高权重时为特定的人“做嫁衣”,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投资,其中隐含着离任后获得人情、感恩式报答的期待。
四、治理圈子腐败的基本路径
圈子腐败已成为侵蚀健康政治肌体的毒瘤,根治圈子腐败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圈子腐败因利益而生,一旦利益分配不均衡或者圈子成员的目的差异性过于明显,特别是当一些圈子成员抱着“搭便车”的心理而只愿意分享收益、不愿意承担风险时,这种利益同盟就会不堪一击。圈子的这种孱弱性为破解圈子腐败问题提供了突破口:稀释圈子的利益聚集度,弱化其利益基础,降低其利益实现的可能性,最终分化其利益同盟。一旦失去利益根基,围绕利益而形成的圈子自然会土崩瓦解。为了分化圈子的向心力,以下措施都是值得探索的。
1.推行官员轮岗转岗制
某一核心人物之所以能结成以其为中心的圈子,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大才能,而是因为他所处的岗位有能为其他人带来谋利的可能性。很多案例表明,一个官员在同一个岗位上任职时间太长,虽然有利于积累经验,但极易形成关系网,为以权谋私者提供可乘之机。从这个角度讲,治理圈子腐败不应忽略“岗位”这个关键词,要把黏附在“岗位”上的圈子腐败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限度。“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如果处在某个岗位上的人是变动不居、经常替换的,则其试图围绕这个岗位而结成圈子的动机就会减小。因此,有必要推行官员轮岗转岗机制,尤其是对那些掌握丰厚资源和大量利益分配权的“一把手”官员实行大跨度的轮岗转岗。轮岗转岗发挥作用的关键不在于所转换的岗位有多少、频率有多高,而在于打破系统内循环,实现多系统、多领域的转岗轮岗。要把热点岗位与一般岗位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只在热点岗位之间“假轮岗”。
2.科学配权,规范用权
“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超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任何一种腐败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权力被异化、滥用的后果,圈子腐败概莫能外。因此,治理圈子腐败应从科学配权、规范用权入手,避免权力高度集中、权力私有化。就科学配权而言,明确权力边界是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减少圈子腐败现象存在空间的重要抓手。可以参照清单管理办法,制定各级各类权力细则,明确具体权力的内容、边界、行使方式等,消除可能产生圈子腐败现象的因素。还可以尝试构建“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的权力制约机制,防止因权力过于集中而出现拉帮结派现象。就规范用权而言,可以在明确权力清单的基础上,按照“一项权力一个流程,一个流程一项细则”的思路,根据某项事务发生、发展、结束的顺序及其涉及的部门,制定详细的权力运行流程图,引导权力规范运行。互联网是新形势下反腐的有力工具,可以通过“互联网+”,建立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部领域的电子政务系统和电子监察平台,将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及其每个环节都呈现在网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信息共享和“电子留痕”的作用,缩小圈子腐败现象的滋生空间。
3.形成强有力的监督
圈子腐败现象之所以产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应的监督制约乏力。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监督缺失将带来行为失范,因此,要通过做实做细监督制约体系,让圈子腐败现象无处藏身。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要通过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担当起权力监督的责任,参与到权力监督活动中,形成监督制约圈子腐败的强大群众基础。有效的监督来自于公共理性的培育。现实中有的人实施监督并不是出于公共理性考量,而是出于私利目的。这就隐含着极大的风险:如果监督者被圈子成员拉拢、收买,就不但导致监督缺失,而且造成更多人参与圈子腐败。鉴于此,必须倡导基于公共理性的监督,防范个体私利化的监督。
4.注重制度建设
在治理圈子腐败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一个关键环节——制度建设。无数事实证明,制度建设对于规范政治生活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制度的优势在于可以给行动者提供一种行为规则,使其不盲目行动。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能明确相关举措,减少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因此,无论是推行官员转岗轮岗,还是实行科学配权、规范用权、有效监督,都要将其上升到制度层面,予以制度化。
注释
①[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7页。②卜万红:《圈子文化与腐败》,《廉政瞭望》2010年第12期。③储建国:《腐败窝案形成的政治机理》,《人民论坛》2013年第10期。④Scott J. C.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2, (66).⑤杨念群:《礼物交换的本土精神》,《读书》1997年第2期。⑥柯兰君、孙瑜、刘亚平:《送礼与腐败——中国送礼形式和功能的转变》,《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⑦⑧吴海红:《利益共同体的缔结:官场庇护关系的形成机理分析》,《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3期。⑨Eric Wolf. Kinship, Friendship and PatronClient Relations. New York: Frederick and A. Praeger,1966.17.⑩陈尧:《庇护关系:一种政治交换的模式》,《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2页。《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0页。
责任编辑:浩淼林墨
Analysis of Circle Corruption and Its Governance Path
Chen Peng
Abstract:Circle corruption is a special kind of corruption phenomenon.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its emergence. Collusion and exchange of interests are the basic reasons. The benefit transfer is the core problem of the circle corruption. The interests are mainly manifested by the intuitive material form and the secret emotional form. No matter what form the interests transfer, it is carried out in a sheltered relationship. For shelter shield, the construction of patronage is to realize the maximiz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the continuation of time of political resources; for shield seekers, they seek shield mainly in order to open up the channel of career promotion and achieve self-protection. The circle forms around the interests, which actually presupposes a path of governing circle corruption: It can reduce the interest base of the circle, weaken its benefit foundation,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alization of its benefit, and finally split the circle of this interest alliance.
Key words:circle corruption; conspiracy; exchange
中州學刊2017年第7期城镇化建设负外溢性问题矫正2017年7月中 州 学 刊July,2017
第7期(总第247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