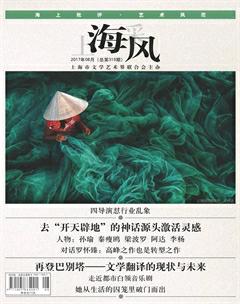宇秀:从海派小资作家到北美痛感诗人
萧元恺
久居海外,对于文学报刊多少有点隔膜了,有时即使就放在眼前也有点熟视无睹。但最近《上海文学》封面上有一个熟悉却久违的名字一下攫住了我的视线。
她是宇秀。曾经让我用过一些力气,却再也抹不掉的名字。
从“下午茶”到“温哥华”的全方位跨越与隐遁
十年前初抵温哥华,在当地中文报纸时评专版初次见识了宇秀不拘一格的文字,并记住了她的专栏“北美第三眼”。后读到了她的《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当时正在国内热销,颇有影响。曾读到一本《上午咖啡下午茶》,该书收录了包括林语堂、周作人、贾平凹等现当代文学大家之作,宇秀“下午茶”里多篇作品赫然进入这本名家名作选集之列。而此时的宇秀却在北美的报刊上以泼辣的文风、犀利的语言评论时政、探讨移民生活和东西文化之碰撞,其观点的尖锐、文字的力度,颇有男性的手笔。难怪有读者来信或来电询问:“这个宇秀不会是那个写上海女人下午茶的宇秀吧?内容和风格都跟她的书不一样啊。”
2007年4月,宇秀的新著《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和再版的《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作为当年中国工人出版社的重点书目,在重庆中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亮相。评论家郭媛媛在《失重的裸露——评旅加作家宇秀散文集〈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一文中说:“她用她绵密而细致的心思,捕捉到了重大人生转换时刻生命的悸动、文化符号与社会认定悖离的分裂,也最终能从容体悟、观照母国与现居国社会及文化。”
评论家认为作家自身作为“标本”的大胆裸露和书写,提供了人类在迁徙过程中社会学层面的贡献。一个有关人类迁徙生存文化的大命题,宇秀以非常私语性的文学表达而呈现,给人以感性、细腻、真实并富有时尚气息的阅读快感。这是宇秀的独特。
然而,就在宇秀以《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再度回归国内读者视线时,她在本地报刊却突然消失了。直到一个瓢泼大雨的夜晚,我作为《环球华报》记者接受了一项采访任务,驱车赶往西温哥华的一家泰国餐厅,才头一次面对面地见到宇秀本尊。原来她和丈夫一起在少有华裔的主流社区西温哥华市创办了一间泰式餐厅,当看到她穿梭往返端盘递水的身影,不由想到一个成语典故:文君当垆。禁不住为一个上海才女坠入人间烟火忙于生计而无暇文学感到惋惜。那晚,外面歇斯底里的雨声与里面推杯问盏的清脆声混杂在一起,她就在这种自然与人为的交响乐中,时不时穿插着与我聊上两句。
那篇访问记《我没有工夫喝下午茶了》的标题是直接引用采访中宇秀的自我解嘲,一句感叹道出了一位沪上女郎曾经有过的张爱玲式的闲适写意,也道出了王安忆式的境界追逐,更道出了当下欲罢不能的一丝惆怅。我当时暗自思量:她是否就此与文学写作告别?还是这段“文君当垆”的生活会成为她以后重返写作的财富?
悄然重返文坛的锋芒难掩和多维度的实力呈现
这次在《上海文学》邂逅“宇秀”,让我不由想到十年前采访她时的感慨,她到底是放不下文学啊!像是失联很久的老友突然有了消息,令我忍不住上网探探她的近况。
就在《上海文学》今年第六期发表她的长篇散文《那年的粉红叫的确良》的同时,《钟山》第三期刊发了她的长篇人物纪实《痖弦,温柔之必要的广义左派》,该文在今年揭晓的由山东文艺出版和大众网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阳光下的风”征文大赛中获报告文学二等奖。第七期的《青年作家》则推出她记述与女儿一起举办慈善演奏会感人经历的散文《锁孔里的日夜》。稍早一点今年第三期的《红豆》刊发了凌鼎年的评论《宇秀散文很小资》,同期配发了两篇宇秀的随笔:《被折衷的粉红套裙》和《外婆、小资、红烧肉》。在《北往——魁北克文学》公众号上,我看到凌鼎年另一篇评论《宇秀散文的海派情愫》,说实话,我比较认同這个”海派情愫”,而她移民后文字里的这份情愫,不同于她在“下午茶”里书写的上海,而是在另一个文化坐标上的文化回望,那优美中的感伤,趣味中的思虑,个体生命透出的时代变迁,早已不仅仅是小女人的小资情调所能负荷的了。宇秀的写作多从日常生活中取材,以小博大,数千字一篇散文,却包含惊人的信息量,如一件的确良,一道《烂糊肉丝黄芽菜》(见《作品》2015年第9期),乍一看平凡琐细,但宇秀笔下的人物却总是那么真切自然地呈现出世态炎凉和时代沧桑,令她的作品颇具现实主义的魅力,让人读后不由掩卷喟叹。
从2014年秋开始,宇秀悄然重返文坛,她的名字跟随着她的文字密集地频现于海内外报刊,许多网络平台和公众号更是频繁密集地出现宇秀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如《解放日报》的“上海观察”、《文汇报》的“文汇”网刊、华语文学网、腾讯、网易、世界华人网、忆乡坊文学城等等。回归写作仅仅两年多时间,她不仅在国内的纯文学刊物上连续发表新作,同时她在文学批评的涉足也显示出不凡的实力和独特风格。在2014年11月于广州召开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高端论坛上,宇秀以《跨界书写的“偏房心态”》发表的演讲,震动全场,其鲜明的立场、独特的视角和率性犀利的语言引起与会者热议。之后宇秀将演讲内容整理成文,发表在《华文文学》2015年第3期,被多个文学网站和公众号转发。另一篇发表在2015年第1期《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的《我是一条变色龙——新移民文学个体生命在迁徙过程中的角色变幻》则是有关新移民文学角色研究的力作,去年该文被两部海外文学研究的论文集收录。这篇论文之所以写得真切有力,那正是基于宇秀自己的创作实践的体会。
随笔小说《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中的双面人形象,是宇秀在新移民文学角色塑造中的一个很有创意的实践。林楠在他的评论集《彼岸时光》和《含英咀华集》中均有对这部作品的评论:“同一人物身上两种不同角色及其心理矛盾,写得细腻而深刻,读来令人酸楚。选择移民,本身就是选择了一种自我颠覆,这种颠覆本来就含着放弃、忘却,而这从零开始的新我,又不可避免地要与旧我之间发生扯不清的万般纠葛。失去原有文化背景的‘新生是异常痛苦的,不可抗拒的。这一点,宇秀揭示得异常深刻。”
著名文学批评家季红真教授如是评论《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详尽地表现了嫦娥奔月一样的追梦所遭遇的一系列反讽,享有特权的知识女性在异国沦为中层平民的巨大落差,心灵所遭际的种种磨难。从物质所不能补偿的心理落差到时空形式的彻底改变,内在的艺术自我与光鲜的外在自我发生了分裂,还有语言带来的心理障碍。如果说汉语是宇秀血管里的血——与生俱来,那英语就像一件外衣需要的时候披一披,有时都不知道自己此时是属于肌肤还是属于衣服。深刻表达了种族身份的转换中自我确立的艰难……”
移民后的宇秀总能够站在东西文化两个坐标点进行观察与介入,使她在不同题材和体裁的书写中,均传递出在异国他乡非母语困境中的跨文化声音。我明显感觉到她的文字与“海派小资”已渐行渐远,更接地气,也更圆润老道,其笔触平添了岁月的积淀与历练。只是让我疑惑的是,她是如何在日常的忙碌和琐碎繁杂中,还能沉浸到文学的创作中,不断给读者贡献品质上乘的美文?当我继续在网上搜索宇秀,惊讶地发现她原来不仅仅是美文高手,更是这两年海外华语诗坛新崛起的实力派诗人。
疼痛的诗学思考与自由式的心灵传达、灵魂叙事
宇秀近年重返写作,诗歌成为她创作的一个高地,其独树一帜的意象创造和语言表达,已引起海内外诗坛的广泛关注。最新一期香港的《华人》杂志刊发了探讨诗坛现状和宇秀诗歌创作的长文《当下,宇秀的诗值得一读》,文章指出:“其诗作充满喜剧诙谐笔触的背后,透出一种深深的痛。这种痛来自于乡愁、亲情、爱情,有对流年易逝的感怀,也有对生存环境的动荡不安。善于以极细腻的笔触和极为敏感的神经,从不同的生活侧面来表达对每个过往的强烈执爱与感悟。”
对于诗人宇秀,是我以往不曾认识的,而作为诗人的宇秀在海外华语作家中显然是一颗耀眼的星。她的诗歌不仅为海内外文坛关注和热评,更受到广大文学圈以外百姓读者的青睐。
2015年以来,宇秀诗作在《诗刊》《世界诗人》《上海诗人》《香山诗刊》《华星诗谈》《流派》《解放日报》《中国时报》以及众多网络平台公众号上被发表被转载,2014、2015年《中英双语中国诗选》年度选本、2015年台湾版《中英双语世界诗选》以及将要出版的2017年《中英双语中国诗选》均收录了宇秀诗作。2015年第35届在台湾举行的世界诗人大会上,她和诗人、翻译家北塔先生共同主持了诗歌朗诵会,并在来自世界各国的诗人面前朗诵了她在《解放日报》“朝花”发表的新作《禅的容颜》:
你在最炎热时节把自己打开
让一池烦恼安静下来
我曾疑惑你是立在水面的云彩
不过云没有心,只是给有心事的人看
你不是,你绽放
是因为有许多未了的情怀
……
最近刚出版了《诗歌编辑札记》的资深诗歌编辑赵中森先生说:“这是70岁的我入夏读过后立刻安静下来的句子。”诗人北塔称其“充满从容的痛感”!把此诗推荐给台湾《创世纪》诗刊的著名诗人痖弦先生读后感慨道:“人这一生这么长,哪能没点儿事儿啊!你这诗有故事有戏剧性,让人想很多。”当代华语诗坛泰斗洛夫先生在台湾《创世纪》诗刊读到此诗和另外的三首宇秀诗作,称赞“既富于抒情性,又非常具有现代感”,称他个人“超喜欢”!
今年年初中国诗歌网转发了一组宇秀的《我喜欢躲在悲伤的死角》十首诗,当天点击破万,和她的另一组四行短诗一道进入“每周”和“每月”中国诗歌点击排行榜。之后不久她把发表在2016年12月《上海诗人》的《我忙着绿花菜的绿西红柿的红》和另一首《打烊》上传到中诗网,不日点击再度破万,又一次进入“每周”和“每月”中国诗歌点击排行榜。这两首诗,显然都是来自宇秀的现实生活的书写,令人称奇的是:现实里的繁琐焦虑似乎与诗相距甚远,甚至会把诗意的灵感消磨殆尽,而宇秀的灵感却是在这样的磨损与挤压中迸发出来,难怪她的诗句直抵人心。日常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到了宇秀笔下却惊心动魄,令人震颤。
在不知菜價也无需了解尿片的时候
我常常像哈姆雷特
延宕在夜空之下思考是生还是死
此刻,我就只顾忙着
绿花菜的绿西红柿的红
却怎么也挡不住日子跟着绿花菜泛黄
跟着西红柿溃疡
偶尔激动的事情像菠菜一样没有常性
转眼就流出腐烂的汁液
所有的新鲜不过是另一种说法的时间
……
今年4月13日的美国《侨报》“文学时代”副刊头条刊登了著名书画家、诗人安家石先生的评论文章《忙红忙绿背后的生命之殇——加拿大诗人宇秀诗歌赏析》,他在文章中这样解读:“诗人借红红绿绿的新鲜蔬菜的速朽,隐喻我们忙碌的日常背后的生命之殇,时间之殇。构思奇特,令普通的生活画面成了诗中的诡异意象。”
香港诗歌协会会长、诗人秀实评论道:“宇秀的诗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状若轻描淡写中, 背后却有浓郁的感情在。不徐不疾的节奏里, 透露了对人间世的无尽牵挂。《我忙着绿花菜的绿西红柿的红》以忙碌的生活琐事始,以惦记母亲终,那是一种极为优秀的述说技法。令人读之难忘。”
旅澳诗人、评论家庄伟杰先生作为海外新移民诗群的领袖人物,在读了宇秀的诗作后从诗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宇秀是一个清醒而明智的多面手写作者。作为旅加新移民女性诗人,由于空间位移带来的生命迁徙、文化迁徙和心理迁徒,为宇秀提供了丰富而独有的经验元素,并因此架构起诗人隐秘的精神空间——在承载中浓缩着诗人的精神世界,包括记忆、想象、怀旧、认同,同时传达了个体的生命感、依附感和归属感。难得的是,在面对现实、历史、命运和生存等命题时,她能够表现出饱含着疼痛的诗学思考。”
我注意到,人们对于宇秀诗歌的评论多提到“疼痛”两字,这与她当年的畅销书给人小资和时尚的阅读感受全然不同。不过有一点我认为,共同之处是宇秀文字上的独到与怪异,它似乎含有幽邃的密码,表面上都是些惯常字体,经她之手的排列组合,就有了华丽而略妖冶的文风,汪洋恣肆又收敛自如,姑且称之为“宇秀体”吧。而”宇秀体”背后透出的跨文化声音,值得海外华文文学界关注和研究。
六月初夏,气候宜人的温哥华,我和宇秀进行了一次文学对话。
笔者:这期《上海文学》来得恰是时候,让咱们省却了寒暄盘带,直接切入文学的话题。你的“的确良”却很不同于通常的怀旧之作,里面蕴藏了很大的文化信息量,在那个年代细腻绵密的少女心思里充满了文明与野蛮的冲撞,这是否和你现在处在西方文明的环境里有关?
宇秀:的确良是我少女时代的一个心结,如果没有出国,我想我也是会把这段心结写出来的,但不会是今天你看到的格局,如果我一直不离开上海,我写不到这个程度。在另一种文化的坐标上回望故国、童年、往事,便有一种超越和自由。
笔者:发生在特定年代中的事件,与回过头来对那个年代所做的文学反映,是有距离的。如何通过当下视角与智识来处理这个距离,考验着作者的文字工夫和体认深度。在这点上,我认为你做的很好,尤其是表姐的描摹刻画,时代感很强。
宇秀:表姐是具象的,她在我童年记忆里代表着上海世俗生活与时尚追求的细微末节。而表姐又是抽象的,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向往,是那个特殊年代禁锢中的突破。我没有写革命运动中的大悲大喜,家破人亡的悲剧故事,而是通过最普通的市井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来呈现那个年代,所以能得到普遍共鸣。
笔者:你怎么看待“重返文坛”这件事?
宇秀:谈不上重返,我是刚刚出发。只是这次出发与孩提时代就有的文学之心隔了太久。没想到《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我在自己的餐厅工作时,常常碰到远道而来的客人问:你是写下午茶的宇秀吗?后来我用了微信,也常常在微信里碰到我的读者,她们把自己保存的不同版本的“下午茶”拍照传给我看。去年我无意中看到豆瓣网读者讨论《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打了7.3分。一本出版了15年之久的时尚女性读物,文中写到的许多咖啡馆甚至连伊势丹这种凡上海时髦女子必光顾的时尚之地都不复存在了,但人们依然愿意阅读这本书,显然不是书中的时尚因素,这是文学的力量。写作该书的时候,我并未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文学创作的位置上去构思和书写,即使移民后写作《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或其它小说、诗歌,我一直比较随心所欲,我基本上自视为“文学票友”而已。
真正开始从文学层面自觉思考我的写作、处理笔下的题材,则是2014年秋天以后的事了。而在此之前的移民生活里,忙于生计忙于家务,特别是繁杂辛劳的餐饮生意,将我牢牢地捆绑在在庸常繁琐的俗务中,我与文学圈几乎绝缘。但愈是那样的困顿之中,内心里的文学火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遏制。恰好碰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伯乐白舒荣老师,她力邀我参加在广州举办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与此同时,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家陈瑞琳女士和著名编剧薛海翔等一行来到我餐厅,鼓励我重新提笔写作。瑞琳更是积极邀请我出席南昌首届新移民国际笔会。于是便有了包括在厦门大学召开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双年会在内的连续三个会议的文学之旅。由此,也开始了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正式启程。
笔者: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以前是文学上的游击队,现在成为文学上的正规军了?想好好打一场文学阵地战?
宇秀:2014年之后,我的确是想好好静下来,正如你比喻的“打一场正儿八经的阵地战”。但是家里有个学钢琴的孩子,要陪她上课练琴比赛,耗费我许多精力和时间。我还有个和丈夫共同打理的餐厅,根本就没有大块时间可以坐在书桌前。你所读到的近年来我发表的作品,多是见缝插针用时间碎片写就的。我这两年诗歌写得相对比较多,这也是个客观原因。我的诗和散文都有丰满的细节,许多人说你不写小说实在可惜了。说实话,我心里很清楚我真正想要写的东西还没触碰呢,那些我一闭上眼就跟放电影似的浮现在我眼前的故事素材,如同一座原矿尚未开采。长篇抑或是中篇,需要相对完整的时间和比较平和的心境才能构思落笔,那是一项工程,我渴望尽快有一段安定的时间。
2015年夏开始,我受邀在本地华文报刊开设了专栏“熟女聊斋”,每周一篇女性话题的随笔,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也算在经营餐厅生意忙碌之外的一种休闲,我准备把这批文字整理一下出本集子,文字一如既往保留了我的“小资情调”,但与“下午茶”的闲适有所不同,读者将与作者一同在跨文化视野中感受女性的生活审美与生命审美的认知与追求。没有诗歌的生活,我的内心空空荡荡,丢了魂儿似的。诗歌是我的自救方式。
笔者:你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知名的校园诗人,你参与创办了大学里的诗社和学生诗刊,应该说你在诗歌创作上的起点是很高的。当年《诗选刊》选登了你的《我怀念吵架的事》,这首诗曾被评论为“无技巧的原味的诗”。虽然你复出后的诗作更为深刻隽永,意象的创造更丰富诡异,但情感的真挚与你少女时代的诗作却是一脉相承。
宇秀:少年时写诗靠才情,中年以后阅历与才情结合才有诗的深刻度。我近年的每一首诗几乎都逃不脱海外生活的阅历和跨文化的境遇。美国知名华文作家刘荒田先生在《华文文学》2016年第3期发表的《曲尽幽微——宇秀短诗欣赏》一文中详细解读了我的一首《农事》,他认为“法式指甲里还藏着中国的土地”是惊人之句!他在文中说:“加拿大女诗人宇秀的短诗,具深入致密的穿透力,在表现海外女性移民的生存状态与心理活动方面,笔力特别酣畅。”
笔者:如果说你在《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里的书写是比较本色地记述了你移民过程中自我颠覆与被颠覆的心理路程,那么你是不是在诗歌中更偏向于通过意象创造去探索灵魂的着落?我看到当代诗坛大家、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洛夫先生对你诗作的评语:“用她自己独特的语言,通过诗歌,她向一切谎言和陈腐思想宣战。意象是她最有力的翅膀,载着她,也载着读者遨游于一个接一个的崭新世界……”
宇秀:說实话,我没想到洛老对我的诗歌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当我看到他将亲笔书写的这段话在微信里拍照传给我时,我颇为惊诧:我从来没有正儿八经把我的诗作整理好发给他看过,他多是自己在微信浏览的。温哥华有个“雪楼诗艺小集——洛夫先生”诗群,洛老把我拉进这个群里,我偶尔也会把自己的新作发到群里让大家评鉴。他在评语中提到的拙作就是在群里看到的。说明洛老平时对我的诗作就很关注。这一点很让我感动。
至于意象的创造,这取决于诗人的想象力。这是上帝给诗人的礼物,这也是写诗和写散文的根本区别。小说家、戏剧家都可以成为职业,但你听说过职业诗人吗?一旦诗歌写作成为职业,这个诗人的诗歌艺术生命也就终结了。诗人是一种宿命,这种宿命里是悲剧性的。作为移民,不管你在移居国住多久,也不可能被当地文化彻底同化,同时你也不可能依然完整地保留你固有的文化,你永远都是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所以在我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两个时空的切换,以及困境中的挣扎与反抗,这种困境更多时候是内在的,外人看不到的。这种抗争在我的诗歌中可能表现得更为强烈,诗歌比任何文字都能更为逼真地裸露内心世界。
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对我的诗作这样评判:“作为置身于英语世界的华文诗人,宇秀的诗作是边际化语言困境中的一种反抗,它们以混杂着批判、谐谑和抒情的独特风格,向我们传递出语言孤岛里的跨文化声音。”我觉得他把诗人所处的境遇和在此境遇中的写作,两者之间的关系讲得很到位。无论是洛夫先生的美言还是朱大可先生的分析,都只是表明:我不过是可以用以解剖的一只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