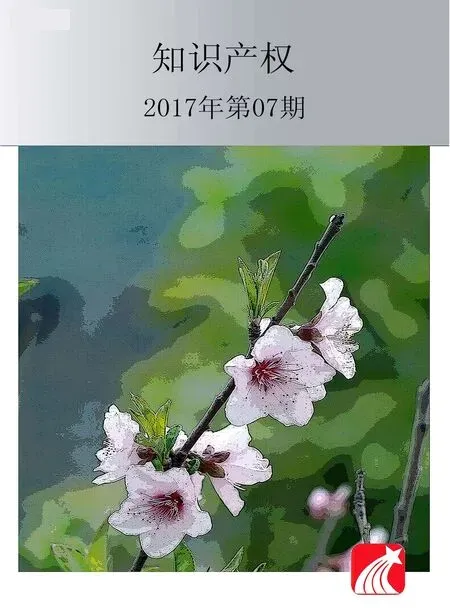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侵权联动执法机制中的错误处理责任研究
姚志伟 沈一萍
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侵权联动执法机制中的错误处理责任研究
姚志伟 沈一萍
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侵权联动执法机制的实施具有必要性,其可以弥补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在处理专利侵权问题上的局限性。基于电子商务领域内专利侵权联动执法的现状,有必要分析电子商务领域内专利联动执法机制中凸显的错误处理下的责任分配问题。平台在基于对知识产权维权中心侵权判定的信赖导致错误处理的情形下,不承担侵权责任。在平台自行判定而作出错误处理的情况下,平台是否要承担责任,要分析平台在处理过错中是否善意,是否以理性人标准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对行政执法部门的责任,按照行政法、国家赔偿法等规定进行责任认定,并追究相关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责任。对出具错误报告的知识产权维权中心不宜适用专家证人制度,而应将其视为鉴定机构追究侵权责任。
专利侵权 电子商务 联动执法
引 言
互联网的发展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其在推动信息自由流动、提升用户使用便捷性的同时,也催生了诸多利用互联网实施的侵权行为,其中就包括了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销售侵犯他人专利权商品的行为。对于此种行为的追责,包括对平台的追责,各国法律普遍适用避风港规则,我国同样如此。按照《侵权责任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在知道经营者利用其平台销售侵权商品时,或收到权利人发出的合格侵权通知后,应采取必要措施制止。
避风港规则在商标和版权领域的适用,一般来说,并不存在争议。但是,在专利领域是否也适用避风港规则,存在较大争议。a详细论述参见王迁:《论“通知与移除”规则对专利领域的适用性——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2款》,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3期,第20–32页。囿于专利侵权认定的技术性、复杂性,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不能像处理电子商务领域内的著作权、商标权侵权纠纷一样简单地作出侵权认定,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在专利侵权认定上的局限性,提升了专利执法在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侵权纠纷处理中的重要性。2014年起,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陆续出台了专利联动执法的规定与举措,推动在电子商务领域内的高效、便捷化的专利纠纷治理。但是,由于专利侵权认定的复杂性,电子商务领域内的专利联动执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处理的情形。本文所阐述的“错误处理”是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专利行政执法部门b我国的专利行政执法部门通常是指知识产权局,本文中两个概念不区分使用。、知识产权维权中心c知识产权维权中心是公益类服务机构,通常附属于知识产权局下,是其下属的事业单位,主要为社会公众提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和知识产权相关技术服务。各地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名称有一定差异,也有称“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本文中统一称为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因收到错误的侵权通知或投诉d通知是针对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而言,投诉是针对专利行政执法部门而言,下同。错误通知或投诉指的是专利权人向平台通知或向专利行政执法部门投诉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侵犯其专利权,但实际上被通知或投诉的平台内经营者没有侵犯专利权人专利权的情形。而作出错误认定,对合法经营者采取删除或屏蔽商品链接等限制销售的必要措施,对合法经营者造成损害的行为。这里的错误处理不包括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行政执法部门主动对专利侵权采取处理措施的行为,而仅指其应侵权通知或投诉而采取的相应处理行为。同时,本文中的错误处理也不包括平台收到正确的侵权通知,但采取超过制止侵权所需必要限度的行为。电子商务领域内专利联动执法是由“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等多方参与处理,该多方共治的模式也导致在发生错误处理情形时,产生各方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分配问题。
一、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侵权联动执法的必要性
(一)平台在专利侵权认定上的局限性
如今,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成为了诸多网络侵权行为的共同被告。在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关于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案件也占据了重要部分。e以国内最大的网络交易平台淘宝为例,其在2012年第四季度,每个月平均有1万件宝贝(即淘宝店铺上的商品)收到专利侵权投诉的通知,参见司晓、范露琼:《知识产权领域“通知—删除”规则滥用的法律规制》,载《电子知识产权》2015年第1期。但是,专利侵权问题不同于著作权侵权与商标权侵权,其特殊性在于专利侵权认定本身的复杂性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对专利侵权审查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不对等。
其一,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难以获得通知所涉商品的专利信息。当卖家在平台上上传商品图片与信息时,其通常不会明确指出所涉专利情况。平台经营者基本上无法根据商品图片或信息判断出具体专利情况,甚至无从得知商品是否具有特定技术特征、落入专利技术的保护范围。
其二,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难以对专利侵权进行判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侵权判定均要以“本领域技术人员”为基准,在判定原则上存在全面覆盖原则、等同原则、禁反言原则等,即使是以“一般消费者”为判定基准的外观设计专利,也要求考虑涉及产品所属的种类,以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定。f陈泽宇:《网络服务商的专利侵权责任认定——兼评〈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七十一条》,载《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论文集》。同时,对于大部分专利侵权的判定而言,判定人员必须具有阅读专利权利要求书与说明书的能力,对所涉专利有所了解,认知专利的技术点,而平台难以匹配大量对各种技术领域均熟悉的专家进行侵权认定审查。
(二)行政执法在专利权保护上的有效性
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相比,行政执法部门在处理专利侵权时具有优势。专利行政执法部门作为专门处理专利事务的机关,配备有大量具有丰富专利经验的工作人员,这是平台所不具有的。专利行政执法部门还具有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所不具有的优势地位,专利行政执法部门在处理专利侵权案件时,与被处理对象之间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地位。与之相比,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与被处理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地位之间的差异也就决定了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处理措施的有限性,只能依赖于平台与商家之间的合同采取扣分、删除、屏蔽、关闭店铺等措施,而行政执法部门则能依靠其优势地位,依靠行政资源进行调查取证,进行行政处罚。因此,专利行政保护相对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专利保护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专利行政保护是专利保护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整个专利制度的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的“护航”作用。
(三)联动执法的优势
由于当前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保护运行面临着较大的压力,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自身难以审查专利侵权行为、对复杂的专利侵权纠纷作出认定。同时,由于电子商务侵权领域内侵权行为的高发性、广泛性,仅仅由行政执法部门负责电子商务领域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也是不现实的,会对行政执法部门造成过重的负担,增加行政运行的成本。同时,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分散性较强,行政执法部门难以掌握众多经营者的信息,而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配合下,行政执法部门方能更有效地执法。g例如,阿里巴巴与浙江省双打办开展的2016“云剑行动”中,依托阿里巴巴大数据,公安机关在短短一年间共立侵犯知识产权类案件284起,破案257起,涉案件总案值达14.3亿元。参见陈佳妮、陈谊:《14亿元假货在阿里大数据面前无处遁形》,载《浙江法制报》2016年12月9日第001版。此外,与行政执法部门相比,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可以极为快速和便捷地通过技术手段对销售侵权商品的店铺采取限售、禁售措施,其制止侵权的效率显著高于行政机关。因此,为有效治理平台上的专利侵权问题,平台应该与行政执法部门包括其所属的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建立电子商务领域的专利纠纷行政执法联动执法机制(以下简称联动执法机制)。
二、联动执法机制的现状及涌现的错误处理责任问题
(一)联动执法机制的现状
2016年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就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的办案量达13, 123件。h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www.sipo.gov.cn/zscqgz/2017/201701/t20170123_130808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3月24日。基于案件数量的庞大,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执法维权专项行动中已经要求由地方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建立联动执法机制,i冀瑜、郭飞翔:《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的必要性》,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7期,第95-99页。该机制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2016年广东开展的“五月闪电”专项行动,共立案查处涉及电子商务假冒专利案件529起。j人民网:《广州多举措加强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维权》,http://gd.people.com.cn/n2/2016/1026/c123932-2920897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3月24日。
从联动机制设立的法律依据来看,2015年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修改了《专利行政执法办法》,新增“专利管理行政部门积极参与电子商务领域的专利权保护,发挥行政执法程序简单、处理快捷的特点优势,适应互联网发展新需求,加强专利权保护”的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5年10月出台的《专利行政执法操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亦设置电子商务专利侵权纠纷调处分为行政处理、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商自行处理和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商提交专利管理工作部门调解或判定三种模式。《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维权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就分别针对明显的、复杂的专利侵权行为与假冒专利行为制定了不同的工作方案,规定明显的侵权行为由平台自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地方知识产权局,而较为复杂的侵权行为,平台可联系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并参照其出具的意见书;投诉人不服处理决定的,由地方知识产权局按一般专利侵权行为程序处理,并通知平台对其认定的侵权行为采取必要措施。(具体程序参见下图1)

图1 专利侵权联动执法程序
(二)联动执法机制中涌现的错误处理问题
虽然联动执法机制在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侵权纠纷处理中具有高效、便捷等优势,但是,在联动执法的过程中,联动机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包括:由于电子商务的跨地域性而带来的管辖问题;具体操作过程中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局处理纠纷的具体时限问题;明显的专利侵权行为由平台采取措施后,将过程及结果报送地方知识产权局,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局是否会介入实质性处理还是仅仅接受材料;平台以何标准从76家知识产权维权中心中选取合适的咨询中心等。
除了上述程序性问题之外,专利侵权联动执法最突出的问题便是基于错误的侵权认定而做出错误的处理措施后的责任承担问题。在专利侵权认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处理的情形。然而,联动执法的特殊问题就在于: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多方参与的情况下,一旦作出错误的侵权认定结果并采取错误的平台治理措施、行政处罚后,如何在多方主体之间合理分配责任承担。
错误处理应当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构成错误处理的前提在于平台内经营者的内容或行为本身未侵犯他人专利权,但该内容或行为因权利人的错误通知或投诉及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维权中心、专利行政执法部门后续的认定而被实际采取了删除商品、断开链接以及行政处罚等措施;(2)错误处理造成被投诉的平台内经营者遭受损害。无论是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关闭店铺等措施,还是专利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通常都会使得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受到损害。(3)被投诉的经营者所遭受的损害与侵权认定具有因果关系,即损害必须是由错误认定而导致的处理措施所引起的。只要满足上述错误处理的构成要件,作出错误处理的有关主体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联动执法机制下的错误处理责任承担分析
(一)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民事责任
对于平台在专利侵权问题上错误处理的责任,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最高院关于人身权的司法解释,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人身权侵权问题上错误处理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其发布的信息被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的网络用户,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收到通知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照该文件起草者的解释,该条实际上是一条免责条款,即免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收到错误通知而错误处理的责任。k杨临萍、姚辉、姜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22-28页。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文并未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问题。按照文义解释,该条意味着,即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错误通知未能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也不需要承担错误处理责任。
有学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有过错,没有对通知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按照错误通知采取错误处理行为,应该与发出错误通知的用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赔偿后,可向错误通知人追偿。l杨立新、李佳伦:《论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及效果》,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6期,第40–44页。本文基本认同该学者观点,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错误处理责任,还是应该考虑其过错问题。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恶意地将不合格的通知判定为合格,并采取措施,其不承担赔偿责任,肯定不合理。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的认定问题。限于文章主题,本文对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在错误处理上的过错认定提出两点意见:
其一,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必须是基于善意(Good faith),而非恶意进行认定并采取必要措施。如果平台为恶意,则显然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善意是指平台是真诚地相信通知成立,并根据通知采取必要措施。如平台明知通知不合格,而判定通知合格,并采取必要措施则为恶意。m对于善意的要求,也有域外法的根据。《美国正当通讯法》230条C(2)规定:“互动式电脑服务提供者或使用者在以下情况下不承担民事责任:(A)采取任何自愿地行动时秉承善意,去限制色情的、淫秽的、令人反感的材料或者它们的提供者进入,无论这些材料是否受到宪法的保护。”该条免除了互动式电脑服务提供者(相当于我国法上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采取阻止非法内容的责任,但免除的条件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善意的。
其二,对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主观过错认定标准,本文主张适用假设的理性人标准。假设的理性人是指对法律或技术不具有专业知识或经验的普通人。nSee Capitol Records, LLC v. Vimeo, LLC, No. 14-1048 (2d Cir. 2016).假设的理性人标准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往往被适用于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用户的侵权行为是否“知道”。如果以理性人标准可以识别用户的侵权行为,则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本文认为该标准可适用于平台对通知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判定上。如果以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为标准,侵权是明显的,应当判定通知成立,并采取必要措施,则意味着平台即使错误处理了,也应认定其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没有过错。
按照联动执法机制,平台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如果侵权较为明显,平台可自行认定侵权并采取删除商品、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如果平台不能自行判定,则交由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判定,平台再根据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判定决定是否采取必要措施。因此,对于平台过错的认定,也应分为以上两种情况考虑。在平台自行判定导致错误处理的情况下,首先应考虑平台是否为善意;其次以假设理性人标准来衡量平台是否有过错,如果平台有过错,则应该承担民事责任。
在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出具错误判定侵权意见,平台根据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意见错误地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由于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在专利侵权判定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平台依照其意见采取必要措施应认定为善意的、没有过失的。因此,平台根据知识产权维权中心意见进行的错误处理,平台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二)专利执法部门的行政责任
对于较为复杂的专利侵权纠纷,如果是专利行政执法部门因收到侵权投诉,作出侵权认定并进行处理,通知平台采取关闭店铺、断开链接、删除商品等措施,专利执法部门同样可能发生错误处理的情形。如果专利行政执法部门的处理决定错误,就会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造成损害,甚至是非常严重的损害。o汪旭东:《专利行政执法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7期,第82-88页。
在此情形下,相对人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p《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46条:“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处罚决定后,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在行政复议或者诉讼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中,申请人可申请行政赔偿。行政赔偿是指“国家对行政主体因行使职权的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害,依法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q杨寅:《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演变与新近发展》,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第107-112页。《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赔偿适用违法原则,但其所指违法包括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r杜仪方:《行政赔偿中的“违法”概念辨析》,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3期,第25-31页。这里主要讨论实体违法的问题。在判断实体违法中,违法认定要件中包含行政机关的合理注意义务,行政机关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就是违法。如果专利行政执法部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就违背了法律的要求。合理的注意义务实质就是认定专利执法部门有无过失。对于合理注意义务的判断,除了审查法律有无明确规定之外,还应结合具体案件的难易程度等情况分析行政机关是否达到合理的注意义务。s陈国栋:《论行政赔偿诉讼中的“违法”》,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8期,第104-112页。例如,涉案专利有无被宣告无效的情况,若专利曾被提起无效宣告就表明涉案专利的稳定性存有问题,若专利执法部门在专利侵权纠纷中因未注意该情况导致错误处理电子商务专利侵权纠纷,则专利执法部门具有过错且违法,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专利行政执法部门的过错除了考虑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问题外,还需要考虑故意的过错。如果专利执法部门是故意错误判定侵权成立并采取处罚措施以及通知平台配合进行处理,其当然构成违法,因而要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专利行政执法部门的赔偿责任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违法原则。同时,在知识产权局先行赔偿损失后,追究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相关行政人员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专利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专利行政执法部门先行赔偿损失后,责令相关责任人员承担全部或部分赔偿费用。对于责任人员的侵害行为是否为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认定,基于主观认定的难度,美国的职务侵权赔偿诉讼中将善意的举证责任配置给有关责任人员,而不需要由受害人证明有关责任人员的侵权行为出于恶意。t吴光升:《论国家赔偿费用追偿程序之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3期,第90-99页。我国可借鉴该举证倒置规则认定行政人员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并根据侵害结果严重情况、过错的大小等情节,作出处理或者处分决定。对于损害和影响重大的过错责任人,由上级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予以通报批评,依情况分别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直至撤职的处分,以及由责任人员承担全部或部分赔偿费用。
(三)知识产权维权中心错误处理的民事责任
关于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在错误处理情形下的民事责任认定,本文建议借鉴鉴定人的民事责任规则。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在联动执法机制中,承担侵权判定职能,通过专利与侵权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并出具侵权认定报告的行为,其要求具备科学性、专业性、中立性,这些特征与司法鉴定的行为具有相似性。同时,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在联动执法中具有辅助作用,其出具的鉴定报告对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具有参考作用,这一功能与鉴定人对司法部门审理案件所实现的功能是相同的。因此,借鉴已有的鉴定人之民事责任规则,认定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在联动行政执法中的民事责任具有合理性。
对于鉴定人的定位,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对抗制诉讼体制下,鉴定人由当事人自主选择,被称为专家证人,u沈健:《比较与借鉴:鉴定人制度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第111-121页。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是指具有专业技术和经历的证人,提供关于该特定领域内关于事实问题的证据。vSee Davie v. Magistrates of Edinburgh 1953 SC 34.专家证人被视为诉讼当事人的助手。当事人与专家证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专家证人应承担的责任应为违约责任。根据专家证人制度规则,在专家证人具有玩忽职守情节、欺骗以及表现低于其职业标准之时,当事人可以起诉追究专家证人的责任。wSee Jones v. Kaney [2011] UKSC 13.同时,对于不具有上述情形的专家证人,美国法院也认为专家证人享有豁免权,认为要确保专家证人不被起诉,确保专家证人必须能够表达其意见的依据,而无需担心对客户不利的裁决而导致的诉讼。xLLMD of Michigan, Inc. v. Jackson-Cross Co., 740 A.2d 186, 191 (Pa. 1999).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将鉴定人视为“法官的助手”,在追究鉴定人的民事责任时以侵权责任为主。德国认为如果法院依据鉴定人的鉴定作出了裁判,而后证明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是错误的,因法院裁判而遭受不利的当事人可以向存在以故意和重大过失的鉴定人请求损害赔偿。y姜志刚:《论司法鉴定人的民事责任》,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3期,第12-16页。
对于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追责原则,本文认为倘若适用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中的违约规则将可能导致受害人所受之权益损害无法填补。平台寻找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出具相关报告之后,平台根据报告决定采取措施,一旦平台内经营者利益受损,可能会直接寻找平台维护其权益。但是,正如前述所言,平台基于对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出具报告的合理信赖而进行错误处理,平台没有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囿于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出具报告是基于其与平台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在平台免于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平台自然没有动力去追究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违约责任。由此将导致平台内经营者利益受损而又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况出现。因此,本文认为对知识产权维权中心民事责任的设计,应该舍弃专家证人的追责规则,而参考鉴定人的民事责任规则来设计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民事责任规则。关于鉴定人错误鉴定的民事责任问题,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适用过错主义原则,并且仅在具有重大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z同注y。
因此对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民事责任规则也应遵守过错主义原则,其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出具错误判定结论,并给平台内经营者造成损失时才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一般过失免责,是考虑到:首先,参考了鉴定人的民事责任规则;其次,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与专利的复杂性,侵权认定过程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一般过失也要承担责任,将极大地增加其风险。最后,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在现阶段还是非营利性的公益机构,其在联动执法机制中的专利侵权判定也未市场化运营,其收取的费用也较少,87这是根据笔者对数个知识产权维权中心调研得出的结论。如果其因为一般过失要承担民事责任,其风险和收益显著失衡,可能使得很多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因为规避风险而退出联动执法机制。
结 语
联动行政执法在电子商务领域内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处理简单的纠纷,专利行政执法部门处理复杂的专利侵权纠纷,让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发挥咨询的辅助作用,推动电子商务领域内多方主体协同共治,高效、便捷、科学地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对于在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处理情况,应遵循“谁行为,谁负责”的原理,由相应的主体承担法律责任。平台在基于对知识产权维权中心侵权判定的信赖导致错误处理的情形下,不承担侵权责任。在平台自行判定而作出错误处理的情况下,平台是否要承担责任,要分析平台在处理过错中是否善意,是否以理性人标准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对行政执法部门的责任,应按照行政法、国家赔偿法等规定,按照违法原则进行责任认定;行政执法人员在其明显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应追究行政责任。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侵权责任认定应适用过错原则,在其对出具错误认定报告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况下,追究维权中心的民事责任。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Patent Infringement Collaboration Enforcement Mechanism in e-commerce, which can remedy the limitation in handling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by the 3rd party e-commerce platform.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Patent Infringement Collaboration Enforcement Mechanism in e-commer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of liability under the fault handling. The platform shall not bear any tort liability in cases where the trust is based on the reliance of the infringement judgment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enter. However, in cases where the platform wrongly processes the same at its own discretion and deal with mistakes, generally, we should analysis that whether the platform has acted in good faith and whether they have reviewed those obligations with rational standards as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do. The responsibility of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related of ficers shall apply the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State Compensation Law.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Center shall not be de fined as expert witness, which shall take tort liability when it makes fault report as an accreditation agency.
patent infringement; E-commerc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of Enforcement
姚志伟,广东金融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沈一萍,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软科学项目“知识产权规则创新与‘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研究——以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专利侵权为中心”(G D I P 2 0 1 6-K 8)。本文的写作同时得到2 0 1 7年广东金融学院创新强校工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