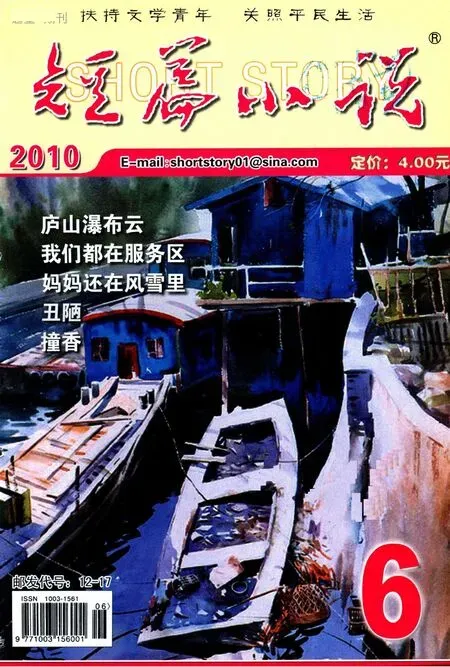又见榆钱白
◎戢建华
又见榆钱白
◎戢建华

郑满堂重回榆树坪的时候,正值四月下黄沙的天气。榆树坪一树树的榆钱已经干白,随着若有若无的风,有气无力地飘零在灰黄的半空中,有些像送葬的纸钱。郑满堂最早这样想时才十来岁。那是比现在稍早些时候,满树的榆钱还含着翠绿的汁液。郑满堂爬在树上,捋一把榆钱嚼在嘴里,硌牙的沙中品咂出一丝沁入牙根的甘甜,又折下一枝扔给树下的梅香。何老财从树下经过时,他们正吃得津津有味。何老财饶有意味地笑:“榆钱也是钱,趁有的时候多享受一下,等过些日子跟你老子的钱一样没了,再想享受也是白想了。”
郑满堂虽小,但还是隐约听出何老财这话中对他老子的不恭。平时他也听到过何老财赢他老子钱和田地的只言片语,于是冲着何老财的背影恨恨地说:“等过些日子,就用这榆钱给你送葬!”声音虽然不大,但还是飘进了何老财的耳朵。何老财停下脚步,回头瞅了一眼郑满堂,随后,目光笑意盈盈地停留在了梅香身上。
但郑满堂还没等到给何老财送葬,却被何老财先给他送了葬。
那是四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父亲郑老棍已经输得要脱裤子时突然良心发现,他给儿子满堂留下四亩水浇地,然后择了良辰吉日给满堂和梅香圆房。这是他这辈子做的第二件有良心的事。然后,他就可以带着他的赌债了无牵挂地走了。
郑老棍做的第一件有良心的事就是在满堂五岁时,从镇上捡回了梅香。当时恰逢郑老棍手气不错,赢了钱带着满堂买糖葫芦,看到墙角衣衫褴褛的梅香冻得缩成一团。郑老棍上前问:“小姑娘,今年几岁了?”
“八岁。”梅香怯怯地回答。一双大眼睛秋水般明净得让人怜惜。
“跟我走吧,我管你吃饱穿暖。”郑老棍脑子里立马蹦出“女大三,抱金砖”的俗语,心里盘算着这姑娘模样不错,干脆捡回去当童养媳算了,也算提早给儿子操了娶媳妇的心,再加上女人走得早,捡一个也算儿女双全。
那天,与婚的宾朋才散尽,满堂和梅香正欲入洞房时,突然一群荷枪实弹的兵丁冲进来。为首的长官手一指满堂,“带走!”然后丢给郑老棍一张收条,上写着“今收到榆树坪郑满堂壮丁壹名”,后面落着镇公所鲜红的大印。
郑老棍一看这情形,连忙揣着一包礼钱硬往当官的口袋里塞,一面苦苦央求:“长官啊,行行好,把人留下吧——”那当官的却坚决把手一推,“前方战事紧,钱再多有什么用?”
几个兵丁冲上来不由分说绑了郑满堂的双手,在郑老棍的哀求和梅香的哭喊中生拉硬拽地把郑满堂抓走了。
郑满堂随着一串壮丁鱼贯而行时,榆树坪的天空正飘着干白的榆钱,连地上的榆钱也随风追着他的脚步。郑满堂长叹一声:“这就算为我送葬吧。”
郑满堂所在的队伍一直奔波在撤退的途中,几乎还没来得及放一枪一弹,突然有一天,长官就宣布率部起义了。于是,一夜间,郑满堂由国军变成了人民解放军。接着,全国就解放了。不久,郑满堂所在的部队又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投入到抗美援朝的战场。
在北朝鲜冰天雪地的战场上,郑满堂第一次见识到了战争骇人的壮观。大炮排山倒海地轰鸣,连大地都吓得颤抖。飞机乌鸦般聒噪不休。枪如林,弹如雨,人其实就苟活在子弹的缝隙之间。终于,在一次穿插中,他们的小分队和南韩士兵发生了遭遇。战斗中,一颗手榴弹在郑满堂不远处爆炸,郑满堂只觉得下腹一热,伸手去捂,血液便从指缝中汩汩而出。
郑满堂被转移到战地医院救治。待他痊愈时,他所在的部队也结束了作战任务奉命准备回国。郑满堂的难言之隐就是在这时候发现的,那段时间经常有朝鲜群众来部队慰问志愿军,有个丰硕的朝鲜女人将花环戴在郑满堂的脖子上,又激动地拥抱郑满堂,久久不愿分开。郑满堂能感受到颈间她潮湿的呼吸和她胸脯剧烈的起伏,能嗅到她身上一股女人的醇香。郑满堂第一次和女人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他觉得下腹升腾起一阵快意的潮热,随即一股液体奔涌而出,湿冷地粘在大腿根部,就像一根没划燃的火柴,嗤地冒了一股激情的烟雾,便沮丧地成了一根干柴棍儿。郑满堂不知道他这病是与生俱来,还是被恐怖的战场吓出来的。总之,这病注定成了他作为男人一辈子无法言说的硬伤。
回国后,郑满堂荣授抗美援朝纪念章,然后光荣退伍,被县里安置为榆树坪供销社主任。
郑满堂穿着军装,胸前挂着纪念章气宇轩昂地走进榆树坪。他要让榆树坪的人知道,他郑满堂还活着,还是作为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又参加抗美援朝的解放军光荣退伍还乡的,而且他还是掌管着整个榆树坪生产生活物资的供销社主任。
在村头的井台上,郑满堂看见一个女人正准备打水,一个齐水桶高的孩子乖乖地立在一旁。郑满堂上前招呼道:“老乡——”那女人回过头来,郑满堂惊呼一声:“梅香!”
郑满堂一路上不止一次地设想过重回榆树坪的情景。他在部队里受过共产党的教育,知道新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社会是不允许赌博的,父亲可能和其他农民一样过着幸福平淡的小日子。新社会提倡婚姻自由,梅香可能因为自己生死不明已经改嫁。新社会是没有剥削的,何老财肯定已被打倒。但他却从未想到过,回来见到的第一个人竟是带着孩子的梅香。
梅香见到穿着军装的郑满堂,惊吓得瞪大了眼睛愣住了。郑满堂问:“梅香,咱爹呢?”梅香突然抱起孩子挑着一担空水桶转身飞快地走了,只留下郑满堂一个人站在井台上半天回不过神来,嘴里喃喃自语:“这井台没变啊——”
这井台郑满堂是再熟悉不过的,榆树坪远远近近的人都在这儿吃水。别家大人打水都是水担钩子钩着木桶很随意地摆一下,桶里水就满了,可自己家吃水是梅香带着自己来抬的,梅香无论怎样学着别人的姿势摆弄,水桶就是固执地浮在水面上。实在没办法,梅香在水桶里放了一个大石头才打起了水。等打上水再把石头捞出来,一桶水就只剩了大半桶。然后,梅香在头自己在尾抬着这大半桶水回家。榆树坪的规矩是过三天年时是不能打水的。有一年初三,家里没了水,梅香就和自己在井台前焚香烧纸敬井龙王,以求得一桶水。路过的乡邻看着两个半大孩子在一起跪拜,打趣道:“这就拜堂了啊。”一句话羞得梅香脸山楂果一样红。
郑满堂推开自家院门,院子里几个晒太阳的人好奇地看着他。有人问:“你找谁?”
“我是郑满堂,我爹呢?”
“你是满堂啊!”院子里的人这才认出了郑满堂,连忙把他拉坐下,继而面露难色,“满堂,你看啊,这房子政府已经分给我们这两家了——”
郑满堂瞬间就明白他已经不是这房子的主人了,“那我爹呢?”
“你爹他——唉,一言难尽啊,这都是何老财造的孽!”
原来郑满堂前脚刚被抓了壮丁,后脚何老财就带人来抢梅香,说是以人抵债。郑老棍气得指着何老财的鼻子咆哮:“我欠你的赌债已经拿田产抵清了,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想强抢不成?”何老财拨开郑老棍的手指,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可以少要你两亩田产,但是我要人,这就是我说了算了。”随即手一挥,就扭走了梅香。一天之内,儿子儿媳尽失,郑老棍气急败坏,急火攻心,一口气没上来一头栽倒在了门槛上。第二天,梅香就被强按着和何老财的傻儿子何大头拜了天地。
何大头是何老财的独子,因是脑瘫,所以头比较大。何老财本不姓何,因入赘到何家才改的何姓,所以虽然没生下个传香火的根儿,何老财也不敢纳妾。
“那跟何大头怎么能生孩子呢?”郑满堂纳闷。
“是啊,跟何大头怎么能生孩子呢?”人们哈哈大笑:“那儿子是何老财的种!”
郑满堂气得一拳砸在自己腿上,“简直是畜生!”
“对!对这样的畜生就应该好好批斗,他老婆被一不小心斗死了,我们要斗得他生不如死。”
榆树坪供销社征用的是何老财的宅子。前任主任已经知道郑满堂要来的消息,还热心地给郑满堂拾掇了宿舍,就是以前何老财的寝屋。郑满堂递上介绍信,和前任主任很快就办完了交接手续,握握手就算走马上任了。
第二天一早,梅香神色慌张地跑来拍郑满堂的门,“满堂,何老财吊死了——”
郑满堂随梅香到了宅子后面的牛圈。何家宅子被政府征用后,何家一家人就被赶到了牛圈里住。牛圈梁上的绳子已被梅香剪断,何老财猥琐地躺在地上,脖子上一道青紫的勒痕。“我昨天告诉他,你回来了。”梅香半晌才说。
“他这是畏罪自杀!”郑满堂气愤填膺,“便宜他了。”
这时,何大头从角落里坐起身,喊:“梅香,我俩来玩抓石子。”
梅香没好气地回道:“就知道抓石子,你爹死了知道不?”
可能梅香是声音太大,床上的孩子一下子哭了起来,梅香立即上前抱起孩子哄,“小满乖,吓着别怕啊。”
郑满堂问:“你儿子叫小满?”
那边,何大头傻呵呵地一笑:“我不和我爹玩,我要和你玩。”说着,将手中握着的石子轻轻一掂,石子便翻入在摊开的手背上,再向上一抛,迅速又一把抓起地上剩余的石子,手再摊开,空中的几枚石子稳稳地落入手中。
何大头抓石子的手艺还是梅香教的。那时他们都还小,何大头由于痴呆,没有人愿意跟他玩。梅香见大头可怜,就教大头玩女孩子抓石子的游戏。谁知道这一教,大头就迷上了。从此以后,身上总是揣着十来枚石子,不管有人没人,兴趣来了随地一坐,一个人就玩得神采飞扬。
在梅香被强迫和何大头拜堂后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梅香觉得浑身怠倦,早早地就躺下睡了。恍惚中,她觉得有什么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下身也胀胀地疼。她努力睁开眼,看见何老财一张破抹布一样的脸。她想奋力推开他,却浑身瘫软。何老财狞笑着说:“榆树坪这么多女子,我哪里花钱买不来一个。知道我为什么偏偏相中你了吗?那是因为你对我家大头好,大头喜欢和你玩。”
梅香痛苦地侧过头,绝望的眼泪漫出来,浸得枕头湿淋淋的一片。
何老财哄着梅香,“你应该笑才对呀,嫁到我何家,你是锦衣玉食,穿金戴银,八辈子修来的福啊!”梅香不言语,只是肆无忌惮地流泪。何老财有些不耐烦地说:“哭,你就哭郑满堂的丧吧!你知道郑满堂怎么被抓的壮丁吗,那是我花钱找的镇公所!”
梅香带着郑满堂来到郑老棍的坟前。郑满堂看到坟头的地上依稀还有纸钱的痕迹,问梅香:“这是你烧的?”
“嗯。”梅香答道,“每年清明我都来。”
郑满堂看墓碑的落款是“孝子郑满堂孝媳梅香立”,说:“谢谢你安葬了我爹。”
梅香看着郑满堂的眼睛,说:“别忘了,他也是我爹。”梅香故意把爹说得很重,“那时兵荒马乱,所有人都以为你一去必死无疑。如今,爹能看到你这样回来,也瞑目了。”
郑满堂不说话。梅香又问:“你知道孩子为什么叫小满吗?”
郑满堂冷冷地问:“他们说那是你跟何老财的儿子,是吗?”
好像经久不愈的伤口又被人撒上一把盐,梅香痛得哭了,“刚生下来时,我也恨不得掐死这个孽种。等孩子满月了,周岁了,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生命是无辜的。其实在我心底,我一直都拿他当你的儿子,所以我给他起名叫小满。你就做他的干爹吧,他今后就叫郑小满。”
在这个没有人的空旷的山野,梅香第一次嚎啕大哭,她哭得畅快淋漓,直至声悲欲绝,几欲瘫痪,郑满堂扶不住,只好抱着梅香以自己的胸膛支撑着梅香的身体。郑满堂第一次看见怀抱中的梅香是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她比记忆中的梅香漂亮了,丰满了。梅香冰凉的泪水和潮热的鼻息浸湿了郑满堂的胸膛,郑满堂感觉有一条肉嘟嘟的虫子在胸前蠕动,一阵欲醉欲仙的酥痒,下身又觉得一股黏湿。郑满堂知道他今生注定将不会有自己的骨血,但要他接纳仇人的儿子,他还做不到。
天才黑不久,郑满堂还没躺下,忽听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窗户纸也映着火把跳跃的红晕。有声音喊:“郑满堂,你出来!”郑满堂开了门,见门外站着十来个人,打着两个火把,站在头前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后生指着郑满堂厉声说:“地主何老财已经自绝于人民,谁都知道,过去榆树坪除了何家就数你们郑家还有几亩水浇地,按成分,你应该是富农,我们今晚要开富农的批斗会,你跟我们到打谷场去!”
郑满堂说:“那等我穿件衣服吧。”转身又进了屋。等郑满堂再出来时,已经穿上了一套军装。军装胸前抗美援朝纪念章上的毛主席浮雕在火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耀得人心畏。郑满堂手里提着一把军刺,高声说:“我郑满堂目前一无房,二无地,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我解放前参加人民解放军,又参加志愿军。我是组织上任命的革命干部,你们今晚有谁胆敢上前一步,我就捅了他个反革命!”郑满堂声色俱厉,一伙人吓得都不敢吭声。
有人提议:“那我们把那个地主婆揪去批斗吧。”
“好。”这个提议立即有人符合,于是人们扭头准备往牛圈的方向走。
见他们要去揪斗梅香,郑满堂大喊一声:“慢!”上前几步,手中刺刀一扬拦住去路,说:“梅香解放前就是我媳妇,是被地主何老财霸占去的,这在榆树坪众所皆知。她是榆树坪广大劳苦大众中最苦的人啊,你们怎么忍心去批斗她。今后,谁若欺负梅香母子,谁就别想在我这儿买到一针一线,一根火柴也甭想!”
人群中有个岁数大的喝斥那个领头的后生:“你个二愣子,还傻站着干什么,等你爹妈来请你回去啊?”
后生耷拉着脑袋小声说:“我是说请梅香去批斗会上诉苦呢。”然后,一伙人讪讪地走了。
郑满堂拎着一小包糖果去牛圈看梅香。门前,小满抱着一个比头还大的木碗在喝稀饭。郑满堂看见碗里照得见人影的米汤泛着一层浅绿。小满吸一口,依稀露出半碗榆钱和些许米粒。
见是郑满堂来,梅香连忙出来招呼:“满堂来了,稀客。”
“跟我还客气什么。”郑满堂把糖包递给梅香,说:“你给小满做的榆钱饭咋能这么稀,孩子需要营养呢。”忽又想到,“榆钱不都落了吗,你在哪儿捋的青榆钱?”
“唉,”梅香叹口气,说:“你看三个人的口粮就靠我一个劳力挣,哪能够吃嘛。这榆钱还是我跑到八里外的阴坡上捋的。”
郑满堂想了想说:“以后有啥困难找我,别太苦了自己。”
郑满堂当下就提了两瓶酒去了趟区里。第二天一大早,郑满堂来找梅香,说:“你给大头收拾收拾,把他送到区福利院去,我跟院长说好了。福利院里包吃包住,挺适合大头的。”
梅香送完大头,又在区里买了几个菜,回来已是郑满堂下班时候。梅香抢进郑满堂的厨房做饭烧菜,郑满堂只好坐在桌子边静静地看。梅香端上菜,又倒上酒,对着郑满堂一笑:“吃吧。”郑满堂不禁想到,当年也是梅香做饭,饿了的满堂在灶台边眼巴巴地望着,对着锅几欲下手,梅香也是这样回眸一笑。那时,他们是一家人,而现在,多么像一家人。
满堂说:“以后,你们娘儿俩的吃穿用我管了,反正我的工资一个人也花不完。”
梅香也不推辞,“那行,反正孩子也随你姓。”
郑满堂要睡时,梅香却也不走,径直来到寝屋,坐在郑满堂的床边,一双眼睛秋水样望着郑满堂。那是郑满堂既渴望又害怕的目光,郑满堂闭上眼睛,说:“小满在呢。”
梅香说:“放心,小满睡了。”一只手顺着郑满堂的胸膛轻轻地滑下去,但她还没握住那股渴望的灼热,手心便一片精湿。梅香心疼地问:“满堂,你怎么了,是在战场上?”
满堂沮丧地侧过头,眼里荡漾着一片水雾。
梅香一把将郑满堂揽在胸前,说:“满堂,你养我们娘儿俩,我们娘儿俩也要照顾你一辈子,我们是一家人。”
在郑小满三十岁时,梅香惊奇地发现世道逐渐变了。农村没有批斗会了,农民也可以自由做买卖了。再经郑满堂确认,国家政策确实放开后,梅香鼓励郑小满去城里经商,郑满堂还拿出攒的两百块钱给小满做本钱。
郑小满的生意在两三年间越做越大。据了解郑小满的人说,郑老板生意上的成功在于他天资聪明,头脑灵活,但主要得益于他资本雄厚。关于郑小满雄厚资本的来源,只有梅香知道。那还是郑满堂退伍回榆树坪在井台上遇到梅香那天,梅香当时慌忙回去将消息告诉了何老财。何老财自知郑满堂不会放过自己,于是告诉梅香,说世道乱时,自己在寝屋东南角的砖下藏了五根金条,以备日后不测,谁知还顾不得转移,家就被抄了,连房子也被没收了。何老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恳求梅香,“你要寻机会查看一下,择时机挖出来留给你的儿子。”梅香住进郑满堂的寝屋后,仔细查看了那块地砖,发现那块砖没有动过的痕迹,知道金条还在。但她不敢把秘密告诉郑满堂,她怕郑满堂会把这些金条交给政府,倘若那样,她和郑满堂的一辈子都被葬送了,苦也白受了。终于,梅香在确认她挖金条和郑小满用金条都安全时,悄悄地挖出了金条交给了郑小满作为本钱。
在郑满堂六十大寿时,郑小满特地从省城请画家画了一幅中堂,画的是一株凌寒绽放的腊梅,题为“满堂梅香”。郑小满当着郑满堂、梅香和满堂宾朋的面亲自将画挂上。酒宴上,郑小满举杯念叨着父母半世的辛苦,说了一些感恩的话,最后大声说,“为我爹妈晚年幸福干杯!”郑满堂跟梅香一脸幸福地碰杯,说:“小满这是长大成人了啊。”梅香笑容中透着一丝不屑,说:“他这人———是跟着好人做好人呢!“郑满堂举着杯思忖良久,忽然发现郑小满笑意盈盈的脸上竟隐着一丝熟悉的狡黠,像——郑满堂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了记忆深处的何老财。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