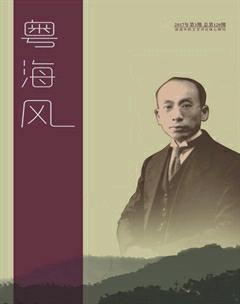回到原初:找寻杂技的自由和梦境
黄介农+牛寒婷
牛寒婷(以下简称牛):介农老师,您好。很高兴能跟您一起聊聊杂技。您是研究杂技方面的专家,是《当代中国杂技》的撰稿人之一,并曾经长期受聘于中国杂技团、上海市杂技协会、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在工作中,您也一直在密切关注杂技艺术事业和杂技产业的发展。关于中国杂技,您能否先大致地介绍一下它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黄介农(以下简称黄):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结合自己二十多年来对杂技艺术的观察和思考做一次梳理。关于中国杂技的发展现状,主要有业务建设和艺术发展两个方面,而我在这里谈的,主要是侧重艺术发展方面。面对社会的迅速发展,就杂技而言,很多老的问题还没解决,更多新的问题就接连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明显,但其实质却很难把握。大家普遍对此感到困惑,这也许会成为我们今天对话的一个难点。
当代中国杂技的起点是1950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新中国文化部在北京组建了现在中国杂技团的前身中华杂技团。中华杂技团成立不久,全国很多杂技艺人云集的大城市,如西安、上海、重庆、武汉以及一些部委、部队,就都按照中国杂技团的模式,建立起了第一批国家经营的杂技团。到上世纪60年代,全国除少数省份和省会城市外,普遍都组建了杂技团。我在参与《当代中国杂技》的写作和几个国家杂技院团团史的写作中了解到,国家杂技院团的发展具有较鲜明的共性。
上世纪50年代,杂技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文艺样式,形成了一种以传达革命乐观主义为基调,以表现革命激情为情感内涵,和以表现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为基本主题意义的现代表演艺术,确立了以舞台表演为基本样式的当代中国杂技形式。同时,随着国有杂技院团的业务发展,从团带班到各地文艺学校杂技班,再到建立一批专业的杂技学校,建立起了中等专业的杂技教育体系。
在艺术发展方面,杂技则经历了一些曲折和漫长的摸索期。上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一批舞蹈界人士进入和参与杂技创作,杂技界提出了“高、精、尖、新、难、奇、美”的创新理念,随后在80年代提出了“新是前提,难是核心,美是归宿”的理论概括。然而,最大的、最深刻的发展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得杂技界与国外广泛交流,为杂技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和外在的强大动力。虽然业内总有“全国杂技一台戏”的批评的声音,但事实上,全国杂技发展已经走上了多样化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
从演出内容和形式来看,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杂技演出的主流样式是综艺晚会。其间,前期晚会中通常会有杂技、魔术、滑稽等节目,不少团的晚会中还有口技、相声。但到后期,则基本上只剩下了杂技。90年代中期以后,杂技演出的主流样式是主题晚会。2005年前后,全国各地杂技团开始纷纷推出杂技剧,也就是说杂技开始了剧目化的发展。不过,以我的观察和了解,剧目化的杂技实质上与主题晚会的杂技区别不大,除少数剧目取得成功外,多数剧目作为剧则显得牵强,总体上处在一个探索杂技艺术发展的阶段。少数剧目,比如武汉杂技团的《海盗!海盗!》是根据国外订单打造;大多数是对取得成功剧目的跟风。这也与政策引导有关,比如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评选,参选的必须是剧目等。目前已有遵义、战士杂技团、上海杂技团、广州、新疆等五台剧目入选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目。这些信息都表明,这个时期杂技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杂技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正如文化部一位领导所说,我们的杂技发展总体上“国际竞争力不强,国际演出还处于低价、低端层面”,“由于种种原因,中國尚未发展成为世界杂技艺术强国。”
牛:谢谢您把当代中国杂技发展的各方面情况做了一个简要介绍,使我们对杂技有了一些认识和了解。正像您刚刚说的,杂技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院团的组建和国家对杂技艺术的扶持,开始进入剧场、走上了舞台表演艺术的发展阶段。但我们都知道,杂技最初在民间产生时,多是“撂地儿”的形式,或在围棚中进行表演,也就是说,杂技最初是一种远离剧场和舞台的“广场艺术”。从民间形式和“广场艺术”到舞台晚会,您认为,杂技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得与失?杂技在失去了广场艺术的质朴之后,在“剧场化”之后,存在哪些问题?杂技的观念是否也在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黄:杂技进入剧场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好的方面主要是一些传统节目得到了几代人的锤炼,比如“顶碗”、“空竹”、“单手倒立”等节目,还有大家习惯称之为肩上芭蕾的创新节目“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等。由于舞台综合艺术手段的运用,这些节目精雕细刻,已经被打造成为当代杂技的经典。在目前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我们的优势也在这里,这些节目在国际赛场上光彩夺目。
但是,问题也在这里,我们的主要着眼点往往都在单个节目方面,这方面的成就似乎一直在鼓励这种发展路子,这样的单向发展,按大家所熟知的类似理论都知道,路子只会越走越窄。事实上目前我国杂技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被一些人称为“出口零部件”。也就是说,我们的单个节目优势较大,能为国外的品牌晚会提供精品节目,而整场晚会绝大多数影响不大,少有自己的晚会品牌。问题是很多业内人士对此似乎还有些满足,一直在以较大的热情发展单个节目,这样一来,对杂技整体的发展就更不利了。
在向舞台艺术发展的过程中,杂技的个性特征越来越不鲜明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非常具有惊险性和震撼力的高空类节目如飞人、秋千等,包括在国外长期受到欢迎的长春市杂技团原创节目《高空高低钢丝》这样的当代经典节目,都由于舞台限制无法进一步发展,一些大型节目如“大跳板”也迅速萎缩。长期发展下来,杂技本来粗犷豪放的特性也慢慢变成袖珍细腻了。杂技正在慢慢失去自己的个性特点而与舞蹈趋同。
有趣的是,舞蹈界的人在研究舞蹈的发展趋势时指出,舞蹈界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生活元素时,常找不到自己的语汇而一味地以“炫技”来弥补,正在“杂技化”。如果说,这意味着杂技和舞蹈在“同质化”,那么也就可以说,是舞蹈和杂技两方面都存在创作力不足的问题了。
特别重要的是,50年前最初的舞台杂技也好,国内曾经有过的马戏大篷演出也好,国外的马戏也好,小丑、滑稽表演都是演出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核心元素。而我们,在这方面,现在几乎全部丢失了,基本上没有了小丑和滑稽表演。杂技越来越成为了一种“高雅艺术”。
牛:您描述了杂技观念上不易被人察觉的某种变化。在杂技剧场化、舞台化的背后,是杂技的高雅化;而杂技的质朴和原初的生命力,那种惊心动魄的在场感和感染力,还有您说的“惊险性和震撼力”,则越来越消失不见了。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看杂技的一个经历,那时我大概三四岁,在沈阳北陵公园的一个空场上,看“飞车走壁”,当时兴奋、惊叹又害怕、刺激的感觉,让我记忆犹新,我还记得自己紧张得满头大汗。现在想来,那就像是一股召唤的力量,一种梦境般的自由,一种像鸟儿一样飞翔的渴望深深地抓住了我。
如果说,杂技的本质脱离不开广场艺术的粗犷豪放、感染力和震撼力,甚至需要带来一种互动,去激发生命内在的激情和活力的话,那么,杂技舞台表演的“袖珍细腻”,甚至是高雅化,就意味着杂技失去了自身的一部分生命特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杂技的根本。
现在我们看杂技时,也许与看一场戏剧、一台舞蹈、一场音乐会、一台晚会的感受越来越接近,正像您介绍的舞蹈界的情况。尤其是杂技现在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一方面,市场的需求推动了杂技的创作,但另一方面,市场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舞台效果上一味追求高科技、现代科技手段的大量运用等,越来越远离杂技艺术的本体。几乎所有的舞台艺术都受到“技术至上”的影响,戏剧、舞蹈莫不如此。
黄:您说到了一个杂技界有些高层人士正在关注和忧虑的一个现象,我把您的话转译成“过度包装”。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并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地区部门或单位领导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与一种创作意念的冲动,或对市场信息的判断等方面有关联。我想,在当前这个社会普遍浮躁的阶段,在院团转企、改制的初期,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初期,也许这都是艺术发展不得不经历的过程。只是,如果多一些理性少走一些弯路,情形也许就会好很多了。
牛:如果说,当下杂技艺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么我们势必要进行反思,反思的途径之一,也许就是回到杂技艺术的原初。杂技这种艺术形式,在产生之初,是要带给人轻松和愉悦的,就如同其他艺术也具备这个功能。但在杂技舞台化以后,尤其是1950年国家杂技院团建立之后,杂技成为代表国家形象的重要艺术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杂技也开始渐渐承载一些重大的主题,在主题内容和表演形式上,杂技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远离娱乐性和大众的接受,缺少与观众的互动,成为仪式化、高雅化的艺术形式。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您说到的情形很对。全国各地的杂技团长期以来都承担着大量的出国演出任务。30年前绝大多数出国演出都是非商业性的访问演出。一直到现在,一些大团,一些经典节目,经常随党和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代表团出访。代表国家形象一直是杂技界很自觉的一个自我定位。这本身是好事,但问题是,今天文化产业获得很大发展,大多数院团已经完成了转企改制,就要真正把关注点转移到市场上了。您提到娱乐性、与观众的互动、大众的接受,是的,从国际竞争的视野看,这都是外国马戏和成功的杂技所不可或缺的。这显然是振兴当代杂技的重要途径。
您说回到原初,这是个很诱人的话题。我理解您是在扩展和深化访谈,非常感谢您使我有机会提到下面的几句话。——如果杂技发展到引进“回到原初”概念这样的阶段,那杂技就可以成为自由翱翔于天际的雄鹰了,因为进行理念的思考和选择可以表明是理论上的成熟,而杂技界其实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艺术理念的历程。要“回到原初”,就意味着要了解和认识“陌生化”这一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和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所提出的“间离效果”,就要去熟悉现代表现主义的理念以及实践成果。其实,整个国际现代艺术的发展就很得益于这些理论的发展和表现主义在表演艺术中的实践。杂技如果真的能回到原初——显然是更高阶段的回归——那简直是在轻松地做一件自己熟悉而观众将会感到惊喜万分的事情,我稍稍设想一下就感到十分兴奋:恢宏的大篷里,五光十色、迷离变幻的灯光下,四面观众簇拥着一个奇迹、一个梦幻。高空、地面、水中,惊险的、灵巧的、奔放的、幽默的,掌声、笑声、惊叹、呼喊,台上台下激情洋溢的互动,观众兴致盎然地参与……但是,这该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在这里很难再展开。回到原初,除了需要“软”性的观念上的改变外,还需要“硬”性的基础条件。现在,上海有马戏城、武汉有马戏厅、郑州有个不大的马戏厅,以及前面提到的番禺大马戏的马戏大篷,即将投入使用的有重庆马戏厅,除此以外,各地能发展大篷杂技的,就很有限了。我本人寄希望于国家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逐步加大投入,逐步关心到这一块的建设。
牛:您设想的杂技大篷表演让人神往。在杂技整体的发展上,国外的马戏艺术是一种参照,也是一种借鉴。您在各种会议上,也多次提到国外的马戏,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国外马戏艺术的发展和特色?另外,在命名上,国外的杂技实际上就是指马戏,是吗?
黄:我国的杂技主要以地面杂技为主,另外也有高空节目、滑稽、魔术等,但地面节目是主要节目形式。国外的马戏是以高空节目、动物表演节目、人和动物一起表演的节目为主,但也有地面节目,特别是必不可少的小丑滑稽表演。在长期的国际文化交往中,特别明显的是,在所有的国际杂技节赛场上,我国的杂技和国外的马戏从来就是在同一个赛场上,我国杂技的国际竞争对手和交流的对象从来就是马戏。这是同一种艺术形式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以不同特点呈现,是同一种艺术在国际上被不同的指称而已,现在说国外的杂技就是指马戏,这已经是共识了。
对目前的杂技发展的认识绝对不能不谈国外马戏。就我实际了解的情况和相关的统计资料都表明,目前我国杂技的主要市场在国外。即使是国内演出,观众主要也是国外游客。除了上海、北京、济南、桂林等少数地方,近年来还有新疆,全国大多数国有杂技团除了出国演出,在国内演出很少。当前说的最多的是发展文化产业以及提倡文化走出去。杂技大规模走出去的时间已经有快40年了,我们现在应该对国外马戏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与国外马戏的发展相比,我们的杂技基本上完全没有产业规模,也不熟悉产业管理和運作。抛开管理层面的问题,我们看到,国外马戏往往具有气势恢宏、场面热烈、感染力极强这样的特点。不说国外吧,就是国内目前具备规模的马戏——广州番禺“国际大马戏”也具备了这些特点。这个只发展了十年的民营马戏团,目前的发展很有声势,在一个拥有八千座席的大篷里演出,每天平均上座居然率达到8成。
牛:在中国杂技界,向来有技巧和艺术之争。中国杂技艺术的主要特征也是以技巧取胜,这在国际上也获得公认。中国的杂技节目获奖往往是因技巧获奖,而不是因为艺术性而获奖。这其实涉及杂技的观念和理念。您能否介绍一下国外和国内杂技界在杂技观念上的异同?以及这种观念的差异所导致的杂技发展的不同特点。在杂技的技巧和艺术的问题上,您持什么样的观点?国外杂技的艺术性都是如何体现的?
黄:这个问题也许不容易取得共识。我一直认为,杂技的技巧就是艺术,因为在杂技中,技巧既是它的目的,又是它的手段,既是它的形式,又是它的内容。对这样的认识我感到有信心的是,舞蹈界评论家苏祖谦在《小议舞蹈和“技巧”》一文中有过同样的论述。中国杂技以技巧取胜是国际同行的共同认识。这句话接下来的或者说对应的,不是“因为艺术性而获奖”,而是,我们在国际上主要以单个节目的优势见长,能在国际比赛中拿奖很多,因为国际比赛的参赛都是以节目为单元的。但是,在做成品牌方面我们成功的案例还极少,在整场晚会上不具备优势。
其实,您说的国外杂技艺术性强,我的看法是,不如说是娱乐性强。如果进一步具体认识国外马戏的特点,我在别的文章中曾写过,应该了解国外马戏团打造晚会的理念。比如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对其《飞越之旅》晚会是这样介绍的:“这里没有束缚,空中飞人、呼拉圈、大力士、洋娃娃、滑稽的小丑,这是一个充满了奇思妙想的世界。这里没有束缚、没有悲伤、没有不平等,大家和睦相处,逍遥自在。昔日威严的国王变成了平凡和蔼的小丑,我们一起返老还童,在这马戏团的帐篷里,每一个快乐的你就是自己的国王。”太阳马戏团导演Franco Dragone还说:“我们不打算力挽狂澜,也无力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在人间的温情中重拾神奇的信念。真正的雄心壮志不是去征服太空,而是伸手去为邻居抹掉脸上的泪珠。”
不应该把这些话简单地看作是宣传标榜的口号或是商业炒作,其实这种追求正是国际马戏长期以来形成并坚持的传统风格,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以来一些文化名人的感受印证以上宣示。高尔基说:“我不十分清楚杂技究竟是什么,但当我看到杂技艺人为了观众的欢欣,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求美的时刻,我想我已经完全清楚了。”海明威说过:“据我所知,当人们观看演出时,只有杂技才能被称为‘幸福之梦。杂技如同梦境,‘飞人飞来飞去,‘飞人抓住‘飞人,就像你被一个美丽的梦抓住一样。”约翰·斯坦培克说:“杂技变幻着生活的节奏,变日常的丑恶为美丽,烦恼为激动欢欣……所有从杂技场里走出来的男女老少,都变得重新充满活力,乐于继续生存。”亨利·米勒说:“杂技演员是自由的精灵。他们心中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不同。他们充实地生存在瞬间,他们放射出的光芒,是一首清澈的欢乐之光。”E·E·卡明斯说:“如果议会通过一项议案,强迫美国的所有成年居民一年至少看两次杂技……全国五分之四的医院、监狱和精神病院就要关门,而成千上万的精神病学家也要面临失业之灾。”
在这些话语中,欢欣、快乐、活力、幸福、自由是最突出的字眼。“马戏面前,我们都是孩子”。马戏总是创造一个把观众带进童话、带回童年的王国,选择的是走进观众内心,体现了一种很朴实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结合象征和荒诞的手法,通过抽象、变形和面具的运用,通过时空的错杂变幻、声光的迷离恍惚,以表现主义的手法使人的内在活力和激情在马戏表演中尽情张扬,感染观众。
牛:您讲的这些把我带入了一个杂技的梦境,一种如同其他艺术带来的同样的审美享受,就像阅读一首诗、一本小说,观看一场戏剧、一部电影,欣赏一场音乐会。我想,这是艺术才能够带给我们的“魔法”,也是我们在庸常、卑微的现实和人生中不断需要艺术、敬畏艺术、渴望回到艺术的理由。所谓回到杂技的原初,就我的理解,是回到这样一种艺术能够带给我们的原初的本真的体验中——通过杂技表演中高妙的技巧、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手法以及极强的形式感和冲击力,通过杂技对幻觉和梦境的制造,我们感受到最为朴实动人的愉悦、惊异、刺激和欣喜,返回生命最单纯、质朴的情绪体验中,感受被激发的生命活力和热情,我们也重新发现自身的生命能量。最终,我们抵达一种梦幻与自由的境界,超越了周遭的生活,也超越了生命和世界的有限。
黄:您说的太对了,原初的本真的体验!您不仅仅是提出问题,而且是指明了出路。我想要补充的只是,对杂技的定位需要冷静客观。就像杂技当初走进剧场,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是一种身份上的被认可。在很长的时间里,杂技并没有明确被认为是一种艺术;杂技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是以争得“艺术”两个字所代表的身份和地位为荣的。而置身于产业大潮的环境中,杂技又重新自我定位为娱乐产品样式,要接受观众广泛的参与,不再去要求观众正襟危坐、认真观赏——在历史上杂技就是那样在百姓身边的。我想,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回到原初”。但是,显然,杂技界还没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牛:魔术在当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近景魔术的表演,因为能够与观众进行一定的互动,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它。魔术的这种流行,或者说这种与观者的互动,是否可以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杂技晚会化、剧场化的弊端?这是否可以让杂技界有所反思,当下杂技发展所出现的问题?提到魔术,不能不提国际上著名的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作为普通观众,我们很难不被大卫制造的魔术梦境所吸引。大卫的魔术证明,魔术或杂技可以是一种制造梦幻的艺术,杂技是一种梦境。这也是杂技作为一门艺术的重要属性。从这个视角反观我们自己的杂技,中国杂技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黄:我国的传统魔术在国际上一直很有地位,影响很大。但是,国外迅速发展起来的近景魔术,其数量和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大型魔术方面,我们和国际水平的差距更大。过去,在我国的杂技晚会中,魔术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实那时候魔术的地位就开始被削弱了,因为在各地杂技团里,即使有魔术,也是作为一道配菜,处在附属的地位。到上世纪90年代主题晚会热以后,就基本上不再有魔术的地位了,因为它往往融不进主题。这也是对你前面提到的杂技舞台化带来的不利方面的一个补充。从国际演艺界的发展来看,魔术一直是独立于马戏之外的独树一帜的娱乐演出样式。从国内目前情况看,以后想把魔术和杂技紧密地捏在一起,也不大可能了。魔术作为杂技的一个同伴,尽管目前还势单力薄,但已经不再是杂技的附属,在艺术发展道路上独立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并且不可逆转。倒是小丑和滑稽,其實三四十年前在杂技舞台上一直是存在的,虽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却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特征,比如形成了单场滑稽、帮场滑稽和窜场滑稽的明晰分类,在全国范围还能够拉起一支队伍,但现在,基本上全没有了。
牛:介农老师,谢谢您接受采访,很高兴与您一同走过了一个畅想杂技自由与梦境的心灵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