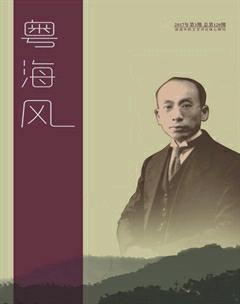从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到胡适《你莫忘记》
魏邦良
陈独秀在《字义类例》的自序中曾说“近代学问重在分析”,所谓分析,就是独立思考,而陈独秀无论是做学问还是进行革命工作,总是坚持独立思考。陈独秀的非凡见解,特立独行,就源自独立思考。
孙中山开始革命时,把革命视为“排满”的种族斗争,革命的目标即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谁革命还是不革命,就看他是否认同“排满”。
陈独秀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安徽俗话报》上撰文,声称清朝皇帝是中国的皇帝,清政府是中国的政府。对于“亡国”,他的看法如下:
“这国原来是一国人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这国里无论是哪个做皇帝,只要是本国的人,于国并无损坏。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字与朝廷分别,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为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可称做‘换代,不可称做‘亡国。必定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
在“驱除鞑虏”口号沸反盈天之际,说清朝皇帝仍是中国人,清朝倒台并非亡国,当然冒着很大的风险。但陈独秀却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我口说我心”。
陈独秀早年也曾参与过对清政府官员的暗杀活动,但很快,他认识到这种活动不明智不妥当不科学,在《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一文中,他写道:
“进行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的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勤于学习,勇于思考,才会有这样的真知灼见。
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陈独秀的认识也颇为深刻。他认为,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不少,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放松了帝国主义侵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
陈独秀的分析,点出了辛亥革命的症结所在。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而陈独秀却提醒我们,国民性的不好也是中国衰亡的主因之一。在其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曾发表了一首《醉东江——愤时俗也》:
“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耐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
这首《醉东江》,把“家鬼”视为中国衰亡的罪魁祸首。而陈独秀说得更具体,他说,中国衰亡的根本原因,“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力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也不是土匪作乱,依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
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陈独秀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
针对当时国人的自私、愚昧、麻木,陈独秀撰写《亡国的原因》予以抨击。在文中,陈独秀批评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做官的,只知道捞钱;普通百姓,各保身家,而且“越是有钱的世家,越发只知道保守家产,越发不关心国事”。陈独秀告诫国人:“列位呀!要知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国若大乱,家何能保呢!”
显然,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批评了国人缺乏“国家意识”,呼吁国人要爱国。然而,不久,袁世凯上台后,陈独秀在给章士钊的信里则感慨:“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
这一方面反映了陈独秀对袁世凯政府的极度失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对“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新也更深的思考。
1914年9月,陈独秀在给章士钊小说《双枰记》所写的序言中,曾这样剖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
“對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动。”
陈独秀还特别撰写《爱国心与自觉心》阐明为何在袁世凯的黑暗统治下,人民不特可以不爱国,甚至还可以期待列强瓜分。
陈独秀在文中告诉我们,“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而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
陈独秀认为,在近代欧美,国家保障了人民各种“载在宪章”的权利,而东方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如此一来,“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
陈独秀认为,既然明白了国家的涵义,“则谓吾华人无爱国心也可”,为何?因为“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陈独秀说,我国自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祚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
由此,陈独秀得出结论:“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而且,陈独秀还断言,倘若我们不理解国家为何物,盲目去爱,则“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
最后,陈独秀指出,若“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则“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那么,人民对国家的态度则是:“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
毋庸讳言,陈独秀发表于《甲寅》1卷4号的这篇《爱国心与自觉心》不乏惊世骇俗之论。诚如当时的一位作者所说的那样:“(此文)好像一颗炸弹放在甲寅杂志中间,震动了全国论坛。”杂志主编还陆续收到十几封信,叱骂陈文:“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不过,这些信只对陈独秀进行谩骂、攻击,却没有对陈文予以有理有力的反驳。后来《甲寅》发表了两篇回应陈独秀的文章,一篇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一篇是梁启超的《痛定罪言》。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是出于“厌世”,出于对袁世凯政府的黑暗腐败才写了这篇言辞偏激之文。他批评陈独秀说:“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李大钊的文章四平八稳,但不过是老生常谈。显然,他并未认识到陈独秀文中的“片面的深刻”。
梁启超《痛定罪言》则几乎完全认同了陈独秀的看法。
梁启超在文中说,虽然目前的中国仍然是中国人之国,未尝受统治于他国,然而国人却不能享有参政权,国人的生命财产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甚至不能安居乐业,不能接受起码的教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反问:“吾不知有国之优于无国者果何在也?”
梁启超还以他家乡为例,说明当时社会官僚腐败,百姓困苦到了“殆不复知人间何世”的地步。“民之黠者、悍者,则或钻研以求为官吏、军士,或相率投于盗贼,而还以荼毒煎迫他人;其驯善朴愿者,无力远举斯已耳,稍能自拔,则咸窃窃然曰:逝将去汝,适彼乐郊。香港、澳门、青岛乃至各通商口岸,所以共趋之如水就壑者,夫岂真乐不思蜀,救死而已。”梁启超说:“夫人至救死犹恐不赡,而欲责以爱国,为道其安能致?”
梁启超在文中,还特别警告政府,千万不能利用人民的爱国心,“术取其财与力”,“以图一时之小补而不复顾其后”。如果政府这么做,那么后果是:“则其所斫丧者,将永劫而不能复。”
梁启超虽然认同了陈独秀的惊世骇俗之论,但他在文中却为政府开脱。认为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我辈士大夫”:“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命,然后国事始有所寄,然后可以语于事之得失与其缓急先后之序,然后可以宁于内而谋御于外。”
梁启超看出了问题的症结,但又不想得罪政府,于是,以唾面自干而又含糊其辞的方式,把矛头指向一个含混模糊的“吾辈士大夫”,这显示了他的软弱与妥协。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五年后,《新青年》第5卷第3号发表了胡适的一首诗《你莫忘记》。这首诗的观点与陈文几乎一脉相承:
“(此稿作于六月二十八日。当时觉得这诗不值得存稿,所以没有修改它。前天读《太平洋中劫余生》的通信,竟与此稿如出一口。故又把已丢了的修改了一遍,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指正——适)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是谁砍掉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
火就要烧到这里——
你跑罢,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
总该不至——如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首诗看成胡适的偏激之词,也不能粗暴地指责胡适在这里宣传“亡国”。
其实,从这首诗的背后,我们可探寻胡适对“爱国主义”的思考,以及他关于“爱国”的矛盾心态。
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908至1909年他在《竞业旬报》发表的四篇《白话》:《爱国》《独立》《苟且》《名誉》证明了这一点。
他在这些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观念,那就是,爱国是所有美德之本:“在家的时候,便要做一个大孝子;在一村,便要做一村的表率;在一国,便要做一个大爱国者。”
他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不少爱国格言,比如荷马的“为祖国而战者,最高尚之事业。”
胡适在那阶段曾写过一篇《讀书札记(一)·读<爱国二童子传>》,把《爱国二童子传》这部“极好极有益处”的小说中的格言译出,如:
“美成洛将死,乃张目作凄恋,颇闻微息作声,大类微风之吹入,颇辨析为‘法国二字。(你看人家到死,尚不肯忘记国家,我们呢?)”
他还撰文《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盛赞她的为国捐躯,并呼吁中国“快些多出几个贞德,几十个贞德,几千百个贞德”。
然而,赴美国留学后,特别是他当选1913年度康奈尔“世界学生会”会长后,胡适开始倾心世界主义。从他的日记,我们可看出,他试图把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融为一体:
“……。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故吾之世界观念之界说曰:‘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顷读邓耐生诗,有句云: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深喜其言与吾暗合。故识之。”
但胡适很快发现,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很难调和。
1914年美国与墨西哥发生冲突。胡适所居住的绮色佳开始流传一句话:“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这句话的实质就是:但论国界,不论是非。这句话在报上刊载多日,无人置辩。胡适对此有所感触,撰文投稿,但报社却不敢登,后在报社某女士的坚持下,报社才将胡适此文,以摘要的方式发表在新闻栏。
胡适在文中指出,人们之所以认同“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是因为有两个道德标准,但这显然是错的。因为:“人人都不反对万事皆有一个对错及正义与否的标准,至少文明国应如此”。然而,一旦涉及国际间事,人们会放弃那个对错和正义与否之标准,宣称“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由此,胡适得出结论:很多人奉行道德的双重标准:“其一用之于国人,另一用之于他国,或‘化外之民。”在胡适看来,这显然是错的:“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否则无法争论此事。”
1914年7月22日,胡适在演说《大同主义》时再次批评了“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 )这句话,认为,这句话的错误在于看问题“但论国界不辨是非”。一位夫人告诉胡适,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应该理解为:“無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胡适承认:“此意已足匡余之不逮。”所谓“不逮”,也就是胡适没有充分考虑一个国民对国家的爱,而是纯粹从学理、逻辑上去思考这一问题。
另有一位教授(M.W.Sampson)也对胡适解释,这句话“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本意应该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这位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兄弟俩外出,弟弟醉了侮辱他人,受辱者拔剑回击,那么哥哥应该保护弟弟,还是置之不顾,抑或帮助受辱者殴打其弟?教授的结论是:“其人诚知其弟之非,而骨肉之义不得不护之,宁俟其酒醒乃责其罪耳。”对于欧洲人纷纷弃欧投美,这位教授的看法是:“其去国之原因,大率以专制政府压制为多,然其悻悻然去之者,未必皆是也。”
对教授的劝说,胡适表示接受:“此言是也。吾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
上述那位夫人和那位教授对胡适说的话,其实是提醒胡适,在坚持是非标准时,不能忽略了一个人对本土本国的感情。胡适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幸师友匡正之耳。”由此,胡适也认识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是非之心能不能战胜爱国之心,就很难说了。
尽管胡适认识到,谈论是非标准时,要考虑到人们的爱国心,但他依旧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基本的原则还是要坚持:
“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师友的“匡正”让胡适意识到自己强调是非标准时忽略国人对国家的感情。但他做出让步的同时也有所坚持,依旧认为,爱国,还是要有起码的原则。
在1914年8月9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顷见卡来尔之爱国说,乃与吾平日所持相契合。录之:
吾辈希望有另一种爱国主义。它不是建立在偏见之上,而将使吾国对吾民更为亲爱,又和吾辈之哲学信念相协调;它将使吾国爱一切人,公正地奖励各个地区,那么国民也将不顾一切地热爱这个严厉的祖国,它的悠久的社会传统及道德生活。”
显然,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爱国,也不能盲目。
1914年10月26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长文《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对狭义的国家主义作进一步的批评:
“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德意志国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临御万方),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此真今日之大患。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胡适在这里明确表明“吾辈”乃“醉心大同主义者”,表达了要做一个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者。1914年11月25日,胡适在当天日记里抄录了“大同主义之先哲名言”,虽然胡适未说一句自己的话,但他所录的这些名言,已充分表露了他的思想:
“亚里斯提卜说过智者的祖国就是世界。——第欧根尼·拉尔修:《亚里斯提卜》第十三章
当有人问及他是何国之人时,第欧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第欧根尼·拉尔修:《亚里斯提卜》第十三章
苏格拉底说他既不是一个雅典人也不是一个希腊人,只不过是一个世界公民。——普卢塔:《流放论》
我的祖国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T·潘恩:《人类的权利》第五章
世界是我的祖国,人类是我的同胞。W·L·加里森(1805—1879):《解放者简介》(1830)”
对胡适喜欢并抄录的“我是世界之公民”这句话,当代学者邵建非常欣赏,他赞叹道:“我是世界之公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响亮的声音之一,这样的声音穿越时间的隧道而经久不衰,放在今天,则更见它的现实意义。”
1914年12月22日,胡适为世界学生会成立十周年赋诗一首。从这首可看出,当时的胡适醉心于“博爱”而不是“爱国”:
“‘且让人类博爱从此开始,
西方东方在此自由相会,
人人一样尊敬,无分尊卑,
我们的安排是相互理解和友谊。
缔造者说。于是开始工作,
这里不是饮宴狂欢的场所。
每个人都立誓教士般奉献
作开路先锋,为人类圣战。
若问我十年来有何成就?
很少,但决不只是海中的一粒盐。
我们深信定将迎来那一天——
今日的梦想将化为现实,
地球上的人们将一起呼喊:
‘人类定将凌驾万邦之上!”
正因为信奉世界主义,当中日爆发冲突时,胡适理性而冷静的表现显得与众不同,因而也特别刺眼。
1915年,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2月至5月,留美的中国学生为此展开热烈讨论,大多数学生主张对日开战。而胡适认为,战争只能带来毁灭,他主张以和平、不抵抗的方式解决冲突。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受到留美学生的冷嘲热讽。在康奈尔大学中国同学会所开的一次会上,胡适因事未出席,却发表了书面意见,当会长代念他的意见时,就连好友任鸿隽也忍不住地讽刺道:“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
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同学的理解和支持,胡适当然失望苦恼。他和好友也是他的精神舵手韦莲司谈到中日问题以及自己的“不抵抗主义”,韦莲司的回答对他颇具启发,这从胡适回她的信中可看出:
“……。
你(韦莲司)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很具有启发性。敌人是使一個国家团结起来最有效的办法。我真诚地希望从这次侮辱的经验中,能带来一些好结果。据报导,政府已经赦免了孙中山和他的许多同党,并在政府中任了要职。我希望这一举动出自诚恳的动机。
……。你说的对极了:‘我们各尽所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份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祠堂每半年举行一次的祭祀活动中,那个老年的司仪,用他庄严的声音说道:‘执事者各司其事!我已有11年没参加这种祭祀活动了,但这句话却一直响在耳际,活在心中。这句话是多么真切,又多么重要!”
显然,韦莲司认为,作为学生,应做好“份内”的读书之事。韦莲司这个各尽所能各司其职的观点,对胡适的影响是深远的。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留美的中国学生抗日情绪愈演愈烈,有人竟然主张“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这些过激之词在胡适听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为了让大家能理智地面对这一问题,冷静地商讨对策,胡适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发表《告留美学生书》,劝同学们要镇静,不能被爱国激情冲昏了头脑。
胡适《告留美学生书》的精华部分就是对韦莲司“各尽所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份工作”的阐释和引申:
“……。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是应该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渡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
弟兄们,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
总而言之,让我重述前言,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胡适把这篇《告留美学生书》寄给韦莲司,请她批评。韦莲司在回信中,赞扬文中有关学生责任那段话“鞭辟入里”,但她对胡适的某些言词也提出委婉的批评。
胡适批评留美学生出于爱国激情的激烈言辞是“不折不扣的疯癫”,他甚至讽刺一些爱国学生为“爱国癫”。韦莲司对此予以含蓄的批评。她认为一般留学生的态度虽不明智,但态度背后却蕴含着宝贵的动力,展现出来的是“元气、生命力以及团结的倾向。”他建议胡适不能只对他们泼冷水,而是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们同学们的爱国激情。韦莲司提醒胡适,如果不能为同学们确立一个高远的目标,那他们是无法接受冷静的劝告的。
胡适完全接受了韦莲司的批评和建议,并按韦莲司的劝导着手写第二封《告留美学生书》:
“……在我呼吁大家冷静的同时,完全没能理解到群情激奋背后的一种精神,而在你的信里,对这种精神却大表赞扬和理解。”
显然,胡适忽略了留学生对国家的感情,而是纯粹从理性和逻辑方面来探讨这种“群情激愤”对万里之外的国家是否有用。经过韦莲司的提醒和批评,他意识到这种看上去于事无补的“群情激愤”,却蕴含着“元气、生命力以及团结的倾向”。而他的过于理性,则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误区。
当然,在国家危急之际,胡适表现得很冷静,这并不表明他不爱国。事实上,胡适对祖国的热爱和那些慷慨激昂的“爱国癫”相比,可谓毫不逊色。
1915年2月6日,有人自称“支那一友”,致信“The New Republic”。信中说,日本在中国占优胜,未始非中国之福。还说:“中国共和已完全失败,中国人不适于自治,日本之干涉,可使中国有良政府,中国之福,列强之福。……”
胡适读后,大不满意,随即去信反驳。他的拍案而起,表明他和那些慷慨激昂,高呼口号者一样爱国家,有血性。
不过,胡适在宣泄感情之后,又会撇开感情,对“爱国”这一问题做深入思考,而“打破砂锅问到底”式的思考,让他常常陷入矛盾与困惑之中,比如:民族主义在什么前提下才能成立?外族治理就全无好处?本族治理就一定强于外族?等等。前文说过,韦莲司女士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密友和精神舵手,胡适有了困惑就会向她倾吐。在给韦莲司的一封信中,胡适就把他的“异端邪说”向对方和盘托出,并请对方为他答疑解惑:
“如果我对你的观点的了解是正确的,你的意思是说:外来统治的问题在于,统治者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发展政策对被治者是最好的;征服者有可能铸成的错误,是强加给被征服者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而其结果正适足以斫丧真正能对他们‘有益的发展。这是你的意思吗?
我的推断如果正确,则我要说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不久以前说民族主义唯一能成立的理由,只是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属于一个民族自己的政府最有可能找到最好的发展政策。请注意,我在这里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然而,我们还有待证明每一个民族确实能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个民族确实能知道这点,我们还有待证明每一个民族都有能力去作到、而且能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实现其潜力。然而,我们有太多的证据可以来证明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僵死的传统,那可以阻碍其醒觉、改革的进取心、以及发挥其潜力。你同不同意?
反之,这是非常可能的:一个外国观察家可能(至少在短期内如此)更了解一个民族所需要、而且迫切所需的是什么。一个有效率、开明的外来政府,反而非常有可能替一个衰老、被成见所囿的民族提供他自己不幸所欠缺的进取心和原动力。你同不同意?
我在这里所说的真是异端邪说!然而,你促使我诚实、不畏缩地去作思考,而这就是其结果!‘直捣其逻辑的尽头常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大部分的人宁愿走到半途就找个退路。”
胡适坦言,他的思考是“直捣其逻辑的尽头”,所以在比较外族统治与民族自治之间的优劣时,完全客观、理性而不带一丝感情,有一说一,毫不掩饰。但同时,他也明白,撇开感情,完全从学理方面去探讨这个问题却会得出在国人看来是“异端邪说”的结论。他的困惑在于:明明是理性深入的思考,为什么会得出异端邪说的结论?那么,是一意孤行坚持这种异端邪说,还是审时度势做必要的妥协?他想从韦莲司那里获得指导,但面对如此尖锐而敏感的问题,韦莲司又如何提供两全其美之策?结果是胡适只能带着这个困惑继续做“直捣其逻辑的尽头”的思考。
胡适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错误在于,他以为关于“爱国”问题可以作纯学理的冷静分析,可以“直捣逻辑的尽头”,其实,对这一问题,是不能撇开感情来作纯理性的思考,倘若不顾及人民对本土对国家与生俱来的感情只从纯学理角度思考探讨这一问题,就会得出“异端邪说”的结论。
说到对祖国的爱,一位美学家有这样的阐述:“‘爱是一种情感,不是一种主义。是生长出来的,不是灌输进去的。没有强烈而持久的切身感受,就不会有深刻而执着的情感。不论是爱的情感、恨的情感,还是其它什么情感。情感总是自发的,无待于榜样的启示,或者理论的开导。唯其无待,所以真实。唯其无待,所以深刻。如果千百年前或者几万里外的某件事情有可能使我们激动起来,那只能是因为它同我们的幸福与痛苦有某种联系。”
你看,对祖国对故土的爱,不会因了某种理性分析而滋生,也不会因为某种逻辑推论而消泯。胡适撇开感情,对“爱国”作纯理性探讨,所谓“直捣逻辑尽头”,注定不得要领,甚至南辕北辙。
1917年3月7日的一则日记,表明胡适还在思考这一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内心的困惑,同时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人对本土对国家的感情与生俱来,深厚绵长,不考虑这种感情,只一味思考,只能陷入困境,甚至步入歧途。
王壬秋给儿媳的一封信里写有这样的话:“彼(指外国列强——笔者注)入吾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
胡适早年读到这些话,非常气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然而,这时候的胡适思想大变,对这番话有了新认识,他在日记里说:“今思‘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一语,惟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平心论之,‘去无道而就有道,本吾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吾辈岂可以十九世纪欧洲之异论责八十岁之旧学家乎?”
胡适在日记里说,国家主义若能成立,必须有一个前提。
“吾尝谓国家主义(民族的国家主义)但有一个可立之根据,其他皆不足辩也。此惟一之根据为何?曰:‘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而已。譬如我国之排满主义之所以能成立者,正以满族二百七十年来之历史足证其不能治汉族耳。若去一满洲,得一袁世凯,未为彼善于此,则不以其为同种而姑容之,此二三次革命之所以起也。
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曾任美国总统——笔者注)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胡适认为,“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这个前提有问题,问题就出在那个“终”字,“终”就是“最终”,是一个弹性的时间概念,无法验证。
在日记中,胡适还提出民族主义成立的另一个前提“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胡适举了两个例子。如“英国之在印度”,如印度人同意,这个由英国人主政的政府就可以接受;若印度人不同意,就可革命。再如,有两百万德国人处于美国政府之下,如他们承认美国政府,则可不革命。
不过,胡适认为,这个前提也有缺陷。因为如果“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那么“承认”“不承认”的标准为何?“若云异族则不认之,同族则认之,是以民族主义为前提,而又以其断辞为民族主义之前提也。此‘环中之逻辑也。若云当视政治之良否,则仍回至上文之前提,而终不能决耳。”
既然,民族主义的两个前提都有问题,那么在胡适看来,民族主义也就不成立了,这样一来,胡适结论就是: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所谓“去无道而就有道”。
宁选威尔逊不选袁世凯,胡适此举正如邵建所说的那样,“完成了一个‘爱国者到‘世界公民的转变”。
当胡适得出这一结论时,完全没有考虑人民对祖国对故土的感情,以为人们完全可以根据某种分析,通过逻辑推导,选择“去无道而就有道”。而实际情况远比胡适所分析的复杂。另外,胡适举的印度人和在美国的德国人例子也不妥。因为印度人一直不满意英国人的统治,最终英国人也不得不离开印度,尽管之后印度陷入混乱之中,但印度人也不会后悔赶走英国人。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在美国的德国人是主动离开故土,奔赴美国的,自另当别论——他们根本不在自己的国家,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异族政府。
“去无道就有道”,强调的是“道”,也就是说,只要政府有“道”,那么人民就可以接受这个政府,哪怕主政者是异族。但胡适完全忽略了,对祖国对故土的感情与生俱来,这种强烈的与生俱来的感情,使人们对异族统治有着强烈的抵触心理,即使这个“异族统治”“有道”。
正因为注重“道”,忽略了“情”,当中日发生冲突时,胡适的态度显得极为不合时宜。此时的他,完全从理性的角度,考慮中国武力不是日本的对手,所以,宁求瓦全,不愿玉碎。最终他撰写的《保全华北的重要》引起了包括傅斯年在内的诸多朋友的强烈不满。胡适在文中强调了保全华北的重要性,提出先保全华北,再收复失地。言下之意就是为了保全华北,不惜忍辱和对方谈条件。而对于傅斯年这样激进的爱国者而言,无视对方侵略的事实,为保全华北和对方妥协,就是投降,就是卖国。傅斯年读罢《保全华北的重要》,暴跳如雷,声言要和胡适绝交,和发表此文的《独立评论》脱离关系。后经友人丁文江的斡旋,两人为此作了长谈,化解了冲突。但胡适对中日危机的态度也渐渐由“和平努力”转向“苦撑待变”。
胡适因为忽略人们与生俱来的爱国之情,沉浸在“没有一丝火焰”的纯粹思考中,于是得出了“异端邪说”,并且发表了不当言论引起朋友们的不满和批评。
毛姆曾说:“感情有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而胡适却从纯理智角度来思考爱国问题,自然会陷入困境。
注重理性,忽略感情,会像胡适那样陷入误区;另一方面,失去理性,一味沉溺在爱国之情中,且把这种感情抽象化、教条化、模糊化,那么,我们也会步入歧途,甚至害人伤己。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从维熙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个“右派”,一男一女,男的叫范汉儒,女的叫陶莹莹, “大墙”之内产生了爱情。后来两人都被释放了,有可能结合而没有结合,反而突然分开了。原因就是男方的“爱国主义”。当范汉儒得知陶莹莹在被划为右派后曾企图越境潜逃时,就坚决赶走了她。他的理由是:企图越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由于什么原因,一概等于叛国。而且,这个错,是不能改的,改了也是不算数的,所以“一次”也就等于永远,万劫不复。
小说中的范汉儒还说了些慷慨激昂,义正辞严的话:“屈原受了那么大的冤枉,并没有离开生养他的祖国土地呀!最后,还是跳进了汩罗江,被称为千古忠魂!陶莹莹尽管五七年受了委屈,怎么能离开生养她的母亲,养育她的大地呢?这个楔子打在我们中间,我和她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呢?”
“我认为无论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的最大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
“你、我、她都应当无愧于我们光荣的祖先。”
对范汉儒这些话,有位美学家做了批评:“当祖国、民族、国家、炎黄儿女和光荣的祖先等这些含义不同的概念被搅在一起,一股脑儿塞给我们的时候,我简直是被弄糊涂了。特别是在小说所引用屈原的例子中,不但把这些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而且把‘祖国这一概念同特定时期特定的政治路线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对于小说中设置的陶莹莹的结局,这位美学家表示了不解和痛心:“迫害者可以受到原谅,被迫害者的逃跑却是不可原谅的。迫害者判她坐牢。我们的作家则判决剥夺她爱和被爱的权利。相比之下,迫害者的判决反而显得温和了。我们的作家的判决书,犹如但丁所看到的地狱之门上的题辞:‘你进来的人们,放弃一切希望吧。设想一下出狱后的陶莹莹的命运,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到困惑:为什么我们的作家——这些本应是最富于同情心和理解力的人,怎么竟然会变得如此残酷了呢?!”
美学家认为,范汉儒和陶莹莹完全是脱离生活的虚假形象,是概念化人物,“而是这些虚假形象表现出来的一种真实倾向:把祖国概念同国家政权混为一谈,为‘极左路线辩护和粉饰。”
美学家还特别指出,如果混淆了“祖国”与“国家政权”的概念,就有可能“拉了祖国来做执政者罪恶的替罪羊”。美学家反问:“这岂不反而委屈祖国,成了不爱祖国了么?”
陶莹莹试图越境是为了逃离极左路线的迫害,而范汉儒据此斥责她叛国,这不是把极左路线犯的错由祖国来承担吗?
陶莹莹是在受到迫害才决定越境逃亡的,这是保命,哪里是叛国?就连梁启超不也说:“夫人至救死犹恐不赡,而欲责以爱国,为道其安能致?”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從维熙后来接受了这位美学家的批评。
当我们小心翼翼把“祖国”和“国家政权”区分开来之后,再去读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读胡适的《你莫忘记》,应会发现,陈独秀胡适所说的“不爱国”,不过是愤激之词,当不得真;他俩的真实意图,不过是激发人们对当时那个昏庸无道、鱼肉百姓的“国家政权”的愤恨,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