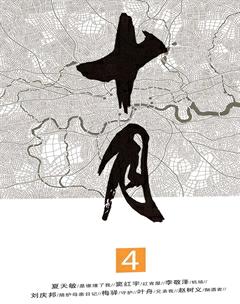旅 行
孟昭旺
1
汽车抵达S镇,天已徐徐暗下来。时间虽是夏末,天气日渐清凉,路旁的杨树却依旧茂盛,墨绿的叶子密密匝匝,遮住头顶散淡的光,公路便愈发幽暗了。
李东走在幽暗的公路上,听到树上传出沙沙的响声,抬头望去,却见许多嫩绿的虫子伏在叶脉上,啮噬宽大的树叶。在董村,这绿虫有个奇特的名字,叫“吊死鬼”,每到夏天,它们便从树上垂下来,蜘蛛一样吐出细长的丝,在半空随风晃荡。李东记得,小时候,他常捉了那些虫子,藏进李红衣领。李红天生胆小,见了虫子更是怕得要命,被李东一吓,便尖叫一声,双手蒙住脸,躲在墙角不敢动弹,嘴里嚷嚷着:“李东,你烦不烦?”
李东嘿嘿笑着,变戏法一样,摊开手掌,那只虫子正在他掌心缓慢地蠕动。他说:“逗你的,看把你吓得。”
李红说:“以后再不许胡闹。”
李东还记得,他常以此要挟姐姐,为他誊作业、抄歌词。李红长得好看,字也写得工整,不像李东那般,写字七扭八歪,又常把“拨”写成“拔”,“免”写成“兔”,十个字却要写错三五个。
天越来越黑了,S镇的天总是灰蒙蒙的,不晴朗,也不明媚,有些说不清的含混和压抑。
一只虫子落在他肩膀上,他把它拿下来,捏在手里,任凭小虫鼓着肚子在手指间挣扎。李东第一次觉得这虫子让人厌恶,稍用些力气,一股绿浆就从虫子身体里喷射出来。
李东想,这么多年了,姐姐还会不会被这软乎乎的家伙吓得丢了魂儿呢?
与若干年前相比,S镇几乎没什么变化。在李东印象中,这个靠生产假冒葡萄酒闻名的小镇与董村是不同的:镇上的公路宽敞而平整,不像董村那条黄土路,坑洼不平,冬夏季节会被雨雪弄得泥泞不堪,春秋两季则会扬起漫天尘土。S镇家家住着瓦房,房前的柳树遮在栅栏上头。电影院、台球厅、发廊、邮局,在少年李东眼里更是新鲜的事物。董村可没有这些东西。董村只有一座接一座的麦秸垛,常有蚰蜒、蟋蟀、潮虫之类的在腐败的麦秸上恣意乱窜。牛啊驴啊之类的牲畜倒是常见,它们常在黄昏时分出现在村外那条黄土路上,在村人的呵斥下慢悠悠地走,董村的空气中常年弥漫着牲畜粪便和毛发混杂的气息。
S镇的人跟董村人也不一样。男人们大都喜欢在胸前挂条金灿灿的链子,女人则热衷于用各种衣服和饰品把自己装扮得花枝招展。S镇的青年极少读书,他们通常读到初中便早早退学,在自家酒厂找个闲差,每日里骑着摩托,浪荡公子般四处招摇。
“他跟他们不一样。”直到今天,李东仍清晰地记得,姐姐李红说起丁洋时的表情。她坐在炕沿上,两只手在黑亮的辫子上缠来缠去,细白的牙齿轻轻咬着嘴唇。她的声音不大,却坚硬,像一块石头投在水面,又直直地坠入水底。
李金贵坐在外间屋,手上端着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他拧着眉,沉着脸,好像没有听到李红的话,或者,他听到了,只是没有想好该怎么回答。在李东的记忆里,李金贵素来是个沉默的人。对于这个老实巴交的木匠来说,姐姐日益隆起的肚子,显然给他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
“他们是他们,他是他。”李红又补了句,照样硬得像块石头,冷冷的。
李金贵便猛地咳嗽起来,烟袋在灶台上磕了几下,鲜红的烟丝掉在地上,一闪一闪冒着火星。又沉默了会儿,终于按捺不住,便站起身来,长叹了口气,对李红说:
“跟你娘去说会儿话吧。”
李红便嘟着嘴,犟乎乎地往西屋走。照片上的刘翠兰留着齐耳短发,一脸漠然地看着李红。李红把相片上的尘土擦去,又点了炷香,插进香炉,磕了个头,说:“娘,你相信我,他跟他们真的不一样。他们是他们,他是他。”
李东跟在姐姐身后,像条尾巴,他那时不过十几岁。对于家里的事,也只模模糊糊的,一知半解。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只得尾巴一样跟在李红后头。
李金贵仍没说话,他再次续了一袋烟,却没点着,连同手里的烟袋锅一并摔在地上。
“贱人贱命!贱人贱命啊!”他说。
李红跑出去,跑到院子里。李东就慌了,他飞快地跑到院子里,拦在李红前面,拽住她的胳膊,不让她走。
李红挣扎了半天,终究没能挣脱。
李东说:“姐,你不许走。”
李红看着他,心就软下来,气鼓鼓地回到屋里,径直奔向自己的房间。
李东记得,那个暗淡的傍晚,姐姐把自己關在西屋,独自在黑暗中待了许久。掌灯时分,当李红从屋里走出来时,已经止住了哭声。看起来,她已从悲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她走到李金贵面前,面带微笑地盯着他。是的,她什么话都没说,就这么直直地盯着父亲。李东觉得,姐姐的目光像钉子,钉到父亲脸上。李红朝着父亲挥挥手,借着微弱的灯光,李东发现姐姐手上握着一把黑漆漆的剪刀,鲜红的血顺着手臂淌到地上。
他不禁大叫了一声。
2
李红正在做饭。接连下了几天雨,灶膛里的柴火有些潮湿,李红使劲拉着风箱,却被冒出的浓烟熏得眼泪汪汪。
李东便蹲到旁边帮忙拉风箱,又找出火筷子,翻腾灶膛里的柴火。火苗渐渐升起,火光把屋子照得通红,屋子里变得暖暖的。李东感觉回到多年前的董村,许多个傍晚,李红就像现在这样,蹲在灶膛前准备晚饭。极简单,无非是熬棒子面粥、贴饼子,玉米渣子磨得粗粝,吃起来拉嗓子。菜倒是现成的,在自家菜园里,摘新鲜的西红柿,拿白糖拌了,酸甜可口。每每那时,李东总忍不住叫她,“姐”“姐”。李红明白他的意思,从案板上拿个西红柿,又从玻璃瓶里挖一勺白糖给他。李东自然开心,却舍不得自己吃,总把西红柿举到姐姐嘴边,让她先尝。李红推辞,他就坚持。李红勉强咬了口,李东才满意地大口咀嚼起来。
水烧开了,铁锅里冒出蒸腾的热气,李东立在旁边,有些局促。这些年,李红没少往市里跑,去看他。李东服刑的监狱在市郊,在长途车站下车后,还要转乘人力三轮车,走上半个多小时。他不知道该说啥,要不是他一时犯浑,跟着那帮年轻人偷挖了地下的电缆,他也不会被关进去。一共不过分得几百块钱而已,不过,他一直没有告诉李红,那些钱,他其实是打算给她买台录音机。李红从小爱唱歌,并且唱得很好听。
李红看出了他的局促,便把他往屋里推,说:“你进屋坐,家里太乱,没个落脚的地方,正说收拾收拾,这几天赶上厂里忙……”
李红在镇上的五金厂上班,负责用车床把一块块钢板加工成轴承啊、螺丝啊之类的东西,虽然挣钱不多,她却干得极用心。
豆豆正趴在凳子上写作业,见有生人来,用手托住下巴,探头缩脑地往外看。李东走到她旁边,把包里的糖果递给她。这孩子怯生生地看了李东一眼,躲到李红身后,不知如何是好。李红说,吃吧,这是你舅舅。她却把手指含在嘴里,不敢抬头。
饭做好了,炸酱面,正是李红拿手的。母亲过世后,李红便把家务担下来。每天放学,就到粮仓里抓了麦子喂鸡,又拿扫帚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呢,就招呼李东,跟她一起往水缸里抬水。李东贪玩,往往不听李红的话,没待一会儿,就借口头晕或肚子疼,跑出去玩儿了。李红就试着自己提水,等到李金贵从地里回来,水缸里已经满满当当。李东呢,就把逮来的黄鹂鸟送给李红,又把刚从树上摘下的槐花插在她头上,悄悄凑到李红耳边,说将来要娶一个跟她一样好看的姑娘做媳妇。李红不说话,只痴痴地笑。
饭菜摆好,李红问:“要不要喝点儿酒?”
李东犹豫着,点点头。
李红便从玻璃柜里拎出个塑料桶,给李东斟上,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劲很冲,李东料想大概是从小作坊里买来的劣质酒,心里忽然一疼。李红走到门口,从墙上挂着的一捆大葱上揪出一根,蘸着炸酱,自斟自饮起来。见李东有些惊愕,李红解释说,她最近总是失眠,要是不喝点儿酒,怎么也睡不着觉。
“丁洋呢?”李东问。他不管丁洋叫姐夫,自打在婚礼上,丁洋借着酒劲,把李金贵的肋骨打断之后,李东便与他断绝了来往。
李红没有回答李东的问话,她端起酒杯,跟李东碰了一下,问:“你有什么打算?”
李东一口把杯里的酒喝掉,思量着。能有什么打算呢?以前倒是想过,跟父亲学木工,做棺材卖,虽说辛苦,但毕竟是个稳当的营生。到春风理发馆跟王师傅学理发也行,门槛低,一年半载就能出徒。可是,世间的事谁又说得准呢,偏偏就出了差错。不過几年的光景,李金贵已经病得不行,嘴角挂着浑浊的涎水,说话支支吾吾,常把张三错认成李四,哪还能教他手艺。王师傅呢,两年前就搬到省城跟儿子住了,现在的理发馆已经成了一家手机维修店,开店的青年染着黄头发,究竟是谁家的孩子,李东却认不出来。还能干什么呢?服刑的这几年,在看守所倒是学了微机操作,但毕竟蹲过监狱,头上顶着犯人的帽子,没那么容易摘掉。
李东不知道该说什么,闷着头吃面。沉默了会儿,又问:“丁洋去哪儿了?”
“先在这住下吧,李东……反正……等忙过这几天,咱们去旅行吧,去云南丽江,我喜欢那里的人,在街边的小店里,他们一边打着手鼓一边唱歌。我记得有一首《红蔷薇》,特别好听。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那个留着短发的女孩,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让我心疼。我想去丽江看看她,让她帮我签名,我还想跟她合张影。呃,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追星,会不会被人家笑话?”
酒喝得有点上头,李红的脸红扑扑的,眼睛里含着血丝,疲惫不堪的样子,兴致却仍很高。一只“吊死鬼”爬到她身上,顺着裤腿往上爬。李东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她。
“你看电视吗,李东?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简直太棒了,我一直追着看,从小我就爱看唱歌的节目。你肯定不记得了,小时候,我总帮你抄歌词,对着电视上的字,一句一句地抄。你们总欺负我,我怎么那么老实呢?他们总是护着你,你是他们的心肝宝贝。我呢,什么都不是,我是个多余的人,好像做什么都不对。从小到大,我一直在犯错……”
李红发现了身上的虫子,曲起手指,轻轻一弹,虫子飞到锅台上,李红从地上捡了块木头,把虫子碾死,照旧大口吃起面条来。
李红说:“今年的虫子可真多,你说,怎么突然会有这么多虫子?”
豆豆听说要去旅行,龇着牙,托着下巴,笑眯眯地瞅着李红。她的牙齿上有个豁口,笑起来憨憨的。这孩子性格有些内向,整个晚上,一句话也不说,就默默坐在那里抠指甲。李东凑过去,问她,爸爸呢?豆豆不抬头,也不说话,倚在李东腿上,把手拿给李东看。她的手掌正在蜕皮,细嫩的指肚上,裂开一道道鲜红的口子。她太瘦了,脖颈后面的脊椎又细又高,她还有点儿驼背,从侧面看,像一根颀长的豆芽。李东觉得,她的身体一定出了毛病,要么是营养不良,要么是肚子里长了蛔虫。
3
豆豆对李东颇有好感。这孩子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装着面镜子,亮堂堂的。吃过饭,不肯睡觉,出来进去黏着李东。也不说话,只扯住他的衣角,不肯撒手。按照李红的说法,这孩子平日里不爱理人,这回可真是破天荒了。
收拾完毕,李红便到里屋,跟李东聊天。也没什么好聊的,无非关于董村的人和事,都是老皇历了。
“对门的四奶奶还跟以前一样疯疯癫癫,逢人就拿着拐棍追打?”
“哦,她啊,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董村小学那个整天醉酒的老校长,也快该退休了吧?”
“他,或许吧……”
“卖豆腐的孙老头,现在还经常唱戏不?他可是个戏迷,唱得空城计,绝了。”
“卖豆腐的孙老头,哦,我想想。”
对于李红的提问,李东大都支支吾吾——他不过刑满释放几个月而已,对于董村,他并不比李红了解更多。
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忽然沉默下来。
良久,李红问:“咱爹……还做棺材卖?”
“呃,不了。”李东说,“爹去年冬天得了脑血栓。”
李红沉吟着:“哦……”
李东说:“姐,你该回去看看他。”
李红挽起袖子,露出一道疤痕,深而宽,像一条肥硕的蜈蚣趴在小臂上。
李东便不再开口。当年,李红用剪刀划开手臂,是他背着去的镇医院,缝了十二针。他还记得,缝针的过程中,李红自始至终没有喊疼,她看着血肉模糊的手臂,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豆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紧拉着李东的手,把一包硬邦邦的东西塞给他。
李东打开布包,竟是几枚核桃。
李红把话题岔开:“嗬,就这几个核桃,可是当宝贝呢,自己舍不得吃,平时,我都不知道藏在哪儿,今儿反倒大方起来。”
豆豆就跑过去,堵住李红的嘴,瞥了她一眼,又羞赧地仰头看着李东。看得出,这孩子心里是欢喜的,她总忍不住笑,把那个带豁口的门牙露在外头。李东觉得,她的眼睛特别好看,水汪汪的,清澈而干净。她笑的时候也特别好看,一颗好看的虎牙,两个深深的酒窝,多少能看出李红当年的模样。
夜深了,月亮透过窗子,照在炕台上。豆豆倚在李东肩上,睡得很沉,鼻翼一张一翕,发出轻微的鼾声。李红把豆豆安顿好,自己打了个长长的呵欠,说:“太晚了,去睡吧。”
果然是累了,身子一挨着炕,眼皮就紧紧合在一起。
李东是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的。已是半夜时分,窗外的月亮已经不甚明朗,一片黑漆漆的云彩擋住了月光。不知是不是被电话惊扰,隔壁邻居家的黄狗开始“汪汪汪汪”地叫个不停。
李东认真回忆了一番,才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隐隐约约地,她听见李红压低嗓音在说话。
在电话里,李红像是在哀求什么,翻来覆去地,她只说一句:
“好的,放心,三哥。”
“三哥,你放心,我一定……”
她被这电话吓坏了,声音里带着哭腔。
显然,那个被称作“三哥”的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这是一个冗长的电话,充满着讨价还价,请求和拒绝,进一步和退一步。李东感觉到,姐姐正在慢慢地矮下去。他想起李红白天说的那句“你们都欺负我”。现在,李红正被人欺负。这样的电话让李东感到心烦,他不喜欢在半夜被人吵醒。电话里的声音断断续续,他们提到了丁洋、打掉的牙齿、被火烧光的仓库,提到了敬酒和罚酒,时间和耐心。李红无话可说,她只能一点点地委顿下去。
“三哥,我保证把他找回来。”
“对,他不是东西,我也不是东西,三哥,过一段,我去找他,我保证……”
4
李红把去丽江的时间安排在下星期。不能再晚了,天气越来越冷,风吹在人脸上,硬生生地疼。冬天就要来了吧,李红一点儿也不喜欢冬天。在她的印象中,冬天太过阴冷,那样的季节,总让人烦躁不安,对许多事失去耐心。
就下星期吧,她想,反正现在有大把的时间。
她被工厂辞退了,这是今天下午的事。辞退就辞退吧,李红想,也许,老天是心疼她,想让她好好休息。反正挣得又不多,满打满算只能维持生计而已,反正厂子的环境又脏又差,车间里到处是机器油腻的味道、食物发霉的味道和老鼠尸体腐败的味道,反正负责验收的工头态度又不好,总用食指对着她指指戳戳,把唾沫溅到她的脸上。有什么好留恋的呢,辞就辞吧,辞了更好。倒是出门的时候碰到侯三,让她有些惊讶。侯三脸上堆着笑,主动凑上来跟她打招呼。他对她倒是客气,一口一个“嫂子”地叫着。
侯三说:“歇几天吧,嫂子,等我哥回来再来上班。你也该歇歇了,歇多久你看着办。反正一天见不到他,我就一天不肯放过你们。S镇的人都知道,我侯三是个说话算话的人。”
侯三点了支烟,递给李红,李红摆摆手说,戒了。侯三突然变了脸色,厉声说:“他不是打掉我满口牙吗?他不是放火烧了我的仓库吗?他可真行。我们可是拜把子兄弟呢。可是,他干吗躲起来不见我呢?他去了哪儿呢?我想和他说说话,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他该回来看看了。就算不看我,也要看看你们啊。半年了,我是真的想他了。他怎么忍心抛下你呢,怎么忍心抛下豆豆呢?哦,豆豆,这小丫头越来越讨人喜欢了。要是他再不回来,过两天,我就派人帮你照顾她。”
侯三后来终于闭上嘴,他一定是被李红的声音吓坏了。李红只对他说了两个字:“你敢!”
李红从工厂出来,沿着河边往回走。河滩上散布的大小不一的鹅卵石,在阴沉的天空下发出暗淡的光。尚未凋零的荻草在风中恣意摇摆。水面漂浮着落叶与被风吹起的波光,随着河水缓慢地朝河心漂去。远处的拱桥上,两个戴口罩的男子,正探头缩脑地朝这边看。
李红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天有些阴沉,似乎要下雨。她已经嗅到了雨水将至的味道——对于这种咸涩的夹杂着土腥的味道,她并不陌生。在她的记忆里,这个秋天似乎一直在下雨。
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李红踩着石子走近河边,蹲下来,从河水里看自己的影子。她的头发有些乱,眼角一条深深的鱼尾纹,像丑陋的疤痕延伸到发际。她对着水中的影子笑了笑,影子也对她笑。她伸手拨了下河水,影子便在水面上晃动起来。有多少年没有这样注视过自己了?她记得,上初中时,丁洋送过她一面小镜子,圆圆的,背面是一个名叫陈德容的香港明星。那时,她总把镜子藏在书桌下面,装作低头看书的样子,偷偷地照,只要那么三五秒钟,她的心就开出花来。那时的她多美啊,那么多人写情书,塞到她书包里,或者在校门口吹着口哨等她。有什么用呢?李红根本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她讨厌那些嬉皮笑脸的家伙。那么多人,她就只喜欢丁洋,原因是,只有丁洋敢替她打架。说是打架,不过是替她挨打而已,拳头啊,脚啊,棍棒啊,有一次打急了,还抡起了链子锁,沉沉的铁家伙砸在额头上,滋滋往外冒血,至今,丁洋的额头上还有一个月牙形的疤。那时候多好啊。丁洋骑着摩托,带着她到处疯跑,汽油燃烧的味道,钻进她的鼻孔,淡淡的,香香的,李红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闻的味道。车子开得飞快,风把她的头发吹到空中,高高飘起。她就把脸贴在他背上,她紧张极了,双手紧紧箍在丁洋的腰际,闭着眼大叫。但她不怕,她的胆子就是从那时候练出来的。死就死吧,她想,死了也值了。
下雨了。雨水淅淅沥沥,落在河面上,也落在李红的头发上,脸上,身上。她感觉眼角湿漉漉的,已经好久没有哭过了。可不是嘛,结婚时没有像样的嫁妆,挎着寒碜的布包袱嫁到S镇,她没有哭。结婚五个月生下豆豆,镇上的人笑话她管不住自己的裤裆,她觉得无所谓。丁洋因为酒厂的生意打伤侯三,侯三一次次找上门来闹事,她也从不害怕。她今天这是怎么了,不过是那句“他怎么忍心抛下你呢,怎么忍心抛下豆豆”,她就觉得委屈了。算起来,这么多年,这是她第一次感觉委屈。她又想到丽江,她记得,丁洋跟她最后一次通话,是在人声嘈杂的街上。她问他在哪儿,他怎么也不肯开口。她只是隐隐约约从话筒里听到了模糊的手鼓声,一个女导游正用扩音喇叭讲解:
“各位游客,欢迎您来到美丽的丽江古城。”
5
李东到街上的药店给豆豆买了点儿药,他料定这孩子肚子里一定有蛔虫。他小时候就曾生过蛔虫,常常肚子疼,李红带他去看病,医生给开了几粒糖丸,吃下去,肚子里排出几条虫子。
路上,李东想,豆豆实在太瘦了,一阵风都能把她吹到空中。
回来时,李红正对着地图研究线路。豆豆跑过来,搂住他的脖颈。她好像受到了惊吓,小手冰凉,脸上也冰凉。李东伸手捧住她的脸蛋,又轻轻刮了下她的鼻子。这孩子却突然“哇”地哭起来。
“我们去旅行吧,李东。我想去丽江,我不能再等了。冬天越来越近,你知道,我害怕冬天。一到冬天,我的鼻炎就会犯,打喷嚏,流泪,鼻子里像塞满了棉花。我的腰椎也不好,阴冷的天气,我的腰就疼得厉害。这里的冬天太难熬,天总是灰蒙蒙的,让人喘不上气来。我不想再熬下去了,这里到处是‘吊死鬼,地上,树上,墙上,它们到处爬来爬去……”
李东把豆豆揽在怀里,她仍在抽泣,嘴里不住地念叨着,语气含混不清,李东听不清她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走吧,李东。我知道丁洋藏在哪里,他不说我也知道。我们去找他,虽然他心里没有我们,但我仍放不下他。你不知道,他那时候有多好。我坐在他的摩托上,沿着公路一直往前,路两旁开满了紫堇、马兰和喇叭花。我必须见到他,你知道吗?最初的时候,他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去了哪里,遇到了什么人。他说过一段就回来,他还说要跟侯三讲和,赔钱,赔多少都认了。或者去坐牢,三五年就够了。后来,突然间他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过得怎么样。有一天夜里,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突然就哭了,他对我说,让我原谅他。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在电话里我听到了手鼓声。后来的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李东,我想去找他,有些话我要当面问问他。这样憋着实在太难受了,问明白了,就死心了。”
“回董村吧,姐,一起去看看爹。他活不过今年的,他认不清人了,逢着有人从门口过,她就喊你的名字。清醒的时候,总念叨你,说你年轻时候的好。你扫地,做饭,提水,受了不少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他说放心不下你,说你打小脾气倔,容易吃亏。他还说,该来看看你的,只是他恐怕挨不到那一天了。姐,回去吧,只要看他一眼,然后,我们去旅行,去丽江,大理,西双版纳,再也不回来了。”
李红就抽泣起来,她一边擦泪,一边点头。她以前很少哭,也许是上了年纪的原因吧。她照镜子的时候,发现鬓角已经有了不少白发,肌肉也变得松弛。她想,时间过得真快啊,用不了多久,她就老了。
李东拿了条毛巾,递给姐姐。李红接过去的时候,李东发现姐姐的胳膊上有几道深深浅浅的伤痕。
他问:“怎么回事?”
李红说:“没,没什么,划伤的,不小心……”
李东又问:“怎么回事!”
李红沉默了良久,终于说:“侯三真的去找豆豆了。在回家的路上,两个戴口罩的男子把她往车上拽。我就哭,就喊,拉着豆豆的手不放。她们打我,踹我,打得我跪在地上,我就不松开豆豆的手。侯三从车上下来,他拿我没办法,就提起丁洋。她知道我的软肋。我快撑不下去了,李东。”
豆豆忽然不见了。明明刚才还在屋里,一眨眼的工夫,却没了踪影。天已彻底黑下来,阴雨的天气,天空如同蒙上一层黑布,黑漆漆的大地,看不见光亮。
李红慌了,她打开所有的灯,疯了似的到处找。找遍了整个院子,却没有豆豆的身影。她坐在地上,眼神暗淡无光。她默念着豆豆的名字,泪水顺着鼻翼缓缓淌下来。
这么晚了,她能去哪儿呢?
李红回到屋里,听见床底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她蹲下身子,用手电朝里面照。她看见豆豆抱着腿,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好像被什么恐怖的场面吓呆了,又像是,她已经什么都不怕。
豆豆没有被抢走,李红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在地上。她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李东,却发现李东没在身边。印象中,他好像出了院子。他走得太匆忙,以至于没来得及跟李红打声招呼。
李红把豆豆抱到床上,把她哄睡着,又等了许久,仍不见李东的动静。
李红心里有些忐忑,她披了件外套,出了门。李红很少在夜晚出门,如今,她走在月光下,隐约觉得,这样的夜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6
侯三的尸体在面粉厂后的水塘里被人发现,已是几天后的事情了。
由于河水的浸泡,原本干瘦的身体变得白白胖胖。鼎鼎大名的侯三眯着眼,面带微笑地躺在地上,像是躺在温暖的阳光下午休。几只绿头苍蝇慢悠悠地从他的眉毛跳到头发上,又从头发钻到鼻孔里。
“他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人们说。
关于侯三的死,当地流传多种说法。有人说,侯三是被仇家杀死的,他的仇家晚上潜入侯三家中,用一把榔头敲碎他的脑壳,然后,把尸体扔进河道里。侯三的身子很沉,扔进去后,溅起巨大的水花,并发出“扑通”一声响。
也有人说,侯三是自己淹死的,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回家的路上,他准备到池塘里撒泡尿,结果,他在河水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打算把自己从水里捞出来,结果,一脚踏空,滑进水中央。
还有一种说法,侯三是被“吊死鬼”缠住,索了命。那天傍晚,正在河边遛弯的人们,看见侯三拼命往河边跑。他们跟他打招呼,他谁都不理。人们说,谁能想到,他是赶着去投胎呢。
总之,侯三的死,在S镇引起不小的轰动,关于他的死因,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时的李红正和李东一起坐在通往云南的火车上,她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丛林和村庄。好几次,她拿出手机,想打一个电话。犹豫再三,她终于拨通了。
“喂?”电话里,李金贵的声音听起来遥远而沧桑。
李红没说话,眼泪吧嗒吧嗒滴在衣服上。
李金贵咕哝了句什么,李红没听清。她想告诉他,她胳膊上的伤已经好了,让他别再惦记。但她终于没有说,她想,尘归尘,土归土,心里长出来的,还是让它烂在心里吧。沉吟一会儿,默默地挂了电话。
豆豆倒是挺开心,手里拿着瓶营养快线,喝了一口,胳膊一甩,用袖子擦掉嘴角留下的白色乳渍。车厢里人不多,她央求李东跟她玩儿躲猫猫。李东跟在她身后,在车厢里跑来跑去。豆豆“咯咯”地笑,那颗有豁口的门牙已经掉了,笑起来露出更大的洞。
午夜时分,豆豆睡着了。李东和姐姐面對面坐着,低声聊天。他们再次说起了董村,槐花,“吊死鬼”,水井和黄鹂鸟。说着说着,他们就沉默下来,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车厢里很安静,昏黄的光在李红身上闪过。坐在她对面的李东有些恍惚,一时间不知今夕何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