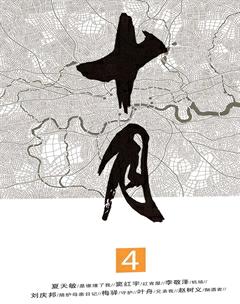马加什教堂顶上的乌鸦
梁尔源
故 乡
小时候经常生病
每当我发烧不醒时
奶奶就给我喊魂
边烧纸钱边呼我的乳名
“回来了 ,回来了”
再用手在我滚烫的额头上刮
直到我睁开眼睛
祖母才轻松地嘘出一口气
我的魂被祖母喊回来了
没几年,祖母的魂
却被菩萨喊走
再也没有回来。很长时间
我的魂
一直在红尘中游荡
远离揪心的故乡
祖母的呼喊不在了
我的魂,还回得去吗
记忆中的月亮很薄
离开古镇很久了
小河中的月亮打磨得很薄
岁月将它揣在背包里
每一次在梦中打开行囊
就轻轻播放出
妈妈哼唱的那首童谣
沧浪之水将月亮
冲刷得像一块薄薄的鹅卵石
在波纹中晃动
我再不想用它打水漂
真担心那些光屁股的镜头
从溪水中飞出
清辉洒上老屋窗棂
月亮薄得像张窗纸,泛着乳白
我蹑足从窗下经过
卧房里有急促的呼吸声
我缩回胆怯的手指
不敢戳穿害羞的月亮
那时候,月亮很白
我经常去小河里抚摸它的脸蛋
它天生丽质
不需我买雪花膏
我走后,月亮也上岸了
有人看见它从后山钻出
时常半掩羞涩
捂着那些天真的秘密
风中的妈妈
风也不捎带我
只有在一棵树上悬着
树上的果子落了
心仍在等它发芽
无奈的眼神
挂着远方的枯萎
用孤独搂紧
一个飘荡的童年
記忆中的补丁
那些粗糙简单的岁月
总把幼小的纯洁

磨得破损裸露
但总有一种情结
把人间的羞耻缝补和遮掩
在那时街坊的世俗里
针线是一曲《女儿经》
补丁被翻看成《弟子规》
生活中的见微知著
都用“四书”“五经”中的精气神
日复一日地缝补出来
行走在耀眼的时尚中
总想从这个光鲜的世界里
找到一块新鲜的裸露
让快要失传的针线派上用途
但我祖传的手艺
已无法缝合,心口的那块补丁
月亮撒了一把盐
那条通往村庄的小径
像一条发不出音的声带
许久没哼出一支山歌
也没吹过一声唢呐
晚风摸不到老屋的心跳
静谧中已听不见
女人的喘息
和老木床摇晃的嘎吱
昏暗的灯光下
只有爷爷的胡子里长满故事
奶奶的瓜藤上缠着枯萎
隔壁那棵羞涩的桃树
春风中飘落了笑靥
李家院内的那枝红杏
在张家的墙头搁着媚眼
小花猫懒懒的
睁着一只眼,闭上了另一只眼
夜色中,月亮给村庄
撒了一把盐
将寂寞腌制在山坳里
岁月从罐子里掏出的
仍是皱褶的身影
扫 墓
坟堆上去年拔掉的杂草野花
今年长得更欢了
父亲生前从不拈花惹草
难道死后葬得孤僻偏远
他自由了,解放了
什么规矩也管不了啦
我最了解父亲
拔掉坟冢上的杂草野花
然后用黄土拍实
让他在阴间也持守晚节
那光秃的坟冢
被雨水浇得溜滑
就像父亲光秃的脑门
记得临终时他用乏力的手
拍了一下脑袋
对同事说,我走了
一根头发都没带走啊
在肖邦故乡
在华沙凛冽的寒风中
那些追赶的枯叶
像钢琴中跑出的音符
跳跃在这个音乐囯度每个角落
北囯的冬草都已枯萎
唯独华沙的小草
仍伸着绿茵茵的耳朵
踏着生命常青的那支乐曲
来到仰慕已久的那栋乡舍
抚摸那架古老的钢琴
优雅的B大调和G小调
弹奏出一个天才少年的身影
在一个古老的教堂里
音乐的心脏安放在上帝身旁
铿锵有力的节奏
伴随着那静谧的神曲
从硕大的管风琴中
迸发出对音乐的虔诚
生活在圆舞曲中奔放
幻想曲将青春陶醉得浪漫缤纷
母爱抒发出甜蜜的摇篮曲
但当那根神奇的琴弦
被病魔绷断时
那永远也不会停止跳跃的音符
却无法为一个伟大的天才
谱写一支《安魂曲》
拉卜楞寺的红袈裟
行走的僧侣
披着宽厚的红袈裟
裹走了尘世杂音
吸附着人间的锈色
神秘的殷红
过滤了多少红尘俗事
那是草原静脉中蠕动的血色
没有跳跃 冲动 翻腾
在雪山冷藏的虔诚里
积淀着太阳溢出的高原红
裹着佛堂的那卷经书
牵动行走的牛羊
好似草地吐出的经文
一张张高原的脸
是离神最近的表情
阳光穿透红袈裟
辉映成高原的红玛瑙
我蛰伏在佛的心中
修炼成一只纹丝不动的昆虫
父 爱
好长时间没有人唤我
藏在小草中的乳名
一旦有人呼出我的乳名
母亲香甜的乳汁
立刻从老胃中反刍
那天,路过后山祖坟
突然听到有声音在隐隱地
呼我鲜为人知的乳名
那么亲切 耳熟
定神一看,原来
父亲坟头上那朵小花
正张着嗓门
马加什教堂顶上的乌鸦
那只从窗外飞来的乌鸦
悄悄地叼走了
一枚陷害囯王的毒戒
挽救了一个囯度的命运,这只
和老家树林一样的乌鸦
在异邦却享有上帝的声誉
那乌黑的羽毛
顿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乌鸦嘴被更换为褒义
它叼走的不是偶然
而是上帝的旨意
驱赶的绝非只是晦气
而是历史的厄运
翻开马加什王朝的兴亡史
从黑格尔哲理中才能
捕捉到这只圣鸟的身影
倘若在历史的必然中
再种植一棵偶然的梧桐
在栖息凤凰的同时
也应给乌鸦
腾出一根幸运的枝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