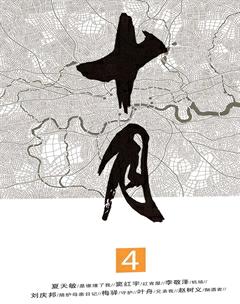夜 宴
刘汀
1
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活向他呈现出非常美好的一面,甚至还让他看见了一个可以期待、令人激动的未来。在这个未来里,他有属于自己的家庭、爱人,有一份算不上多令人羡慕,但足够生活的收入;周末的时候,能带着家人去看一场最新上映的团购电影,五一或十一小长假,能租一辆车到郊外,或者到离北京不远的北戴河玩几天;对,还有三五个聊得来的朋友,他们偶尔去吃个羊蝎子火锅,喝精品二锅头,然后在夜色里醉醺醺地道别。
当然,那时候他还无法具体化这些场景,所谓的看电影、小长假、羊蝎子火锅,都只是他根据后来的生活所归纳出来的。他在想,如果当年自己对未来有过期望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只可能是这个样子。他从来都不是个有野心的人,即便你给他一盏阿拉丁神灯,他所能提出来的愿望也不会超出要点钱、要个房子这一类基本需求。
这段时间成了生命里唯一能支撑他幻想的日子,也成了他的魔咒:我曾有过机会,但最终我没能把握住。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是十年前,他刚刚从公用电话上查到自己的第三次高考分数,确定自己能被北京的一所很著名的大学教育系录取了,这个教育系在全国也很著名。几周后,他收到了邮局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这张不大的纸最终确认了这件事——他要彻底地从老家那里的生活中抽身而出了,像村里十年前的第一个大学生罗昊一样,从此去过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也就是在这年秋天,他拿到通知书的几天后,罗昊带着老婆孩子回来探亲。他是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回来的,车子刚进村,罗昊的父亲就在院子里点燃了一万响的鞭炮。几乎沿路的每户人家都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一家人站在大门口,看着罗昊的车缓缓驶过。他也在人群里,但他注意到的并不是车的轮子和冒烟的屁股,而是后排座位上那个美丽的女人和一个同样美丽的小女孩,那是罗昊的妻子和女儿。全村人都知道,罗昊读的是地质研究,做了几年科研,后来进入了政府系统,现在是某个地级市的副市长了,是他们十里八乡官当的最大的人。
汽车他见过,并不感到惊奇,但是罗昊的妻子和女儿才是最令他意外的。他从来没见过那么白、那么干净的人,就他当时的感觉来看,她们比电视上的模特们好看得多,因为车从他跟前路过的时候,离他还不到两米。透过褐色的车窗玻璃,他看见罗昊的妻子正拿着一根小东西在涂自己的嘴唇,那是一双火焰般的唇。读大学后他才从女同学那里了解到,那是润唇膏,防止嘴唇干燥的。
罗昊家里杀猪宰羊,村里乡里县里的干部们轮番来见他,每一个都带着一堆礼物。罗昊的父亲把礼物装在院子的仓房里,锁上一把大铁锁,钥匙就叮叮当当挂在腰间。每天晚饭后,他都要揣着一盒烟到小广场上,给老人们发带过滤嘴的香烟,有时候他的那个洋娃娃般的小孙女跟着他,手里也拿着一根带着一块糖的小棍子。
有一天晚上,罗昊的父亲第一个把烟递给他,他有点意外,因为那儿不但站着自己的几个叔叔,还有几个年龄更大的老人。看到我家罗昊了吧?老头示意他赶紧接过去,说,当年我跑到城里去淘大粪,也一定要送他去读大学,现在怎么样?他接过了烟,没有吸,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夹在了耳朵上,他想带回去给父亲抽,父亲从没抽过这么好的烟。燕云,我早就知道你行,你是咱们村罗昊之后的第二个大学生,你将来也有机会过我们罗昊过的日子。
别人也都附和,说,是呀是呀,胡家的祖坟上也冒了青烟了。看你爹给你起的名字,胡燕云,完全不像是农民。罗昊父亲咳嗽了一声,吐了一口浓痰:他俩的名字都是一个人取的。众人就问是谁,罗昊父亲指了指村子的西头。众人恍然,那儿住着已经八十九高龄的老中医,当年的秀才。
一瞬间,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如果说有什么是可以具体些的话,那就是他觉得自己也有机会娶一个罗昊妻子那样的女人,生一个漂亮的女儿,开小车回来看父母,接受乡亲们的夹道欢迎,让父亲挨个给村民们发高档香烟。或者这么说吧,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命运就是重复罗昊走过的道路。
晚上,他把那根烟递给父亲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爸,我将来要让你天天抽这个烟。父亲听了,嗷的一声哭了起来。他当时以为父亲是被自己的话感动了,或者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含辛茹苦终于看到了希望。后来等父亲死了,他再去回想那个时刻,父亲的号啕大哭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等不到每天抽这么好的烟了。父亲死在他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期中考试。那天是英语考试,考听力的时候他的耳机坏了,什么也听不见,他举手喊老师,老师拿过来一试,没有问题,可他再接过去还是没有声音。如此折腾了几次之后,老师给他换了一副耳机,还是只能听到一种沙沙响的噪音,这时候听力题已经念完了,他只好随意蒙了几个答案。但是后来试卷发下来,他的听力题竟然是历次考试中得分最高的一次。
他给家里写信,说自己期中考试成绩有所上升,终于突破了班级的中线,他们班有七十个人,他一直是在三十五名之后,这次考了三十名。他还说,自己接了三份家教,已经能把生活费赚出来了,不用家里给他寄钱了。他的学费是贷款的,生活费也可以自己解决,这让他很自豪。就算是上大学的时候的兼职,他一个月也比村里种地的堂兄弟们赚得多。
寒假回家,他走进家里的时候没有人,他喊父亲,又喊母亲,屋子空荡荡的,连个回音都没有。这时候西院的邻居走进来还一把斧子,看见他愣在了那儿。他问邻居知道自己父母去哪兒了吗,邻居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来,放下斧子急匆匆走了。
不一会儿,母亲背着一篓子从田野中拾来的柴火回来,看见他,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我爸呢?他问。他省吃俭用,用自己做家教的钱给父亲买了一条好烟,罗昊父亲发的那种,一条烟花了他两百多,一个月的生活费。他从包里把烟掏出来,说这是给我爸的。母亲说,你爸抽不到了。他蓦然一惊,问怎么了?
你爸……没了。
母亲告诉他,父亲临死前叮嘱了,不告诉他自己的事,既不想让他因此耽误学业,也不想他跑回来浪费几百块车费。母亲说,其实你第一年复读的时候,父亲就查出了不好的病,但是没有跟他讲,讲了也没用,徒增烦恼,听说花几十万是能续几年命的,家里不可能有几十万,就算有,用来换几年命也不值。他们打听了,花了钱也不一定治好。他于是明白那天父亲的痛哭的缘由。
天色晚了,但他坚持要去坟地看望父亲。母亲要陪他,他拒绝了,他不想让母亲看见自己悲伤的样子。
事实上,他有点多虑了,等他走了半个小时,走到父亲的坟地所在的山坡时,太阳已经落到了山下,大地被黑暗笼罩。好在这一天的月亮还算亮,挂在夜空里,努力用自己借来的光照着大地。
他跪倒在父亲的坟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悲伤,甚至没有掉眼泪。他把那条烟全部拆开,一根接一根地点着,然后绕着父亲的坟头摆成圈,最后留下一根,自己蹲在那里吸。他想这样可以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陪父亲抽一支烟。这一次拜祭,让他的心越发坚定,我一定要成功,他想,要成为罗昊,不,要成为比罗昊还要牛逼的人。
他的烟瘾,就是从这一次开始染上的。
2
从此之后,时间仿佛加速了,他很快就到了毕业阶段。他拼了命,才留在了北京城,到了北京延庆的一所中学做了老师。虽然是学教育的,但他们同学中做老师的并不多,因为他们没有专业,不像学英语、历史、化学的,中学里都有一门课程对应着,学教育的去给学生讲什么呢?只能去行政岗,做教务或者后勤。
他其实是很不甘心的,因为他想过考研,罗昊要不是念了研究生,根本不可能分到国土局,也就不可能后来当市长。可是自己的成绩在四年里最好的一次就是第三十名,英语也不好,考研基本没什么希望。还有就是,他本科贷款的一万块钱学费,从下半年开始必须给银行还钱了,一个月两百多。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似乎早就偏离了重复罗昊的那条路,或者说,他根本就没在人家那条路上出现过。但他还抱着希望,就像偶尔从电视里看到的赛车那样,在一个弯道加速超车,最终夺取冠军。机会并没有把全部的路封死。
每当在办公室处理文件或表格到深夜时,他都会回溯自己的人生,越来越确认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等着上大学的那段时间是最美好的日子。他会陷在回忆里几分钟,然后揉揉眼睛,打一杯开水,点一支烟,继续整理文件和表格。
工资不算多,还完贷款,再除去给母亲的生活费和自己的生活费,每月还能攒下五百块钱。好在学校提供了单身宿舍,要不然这五百也得交了房租。但是烟钱似乎越来越费,一开始他一天都抽不了几支,现在每天至少要一包,而且他只抽当年给父亲买的那种烟。工作后他了解到,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烟,连中档都算不上,但相对于他的收入来说,却不算便宜。他有一种幻觉,他吸的每一支烟都像是替父亲吸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兑现答应过父亲的事。
另一个让他烦恼的,是同事小丛,那个办公室里和他同年入职的女孩。他有点喜欢这个女孩,因为她看起来跟记忆中的罗昊的妻子有点相仿。可能并不太像,只不过有一次他早晨上班的时候,小叢刚好坐父亲的车进校,就坐在后排,正巧用润唇膏在涂抹自己的嘴唇。这个动作一瞬间把他带回到了当年的记忆中,他认定这是一种预示,提醒他不该忘记当年所想象的未来生活。
他觉得小丛对自己也充满好感。那次之后,他曾问过她,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润唇膏,是否好用。小丛很积极,把自己的润唇膏拿出来,说给他涂一点试试。他有些不知所措,怯懦地说男人怎么能用这个。小丛笑话他,说现在男人都用,还做面膜呢,然后拧开唇膏,涂在他的嘴唇上。他感到一种很腻人的香甜味,瞬间想起,这支润唇膏不久前才在小丛的嘴唇上涂抹过,心跳就加速。他觉得自己似乎借着唇膏吻到了小丛,开始满脸通红。还有他们去食堂吃饭,小丛会把自己餐盘里的肉夹给他;她有任何困难,都第一时间找他帮忙。他并不确定小丛喜欢自己,但基本确定她不讨厌自己。他渐渐掌握了小丛的基本情况,她就是延庆人,在一所市属大学毕业后,借父亲的关系进了学校。他父亲是延庆一个什么局的副局长,没有太大的实权,但大小是个官,有自己的人脉;母亲也是公务员,不过开了长期病假,很少上班。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家庭。
在判断了几个月之后,他决定试一试,向小丛表明自己希望两人更进一步,成为男女朋友。他的表白技巧很普通,但也不算太差。那天是小丛的生日,她请同事们出去吃火锅,之后他送她回家。在路上,路灯昏暗,晚风轻拂,所有的事物都轻声细语般温柔。我想每天都送你回家,在你家楼下,他跟小丛说。什么?她喝了点酒,有点没明白他的意思。我是说,我喜欢你,我想每天都送你回家。他也喝了点酒,终于直接说出来这句话。
小丛并不感到意外,她甚至笑了一下,说:这样啊。就上楼去了。
她只说了这三个字,这样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第二天在办公室遇到,她还和以前一样,说说笑笑,仿佛他的表白根本没发生。他自己都有点怀疑了,怕是喝多了酒之后的醉梦或幻想,可是他翻看了那天的日记,白纸黑字记着这件事呢,还画着大大的三个问号。
小丛没有给他任何明确的答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种心绪影响到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他提供给校长的一个有关高三年级的成绩统计表格,出了个大纰漏。校长把他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而且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当着所有同事的面。他非常受伤,但并不恨校长,他是气自己,这只能是活该。他反而有点埋怨小丛,认为都是她的模棱两可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的,但他的反击只是尽量回避她。不知道小丛是迟钝,还是怎么,一周后她才反应过来他无声的反抗,在午饭的时候特意坐到他旁边。你是在故意躲着我吗?她说。他不说话,只是低头对付自己餐盘里的地三鲜和西红柿炒蛋。啊,不会吧,你那天是认真的?小丛又说。他吃不下了,端起餐盘到垃圾桶那里,把饭菜全部倒掉,直接走出了食堂。
小丛追了出来,在他身后大声说:喂,燕云,我以为你是在开玩笑,我的朋友经常这样开玩笑。他心里冷笑一下,转过身说,是啊,是啊,我就是在开玩笑。他还是抛下她走掉了。
他在一个酒馆喝了半夜酒,花生米吃掉了三盘,思前想后,甚至都考虑辞职了。他前几天查过,自己的存折里有一万块钱存款,不多,但能保证自己几个月饿不死。他想干点别的,离开这个地方。但最后还是没勇气,醉醺醺回家的路上,他给小丛发了一个短信,说不好意思,我把玩笑当真了,你把真的当玩笑了。小丛回了一个字:哦。
第二天起晚了,头还疼,他没吃早餐就去办公室。一切都没他想得那么严重,他忽然间有点顿悟,不管什么事,你只要第二天还是按照前一天的节奏去过,它就能过去。他跟小丛的关系又开始正常化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不过他开始在宿舍里看一些三级片,自慰,一次又一次,有时候他也会把电脑上赤裸着呻吟的女性想象成小丛,想象成他认识的所有女性,甚至是罗昊的老婆。他对她的印象早就模糊了,唯一清晰的是那只拿着润唇膏的手和红润的嘴唇,所以在他意淫的想象中,女人們都是在给他口交,他的阴茎是一支巨大的润唇膏,不停地把那些蛋白质为主的液体涂抹在她们的嘴唇上。
有时候,阴茎变成一支点燃的烟,叼在她们的嘴唇上。他在变态的快感中,感到下体一阵灼痛,只有这种痛才能把他从迷狂中唤回来。他把手机里保存的小丛和其他女性的照片打印出来,装订成册,每一次幻想的时候,就调出一张来。每次这么干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点像古代的皇帝宠幸后宫的妃子。
最开始,他还保有一种强烈的道德感,在第二天看见自己意淫过的女同事,会脸红心跳,觉得她们知道了自己的秘密。但是他很快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她们只是一些幻影,他想,我也是,我们活在幻想的空间里,没有一条法律规定我不能使用自己的幻想。他也会有点悲哀地想到,他唯一能左右的只有自己的幻想了。
这一切是被一个意外事件打破的。
秋天的时候,小丛有三天没来上班。他给她发了短信,没有回,打电话也没人接。他觉得小丛可能不告而别了。
他在复印室复印要发给老师们的学习材料,警察走进来把他带走了。在派出所里,他们问了他过去几天的行程,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小丛没去上班,是因为在三天前的晚上,她在回家的路上被人强奸了。警察从他的宿舍里搜到了那些淫秽的光碟,还有他制作的那个相册,确认他是最大的嫌疑人。他被带走后,学校里就传言他是个变态,强奸了自己的同事。但是警察很快把他放了,因为他们从小丛的内衣上提取的精子的DNA和他的对不上。
他回到办公室等着,但小丛再也没回来。半年后,他也被解雇了,理由是消极怠工引发了教学事故。一次很重要的考试,他把应该带到学校的卷子忘在了家里。他没有做任何解释,收拾了东西,离开了延庆,从郊区到了城里。
3
三年后。
胡燕云走在人大西门外面的路上,背着巨大的双肩包。背包里是一大摞考研资料,不过并不是他自己考研,而是去见一个学生。胡燕云现在是中关村各大考研培训机构的一个工作人员,他通过到各个高校刷小广告,在各个高校的论坛发广告帖,在学校食堂门口发传单,再加上用QQ群等宣传,已经成了公司的销售标兵。仅这半年,通过他报名考研班的就有五百多个人。当然,他的提成也很可观。为了工作方便,他在双榆树的一个老旧小区里租了一间房,不到八平方米,每个月不含水电费一千两百元。这是一个小两居,房主一家三口住大卧室,他住小卧室。签约的时候房主说,你最好不自己做饭,如果要做饭,煤气费每个月多交二十,而且只能等我们做完饭了再做。他连忙说,我就一个人,不做饭,主要是找个住的地方。
其实中介还介绍了比这条件好的一间房,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因为他从门缝里瞥到了房主的女儿。小女孩还不到十岁,跟当年他见到的罗昊的女儿差不多大,就那么一瞬间,他就决定租下了。
第一天住进去的时候,两家人都静悄悄的,有人去厕所都蹑手蹑脚,好像生怕惊动了对方。他躺在占了屋子一大半地方的小床上,发现了这个房间的另一个好处,那扇小窗子外面就是一棵槐树的树冠,时节正是春散夏来的时候,即将绽放的槐花已经发出了诱人的香味。偶尔,他还能在树影中瞥见一星半点的月亮。那个有关未来的幻想,再一次从心头浮了出来,他忍不住坐起身,点燃一支烟,把窗子推开一点,让微风吹进来,随手把烟灰弹在窗外。
轿车,妻子,女儿,响彻全村的鞭炮……让他着迷的似乎不再是这些了,而是当年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一切都充满希望,都值得奋斗的感觉。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起了小丛,心里多少有点负罪感,觉得自己好像是那个强奸她的人的影子。
他开始充满一种异样的斗志,每天除了睡六个小时的觉,都是在工作。他推销出去的课程数量直线上升,半年后,就被破格提拔为项目经理,专门负责公司在天津高校的招生工作。他开始频繁往返于天津和北京,每周都要去三四次。偶尔,他会感到头晕或恶心,他知道自己有些太拼了。但看着银行卡里的数额不断地增长,他不想停下来,目标从来没这么明确过,他要赚钱,赚足够的钱。至于赚钱之后干什么,他还没好好想过,只是单纯地喜欢看存款数额飞速增加。
他再也没看过黄片,也没自慰过。每一次他刚要开始,小丛的脸就会浮现,说:小胡,是不是你?那天晚上伤害我的人是不是你?他便兴味索然。只有烟抽得越发的勤,价位也越来越高,他因此得了咽炎,但还是继续抽。
虽然每天晚上都住在租房里,可他几乎很少见到房东一家人。他回去的晚,上楼前先在成都小吃或沙县小吃吃个饭,上楼的时候他们似乎都睡着了。他家客厅里的电视,很少打开,对于这家人,他听到的最多就是他们出来倒水、上厕所的声音。极少的几次,他正面看到了这家的小姑娘,戴着一个牙套。原来小姑娘有些龅牙,特别是张嘴说话的时候,门牙和粉红的牙龈明晃晃地露出来。有点像马,他不太厚道地想。你好,他跟小朋友打招呼。小朋友有些吃惊,小声地说了句你好,就飞快地逃回了他们的房间里。
他想,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可能不这么安静,应该和别的家庭一样,看看电视,聊聊天,做做小游戏,其乐融融。有一次,他回来得早一些,刚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屋子里的声音就立刻安静下来。这更证实了他的猜测。
他万万没想到,这家人竟然救了自己。
一个晚上,他出来上厕所时头一晕,倒在了过道上。他们打了120,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给他打上吊瓶,第二天又做了各种检查后告诉他,好像内分泌有点问题,血糖高。他没当回事,第二天买了好多水果回来,感谢这家人。男主人把水果从门缝里接了过去,递出来一张单子,是120的钱和药费,他赶紧掏钱包。男主人摆手说,不急,和下个月的房租一起付吧。
从这次开始,他们的关系开始慢慢热络了些。有一天,他们还在厨房留了半碗炒饭,他知道这是给自己留的。他就着烟,把半碗饭吃掉了,然后回到厨房把碗洗了。第二天回来,他就放了半个西瓜在冰箱里。来来往往中,气氛开始变得随意起来,特别是小女孩,偶尔会跑到他屋里来问一个问题。她的数学作业,父母完全帮不上忙。
他又晕倒了一次,不过不严重。他不得不去医院里看一下了,房主建议他去看中医,他就坐地铁去了西苑醫院。大夫给他开了中药,让他先吃一个月再说。他拎着一大袋子已经熬成液体的汤药,走在路上就忍不住喝了一袋。忍着反胃喝完了中药之后,他没找到能漱口的水,就一直带着满嘴的药渣味走回家。一开始,这味道是苦、涩,似乎有很多草根的味道,可是后来随着唾液的不断分泌稀释,好像也发生了什么神秘的反应,味道开始泛出一阵甜味,嗯,有点像他小时候吃的甜草根。甜草根也是一种中药,在村子后面长得漫山遍野,这种东西的根茎似乎是直直插入地里的,很难拔出来。田地旁边有一些山洪冲泻出来的沟壑,都是黄土,沟壑壁上裸露出许多甜草根来,他们只要揪出一头猛扯,就能扯下一米长的甜草根。这种东西据说是降火的,带着一种药的甜味,他跟小伙伴们经常会咀嚼一段。糖太稀少了,他们唯一能以甜的名义摄取的糖分都是从山野中来的,甜草根,秋后的玉米秸秆,一种酸巴溜,各种野果子。他们那儿的自然界似乎没有纯粹的甜,所有的甜里面,要么掺杂着苦,要么掺杂着涩,要么掺杂着酸。
这是一个大玩笑,他又拿出那张化验单来看空腹血糖12.9,超标了一倍还多。
毫无疑问,医院里的大夫跟他说,糖尿病,不用再做其他检查了。
可我才二十五岁。
是,年纪还小,按说不应该,你们家族有糖尿病遗传病史吗?
他只能摇摇头,事实上,他们家没有任何遗传病史,这么说不准确,不是没有任何遗传病史,而是就他所知除了高血压和感冒,他们家的人不知道自身病痛的任何名字。那些病都只是一种感受,一种生活命名,腰疼,头疼,腿疼,肚子疼,没劲,恶心,眼花……
他回想了一下,自己的日常饮食似乎也并没有摄入多少糖,虽然现在他有工资了,要吃糖完全可以随意买了。大夫告诉他,糖尿病病人在上午十点多的时候,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他想起来了,自己的两次晕倒,确实都是在上午十点?左右。
他按时按量吃完了一个月的药,再去检测,血糖还是高,就又吃了一个月,还是高,但他的精气神似乎恢复了,也没有再晕倒。过了一段时间,业务又忙起来,他就把吃药的事情忘记了。那一段,北京的房价因为政策调控,停止了疯狂的增长,甚至有一部分有所下降。他刚好纳税五年了,有了买房资格,盘点了自己手里的钱,大概四十万左右,又算了一下今年的年底分成,有五万,火速找中介在地铁十三号线的天通苑站三公里处贷款买了一个小一居。贷款五十万,每个月还三千多。
过户那天,他没有想象的激动,因为昨天晚上他加入了一个房子所在小区的QQ群。群里都是业主,全是报怨小区物业的,很多人都后悔买了这里的房子。他觉得自己有点冲动了,应该再看看其他地方再做决定。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他就想,买了就买了,反正自己还是租住在双榆树那里,天通苑的房子是肯定要租出去的,交给中介,也不用太操心的。
让他操心的是另一件事,母亲在老家犯了一次心脏病,差点死掉。他没办法,只好把母亲接到北京了,这样租住的那间房子就不够住了。他得租一个大点的房子,还得能做饭。
那天晚上,他敲了房东的门,门开的时候,他看见三个人正在写字台上吃饭,一盘西蓝花,一个排骨,三碗米饭。吃饭呢?不好意思,有点事。房东有些尴尬,问你吃了吗?他还没吃,但赶紧说吃过了。房东问他什么事,他说了母亲的事,自己可能得提前搬出去,有点违反合同,想商量一下违约金能不能少点。房东有些发愣,你要走了?他点点头,说我妈来了,这里住不开了。房东说,等会吧,我们商量一下,就关上?了门。
他就回到自己房间里,靠着窗台抽烟,把烟灰弹到窗外。这时候是秋天了,再有半个月就十一了,但气温还是很高,好在开着的窗子能透出些风来。他已经做好了打算,如果房东愿意,他可以掏半个月的违约金,一周内搬出去,他们也能早点找到下一任租客。如果房东坚持一个月的押金一点都不退,他也只能认了。
半个小时后,房东在门口喊他:胡先生,你出来一下。
他推门出去,惊讶地发现一家三口都在客厅里。房东指了指沙发,让他坐,他有点犹豫地坐在小沙发上,他们三个则各自坐了一把小凳子。
我们商量了,押金都退给你,违约金也不要你缴了。房东看了一眼妻子和女儿说。
啊?这让他有点出乎意料,这样不太好吧,是我违约,我总该出一点钱的。
房东说,不用了,我们家里情况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小的房子还租出一间,你是五年来最好的一个租客,从来没给我们添麻烦,所以我们不要你的违约金了。
这样,但是……我还是要……
胡先生,真的不用了。女主人说。他很少听到她说话。
那好吧,谢谢你们,实在抱歉,如果条件允许,我肯定会继续住下去的。
房东找出两张纸来,简单写了一个终止租房的协议,签了字,每人拿了一张,这事就算结了。
他准备第二天搬家,这是他在这里的最后一晚了。
4
母亲到的那天晚上,他本想带她出去吃饭,可母亲说坐了一夜车,累了,就在家里吃。他觉得也好,就去超市买鲈鱼和青菜,蒸一条鲈鱼,炒一个青菜,再做一个西红柿鸡蛋汤,两个人就够了。母亲一辈子吃得清淡,肉的话只喜欢鱼,他知道的。鱼得买活的,鲈鱼好吃,可是比草鱼鲤鱼白鲢贵得多,但这是母亲到北京的第一餐饭,总要吃一点好的。
搬来的第二天,他已经调查清楚,这附近的几个超市里,只有街对面的那家有活鱼卖。他让母亲先休息会儿,自己拎着一个袋子去超市。
他经过水族箱的时候,平时卖鱼的工作人员正在从里面捞鱼,捞出一条,猛地掼在地上摔死,然后再捞一条摔死。一条鱼突然从里面飞了出来,“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一个工作人员看了看,并没有停下手来去捉它,而是继续对付水族箱里的鱼,捞出来,摔死。那条鱼就一直在地上摆着尾巴,好像要逃脱被摔死的命运,每一次摆尾,身体都有移动,但下一次摆尾又移动回来。他忽然笑了一下,想起了大学时哲学老师讲的西西弗斯,就那个整天把大石头推上山,然后石头自己滚落,他再推,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那个人。那时候,他觉得哲学挺无聊的,可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了点,哲学还是有用的,至少对一条鱼来说是这样。
他想让工作人员留一条活的给他,工作人员却说,所有的活鱼都不卖了,要买买死鱼。
为什么?
工作人员一耸肩,我哪儿知道,我只知道经理下了死命令,活鱼必须弄死,然后冷冻起来,一条都不让卖了。
最后,他只能买了一条更贵的海鲈鱼回去,死的。
他已经很久没有做过饭了,之前在双榆树那里住,从没跟房东抢过厨房。他把清理好的鱼带回去,母亲说她来做饭,他说自己做。母亲说,妈妈没事,做个饭还是可以的,他只好从狭小的厨房里出来。
后来他刷朋友圈,看到新闻说那一天,几乎北京所有的超市都没有活鱼卖了,有人说是因为活鱼运输途中为了保鲜,使用了某种有毒的化学物质;也有人说是因为食品检测部门要展开一次水产品检查,超市们都对自己进的鱼没信心,所以全部下架。
吃饭的时候,他偶然说起超市里的事,母亲说咱们那儿吃的都是死鱼,怕什么。他说今天这条是海鲈鱼。母亲顿了一下,叹气,说我知道,我刚才看见标签了,一条鱼五十几块钱,好贵。你就放心吃吧妈,吃条鱼我们还是吃得起的。母亲又问他房租多少钱,贷款月供多少钱,问一次,叹一次气。
母亲收拾碗的时候,他拿出五百块钱,说:妈,生活费给你,你来了,我就每天回来吃饭了。
母亲说不用的,我这里还有一點钱。
他塞到母亲手里,说:你的钱能有多少,攒着吧,还有下周我带你去医院再查一下心脏。
母亲连忙摆手:不要去,我在镇子上已经查过了,是先天性的心脏病,治不了的,做手术好贵,而且不见得好。
他没再坚持。
母亲说,妈只是惦记着一件事……
他知道是什么,他的婚事,这年头所有的家长都在担心儿女的婚事,没对象的着急,有了的没结婚着急,结婚了没孩子着急,有了孩子不和睦还着急。
他永远都不可能想到,这竟然是自己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谈话。第二天,他敲母亲房间的门,没有回应,他想可能母亲还在睡,就自己出去买了油条和豆浆,吃完了,母亲还没有声音。他推开门进去,看见她在床上蜷缩成一团,已经没有了呼吸。后来医生检查说,母亲在晚上心梗发作,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她在这痛苦的二十分钟里,竟然没有喊过一声,她以为可以和其他所有腰腿疼一样,只要忍过一阵就没事了。
他有点不知所措。还是医院的人指导着他,找了专门做丧葬服务的人,把母亲的后事办了。告别仪式上,丧葬公司的人说,就你一个人?他点点头,一个人把母亲送走了。
随后,他跟公司请了几天假,把母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去,跟父亲合葬了。
5
都快晚上九点钟了,他才走进了饭店,看见约的人已经到了,穿一件粉红的毛衣,头发有点像假发,在十三号桌坐着。桌上已经摆满了菜,他坐下,拿起服务员贴在桌边的点菜清单看了一眼,二百多,有点小贵。
红毛衣有点抱歉地说:不好意思,等你来,我先把菜点了,我不点菜服务员就跑来念叨。
没事没事,挺好挺好,他说。
路上有点堵吧?
嗯,是我对不起,我来晚了。
嗨,在北京晚到太正常了,咱们边吃边聊吧,提前约定一下,谁也不用让谁,也不用瞎客气,权当是两个人的自助,行吧?
这样好,我完全同意,反正吃饭不是主要?目的。
你来的时候没戴口罩?
没戴,不习惯,闷得慌。
得戴着呀,今天污染指数都爆表了,戴上总比不戴强。
算了,我觉得中国人要想活下去,只能靠自我进化了,别的什么都没用。
哈哈,你挺有想法。
到现在为止,他都对这个见面很满意,对方看起来很真诚,也很放松。这很好,他想,而且谁也不用照顾谁,各吃各的。
红毛衣夹了一筷子糖醋排骨,放在嘴里嚼着说:我们家那位,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你要再踹一脚,就踹死了。对我倒还行,情人节圣诞节结婚纪念日,都不忘了买个小东西讨我高兴,东西不贵,但他能惦记着,让你觉得是一种安慰。
嗯,他迎合着,挺好的。
红毛衣继续吃糖醋排骨。他有点惊讶地发现,红毛衣似乎非常喜欢酸甜口味的菜,除了糖醋排骨,还有菠萝古老肉,宫保鸡丁,糯米藕,酒酿丸子,唯一其他口味的菜是花生米。
红毛衣突然停住口,说:是不是我点的菜你不喜欢?你可以再点几个喜欢吃的,钱不是问题的,对了,再要点啤酒吧,你们男人一般吃晚饭不是总要喝点的么。
这些菜他确实不能吃,因为他那个怎么也降不下去的血糖,他必须控制甜食。他跟服务员要了菜单,只点了一条清蒸鲈鱼,啤酒,犹豫了半天,还是没要。他觉得没必要喝酒,吃饭也是次要的,他来这,就是想跟她好好谈谈。
鲈鱼上来的时候,她正跟他说自己小时候的事。在我们老家,她说,每一次有人结婚的时候,都要在夜里摆一桌宴席,我那时候最喜欢这种宴席了。我们小孩子,可以不用那么早睡觉,还能吃到各种好吃的,哦,我也喜欢看着大人们围坐在桌子上,男人们划拳喝酒,女人们就说三说四。后来我离开老家,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的宴席。
你老家是哪儿的,他问。
南方嘛,就是南方嘛。
他想她可能不太愿意告诉自己太多具体的信息,刚才说的有关她老公的那些话,也可能不太准确。无所谓了,我们本来也不是为了调查对方而来的。
接下来,他跟她说了自己当年看见罗昊的妻女的那件事,说得特别详细,还有小丛的事。最开始,她还笑话他,说他太幼稚了。等听到小丛被强奸的时候,她不笑了,愤怒地拍着桌子:阉割,这样的坏人就应该阉割,而且不要用医生,就找我老家劁猪的兽医。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有些过了,便指着鲈鱼说,翻过来吧,另一面还没吃呢。
他们两双筷子合力把鲈鱼翻了过来。
各自又讲了不少事,结账的时候,竟然刚好二百五十块钱,两人听了都笑了,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收尾了。各自付了一半,他们就出门了。
回到家之后,他躺在床上,把手机里的约饭APP卸载了。
他跟红毛衣完全不认识,是通过这个软件才约上的。有一天,一个群里有人推荐这个软件,说注册后可以随即约到一个饭友,然后系统会随意选一家饭店定位子,两个陌生人在一起吃一餐饭,互相说话,AA制,等结束后,系统会自动注销两人的ID,也就是除非他们自己要互相留联系方式,否则他们再也不会联系了。
他其实早就下载了软件注册了,前两次系统都给他约好了人和地点,但是他临阵退缩了。每个身份证号只能约三次,第三次他不想浪费机会,赶着来赴约。
现在,他住在了自己在天通苑的房子里,房子不大,还是显得空荡荡的。他没买电视,也没买冰箱,甚至厨房里也只有一只锅和一副碗筷,偶尔在深夜煮个泡面而已。他不做考研培训了,现在是一家民办教育在天通苑地区的课程经理,单位很近,从家里走过去只要五分钟。但是在天通苑那些成千上万栋面貌相似的楼宇之间,他常常迷路,绕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自己家那个小区的门。有几次,他按照手机地图上的导航,都没回得了家。
后来,他花了一个月的四个周末时间,用脚步把天通苑的所有小区都走了一遍,自己画了一个简易的地图,从此再也没有迷路过。
跟红毛衣约饭回来后,他很快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像那条超市里逃跑的鱼。当然跑不掉,但是要逃,在水泥地上拼命摇着尾巴,那声音听上去,好像一个悲伤自责的人在使劲儿抽自己的耳光,啪,啪,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