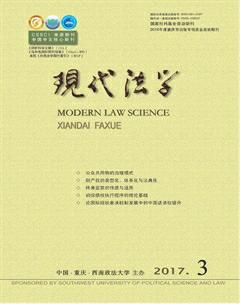故意伤害“轻伤与否”定性共识的刑法质疑
石经海
摘要:故意伤害需“轻伤”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是理论上和实践中几乎不受质疑的“共识”。然而,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定性尴尬情形表明,如此“共识”实际上是片面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主要在于没有真正认清刑法总分则的系统关系及其所决定的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继而造成对个案适用法律的不完整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由此,故意伤害罪是否以“轻伤与否”作为定性标准,不能一概而论,需基于刑法总分则关系的系统化理解,将其置于个案完整法律评价体系进行具体考察,其中,对故意伤害“轻微伤”案并非都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对故意伤害“轻伤”案并非都成立犯罪。
关键词:故意伤害;轻伤;总分则关系;规范实质;完整法律适用
“打假斗士”方舟子等被报复伤害案早已成为过去,但本案因其故意伤害为“轻微伤”从而不以故意伤害罪却以寻衅滋事罪追诉处理的定性颇为尴尬,至今未能消解。其引发对故意伤害需“轻伤”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共识的刑法质疑以及在个案法律适用上因片面理解和适用了刑法总分则关系而带来完整法律适用上的担忧。基于刑法总分则关系的系统化理解与完整法律适用,对于故意伤害未达到“轻伤”的情形,在通常情况下确实因其可以被评价为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从而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但这并非当然意味着所有故意伤害未达到“轻伤”的,都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司法实践中诸如方舟子等被报复伤害案的定性尴尬,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一、故意伤害“轻伤与否”之定性共识与尴尬
(一)故意伤害“轻伤与否”之定性共识
在我国实践中和理论上,对故意伤害需致“轻伤”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是几乎不受质疑的“共识”。然而,据笔者进行的立法和司法考证可知,如此“共識”其实除了在2005年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29条有规定(即“被害人伤情达不到轻伤的,应当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外,没有其他任何立法、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直接依据。据我国《刑法》第234条第1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立法对故意伤害罪基本犯的客观方面要求是“伤害”,而不是“轻伤”,也未将“轻微伤”当然排除在外。
事实上,要求“轻伤”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将“轻微伤”排除在以上“伤害”之外,并不是立法上的规定,而只是理论上和实务中基于“情节显著轻微”评价形成的“共识”而已。我国早期的刑法学教材就认为:故意伤害罪的“伤害”程度,只包括“轻伤、重伤和伤害致人死亡三种情况”,而不包括“轻微伤”,轻微伤情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对这些行为,“采取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或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解决,不以伤害罪论处”。以上这一通说性认识,一直未受到刑法理论和实务界的质疑,并沿袭至今,甚至在当前各刑法教材、权威性刑法工具书和相关实务手册中,直接把“轻伤与否”作为故意伤害罪基本犯成立与否的评价标准,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伤害结果的程度分为轻伤、重伤与伤害致死”“有些殴打行为表面上给他人身体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是显著轻微,即按照《人体轻伤鉴定标准》不构成轻伤的,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无论在理论界抑或实务界,非法伤害行为致人轻伤以上损害的,才按犯罪处理”,无论是刑事公诉还是公民自诉的伤害案件,只有经合法程序鉴定取得轻伤以上的伤情鉴定结论,法院才予受理。
(二)故意伤害“轻伤与否”之定性尴尬
对于以上“共识”,在案件案情被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情况下,其显然是无可置疑的。但若案件案情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则会遭遇定性上的尴尬。方舟子等被报复伤害致“轻微伤”案,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0)石刑初字第333号《刑事判决书》所述,本案是由于被告人肖某因方舟子、方玄昌等人质疑其学术成果而不满等恩怨,继而雇人持铁管、铁锤、喷射防卫器先后殴打方玄昌、方舟子,致方玄昌头皮血肿、多处软组织挫伤、头皮裂伤,致方舟子腰骶部皮肤挫伤的行为。对于如此行为,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但在侦查中因伤情鉴定是“轻微伤”而改以寻衅滋事罪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做出判决。
本案以上仅因是“轻微伤”而不是“轻伤”而变更罪名的做法,实际上是无奈和尴尬的。其一,本案是基于特定报复内容、特定报复对象实施的报复伤害行为,属于典型的故意伤害行为,在情节符合刑法规定和要求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这一点,也为公安机关在伤情鉴定结果出来前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的现实所呈现。其二,在伤情鉴定为“轻微伤”而未达到“轻伤”程度后,就遇到了尴尬。一方面,本案的案情和社会影响均较为恶劣,其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完全达到和符合《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成立的要求和第234条等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基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不可能不定罪处罚,可另一方面,因其“伤害”未达到“轻伤”,而按前述“共识”,又不能以故意伤害罪处理。其三,基于如此尴尬,办案机关误认为可以按《刑法》第293条关于“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寻衅滋事罪立法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对行为人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做出判决,可殊不知,这一定性改变的唯一根据实际上只是伤害程度的不同,从而使得“轻伤或是轻微伤”成为了在“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这类行为上界分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唯一根据和标准,即若为“轻伤”就定故意伤害罪,若为“轻微伤”就定寻衅滋事罪,进而让这一定性陷入在立法、司法和理论上都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更大尴尬。
事实上,从立法上看,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在“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这类行为上的定性界分标准是多方面的。按刑法理论的通说,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从其成立条件来看,它是故意损害刑法所保护的个人身体健康权即个人身体法益的行为。这与既故意侵犯刑法所保护的个人身体健康权又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公共秩序的“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罪,明显不同。申言之,“殴打他人”的客观行为要成立寻衅滋事罪,需在主观方面具有“随意”性,即“耍威风、取乐等目的下的无故、无理”和在法益侵害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公共秩序)”。虽然在理论上认为,“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行为,可基于想象竞合犯的“从一重罪论处”定罪规则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那些具有明确指向的、故意损害刑法所保护的个人身体健康权的行为,按罪刑法定原则关于严格依据立法关于犯罪本质特征及其构成要件等的定罪要求,只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以上情况表明,虽然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也有竞合方面,但是“轻伤”还是“轻微伤”在“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这类行为上不是也不应当是界分二罪的真正标准。以不是真正界分标准为标准,去界分二罪和做出定性,不仅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而且也会带来司法定性的混乱与司法公信力的受损,继而带来定性上的尴尬。
也正是如此之“尴尬”,本案的定性引发了包括被害方和被告方双方质疑在内的诸多争议。就被害方而言,他们认为“本案这些被告人他们蓄谋已久,犯罪对象明确,而且确已对受害人实施了持械向头部袭击这样严重的伤害行为”“如果警方取得了被告人故意杀人意图这方面供述的话,这个案件应该按故意杀人未遂处理;如果确实刑事被告人未供述有任何杀人意图的话,那么此案应该按故意伤害案件处理”。就被告方而言,辩护律师认为:“肖某就是要故意伤害方舟子”“现在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就偏离了法律的轨道”;被告人肖某在法庭上也强调:“我就是故意伤害,不是寻衅滋事,我根本没想通过殴打两人,来让全国的质疑者闭嘴”“我明明是要报复他们两个人才实施的故意伤害”。不仅如此,更有实务界人士质疑:“方舟子所说的故意杀人虽然还可以商榷,但是却比检方提出的寻衅滋事更靠谱些”。
二、刑法总分则关系下故意伤害“轻伤与否”的定性尴尬分析
以上故意伤害“轻伤与否”的定性尴尬(以下简称“以上定性尴尬”)表明,对故意伤害需致“轻伤”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的“共识”是片面的。究其缘由,主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没有真正认清刑法分则罪名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和很好贯彻刑法总分则的内在关系,继而带来个案的不完整法律适用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
(一)刑法分则的规范实质及其与刑法总则的内在关系
从立法来看,刑法分则关于罪名条文的规定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刑法规范。从其构成内容来看,它只是关于具体犯罪定性处罚的部分犯罪构成要件规定和部分刑罚处罚配置而已,并没有对具体犯罪成立的全部构成要件和需适用的全部处罚方法(刑罚处罚、非刑罚处罚、不给任何刑罚)做出规定。具体表现在,我国刑法分则关于罪名条文的规定,一般包括罪状与法定刑两个部分内容。其中,罪状是关于该抽象个罪成立的部分要件规定,法定刑是针对该抽象个罪(含基本犯、加重犯、减轻犯等)所应承担的基本刑事责任所做的部分刑罚配置。这里的“部分定罪要件”和“部分刑罚配置”意味着刑法分则关于罪名条文的规定,并不是对该犯罪定性处罚、法律适用的完整刑法规范。对于决定抽象个罪成立与否的全部构成要件及其所应承担的全部刑事责任的刑罚配置,即能评价一个行为是什么和如何处罚的完整刑法规范,需要刑法总则“指导”下的刑法总分则的所有相关规定体系化地完成与实现。其中,在刑法分则规定在总则“指导”下而不符合总则规定时,需要刑法总则规定予以补充、限制甚至修正。否则,就会因法律适用不完整而导致该罪定性处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首先,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用以个案定罪量刑评价,需总则视情况予以“补充”。例如《刑法》(分则)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即“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只规定了部分定罪要件和刑罚配置,需要刑法总则的规定对其犯罪主体、死刑执行制度、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有期徒刑的上限、拘役等定罪要件和刑罚配置予以补充。
其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用以个案定罪量刑评价,需总则视情况予以“限制”。例如,《刑法(分则)》第170条规定(伪造货币罪):“伪造货币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仅按照以上刑法分则意义上的该规定,行为人伪造1元货币也应构成伪造货币罪。显然,这是不恰当的,需要《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即“一切危害……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予以限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26号)也做出了相应明确规定(第1条),要求“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30000元,或者幣量在200张(枚)以上不足3000张(枚)的”,才“依照刑法第170条的规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即在司法上,并非仅依《刑法(分则)》第170条规定行为人伪造了货币就构成伪造货币罪,在客观数额上至少需伪造2000元或200张(枚)的,才构成,否则就会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再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用以个案定罪量刑评价,需总则视情况予以“修正”。例如,按《刑法(分则)》第202条规定,即“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处3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以残忍的暴力方法拒不缴纳税款,致税务人员重伤的,仅按刑法分则的以上规定,只能认定为抗税罪和至多处7年有期徒刑。显然,这无法做到罪责刑相适应,需要刑法(总则)关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规定(第5条),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予以修正,按故意伤害罪定性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于甲乙合谋抢丙财物,按分工甲故意伤害丙致重伤,乙抢夺丙财物数额较大,仅按刑法分则规定,对甲乙只能分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和抢夺罪,只有基于《刑法(总则)》第25条的规定,即“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才能将甲乙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据此而论,无论是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规定而做出一般罪或特别罪的定性,还是基于共同犯罪规定而给予的第三个罪名的定性,都是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的罪的修正。这一点,其实是刑法中所有修正的犯罪形态(共同犯罪形态、故意犯罪过程中的未完成形态和罪数形态)的基本要求和体现。除此之外,刑法总则还有对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法定刑的修正功能。例如,根据《刑法(总则)》第37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从而使得刑法分则关于罪名条文规定失去“给予刑罚处罚”的意义;根据《刑法(总则)》第63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或者“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从而使得刑法分则具体罪名条文规定的法定刑变成了处断刑。
综上,刑法分则关于罪名条文规定,在实质上并不是對该犯罪定性处罚法律适用的完整刑法规范,需要刑法总则规定予以指导,并在刑法分则规定不符合总则规定时,需要总则规定对分则规定予以补充、限制和修正。刑法总则对分则的“指导”,并不是抽象和形式上的,而是有具体的内容,即基于具体个案的完整法律适用需要而通过总则规定对分则规定予以补充、限制甚至修正。
(二)刑法总分则关系下个案的合法性评价与完整法律适用释读
前述关于刑法分则罪名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及刑法分则与刑法总则的关系原理表明,罪刑法定的“法”也并不是刑法的某个规定,而是基于个罪个案情况的所有相关刑法规定。由此决定了,定罪量刑的合法与否并非孤立地取决于刑法分则关于罪状和法定刑的某个规定,而取决于刑法总分则关系下个案的完整法律适用,即应综合地取决于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所有相关规定。具体为基于个案定罪量刑所需要和所具有的相关法律规定所形成的个案法律评价体系(系统),包括个案犯罪成立(定罪)法律评价体系和个案刑事责任大小裁量(量刑)法律评价体系。
其一,定性需基于个案形成个案的犯罪成立(定罪)法律评价体系。在司法上,罪刑法定的“法”即个案合法性评价的法律根据,并不是抽象个罪的某个抽象的规定,而是具体基于个案案情所形成的个案法律评价体系(系统)。具体是基于《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成立的基本条件规定以及由此对应的刑法总分则中所涉个案犯罪成立评价的所有刑法相关规定,如刑法分则关于抽象个罪的特别规定和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进行指导适用的原则性、补充性、限制性和修正性规定。其中,《刑法》第13条规定的只是关于犯罪成立的基本(一般)条件规定。据《刑法》第13条规定,犯罪的基本成立条件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三个有机联系的基本特征组成。基于系统论原理,这三个基本特征(基本成立条件)不是独立存在和发挥其评价功能的,而是通过形成相关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才能发挥其定性上的评价功能。如“醉驾”在《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人刑前后的“社会危害性”自身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醉驾”的社会危害性是刑法上、犯罪上的还是行政违法上的,不取决于其自身,而取决于立法是否将其入刑而赋予其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取决于立法和刑事政策是否认为其“应受刑罚处罚”而赋予其犯罪上的社会危害性。从立法上看,不仅“刑事违法性”是有立法相应规定对应的,而且“应受刑罚处罚性”也有其相应的立法规定相对应。综观我国刑法立法,大体有两大方面:一是《刑法》第5条关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规定,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如此规定意味着,虽然刑法将某个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人刑了,但对于个案是否要定性处罚,还要考察“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而决定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和是否应当将该个案认定为犯罪。二是刑法立法上规定的那些不“应受刑罚处罚”的排除性规定。综观我国现行刑法立法,对于排除性规定,除了《刑法》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这个但书规定外,还包括《刑法》第7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的三年以下轻罪、第12条规定的因刑法时间效力而不追诉为犯罪、第87条规定的因过了追诉时效而不追诉为犯罪等情形。根据以上立法的排除性规定,对于案情被评价为(属于)这些情形的,一般就被视为不“应受刑罚处罚”而不认定为犯罪或按刑法以外部门法处理。
其二,处罚需基于个案形成个案的刑事责任大小裁量(量刑)法律评价体系。具体是基于《刑法》第61条关于量刑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基本要求规定以及由此对应的刑法总分则中所涉个案犯罪人刑事责任大小评价的所有刑法相关规定,如刑法分则针对抽象个罪所配置的法定刑规定(针对抽象个罪所负基本刑事责任的特别刑罚配置)和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进行指导适用的原则性、补充性、限制性和修正性规定。自然,这里第61条的规定只是关于个案处罚的基本(一般)条件规定,基于本个案所涉总分则的所有其他相关规定,都是与其相对应的个别性具体规定。其中,据《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量刑需“以量刑事实为根据、以量刑法律规定为准绳”。这意味着,对具体个案在定性后如何处刑,既需要基于能够影响对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评价的事实以及法律基于人权保障、人性关怀、提高诉讼效率的功利目的而要求的事实;也要适用基于个案处刑所需适用的所有法律规定,包括刑法分则针对抽象个罪配置的具体法定刑幅度以及刑法总则的诸如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规定。
刑法总分则关系下的以上个案合法性评价与完整法律适用表明,刑法分则意义上的所谓行为犯、数额犯、结果犯等犯罪形态,实际上只是刑法分则条文仅就抽象个罪犯罪成立的客观方面要件规定而已,其在司法上的定性评价功能需要结合刑法总则中含“限制”、“修正”规定在内的各相关规定才能实现。理论上和实践中认为行为犯、数额犯、结果犯只要有刑法分则规定的相应行为、数额、结果就可以甚至就要成立犯罪的观点,是对以上刑法总分则关系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常识性弱视。同时,理论上关于“在已然考虑到了刑法总则对犯罪概念所要求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我们就没有必要在此多此一举地认为仍需再受《刑法》第13条‘但书的限制”的观点,是不符合刑法总分则关系的系统化理解与完整法律适用的。其势必会带来对具体个案定性处罚的法律适用不完整,继而致个案定罪量刑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被称为所谓“世纪奇案”的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案之所以陷入合理量刑困境和“醉驾”入刑后之所以出现要不要一律定罪争议,其实都是弱视刑法分则与刑法总则的以上关系所致。
具体就故意伤害罪基本犯的定性而言,《刑法》第234条第1款关于“伤害”的规定,仅是为本罪基本犯定性提供了一个个别性的客观方面要件,并不是本罪成立的全部要件,更不是刑法总分则关系下的全部相关法律规定。如此规定,其在本罪定性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发挥,需交由刑法总则关于个案犯罪成立的各相关规定进行指导性评价,包括视情况需分别接受《刑法》第13条关于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限制”评价、第17条关于是否符合犯罪主体要求(刑事责任年龄)的“补充”评价、第22条至第29条关于是否是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和共同犯罪形态的“修正”评价。前述方舟子被报复伤害案之所以出现定性尴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把《刑法》第234条独立于刑法总分则关系之外,机械、片面、孤立地理解和适用了理论和实践中关于以“轻伤”为故意伤害罪基本犯的“共识”定性标准。
三、刑法总分则关系下故意伤害“轻伤与否”之具体定性分析
前述研究表明,故意伤害致“轻伤”和“轻微伤”是否以故意伤害罪定性,不能一概而论,需基于刑法总分则关系的系统化理解以及由此决定的刑法分则规定为不完整刑法规定的规范特点,具体考察案情的定性法律评价是否符合个案犯罪成立的完整刑法规定。其中,对故意伤害“轻微伤”案并非都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对故意伤害“轻伤”案并非都成立犯罪。
(一)故意伤害“轻微伤”并非都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
基于《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成立的基本条件及其“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故意伤害罪的“伤害”在通常情况下确实需为“轻伤”。故意伤害致“轻微伤”案在通常隋况下,确实是属于那种案情被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作为民事侵权或治安案件处理更有利社会和谐稳定的情形。但这个“不认为是犯罪”的“通常情形”,其前提是轻微伤案的案情被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若故意伤害“轻微伤”的案情不能被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可能需以故意伤害罪定性。
在司法实践中,故意致“轻微伤”案需以故意伤害罪定性的通常情形是,在客观上需造成一定程度(如接近轻伤)的轻微伤害,且是在一定主观恶性支配下实施所致,如有雇凶,使用了致死伤性武器、器具、物品,打击了致命性部位,多人预谋实施等。具体就方舟子等被报复伤害致“轻微伤”案而言,综观全案,肖某等的报复伤害方舟子等并致“轻微伤”的行为,其情节是十分恶劣的。这些诸如雇佣多人蓄意准备多种致伤工具进行打击报复等恶劣情节,决定了本案案情不可能被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完全符合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刑的立法规定、司法标准和法理根据。
(二)故意伤害“轻伤”并非均成立犯罪
基于《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成立的基本条件及其“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故意伤害罪致“轻伤”在通常情况下确实需以故意伤害罪定性。但这同样只是“在通常情况下”,即在故意伤害罪致“轻伤”的案情不被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时。也就是,在故意伤害罪致“轻伤”的案情被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时,同样不能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在司法上,“轻伤”被界定为“使人肢体或者容貌损害,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功能部分障碍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中度伤害的损伤”。“轻伤”本是令人受到较为严重的伤害,但在案件定性的法律评价中,它只是案件定性中的客觀方面的一个要件而已,需结合支配故意伤害行为实施的直观故意的恶性程度等要件,才能判定其应否受刑罚处罚和是否需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理论上有观点认为,刑法分则关于人罪门槛的规定在立法时已经考虑了《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犯罪成立条件)的规定,并排除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这个但书规定情形,所以司法上在适用刑法分则规定时,就不再考虑和适用《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规定。这种观点不仅缺乏对刑法总分则关系的正确认识以及对整个刑法中规定的系统性存在的弱视,而且也是对以上关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中“情节”的误解:这里的“情节”不只是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个数额、结果、行为方式等,而是整个“案情”。刑法分则关于某个特别“情节要素”规定的评价(如“轻伤”)不能替代整个“案情”的“情节”评价。也正是因为如此,张明楷教授强调:“在解释分则时,一定要以总则中规定为指导”“对犯罪构成及其要件的解释,应以总则中的犯罪概念为指导”,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对所有案件,“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
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轻伤害案件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的情形,通常是基于被害人过错、被害人承诺、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谅解等因素,或者因故意轻伤害案件的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或者经过当地村委会、居委会或公安机关等组织的调解,从而达到减小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效果,进而可以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不是“应受刑罚处罚性”情形。这早就体现在2005年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29条中,该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规定”,“对故意伤害他人致轻伤,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应当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需要指出的是,在《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那些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关系明确、不需要立案侦查的故意轻伤害案件,可以作为自诉案件处理。但这并不是说,故意伤害轻伤害案件是可以由当事人或办案机关随意选择或任意选取为犯罪或治安案件或民事侵权案件处理,而是这些可以作为自诉案件处理的故意轻伤害案件,按《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成立基本条件的规定,因被害人的谅解(自诉中放弃刑事追诉的选择)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减小情节,而可以被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定为是犯罪。
故意伤害“轻伤”并非均成立犯罪除了以上案情被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这种常见的情形外,如前所述,还有《刑法》第7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的三年以下轻罪、第12条规定的因刑法时间效力而不追诉为犯罪、第87条规定的因过了追诉时效而不追诉为犯罪等情形。对于故意伤害“伤害”案情不能被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情形,但属于以上立法的排除性规定情形的,也应基于以上规定和属于不“应受刑罚处罚性”而不认定为犯罪或按刑法以外部门法处理。
另外,在立法上,对于故意伤害的“伤害”行为,在《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侵权责任法》等中都有相应规定。对这些立法规定如何界分,在理论上有很多探究。但从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来看,这些探究似乎并未形成解决实践问题的共识。其实,鉴于刑法的保障法、补充法和谦抑法性质,其立法规定必然与其他部门法规定间有对接性、交叉性、竞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间就没有明确的界分标准。综合前文所述,这个标准,就是案情是否符合《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成立基本条件规定(含“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但书规定)。符合本成立条件的,按犯罪处理,否则就按其他部门法规定处理。具体就故意伤害“轻微伤”案而言,通过评价,在案件符合《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成立基本条件及个案所对应的刑法所有相关规定的系统化评价时,就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定性处理;否则就按《治安管理处罚法》《侵权责任法》等关于治安案件的行政处罚或民事侵权案件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等非犯罪方式处理。因此,《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犯罪成立条件)的规定,实际上也是界分刑事犯罪与行政处罚、民事制裁等定性的基本标准。
本文责任编辑:周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