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溪
傅菲
可能是我见过流程最短的一条溪流。白溪,说是一条溪流,倒不如说是空空的河床。床,是人安睡的地方,人三分之一时间在床上度过。动物固定睡觉的地方,有的叫巢穴,有的叫巢,有的叫窝,有的叫窠臼,有的叫泥洞。大部分动物睡觉没固定的地方,躲在树叶背面,躲在花蕊里,躲在屋檐下,躲在墙洞里,躲在岩洞里,躲在石缝里。牲畜睡觉的地方,叫圈。家禽睡觉的地方,叫笼舍。牲畜家禽,是人最亲近的动物了,它们睡觉的地方都不叫床,怎么溪流淌过去的地方,叫床呢?溪流会疲倦,会停下来睡觉吗?棺椁称眠床,溪流也像人一样需要眠床吗?
溪流是躺不下来的,它的命运是流,是淌,是奔腾。躺下来的溪流,是终结的溪流。在雁荡山,我踱步河畔,大叶桂樱在堤岸伞盖一般,罩下来,墨绿墨绿,沙地上菖蒲略显焦黄,裸露的河床,赫然吞噬我。它像一条灰白舌苔,长长的,粗粝的,随时可以把一个注目它的人,吸进它巨大的空腹——在冷冬,它有着一副贪婪的面孔,那么饥饿,午间和煦的阳光也不能填饱它。河床还是原始的模样,河石看似杂乱却有序,曾经的洪流和时间,把任何一个石头,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交叠,彼此支撑,或孤陈在泥沙里,露出半截圆头。河沙和卵石把河石浮在虚空。我沿着能仁村,往下游走。一个不存在的下游,像一条(不存在的)溪流的下半生。逐日凋敝的洋槐,衰老的柳杉,冰凉的山风,在一个远游人的眼里,会慢慢汇聚,缩小,如一滴寒露,那么重,相当于一个时间的背影。
堤岸约高两米,斜在河床上的野树遮住了不多的村舍,拾阶而上的菜地箍在山边。河床像一条被甩出去的鞭子,而握鞭的那只手,突然被什么抽空力气,鞭子落下来,却保留着弯曲扭动的弧形——和蜕皮的蛇差不多,蛇跑得不知踪影,蛇皮干枯在那儿,把蛇痛苦的形状留在影子上。
白溪在雁荡山镇境内,源头之一始于大龙湫瀑布。大龙湫瀑布与贵州黄果树瀑布、黄河壶口瀑布、黑龙江吊水楼瀑布并称中国四大瀑布,而大龙湫以其落差为190余米,誉为有“天下第一瀑”。雁荡山于亿万年前,东海火山喷发,落熔成岩,因山顶有湖,芦苇茂密,结草为荡,秋雁南归栖息于湖,故名雁荡。雁荡山脉,绵延几百公里,山岩如屏,飞瀑叠泉,百溪成流。白溪自源头而下,溪水淙淙,明澈透亮,溪出三里,过能仁村,溪水渐渐干涸,了无影踪。河石有黑褐色巨如方桌火成岩石,有灰白色圆石,有长满苔藓麻石,河床有了河石的方阵。河床凹处,有了潭,深蓝,小鱼嬉于间,如山中童子。不足千米,每每有石拱桥跨两岸。石拱桥均以麻石修建,石栏杆,在密林间隐约。桥头三五屋舍,或庙宇。
每一条溪,都曾经有过洪流。洪流是溪的盛年。溪为洪流而存在。每一年,洪流会三番五次横扫裸呈的河床,摧枯拉朽,万马奔腾,不绝于滔滔。人的一生,又會有几次洪流呢?我们去爱一个人,去面对一次生死,便是历经一次洪流。而洪流总是把我们带走,把自己的灵魂带出了自己的身体,让我们干涸,干瘪,丧失很多生趣。在雁荡山南麓北麓,我走了两天,我几次问自己:我爱的,是什么,不爱的,又是什么,怎么去迎接下一个洪流。
村因溪而生。能仁村、灵岩村、谢公岭村、响岭头村、白溪村、咸淡冲村。村人多种石斛、椪柑、菜蔬。也多小生意人,卖山珍,卖地方小吃,卖盆景。山不高,连绵,峰石突兀,岙深通幽,曲径若现。密林多水,水汇成溪。冬深雁高,树木层染,草白草黄,溪水羸弱,渗入河沙而消失。春夏之际,海边会有绵长的雨季,雨从雁荡山披散而下,雨势乌黑,盖压而来。岩壁哗哗,水奔泻飞溅。树林,竹林,芭茅,雨水一阵阵白亮油绿,晶莹如珠,沿树根,沿草根,顺着屋檐,顺着沟壑,来到了河床,溪流汤汤,咆哮,响彻山岭。临溪而眠的人,有福了。溪流洗涮着泥尘,洗刷着人的脏器,洗涮着山河。
水急,则速快。白溪不过三十余华里长,要不了一个时辰,便入了乐清湾。浑浊的海水早早地等着,如一个巨大的容器。白溪消失在海里,一滴水消失在汪洋里。雨也最终消失在海里。雨再次从海面升起。海是另一个巨大的人世间,一层层的泡沫泛起,破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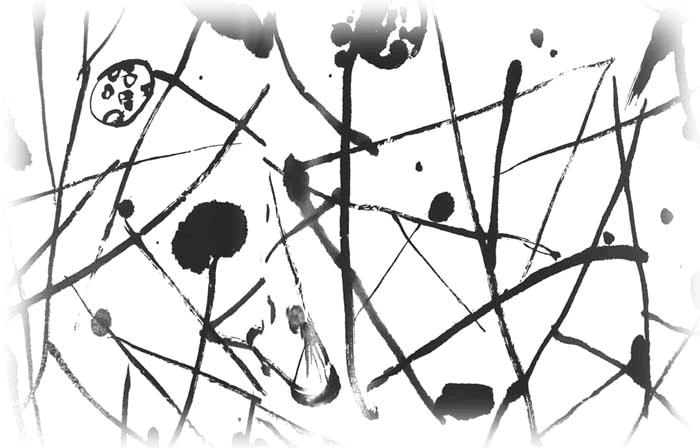
冬日的阳光,如旧年的棉花。淡淡白淡淡黄。雁荡山的野花,大多已凋谢,只有路边的山茶旺盛地生育红花,那么艳丽多姿,和冷涩肃穆的山色形成强烈的反差,似乎喻示苍山不老,大地俊美。河岸杂芜的菜地边,金盏菊开得秘不示人。屋墙挂下来的白英,结满了红浆果,圆圆的颗粒状。矮墙上的草本海棠,花朵卷缩,成了干燥花——它已忘记了凋零,忘记了盛开,忘记了雨水的浸润和阳光的催生,它甚至不在乎白溪的暴涨与干涸,时间交给它的,它交还给了时间,生命若无,四季无情——这是最好的来,最好的去。白溪直条条地裸呈了自己的骨骼。那是一张溪流的眠床。溪流不会死,也不终结,而是散去,散到了沙泥里,散到了云层里,散到了植物的身体里。溪流在等待来年的复活。它要旺盛地繁衍,为生而息。白溪,是另一个我,在东海边,被我毫无意识毫无预料的遇见。这两年,我去很多地方,去深山,去海边,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那么盲目。一个人在没有尽头的铁轨上,一个人在高山之巅深夜遥望月亮,一个人在武陵源听深冬冷雨,我似乎在期待一种我并不知道的东西降临,等待一个天之崖的人坐在我身边,等待一滴寒露塌陷在我额头。
无论走多远,只为和自己相遇。劫后重逢。洪流之后的再度拥抱。山河多故人。在白溪边,在显圣门山谷,我眼前几次出现了幻觉:穿黑色复古服饰的人,金边绣花看起来像凤凰,这个人一直走在我前面,头发有瀑布的流线型,在转弯的山道,不时回头看我。这个人以前来过,以后也会来。我随着这个人的影子来。或者说,我带来了影子。这个人,提一个水罐,银饰叮当作响。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人,降紫的头巾落了一层细细雪花。我贪恋生。从未有的贪恋。第一次贪恋。在这异乡的溪边,太阳如树上的野柿。我爱这个无常的尘世,爱深冬枯草败枝,爱没有水流的河床。这个世间,有我爱的人,有我爱无言的人,有我爱不够的人,有我完全爱的人。一生并非如自己所愿,但命运已经作出最好的安排。山梁安排了日落,悬崖安排了飞瀑,潮涨安排了潮落。你安排了我,生安排了死,在没有结束之前,我不会安排自己遗世独立。
白溪的旅程很短,我以踱步的方式,走到了它的尽头。在乐清湾的西门岛,冬日灰色的天空铺满了云翳。苍莽的海面,不见帆船,不见海鸥。沼泽地的海草被风吹得倒伏。雁荡山的溪流在这里,与大海相汇,清浊交融。
白溪,在雁荡山方言里,即无水之溪。无水亦可成溪,是生命的大浩瀚。河床在等洪流的到来。我等的是什么呢。
摘自 文学报 2017年2月23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