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势
一
天还黑得像张鬼脸,朱老蔫就被夜尿胀醒了。
他拉亮灯,看见桌上闹钟才三点多。他掀开棉被坐起来,被刺了一刀似地打了个寒颤,急忙抓起帽子扣在头上,还扯了棉被把自己包粽子样裹紧。
屋外,硬风一鞭接一鞭挟着呜呜啸音甩过来,抽得窗户噼啪乱响。电线成了鬼的嘴巴,呜哇乱叫。夜鸡也凑热闹,沙哑着嗓子啼出泣血的第一声。
朱老蔫伸屈手指,子丑寅卯掐了一轮。五更鸡叫,这才三更,没到鸡叫的时候呢,鸡却叫了。老人们讲这叫“夜鸡啼”,也称“亂鸡啼”,是不吉利的兆头。
“狗日的!叫你娘个卵。”朱老蔫低声骂了一句。
朱老蔫是粟米胆小。他平时不敢骂人,最憋屈的时候也只会在背地里骂鸡骂狗骂猪骂牛骂树骂石头。骂过之后,朱老蔫心里舒畅了一些,但他还是很纠结要不要开门。终于,他扛不住尿胀,还是下床蹬上拖鞋,披了棉衣抖抖索索抽开了门栓。
不待朱老蔫拉门,门哐当开了,像被人踹了一脚,其实是被风推开的,朱老蔫也被推得打了一个踉跄。他急忙用手按住脑袋,不让帽子被风吹掉。啊呀,门外好大风,飞沙走石,像有千军万马在混战撕杀,黑乎乎的吹得人睁不开眼。
“鬼风。”朱老蔫一边揉着眼睛撒尿一边咕哝,热尿落到地上嗤嗤有声,臊臭刺鼻。尿完,他全身抖动打了一个很舒服的尿颤,赶紧进屋关门。
一泡尿把瞌睡赶跑了,朱老蔫再也睡不着。他披衣坐在床上,往竹烟杆里装了一锅烟,吧唧吧唧抽着。这根竹烟杆有两尺多长,枣红色,油光铮亮,像一根牛鞭,头粗尾细,中间鼓起一轮一轮的竹节。烟锅部分包铜,是一个葫芦造型,有花叶纹饰;尾部嵌了一个白玉烟嘴;烟盒是一个黄杨木雕桃果,盖钮是一只坐着的老猴,上了包浆,和烟杆一样的枣红色,油光铮亮。
朱老蔫原来不晓得这烟盒是黄杨木。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下乡收古董的人,捧着他的烟杆反复摩挲爱不释手。那人告诉他,这烟盒是黄杨木雕,烟杆是罗汉竹,烟嘴是和田白玉,年代应该在明末清初,他愿意出价三千块钱买下。
朱老蔫一听,吓得夺过烟杆鬼追样掉头就走。他哪敢卖烟杆?卖烟杆就是卖他的命。他家是劁猪世家,这烟杆是他祖传宝物,是劁猪身份的象征,就像丐帮的打狗棍。
朱老蔫走村串巷替人劁猪,全靠这烟杆助力。雨天路滑,烟杆可当拐杖使用;走穷村陋巷,也可以防狗。狗通人性,见到衣着整齐、声音洪亮、昂首挺胸的人,它就会摇头摆尾阿谀逢迎;见到低眉垂眼缩头缩脑的人,他就会凶相毕露仗势欺人。有一回朱老蔫被两条恶狗堵在一条小巷子里,急中生智把烟杆一抡,那狗立即夹尾逃跑。从此,朱老蔫就晓得这根烟杆的重要了。他一直感到很奇怪,为啥人和狗一见烟杆就晓得他是劁猪公呢?
想到劁猪,朱老蔫记起今天正要为盘村花寡妇去阉一头公猪。听讲这头公猪不是普通的公猪,它发情的时候不吃不喝,在猪圈内狂走嚎叫,拱泥巴,咬栏板,闹得花寡妇睡不着觉,半夜爬起来去给猪讲好话。月光底下,骚公猪看见花寡妇袒胸露乳一身白肉,竟然一跃而起把花寡妇掀翻,差点要了她的命。花寡妇恼羞成怒,第二天请了几个壮汉把骚公猪掀翻,用铁链把猪脚捆了,决定请朱老蔫去给她报仇。据说花寡妇本来不想劁猪的,她想再买几只母猪回去和骚公猪配种,准备养一窝猪仔赚大钱。今年猪肉贵,而且养殖户可以算扶贫对象享受国家的资助,好多人都准备养猪了。但是现在她等不及了,迫不及待要把骚公猪阉掉。
朱老蔫当然不相信会有猪欺侮人的荒唐事,一定是那些闲人看不惯花寡妇平时不检点故意编故事埋汰她。
朱老蔫马上在鞋底上搕掉烟灰,收起烟杆。他已经烧了五锅烟,把天都烧亮了。他把劁猪刀找出来,架起磨刀石,唦唦唦磨起劁猪刀来。劁猪刀有两把,不长,二寸左右。刀的形状都很奇怪,一把刀叶呈桃形,有一根细长的柄;一把刃宽柄细,像一片窄窄的柳叶。两把刀就像两件奇门暗器。
磨了一会,突然听到隔壁响起哼哼呀呀的呻吟声。隔壁是朱老蔫婆娘的睡房,两人虽是夫妻,但已分床好几年了。
朱老蔫婆娘也姓朱,名字就叫朱娘。朱娘比朱老蔫年轻十五岁。
那一年朱老蔫还在乡兽医站当兽医,有一次到朱娘的家里去劁猪,看上了年轻漂亮的朱娘。朱娘的父母见朱老蔫本分老实,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门好技术,就做主把朱娘嫁给了他。
那时候,一个农村女孩要“跳农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考大学分配工作,一条是嫁一个吃国家粮的男人。朱娘家里穷,供不起她读书,但是让她走通了后一条路。那一年天气奇热,盘村好多人都患红眼病,特别是年轻女孩居多。有人就怪朱娘,都讲是她害的。
结婚之后朱娘才晓得,朱老蔫骗了她,因为他只是兽医站的临时工。朱老蔫由于拙嘴笨舌不会讲话和处世,巴结不了领导,得罪了很多人,迟迟转不了正。
朱娘后悔不已,和朱老蔫大闹一场。朱老蔫呢?只有向朱娘认错,拿起朱娘的手扇自己的耳光,保证以后对朱娘好。朱娘骂他不还口,打他不还手。朱娘指东他不向西。只要朱娘能够原谅他,哪怕叫他上刀山下火海他都愿意。
朱娘打掉牙齿连血咽,吞下一口怨气,因为生米已煮成熟饭,而且她已怀了孕,只好认命。不料,这时计生站的人盯上了她,三番五次动员她生育之后去医院结扎。朱娘死活不同意,惹恼了计生站的人,说朱娘如果不结扎,就会影响整个乡计生工作的开展。也会影响朱老蔫,他不仅转不了正,还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
这是考验朱老蔫对朱娘是不是真好的时候。朱老蔫无奈,只好鼓起勇气代替朱娘挨了一刀。朱老蔫成了阉人,就像被铁锤敲进地下的木桩,矮了一大截,比以前更蔫了。人们在背后笑话他,讲他劁猪太多了,最后自己也像猪一样被劁,这就是报应。朱老蔫只当自己是聋子,啥也没听见。不巧的是,朱老蔫被结扎之后,朱娘意外流产了。有人就幸灾乐祸讲他活该断子绝孙。祸不单行,接下来朱老蔫又在机构改革中被单位清退,只好带着朱娘回了老家,还干老本行,给猪马牛羊治病、去势。
这时候,朱娘已经和其他人一样把朱老蔫看成是一个无用的阉人,虽然和他同锅吃饭,但是坚决和他分床睡觉。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半老徐娘的朱娘晚上常常在睡梦中发出痛苦的呻吟。
奇怪,朱老蔫一听到这个声音身体竟然有了反应,浑身燥热,猫抓似的难受。更奇怪的是,他那已经去势的部位也在蠢蠢欲动。朱老蔫的心一阵嘭嘭直跳,不晓得是高兴还是害怕。他想这是怎么啦?明明已经去势了,怎么还有那种欲望?难道是主刀医生为他结扎时手术失误?或者是他吃骚猪公的睾丸吃多了身体自动康复?朱老蔫劁豬几十年,被他阉了的猪从没有再发情的,可是这种意外却发生在人身上,而且是他,朱老蔫,一个专门给动物去势的人。他头上冒出冷汗,像做贼一样偷看窗外,生怕有人发现了他的秘密。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对传宗接代本已绝望,现在这希望却又死灰复燃。
尽管有了欲望,朱老蔫还是压制着自己,因为他觉得对不起朱娘,内心有愧。再有就是怕这事传出去会引起风言风语,也会连累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有好几次他鼓足勇气要对朱娘讲出来,但朱娘不等他开口就像看见癞皮狗似的横眉竖眼一副嫌弃表情,朱老蔫只好哑子吃黄连把苦水咽回去。有两次,朱老蔫鼓起勇气进了朱娘房里,但却缩手缩脚站在她床前不敢吭声。朱娘醒来睁眼一看,吓得半死,破口大骂:“你个阉鬼站在这里干啥?滚!”朱老蔫只好灰溜溜退出朱娘的房间。
有一次,朱老蔫从外面劁猪回来,刚到家门口,正碰上村长朱老麻从屋里出来。朱老蔫以为朱老麻来找他有事,刚想打问,朱老麻却主动招呼:“哎呀老蔫兄弟,你真是个大忙人啊,我都三顾茅庐好几次了,硬是遇不到你。这不刚要走,你就回来了。”边讲边掏出烟来敬朱老蔫。
朱老麻比朱老蔫大几岁,是朱老蔫的远方堂兄。朱老麻平时把朱老蔫看成是一堆狗屎,都不拿正眼瞧他,这次却热情得离谱,真是狗打筋斗鬼唱歌,怪得很。朱老蔫就像瞎子和聋子,对朱老麻的热情看不到听不见。他用烟杆把朱老蔫的纸烟拨开,不冷不热地问:“朱村长这样着急找我,有啥好事啊?”
朱老麻煞有介事说:“老蔫兄弟,我是找你讲低保的事啊。你看你都是一担米吃完半筐过五十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又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啊不,是计划生育工作的贡献者。现在上面来了农村低保指标,你不能享受还有哪个有资格享受?所以呀,我特意来跟你讲一声,准备给你争取一个噻。”
朱老蔫想,我还以为他有啥急事来找我帮忙呢,原来是为了这个。不对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村子里求朱老麻的人像赶庙会的香客那样多,把他家的门槛都踩凹了,他怎么会主动登门来找我?这不是日头从西边出茄子倒开花了吗?
朱老蔫多了一个心眼,说:“这确实是好事,谢谢朱村长了。夸我为计生工作做贡献不敢当,讲我身体有病更不对。我身体好得很,一餐能吃三碗饭,能喝四杯酒,掀得翻二三百斤的野猪公,让它去势它就去势,所以这个低保我就不要了,你还是多做善事让给那些比我更困难的人吧。”
朱老麻本以为朱老蔫会对他感恩戴德,想不到自己却把热脸贴了冷屁股。他平时习惯了别人的吹捧和奉承,哪受过这种冷气?一时间他的脸就像一张看到劁猪刀的公猪脸,一阵青一阵灰。“好好,你不要就算了。”他说,“是我咸吃萝卜淡操心。但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要不然你会后悔的。”讲完急匆匆走了。
朱老麻的话就像一股风,从朱老蔫耳边吹过,他根本没有听进去。他走进屋,像往常一样把从猪身上劁出来的猪腰、猪花和猪睾丸交给朱娘,让她去处理,把它们做成下酒菜。朱老蔫不仅抽烟,而且喝酒,每餐都要喝上二三两。往常朱娘把酒菜摆在桌上就离开,她嫌那下酒菜臊臭、恶心。但这次她一反常态,陪着朱老蔫坐下,朱老蔫一喝完她就把酒给他倒上,搞得朱老蔫反而浑身不自在。他想今天这是怎么啦,连婆娘的态度也变了,真是六月下雪泡腊月开桃花奇了怪了。
朱娘试探着问朱老蔫遇到朱老麻没有。
朱老蔫好像没睡醒,半眯着眼回答遇到了。
朱娘忙问:“朱老麻他……讲啥了没有?”
朱老蔫打开一只眼看着朱娘:“他不是从屋里出来的吗?你没在家呀?”
朱娘愣了一下,忙说:“在在,我是问你他和你打招呼了没有?”
朱老蔫把打开的眼又眯起来:“打啥招呼?”
朱娘低声说:“低保的事呀,他帮我们种了一棵摇钱树,要给我们一个低保指标,每月都有钱领呢。”
朱老蔫无精打采:“他好像讲了。”
朱娘忙问:“你答应了没有?”
朱老蔫像要睡过去一样哼哼说没有。
朱娘一听就变了脸,把酒壶在桌上啪的一顿:“你为啥不答应?”
朱老蔫的“瞌睡”被吓醒了,端杯的手抖了一下,酒淌了出来。他低声说:“我有吃有喝没灾没病,要低保干啥?”
“你有病!”朱娘怒道,“你不可救药了。”
晚上,朱老蔫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朱娘房里一反常态没有了往日哼哼呀呀的声音,他反而不习惯了。朱老蔫挨到半夜,好不容易迷糊了一会儿,却又被那种哼哼呀呀的呻吟声惊醒了,还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呓语:“哎呀我的亲……我的乖……”
这臭婆娘,原来一直在防着朱老蔫。朱老蔫没睡她也不睡,朱老蔫睡了她也睡了。但是她没想到朱老蔫比她醒得快,她竟在梦里和哪个野男人搞在一起了。朱老蔫心里骂着,身体又有了反应。他爬起又躺下,躺下又爬起,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最后,他终于克制不住了,一翻身爬起来,鼓起勇气准备推门进朱娘的房。臭婆娘!朱老蔫咬牙切齿暗骂,老子今晚豁出命来也要去了你的势。
“哎呦我的个亲麻哥噻,你别走呀……”朱娘又哼哼呀呀说:“人家还……”
朱老蔫一下懵了,像中了魔法。又像在寒冬腊月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全身一下子冻僵麻木,啥感觉都没有了。
他终于明白了,朱老麻为啥愿意热脸贴他的冷屁股;朱娘为啥一反常态对朱老蔫亲热起来,原来他们两人已经勾搭在一起了。大概整个村子的人都晓得了这事,就剩下早出晚归的朱老蔫蒙在鼓里,难怪人们看他的眼神都像鬼眼那么怪怪的。
朱老蔫把头上的帽子掀掉,咬了一下牙,这是他发狠时的表情。他一生气就掀帽子。那帽子常年戴在他头上。新帽子当年是草绿色的,现在已经洗得变成了灰白色;他咬牙是因为劁猪时经常咬劁猪刀,久了就变成习惯性的表情。为啥要咬劁猪刀?因为劁猪时只有把劁猪刀咬在嘴里,才能腾出手来去猪肚子里掏腰花去膀胱里掏睾丸。朱老蔫咬牙的表情非常可怕,先是嘴一咧,推动脸上的法令纹往两边撑开,露出两排黄板牙。眉毛上挑,双眼圆睁,就像一只发怒的大猩猩。朱老蔫劁猪时都要先对猪作一个这样的表情,小猪看到会腿一软瘫在地上;大猪看到会吓得战战兢兢大小便失禁。那晚,朱老蔫怒不可抑。他掀掉帽子,咬了劁猪刀,要冲进朱娘的房间给她一刀,先把这骚婆娘去势。但是朱老蔫一抬腿却拌倒了一只陶罐。哗啷一声陶罐破了,隔壁的呻吟和呓语立即没有了,朱老蔫也清醒了,他觉得为了这骚婆娘,不值得把自己的一条命搭上。
现在,朱老蔫又听到婆娘在隔壁呻吟。他照例狠狠地掀了一下帽子,把牙一咬,咽下一口恶气,然后不急不慢用酒精把磨好的劁猪刀消了毒,出门直奔盘村去了。
二
花寡妇早就在家门口等着朱老蔫了。
看见朱老蔫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破单车摇摇晃晃过来,花寡妇立即跳舞似地扭出院子,唱歌一样招呼:“哎呦我的蔫哥哥喂,你怎么现在才来哟?花妹我等你等得头发都白了噻。”
“我看你是等得花都谢了吧?”朱老蔫偏腿下车,破例讲了句笑话。讲实话,这花寡妇确实有几分姿色,要胸有胸,要臀有臀,讲话声音也清脆。自从朱老蔫发现朱娘和朱老麻的丑事后,朱老蔫就喜欢听花寡妇讲话,花寡妇讲得越肉麻越令人耳热心跳他越爱听,他把这当成是对朱娘的报复。花寡妇从不把朱老蔫当阉人看,所以朱老蔫每次路过她家都要找借口进屋和她讲讲话。
“哎呦我的蔫哥喂,连你也取笑起花妹来了噻。”花寡妇说,“难怪别人日夜想打花妹的主意呢。”
朱老蔫瞧了院子里一眼,那里坐着花寡妇请来帮她抓猪的两个男人。那两人正在喝茶抽烟,咧嘴看着花寡妇傻笑,一脸蠢相。
“我送一把劁猪刀给你,哪个敢打你的主意你就阉了他。”朱老蔫边说边把单车搁在院角。花寡妇正好端了茶出来,听到朱老蔫的话笑得花枝乱颤,连茶汤都淌了出来。
朱老蔫喝过茶,抽了一锅烟,把烟杆挂在屋柱上,对两个男人一歪嘴:“开始吧。”
两个一脸蠢相的男人马上脱了衣服,把裤腿挽起,赤膊跳进猪圈里,動手去抓猪腿。那猪是一只黑毛短腿的种猪,像一条小牛犊似的粗壮,虽然没有像传说的那样被花寡妇用铁链子锁住,但一点也不温柔。它们嚎叫狂走,在猪圈内转圈,和两个男人对阵。两个男人虽然身粗力壮,但却屡屡扑空,满头满脸都是臭烘烘的猪粪,累得气喘吁吁。
花寡妇见了,气得破口大骂:“瞧你们这些酒囊饭袋,平时揩老娘油时一个比一个强,现在抓猪了却一个个像去了势的不中用了。”
朱老蔫看着两个蠢男人累得吭哧吭哧,却不讲话,嘴角挂了冷笑。等两个蠢男人折腾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你们一边去吧,让我来。”
两个蠢男人不服气地退开,等着看朱老蔫的笑话。只见朱老蔫把头上的帽子一掀,将劁猪刀咬在嘴里,一张苦瓜脸说变就变,眼球瞪得比牛眼都要圆。他们不晓得,朱老蔫眼里的黑公猪此时已变成了朱老麻。朱老蔫怒发冲冠,鼻孔里炸雷似地哼了一声。真是奇怪,那猪懵了一下,顿时四蹄发颤,屁股后面射出一股臊尿喷在两个蠢男人脸上。花寡妇喝一声:“还不快给我拿下?”两个蠢男人顾不得揩脸上的猪尿,趁机扑上去抓住猪腿,把猪掀翻,死死按住。
骚公猪被按在猪栏里嗷嗷哀嚎。
朱老蔫跳进猪圈,用醮了酒精的药棉洗了猪膀胱,从嘴里取了刀,狠狠地骂一声:“去你妈的吧!”嚓嚓两刀,已把两只猪睾丸摘了下来,把端着碗在猪圈外等着接睾丸的花寡妇看得目瞪口呆。
两个蠢男人等朱老蔫把猪膀胱缝合后才把猪放开。这时黑公猪已经去势,趴在猪圈里痛苦地哼哼着。
朱老蔫忙完,吐出一口恶气,又恢复了原来无精打采的蔫样,安安静静坐在院子里喝茶抽烟。
两个帮忙抓猪的蠢男人洗了手脚,站在旁边傻乎乎地看着花寡妇,想说啥欲言又止。花寡妇明白他们的心思,故意瞪了他们一眼:“你们还站在这里干啥?是想要工钱还是讨酒喝?”两个蠢男人被她一喝叱,梦醒似地傻笑了一下,屁颠屁颠走了。
花寡妇已经把猪睾丸炒成香喷喷的下酒菜摆在桌子上,另外还炒了一盘寡鸡蛋,煮了一个猪肝粉肠汤,很丰盛的早餐。她还把院门和屋门都关了,坐下来陪朱老蔫喝酒。
朱老蔫问花寡妇:“青天白日的你把门都关了干啥?”
花寡妇暧昧地笑:“你不晓得我寡妇门前是非多?我一个寡妇陪一个劁猪公喝酒,不怕别人指背壳讲闲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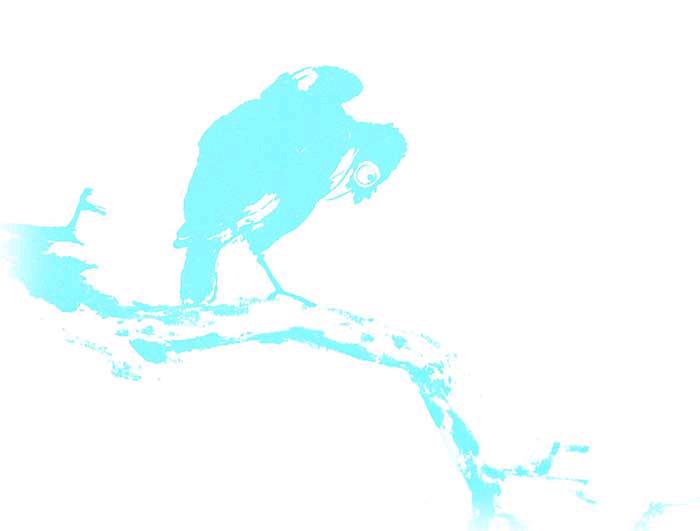
“真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朱老蔫暗笑,“哪个不晓得你花寡妇是朵狗尾巴花?”他肚子早已经饿了,桌上的酒菜这时比花寡妇更有吸引力,所以他也管不了那么多,端起杯子就狼吞虎咽起来。
花寡妇酒量没有朱老蔫那么好,一杯酒下肚脸上早已桃花盛开。她虽年过四十,但仍徐娘半老风骚不减,讲出话来又香又甜又有黏力,没有几个男人能够抵抗得了:“我讲蔫哥喂,平时看你是一个蔫不拉叽的草人,想不到劁起猪来那么雄扎那么有男人气派。”花寡妇一双桃花眼色眯眯盯着朱老蔫,“连我这个阅人无数的小女子都被你迷倒了噻。”
朱老蔫也有了三分醉意。他被花寡妇看得脸热心跳,身体又有了反应:“俗话讲瞎子的耳朵瘸子的拐。”朱老蔫说,“人生来就会强弱互补,要不为啥金能克木火又能克金呢?”
“哎呦呦我的蔫哥哥喂,想不到你嘴也这么会讲噻。”花寡妇放肆地在朱老蔫腿上拍了一巴掌,“看来你年轻的时候对付女人也一定像对付猪那么厉害吧?”说完嘻嘻浪笑起来。
“你是笑话我现在不行了?”朱老蔫瞪着眼说,“我一直都很厉害呢。”
“哎呦喂,夸你胖你还真的喘起来了?”花寡妇撇了一下嘴,拿指头点了一下朱老蔫的额头,“你还一直厉害了,哪个信你呢?”她想讲你一个阉人,还能厉害到哪里去?但她不敢讲,怕惹恼朱老蔫,因为朱老蔫劁猪时的那一副怪样还一直让她心有余悸。
朱老蔫突然把花寡妇的手抓住:“你不信?”
花寡妇愣了一下,她想抽回手,但朱老蔫抓得很紧,抽不回,只好放弃,让朱老蔫继续抓着,但嘴里仍坚持:“我不信。”
朱老蔫红着脸问:“要怎样你才信?”
花寡妇心里突然翻起一股热浪,好紧张好刺激,这是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时没有的感觉。她突然有了一个恶作剧念头,她要试试这个不阴不阳的男人到底是阉人还是真男子:“你如果让我见识了你的真功夫我就相信。”她眯起狐眼呓语一样喃喃道。
朱老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把帽子一掀,用力一拉,将花寡妇拉进自己怀里,嘴和手都在她身上忙碌起来,就像很久没有吃到羊肉的狼一样。“臭婆娘,你可别怪我了。”他暗叫着朱娘的名字,一种报复的快感在全身扩散,“是你先不仁我才不义呢。”
花寡妇在朱老蔫怀里哼哼呀呀呻吟起来。
听到花寡妇呻吟,朱老蔫像被蝎子咬了一口,突然把她推开。他浑身害伤寒似地颤抖起来。
这种声音太熟悉了,就是朱娘夜晚梦呓的声音。
这种声音还让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去年一个冬天的夜晚,朱老蔫从外地劁猪回来,路過花寡妇的院子。他又冷又饿,看到花寡妇屋里亮着灯,就想到她家里喝口热水暖暖身子。他推了一下花寡妇的院门,推不开,是从里面闩住了。他想喊一嗓子,又怕更深夜静引起村人的怀疑。刚想离开,却听到屋子里有人讲话。朱老蔫想,一个寡妇人家,深更半夜把门关了和哪个在屋里讲话呢?好奇心促使他绕到花寡妇屋后的窗户下偷听,结果就听到和朱娘一样的哼哼呀呀的呻吟声。呻吟声断断续续,中间夹杂着花寡妇和一个鸭公嗓男人的讲话声,十分耳熟。花寡妇的声音:“你个挨千刀的好久不来,是不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和别的骚女人好上了就把老娘丢在冷水盆了?”鸭公嗓的声音:“你这是冤枉我了,有你这蜜糖甜了我的嘴,我吃别人哪里还有啥味道?你不晓得,我前段时间忙死了,吃不下睡不着,哪里还有心思玩女人?”花寡妇问:“你忙啥?”鸭公嗓答:“这是机密,我不能讲。”花寡妇生气了:“不讲说明你心里没有我。”鸭公嗓忙说:“我讲我讲。我们这段时间在忙着配合工作组搞低保调查和扶贫噻。”花寡妇问:“低保我晓得,扶贫是怎么回事?”鸭公嗓答:“扶贫就是帮助你这样的贫困户脱贫致富噻。”接着就是一阵手忙脚乱和哼哼唧唧的呻吟声。花寡妇嘻嘻浪笑:“还脱贫呢,我看你这个老色鬼就晓得脱女人的裤子吧?”鸭公嗓委屈道:“我脱女人裤子是给了她们好处的啊。就像你,领的低保在全村是最高的了,就为这我还得罪了好多人,有人还扬言要告我呢。”花寡妇说:“那你可要小心了,今后讲话做事都要藏着掖着点,别叫人揪住狗尾巴噻。听讲鸟仔窝村的吴石宝告你不发给他救灾款;野猪凹村的马三民告你霸占他家的自留山,还被你兄弟朱老五打成重伤是不是?”朱老麻气呼呼道:“是又怎么样?这些都是刁民,得不到好处就造谣生事。你不用担心,他们奈何不了我的,因为我上面有人罩着,下面有人撑着,论文论武我都不怕。再讲我也就是当这最后一届村长就退休了,所以趁我还有权力,我准备给你一个扶贫指标,帮助你发展养猪事业。”朱老蔫终于明白,这鸭公嗓音为啥这样耳熟,原来是朱老麻这条老狗。他一掀帽子,嘴一咧,手下意识去包里摸刀。一只野猫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惊叫了一声,朱老蔫慌忙逃走了。
现在,花寡妇正入戏,突然被朱老蔫推开,吃了一惊:“你干啥呢?”她问。
“我恶心。”朱老蔫说。他站起来,推开门,到院子里推了单车就走。
“你发神经噻?”花寡妇在后面追出来,“占了老娘的便宜就想脚板抹油开溜?”
朱老蔫不理花寡妇,骑着单车头也不回走了。
三
朱老蔫大病一场。
朱老蔫是从花寡妇家回来的路上淋了雨,受风寒感冒。那天,半路上突然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单车失控,把朱老蔫掀翻在泥沟里。他索性躺在地上,让大雨洗刷自己。朱老蔫一边淋雨一边嚎啕大哭,他啪啪扇自己耳光,骂自己混蛋。回到家里,朱老蔫就上吐下泻,发高烧讲胡话。
朱娘吓坏了,忙把村医疗室的医生请来,给朱老蔫打针吃药。朱老蔫虽然退了烧,但仍然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任朱娘把软话讲了一箩筐磨破了嘴皮子都不理她。
这天,朱老蔫正迷迷糊糊间,忽然听到门口有人叫朱娘的名字。朱娘答应一声,出去开门。朱老蔫爬起来,走到窗口一看,外面黑乎乎的,看不见人影。朱老蔫想这天真黑得快,我刚睡下就到了夜晚了。听来人的鸭公嗓音,是朱老麻。朱老蔫咬了一下牙:“这条老狗居然还敢到我家里来?真是太不要脸了。”他顿时气冲血涌,欲立刻推门出去,但又一想,自己并没有抓到他们的把柄,出去又能怎样呢?于是他克制住自己,想看看他们到底要干啥。他听到朱娘把朱老麻拦在门口说:“你还敢来?朱老蔫在家呢。”朱老麻似乎愣了一下:“他在家我就不能来了?我又不是坏人。”
“你不是坏人哪个是坏人?”朱老蔫暗骂,“你他妈的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顶了,死一百回都不算多呢。”他又听到朱娘说:“有事你快讲,我要关门睡觉了。”朱老麻说:“也没啥大事,就是上回跟你讲的低保,问你还要不要噻?”朱娘说:“要!怎么不要?”朱老麻故意说:“可我上次问过朱老蔫,他讲不要了。”朱娘说:“他一个阉人,讲的是气话你也信?”朱老麻嘎嘎笑了:“想要就跟我走。”朱娘问:“跟你到哪去?”朱老麻答:“去村委会,填表签名字。”朱娘犹豫:“明天早上去不行吗?天黑路歪的,非要今晚去?”朱老麻说,“不行。明天一早我就要把报表送到乡里去了。”朱娘说:“那……你等我一下。”她边说边向屋里走来。朱老蔫急忙退回去躺到床上,假装睡着了。“老蔫!老蔫!”朱娘站在朱老蔫的床边轻轻唤他,朱老蔫不应。朱娘又推了他一下,朱老蔫还是没反应,朱娘才退出去,走到门口对朱老麻道:“走吧。”
朱老蔫听到院门一阵哐啷啷响,是朱娘把院门锁上了。他再一次爬起来,把劁猪刀带上,从院子里翻墙出去,跟上朱老麻和朱娘他们。
朱老蔫奇怪自己身体好的这么快,翻墙像腾云驾雾一样毫不费力,走路也是脚不点地悄无声息,不远不近跟着他们。他想猪卵子真是好东西,滋阴壮阳,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一样能把一个阉人变成一个雄壮的汉子,以后要多吃呢。
村委会很快就到了。朱老麻把朱娘领上二楼,进了一间小房,咣当把门关上了,朱老蔫只好站在门外侧耳偷听里面的动静。
房里有讲话的声音传出来。先是朱娘的声音:“表在哪里?快给我填了吧。”朱老麻的声音:“别急嘛,坐下来喝口水吧。”朱娘的声音:“我不渴。”朱老麻的声音:“那就陪我讲讲话吧。”朱娘的声音:“还有啥可讲呢?我要快点回去,老蔫还在家里呢。”朱老麻讲:“一夜夫妻百夜恩,你这么快就把我忘记了?”朱娘说:“我们都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再对不起老蔫。”朱老蔫听婆娘这么讲,暗想这臭婆娘还算有良心,眼睛就有些湿。房间里又传出来朱老麻的声音:“我也快退了,人走茶凉,晓得今后你也不会再理我了。看在我帮了你那么多忙的份上,今晚你就陪我最后一次吧。”朱娘说:“不行。”接着就听到有扭打的声音和凳子倒地茶杯砸碎的声音。朱娘大声叫:“放开我。”朱老蔫不再犹豫,把帽子一掀,取劁猪刀咬在嘴里,飞起一脚把门踹开。朱老麻还没反应过来,朱老蔫就把他像猪一样掀翻,踏在地上,照着他的裆部飞快的一刀……嘭!一声巨响,朱老蔫浑身一震,惊醒过来,原来是做了一个噩梦。
朱娘见朱老蔫醒了,忙问:“你梦到啥了?手舞足蹈的,吓死我了。”
“嘭嘭嘭!”屋外又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朱老蔫一翻身爬起来问:“外面怎么啦?”他看了一眼窗外,青天白日,并不是黑夜,这一次是真的睡醒了,是从噩梦里醒来。
“上面把朱老麻和朱老五抓了。”朱娘回答,“村里人放鞭炮祝賀呢。”
“真的?”朱老蔫问,“你看见了?”
“我刚从外面回来呢。”朱娘说,“看见两部警车直接开进村里,那些带枪的公安给朱老麻和朱老五戴上手铐,像丢麻袋似地把他们塞进车里直接拉走了,吓死人噻。”
“去势了!去势了!”朱老蔫忽然跳起来掀掉帽子,手舞足蹈叫道,“去势了!去势了!”
“你怎么啦?”朱娘慌忙抱住朱老蔫,她晓得他这是高兴过头了,会疯的。她小时候听老人讲过,过去有一个中了举人的书生就是这样疯的;前些日子村子里有个老人买彩票中了大奖,只说了一声:“发财了。”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朱老蔫忽然将朱娘掀翻在床,粗暴地把她压在身下。朱娘没有反抗,她惊奇地发现朱老蔫的身体出奇的硬朗和强壮。“你没有病?”朱娘吃惊地问。
“我有啥病?”朱老蔫呼嗤呼嗤喘粗气,“我一直都这么厉害呢。”他记得这是他对花寡妇讲过的话,他一直想对朱娘讲,总没有机会。现在,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
“你个挨千刀的,你没有病你怎不早讲噻?”朱娘狠狠咬着朱老蔫的肩膀,呜呜哭了,“我等你这一天等得头发都白了噻。”
“这都是天意弄人呢。”朱老蔫叹了一口气,“大概老天可怜我,才不让我断子绝孙。”朱老蔫听人讲过,曾经有做过计生结扎的人还能够生育。以前他不信,但现在他信了。朱老蔫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娘的,我要让你给我生许多小老蔫,让他们个个当兽医,接着给畜生们去势。”
【作者简介】秋人,原名伍秋福,广西作协会员,中国长征精神研究院研究员。作品散见《广西文学》《滇池》《小说月刊》《北方作家》《南方文学》《上海故事》《天池》《精短小说》等刊物,曾获浩然文学奖、冯梦龙文学奖、登沙河杯全国短篇小说奖和广西小小说奖,有作品入选《2015中国年度微型小说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