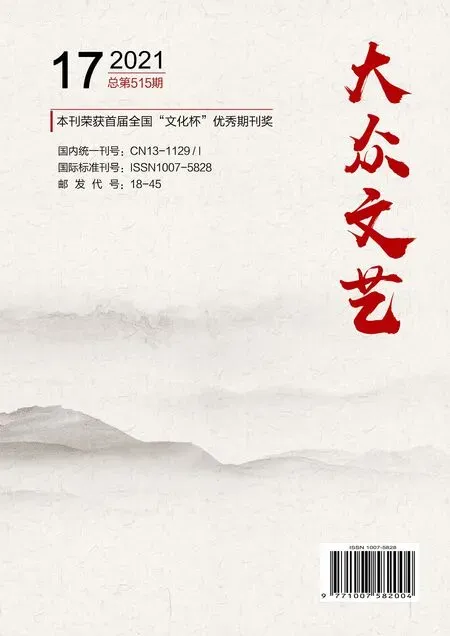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后九七”香港电影中的广州景观
霍胜侠 (中山大学 510275)
“后九七”香港电影中的广州景观
霍胜侠 (中山大学 510275)
本文关注“后九七”香港电影中的广州景观。一方面,其建构的广州景观是分化的、多元的:以《逃出生天》为代表的合拍片借助广州与香港的地理、文化亲缘关系,将广州作为香港替身,从而在合拍片框架下保留本土特色;以《树大招风》为代表的中型商业片把广州作为内地的缩影,流露了“后九七”香港的身份焦虑及渐趋激进的本土主义倾向;以《三条窄路》、《幸运是我》为代表的小成本制作则把广州作为连接香港与内地的中介,提供了新的跨境身份想象。另一方面,“后九七”香港电影中的广州景观又有一定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在不同程度上重视本土性的表达,试图在国族身份与本土身份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后九七;香港电影;广州
一、 引言:九七前的省港“双城记”
说起香港电影中的“双城记”现象,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由香港、上海构成的影像双城。正如李欧梵指出的,由于香港与上海共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以及“一种扎根于大都会的都市文化感性”1,香港电影常将上海作为怀旧对象和镜像他者。相较而言,有关香港、广州双城的研究还比较少,仅有的少量论述多是钩沉早期香港电影史。比如罗卡在《香港电影跨文化观》中回溯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港粤两地电影业的早期互动情况。2黄爱玲的《梦中曾相识——香港电影中的广州回忆》则列举了1950到1960年代香港粤语片中的广州印象。3
然而,香港电影中的省港“双城记”并非仅仅局限于早期历史。恰恰相反,相关的影像呈现一直绵延不绝,且在“黄金时代”(1980年代初-1990年代初)蔚为大观,对“后九七”香港电影产生了深刻影响。概而言之,“黄金时代”再现广州景观的香港电影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第一类着力表现在香港和广州都具备影响力的真实历史人物。这类影片基于两地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渊源,将香港与广州视为一体化的文化空间,或把广州作为香港的隐喻。如在徐克的《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1992)中,黄飞鸿所造访的广州城华洋杂处,中西之间既有误解和偏见,也存在互通与融合的可能。不难看出,这样的广州城正是对处于中西交汇处的香港的自况。又如高志森导演、杜国威编剧的《南海十三郎》(1997),以粤剧编剧江誉镠(又名南海十三郎)为原型,讲述他学于香港、发迹于广州、最后又终老于香港的曲折一生。南海十三郎在省港两地的流连回转,恰恰凸显了广州与香港在文化上的亲缘互哺关系。
第二类以1980年代广州“大圈仔”跨境作案事件为现实基础,将广州形构为中国内地的缩影和区别于香港的他者。典型代表是麦当雄的《省港旗兵》(1984)。影片中无论是刷着革命标语的广州街头,还是贴着邓丽君海报的广州室内空间,抑或既凶猛斗狠又忠诚义气的大圈仔形象塑造,都集中地体现了开始面临回归议题的香港对于当时中国内地的“原初性想象”4。
第三类介乎前两者之间,其再现的广州是一个既亲密熟悉又隔膜疏离的混合体,反映了香港人对于广州的纠葛心态。例如在许鞍华自传性电影《客途秋恨》(1990)中,广州既是主人公晓恩最亲爱的爷爷奶奶所生活的地方,充满对于美好童年的温煦回忆,又正处于1970年代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期,让晓恩感到心酸陌生。这种纠葛心态,反映在一些同时涉及广州和其他内地城市的香港电影中,就表现为广州成为连接香港与其他内地城市的中介。一方面,广州与香港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相较其他内地城市广州又显得更为亲切,对香港也更易认同。比如在《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1990)中,一群大圈仔到广州接应几位从北京来的学生并护送她们到达香港。广州在这里就扮演了一个连接北京、香港的中转站角色。其中广州人的面目也比北京人更为亲切和正面。更具代表性的是陈可辛的《甜蜜蜜》(1996)。来自广州李翘与来自天津的黎小军虽然同为新移民,但李翘显然比黎小军更具香港认同感,而她也是指引黎小军融入香港社会的向导。
“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对于“后九七”香港电影的广州景观再现影响很深。它所建构的广州空间多重内涵——分享共同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体化空间、作为中国内地缩影的他者空间、连接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中介空间,在“后九七”香港电影中也都得到了继承、发展与转化。
二、 替身、他者、中介:“后九七”香港电影中的广州景观
回归二十年以来,特别是2003年CEPA签署之后,香港电影发生重大分化。香港学者朱耀伟用“M型”来形容新的香港电影生态,即合拍大制作与小成本电影各自壮大,中型的商业电影逐渐萎缩。5与这种电影生态相对应,“后九七”香港电影中的广州景观在继承“黄金时代”传统的基础上也出现分化之势:在大制作的合拍片如《东成西就2011》(2011)、《英雄•喋血》(2011)、《同谋》(2013)、《逃出生天》(2013)中,广州景观与香港越来越具同质性。其中尤以《逃出生天》的空间建构最有代表性。中型商业片《树大招风》(2016)则延续《省港旗兵》传统,将广州作为当下内地的缩影,表达了“后九七”香港新的身份焦虑。在小成本电影《三条窄路》(2007)、《幸运是我》(2016)中,广州则再次扮演了连接中港的中介角色,提供了重构中港关系的新的可能性。
(一)《逃出生天》:广州作为香港替身
《逃出生天》(下称《逃》)是由香港导演彭氏兄弟执导、香港寰宇娱乐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英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中港合拍片。故事取景广州,讲述一次发生于珠江新城的火灾中,消防员大军(刘青云饰)在奋勇救人、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实现了与弟弟阿强(古天乐饰)、妻子思乐(李心洁饰)的和解。有评论认为《逃》在遵循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不失港味,是一部“偏港风”的合拍片。6影片之所以能够保留港风港味,是与取景广州密不可分的。
《逃》的故事地点是现实中的真实空间——广州CBD珠江新城。彭氏兄弟利用位于珠江新城珠江西路的中国移动大厦、无极限中心和凯逸酒店结合拍摄。依照香港影评人列孚的猜测,彭氏兄弟之所以选择广州珠江新城而不是北京或上海CBD,很大程度是因为相较于马路过阔的北京CBD商厦以及楼距过宽的上海浦东商务中心,珠江新城更具紧凑性的空间特点。而空间紧凑感也正是香港金钟地区CBD楼宇的特点。7因此《逃》表面上遵循合拍片原则,背后却隐藏着浓厚的香港印记。而借用广州珠江新城与香港商务中心相似点的导演,除了彭氏兄弟还有杜琪峰。杜琪峰的《单身男女2》和《华丽上班族》中的香港写字楼场景其实都在珠江新城取景。杜氏的偷梁换柱并未引起电影画面的违和感和观众的代出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两地空间的相似性。
如果说广州珠江新城的摩天大楼暗合了香港现代空间的特质,那么其周边空间则颇具香港传统空间的神韵。在拍摄一场救火车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的场景时,镜头跟随救火车完成了一次对广州传统空间的巡礼。救火车所过之处,既有古旧的粤派骑楼,也有狭窄的巷道,巷道中还有老人在饮早茶、“打麻雀”(即打麻将)。而无论是粤派骑楼、狭窄巷道,还是饮早茶、打麻雀的生活习惯,都是香港日常空间和习俗的一部分,对于香港观众而言也绝不陌生。因此,无论是现代空间还是传统空间的再现,《逃》都刻意凸显了广州与香港的相似之处。换言之,广州“在画面感觉上可作为香港的‘替身’”。8
在将广州空间作为香港替身的基础上,《逃》在叙事话语上也得以“借身还魂”,更多地承接了传统港产片特色。主人公大军既是国家意志的代言人,也是灾难片类型中常见的孤胆英雄。而大军与弟弟阿强两个角色相反相成,延续了香港英雄片的“双雄”模式。两兄弟带领众人逃离大厦的一系列情节,又巧妙化用了彭氏兄弟特别擅长的惊悚片元素。像《逃》这样具备港片风格的粤港合拍片并非孤例。谢小芬在分析粤港合拍片与北上合拍片的区别时,以《同谋》、《猛龙》、《全城戒备》、《花田喜事2010》、《东成西就2011》等大量影片为例,指出相对于北上合拍片通过迎合主流价值观以缝补与内地在意识形态上的裂隙,粤港合拍片却基于两地的地理文化亲缘关系而“呈现出对港式人文理念的最大化保留及认同趋势。”9
(二)《树大招风》:广州作为大陆他者
《树大招风》(下称《树》)由银河映像制作,许学文、欧文杰、黄伟杰三位青年导演联合执导,该片获得2017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不同于合拍片《逃》,《树》完全放弃内地市场,讲述了一个“男盗女娼”式的地道香港故事:叶国欢、季正雄、卓子强“三大贼王”由于偶然在广州酒楼同时出现,引来三人将要合作的江湖传言。正当三人决定将错就错计划合作时,却于九七回归前夕各自覆灭。影片的故事时间虽终结于九七之前,却投射出九七之后的中港关系问题。其中尤以叶国欢的故事支线最能反映回归后中港位置关系的逆转和置换,以及由此滋生的对于大陆的疑惧情绪。
叶国欢由于在香港打劫销赃越来越困难,转而和许多北上“揾食”的港人一样,到广州番禺做走私家电的生意。为了在内地生存,叶不得不打点贿赂各级官员,并在这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挫败感。发生在广州酒楼里的三场饭局戏,特别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挫败情绪的步步升级。第一场戏是在“风满楼”,叶为拿到工商局批文而宴请陈科长。饭局上叶不但要以买古董为名、行贿赂之实,还要迎合不醉不归的“酒桌文化”,更因点一道略显寒酸的梅菜扣肉受到嘲笑。如果说叶在风满楼还算顺利达到目的,那么第二场饭局戏就增加了更多波折。这场戏发生在“大富贵”,叶为了拿回被海关扣押的走私货物而宴请龙科长,却受到龙科长的多方刁难。而在此前,为了请到龙科长,叶已经多次登门拜访并吃闭门羹。第三场戏是在一个私人官邸,叶感谢公安局宋局长为他找回了两个抢劫货物的小混混。但是宋局长因为人情关系请求叶放过这两个小混混,让他在象征和解的“茶”和象征决裂的“枪”之间做个选择。叶虽大为光火却发现自己作为弱势一方根本没得选择,只得饮下一杯茶。在这里叶的屈辱感达到顶峰,电影的戏剧张力也走向高潮。这种戏剧张力不仅来自于三场饭局戏的层层推进、步步升级,还来自于宋局让叶在“茶”与“枪”之间做选择的情节恰恰呼应了电影开头叶在香港做贼时让赃物买家在“金”和“枪”之间做选择的情节,凸显了叶从主动强硬到被动无力的身份滑落。
纵观三场广州饭局戏,充满程式感和象征性。影片似乎是以叶国欢的个人故事喻指香港在与内地融合过程中两者位置关系的翻转,以及由此带来的优越感的消失和挫败感的增强。香港影评人陈志华在评论《树大招风》时指出,影片“以‘贼王’为隐喻,透过枭雄的穷途末路,抒发香港人经历近年种种挫败之后的唏嘘。”10与故事的隐喻性相一致,片中的广州空间也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实指性的。为了凸显这种象征性,一方面,影片在再现广州时基本上仅局限于酒楼室内空间,且并未刻意强调广州特色,观众其实可以将它想象为内地的任何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在酒楼空间里反复出现的各个物象和符码——古董花瓶、酒、茶、枪等——本身也都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因此,从空间场景的设计和空间物象的选择两方面来看,《树》中的广州是一个象征空间,喻指大陆他者。
(三)《三条窄路》、《幸运是我》:广州作为中港中介
《三条窄路》(下称《三》)是香港导演崔允信的第二部独立长片。崔允信的名字虽然还不为内地观众熟知,却在香港独立电影界占据一席之地。执导独立电影之外,崔还组成非盈利组织“影意志”,制作发行香港独立电影并主办香港独立电影节。《三》讲述香港一家集团公司在广州投资设厂,却由于偷工减料造成工厂爆炸。爆炸引起的水源污染还导致周围居民的中毒。香港公司担心负面事件影响股价便将知情人灭口。代号6277的离职香港警察、年轻的新闻记者Eva以及心怀信仰的马牧师被偶然卷入这起谋杀案。三人决定追查事件揭露真相。在追查过程中,又联合广州警察方毅、广州经商的前香港记者陈傲云,终于将真相公之于众,迫使香港集团向公众道歉。
《三》以香港电影少见的政治惊悚片类型为外壳,内里包裹的是对香港社会价值观的新诉求——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反思金钱至上、物质主义的主流价值观。片中三位主人公正是这种新价值观的化身。警察6277、记者Eva以及马牧师追查真相的动力并非为一己私利,而是谋求社会公义。应该说,影片主旨恰恰暗合了近年香港社会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向。非典、保护菜园村、反对拆除永利街等一系列事件都昭示香港民众对于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社会公义等等的关注度逐渐上扬。11
从这个层面说,片中香港与广州的空间并置显得意味深长。它似乎暗示,香港新价值观的树立、新主体性的标举不可能由香港自己孤力完成,而是需要通过与内地的通力合作。香港新型主体性背后所依托的,是一种同样新型的跨境身份想象。在片中,广州成为香港首当其冲合作的对象,扮演了与香港互帮互助的伙伴角色。一方面,主人公追查真相的过程中得到广州方面的协助。广州公安方毅帮助搜集罪证,生活在广州、曾经身为香港记者的陈傲云则帮助联系广州的新闻业,侧面为香港媒体报道真相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真相大白于天下的结果又反过来帮助中毒的广州村民讨回公道。公义的追求与彰显不仅惠及本土,也惠及非本土的底层民众。因此,《三》通过一个香港、广州跨境故事,提供了一种理想性的跨境身份想象。在这个跨境身份想象中,本土主体性得以重构的同时,又不会对非本土有所拒斥,避免陷入狭隘的本土主义局限,是一种颇为开放和包容的身份想象。
与《三》类似,《幸运是我》(下称《幸》)同样提供了一种开放包容的“后九七”跨境身份想象。只不过其路径并非通过重构新的本土主体性,而是回溯香港的固有传统。《幸》中的主人公阿旭从广州到香港寻找生父,却不被父亲接纳。在心灰意冷之时,阿旭幸运地结识了患有老年痴呆症但善良热心的老人芬姨。两人从最初的算计提防,到后来的理解融洽,直至最后建立起母子般的亲密情谊,使彼此都在香港重新找到家的归属感。
扎根本土的“老香港”芬姨和来自广州的新移民阿旭之所以可以跨越巨大差异实现相知相守,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芬姨对香港传统精神的坚守。片中芬姨反复说起的一句话“做人的事嘛就是你帮帮我、我帮帮你”,正是对于同舟共济、互帮互助的香港精神的生动诠释。凭借这一精神传统,香港将来自五湖四海的难民团结凝聚在一起并创造了本土家园。这一点在粤语旧片《危楼春晓》(1953)、《难兄难弟》(1960)、《七十二家房客》(1973)中也都有所体现。而《幸》藉由芬姨和阿旭相互扶持与守护的故事,试图说明这一精神传统在“后九七”社会现实中也仍未过时,依旧可以为今天民众跨越本土与非本土的鸿沟、重建包容性的身份认同提供有效的历史资产。
总而言之,《三》与《幸》虽然在故事内容上十分不同,却都诉诸于一种开放、包容的跨境身份想象,并且不约而同地选择把广州作为通往跨境融合的中介角色。
三、 结语:延续与发展
综上所述,“后九七”香港电影中的广州景观在延续九七前(特别是“黄金时代”)电影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变化。以《逃出生天》为代表的合拍片继承了《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南海十三郎》等将广州、香港视为一体化空间的做法,所不同的是将空间场域从历史拉到了当代。其做法对于今天中港合拍片如何在迎合内地意识形态的同时避免本土意识的消弭、如何保留本土特色颇有启示意义。以《树大招风》为代表的中型商业片则与《省港旗兵》系列一脉相承,将广州喻指大陆他者。不过仔细辨析的话两者又有微妙的差异。《省港旗兵》系列对于大陆他者抱持较辩证的态度。像麦当雄的《省港旗兵》既表现大圈仔的凶恶斗狠,又肯定他们的忠诚义气。相比之下,《树大招风》对大陆他者的论调更为灰暗,态度也更为拒斥,反映了近年部分港人的身份焦虑及激进本土主义的抬头。以《三条窄路》、《幸运是我》为代表的小成本制作则与《客途秋恨》、《甜蜜蜜》等较相似,将广州作为连接中港的中介。此类作品虽然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却提供了更具建构性和想象性的“后九七”跨境身份认同策略,其价值不容小觑。
需要说明的是,勾勒广州景观的“后九七”香港电影虽然是分化的、多元的,但也有一定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在不同程度上重视本土特色的保留和本土意识的表达。放置于“后九七”语境之下,这对于香港电影如何在参与国族身份建构的同时,保留并更新本土身份,实现国族身份与本土身份的平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这也正是探究香港电影省港“双城记”的价值所在。
注释:
1.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33页。
2.参看罗卡:《香港、上海、广州的交流》,见罗卡、法兰宾,《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0-127页。3.参看黄爱玲:《梦中曾相识——香港电影中的广州回忆》,见黄爱玲编,《粤港电影因缘》,香港电影资料馆,2005,188-199页。
4.参看张颐武:《后原初性:认同的再造和想象的重组》,《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39-44页。
5.Chu Yiu-wai, “One Country Two Cultures? Post-1997 Hong Kong Cinema and Co-productions,” Kam Louie ed. W ord and Image: Hong K ong Culture, Hong K ong University Press,2010: 131-145.
6.王妍如:《主旋律与类型元素结合的成功尝试——“《逃出生天》电影座谈会”综述》,《当代电影》,2014年第4期,108-110页。
7.列孚:《CEPA十年看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嬗变》,《电影艺术》,2014年第3期,20页。
8.同上。
9.谢小芬:《新世纪广东电影的身份认同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论文,2015,32页。
10.陈志华,《<树大招风>: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城市的唏嘘》,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11-culture-columnchanchiwa/。
11.M a N gok, “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 risis in Postindustrial Hong K ong,” in Asian Survey51, no.4 (2011):683-712.
[1]黄爱玲.《粤港电影因缘》[C].
[2]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M].
[3]列孚.CEPA十年看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嬗变.《电影艺术》[J].
[4]罗卡、法兰宾.《香港电影跨文化观》[C].
[5]Kam Louie. W ord and Image: Hong Kong Culture[C].
[6]王妍如.主旋律与类型元素结合的成功尝试——“《逃出生天》电影座谈会”综述.当代电影[J].
[7]谢小芬.新世纪广东电影的身份认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8]张颐武.后原初性:认同的再造和想象的重组.《文艺研究》[J].
[8]Ma Ngok. 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risis in Po st-industrial Hong Kong. Asian Survey[J].
[9]陈志华.《树大招风》: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城市的唏嘘.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11-culture-columnchanchiwa/[OL].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华语电影中的广州城市形象研究”(GD16XYS07)阶段性成果。
霍胜侠,女,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