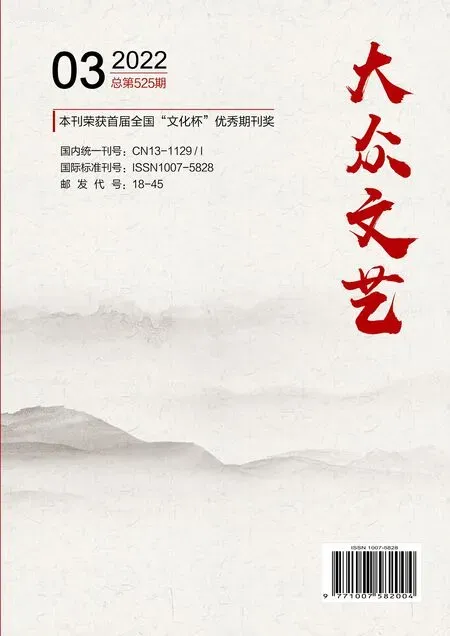论东晋是我国古代诗书画结合的初步成型期
陈志刚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655011)
论东晋是我国古代诗书画结合的初步成型期
陈志刚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655011)
诗书画乃我国古代文人名为三项实为一体的鲜明标志,它承载着文人的道德情操、人生情趣和美学风尚等,兼通诗书画是古代文人梦寐以求的艺术极境。时至今日,秉持上述艺术追求的文人学者仍不绝如缕。那么,诗书画三种艺术初步相互结合成型并被文人如此看重到底发端于什么时候呢?汉代以前,诗歌主要承载着政教伦理的讽谏教化功能,书法以实用为主,绘画以劝善惩恶的人物画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书画能够相互结合是不太可能的。汉末儒家思想衰颓,道家思想兴起,玄学兴盛,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而且日益发展、兴盛。汉末、魏、晋时期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士人的个体意识觉醒,文艺也随之觉醒。此一时期,诗歌抒情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书法进展迅速且开始脱离单纯实用的状态,自然山水在绘画中的不断增多且改变着过去人物画为主的绘画格局,绘画的鉴戒功用不再那么强大。因此,自汉代末年起,我国实际已经初步具备诗书画三者相互结合的基本条件,汉末、魏、西晋依然是诗书画结合的积蓄期,东晋成为我国诗书画结合的初步成型期。本文从诗与画的结合、诗与书的结合、书与画的结合三个方面揭示东晋确为我国古代文艺史上诗书画结合的初步成型期。
一、诗与画的结合
王彪之(王廙弟王彬次子)《二疏画诗序》云:“因扇上有画二疏事,作诗一首,以述其美。”王彪之观扇画作诗称述疏广、疏受叔侄俩的故事,因观画而生诗情。虽然王彪之的诗歌未能流传下来,但是应为咏史抒怀类诗歌,抒发的该是淡泊功名、急流勇退的情感吧!王彪之是与谢安齐名的少有的东晋贤臣,其观画作诗抒怀之举对东晋士人的影响应该很大。张可礼先生认为,王彪之的《二疏画诗》“可能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题画诗”
《世说新语·巧艺》载:“戴安道(戴逵)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东汉张衡有《南都赋》),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晋书·儒林传·范宣传》载:“(范宣)尤善三礼……(庾)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太儒?’宣曰:‘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恪守儒家思想甚至批评道家思想的范宁是东晋的纯儒,他轻视绘画,认为绘画是“无用”的。然而,在看了戴逵画的《南都赋图》后,他改变了以前的看法,认为画“有益”而重视起来。大概范宣以前所见的绘画与戴逵的绘画有很大的不同,范宣所见的承载着儒家鉴戒功能的绘画在东晋已经被人乔装打扮地加以利用,粉饰、颂赞之意太浓,所以范宣对这种画比较反感,故而视其为“无用”。戴逵据张衡《南都赋》画的《南都赋图》显然属于景物画,主要显示了绘画的细致入微的描摹技艺,可以增长见识。由此,东晋的绘画已经不是只有承载鉴戒功能的人物画,而是逐渐产生了以描摹自然、人文景观为主的景物画,就连范宣这样的纯儒也因此改变了以往对绘画的看法。东晋绘画借文学发展新变之走势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综上所述,不论是王彪之感扇画作诗,还是戴逵将赋绘成图后让纯儒范宣改变对绘画的看法,都表明,东晋士人已经开始朦胧意识到诗与画进一步结合的可能性。德国美学家莱辛(1729—1781)在《拉奥孔》中说:“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莱辛着重分析诗与画的规律和差异,从而批评当时甚为流行的诗画一致说。莱辛所说的“诗”指广义的文学,而且是以叙事为主的西方传统,他所说的“画”可以泛指一切造型艺术,且是以焦点透视为主的西方传统。所以,照西方的传统和思想来看,诗与画的差异是远远大于相同的。其实,这也可以用来反思我国古代诗与画的关系。我国古代诗歌从一开始就形成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我国古代绘画的从一开始就是以线条塑形从而传神的传统,因此,绘画重在传神与诗歌重在抒发内在情感是可以产生共鸣的,是可以融合的。这就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独特之处。
汉代以前,诗歌的抒情传统在先秦发端,尔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兴盛而渐趋衰颓。自汉末以来,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诗歌的抒情传统重又兴盛,魏晋承续着这股抒情传统。陆机《文赋》首倡“诗缘情”,但理论意义大于实际创作中的意义,西晋士人遗落了汉末和魏之抒情传统,走向消极颓放,东晋士人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和玄远的人格,在看似抽象的哲理外衣下涌动一股浓郁的抒情传统。绘画的发展远没有诗歌那么曲折,晋以前,还是以人物、动物为主要题材,注重的是绘画的形似和鉴戒功能,故有以“画赞”命名之作,如:潘岳《故太堂任府君画赞》。至东晋,随着士人投入自然,山水题材开始兴盛,绘画的鉴戒功能弱化,绘画也不再以形似论高低优劣,而是模糊朦胧地开水追求自然山水中蕴含的哲理和意趣。可以说,诗歌的抒情传统与绘画的传神思想在东晋初次相遇,终于即将叩开我国古代诗画相通的大门。在这里,我国的传统与西方的传统是不一样的。
二、诗与书的结合
诗与书的结合可以说就是文学与书法的结合。在书法的实用性还很强的时代,在书法的抒情性还没有得到发展的时代,书法仅被视为文学的媒介和载体,实在谈不上什么结合。我国书法在东晋十分兴盛,不仅因为各种书体均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也不是因为出现了书法象征——王羲之,而是因为此时书法的抒情功能首次盖过了书法的实用功能。王羲之《又遗谢万书》云:“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所谓“言所不尽”的“书意”,可以说既指书法的形式美,又包含了书法家的情感和思想。《世说新语·文学》载:“羊孚作《雪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遂以书扇。”羊孚的《雪赞》如此之清美,桓胤忍不住将其书之于扇,这完全是出自一种审美的冲动,书法的抒情性、审美性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再有,王献之书魏曹植《洛神赋》。在东晋,似这样的情形是比较多的。从西晋开始,研究探讨书法用笔、体势等问题的专门文章逐渐出现且呈增多之势,这表明,两晋士人对书法的美有了比前代更加自觉的关注,由此再前进一步,书法家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融进书写中,书法的抒情功能得到初步的展示。
东晋书法传世的真迹不多,但留下的书帖却很多。下面引录数则“二王”书帖,以此领略东晋书家信笔所书的闲情逸致,有的书帖简直就是一篇极简短的小品文。由此可见东晋诗与书的结合状况。
先看王羲之的书帖: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
“雨寒,卿各佳不,诸患无赖,力书不一一。羲之问。”
“六月十六日羲之顿首:秋节垂至,痛悼伤恻,兼情切割,奈何奈何!”
“初月一日羲之白:忽然改年。新故之际,致叹至深,君亦同怀。近过得告,故云腹痛,悬情灾雨,比复何似?气力能胜不?仆为耳。力不一一,王羲之。”
综观上引杂贴,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点:首先,书法的实用功能似乎仅仅只剩下互通消息、互诉情感的载体;其次,书法的抒情功能大大彰显,或抒发“逸民之怀”,或抒发“无缘言面”“瞻近无缘”的相思之叹,或抒发由季节变迁引发的“痛悼”“致叹”之情,在严可均先生辑录的《全晋文》“王羲之”部分,这样的简短抒情书帖简直太多了;再次,书帖颇有文学色彩,读者稍加细读,羲之书帖流露出的自然、真挚之情是不难体会的。“秋节垂至,痛悼伤恻,兼情切割,奈何奈何!”这些语句颇似四言诗歌,读来不禁让人与作者一道体会由自然变化引起的伤感和对生命的忧虑之情。而这些极具文学抒情、简洁叙事的文字又是由大书家“二王”所写,其缘于诗书结合的内外之美自不待言。《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成为二宝。”谢灵运一生跨越晋宋,但从其情感、心态等来看,其实更有晋人神韵。宋文帝将灵运手书的诗歌称为“二宝”,这透露出当时的人们已经朦胧认识到诗书结合后生发出得一种更加倾人心魄的艺术之美。这种不刻意于诗书的书帖和诗歌恰巧体现出东晋诗书两种文艺形式亲密无间的关系,待到后世有意为之的时候,诗书结合的那种自然之美随之多了几分刻意的人工气。由此,我们不得不惊叹东晋由诗书结合衍生的这种天然艺术美。
下面,再来看几则王献之的书帖:
“得书为慰。吾先夜遂大得服汤酒,诸治渐折,故顿极难劳。知足下便去,不得面别,怅恨,深保爱。临书增怀。王献之。”
“献之等再拜:不审海盐诸舍上下动静,比复常忧之。姊告无他事,崇虚刘道士鹅群并复归也。献之等当须向彼谢之。献之等再拜。”
“南中佳音一一,小慰解数月也。吾甚忧虑卿,君何如耶?献之。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由上引献之杂贴可见,“临书增怀”“常忧之”“甚忧虑”等表明了书法的抒情功能。书法还可以用来记录自然山川之美。在献之的杂贴里,“驰情”出现了三次,这说明献之也是一个极其敏感多愁的人,他的忧愁借与亲人、朋友间的简短书信得以宽慰消解。
总之,以“二王”书帖为代表的东晋书法的抒情功能远甚于其实用功能,简直就是一则则简短的记录日常生活琐事的精美小品文,抒情就是诗与书互相结合的紧密纽带。张可礼先生将东晋书法与文学融合后形成的文艺现象概括为“书法文学”。窃以为,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三、书与画的结合
我国古代文艺书与画的结合向来就有天然的优势,且有着迥异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色。书画均用同一种书写工具,汉字早期发展演变中的象形文字就颇有几分绘画的意味。我国书法讲究的是笔画(早期实为线条)和,我国绘画也逐渐形成一个以线条为主的传统,这是形成书画相通的基本条件。唐代张彦远说:“是故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又说:“故工画者多善书。”又说:“故知书画用笔同法。”东晋书法是我国书法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各种书体都已经出现,有的书体还达到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被后世称为“晋书”或“晋字”。东晋绘画还是我国绘画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之一,其时山水画开始萌芽,打破了人物画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对绘画的功能的认识更趋于多样化。这都是促成东晋书画相通相融的有利条件。
在初唐史臣撰的《晋书》中,记载了一些兼擅书画的士人。《晋书·王廙传》载:“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王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戴逵)能鼓琴,工书画。”以上是明言兼擅书画,还有《晋书》虽未明言其兼擅书画,但也可隐约看出其兼擅书画的,如:明帝司马绍、王濛、王羲之、谢安等。再如顾恺之和宗炳。“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说顾恺之“尤善丹青”,那么意味着顾恺之也是擅长书法的,只不过其书法没有绘画那么精进罢了!所以,顾恺之也是一位书画兼擅的东晋文士。
东晋书法已经发展到不仅要写得美,而且广泛被人们认为能体现书写者人格、美学情趣的一种文艺。东晋绘画中自然山水成分的增加与此时期士人普遍以玄学眼光观看、体悟自然同步前进,正在改变着以前绘画的题材和寄寓,酝酿出一种可以寄托士人个体情趣和精神的绘画。这就给书画的深入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东晋士人的文艺实践表明,书法与绘画的结合已经达到了我国古代文艺史上的最高潮。
综上所述,在诗画结合方面,东晋士人已经开始朦胧意识到诗与画结合的可能性。与西方诗画相异的传统不同,我国古代诗歌以抒情传统开端,我国古代绘画开始虽以线条塑造形象开始,但发展至东晋日渐趋向传神,东晋士人虽沉迷于玄、佛义理之中,但也涌动着追求超俗人格和精神自由的情感暗流。诗歌抒情传统与绘画的传神旨趣在东晋相遇,注定了诗画结合的深度将大大得以开拓,东晋因此成了我国古代诗画结合的初步成型期。在诗书结合方面,东晋书法兴盛,书家自觉探索书法本身的美,书家在实际的交往、应酬中大大减弱了书法的实用功能,发展了书法的抒情功能,诗书结合具备了历史最好条件。以“二王”书帖为代表,简直就是用书法记录日常生活的小品文,其中的抒情因素是非常浓厚的。抒情是诗书结合的纽带。在书画结合方面,东晋书法兴盛,书法的抒情功能特别明显,东晋绘画摆脱了寄寓鉴戒的人物画一统天下的局面,自然山水开始浸入绘画,这极大地促进了东晋书画的相融相通。各种典籍记载有的东晋士人兼擅“书画”,没有明言的更多,这表明,东晋成为我国书画相融相通的初步成型时期。历史给了东晋士人千载难逢的机会——诗书画的结合,有时还是相融相通的深度结合,因此,东晋是我国古代文艺史上诗书画结合的初步成型时期。我国文艺史表明,唐宋文人士大夫最终铸成我国文人诗书画兼擅的传统,然也不能忘记东晋士人对此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在这方面,学术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1][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2页、第209页、第209—210页、第210页、第221页、第223页、第225页、第268页、第271页、第272页。
[2]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125页、第194页。
[3]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386页、第388页、第387页、第149页。
[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60页、第2405页、第2002—2003页、第2104页、第2457页、第2405—2406页。
[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483页。
[6]宫建华:《文艺评论》,2011年第7期,第115页。
[7][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8][梁]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2页、第2278—2279页。
[9][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2页、第16页、第26页、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