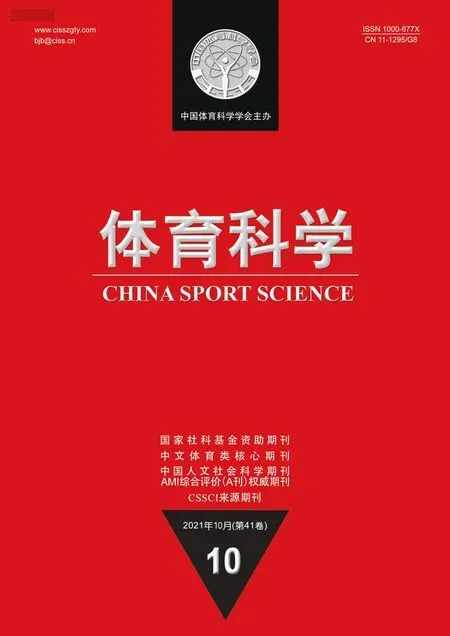民国时期体育议决案对武术教育发展的影响
刘帅兵
LIU Shuai-bing
民国时期体育议决案对武术教育发展的影响
刘帅兵
LIU Shuai-bing
民国时期由教育家和体育家针对当时的体育现状并结合时代背景所提出的建议,通过大会形成议决案。议决案的形成不仅映射着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历程,而且推动着武术教育的发展。通过对民国时期与武术教育相关的体育议决案进行整理与分类,大致以军国民教育的议决案、学校体育的议决案、学校武术教育的议决案、社会武术教育的议决案、武术师资培育的议决案、武术教材编订的议决案等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体育议决案对于武术教育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军国民教育为武术在学校教育中提供合法地位;兵式体操的废除为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提供有力时机;推动武术成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必修课;推动武术师资的培育;推动武术教材的编订;推动武术教育的社会化。体育议决案的制定体现了社会精英们把中国武术与时代命题进行关联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反思。
民国;体育议决案;武术教育;影响
1 引言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国人鉴于体格之弱,学步列强,提倡体育。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体育家针对当时的体育现状在各种不同的教育、体育会议上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并通过大会形成议决案。议决案是经会议正式讨论通过,并作成书面文字记录在案的事项,是形成中国近代体育法规的基础,亦反映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在各个时期的特色。在以往对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研究中,体育议决案是学者很少关注的一个视角。体育议决案对于推动近代中国武术教育的发展同样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性力量。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体育议决案的梳理和分析,大致以军国民教育的议决案、学校体育的议决案、学校武术教育的议决案、社会武术教育的议决案、武术师资培育的议决案、武术教材编订的议决案等为切入点,结合民国时期的历史语境,就体育议决案对武术教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初步研究和讨论。
2 军国民教育为武术在学校教育中提供合法地位
军国民教育主义是清末民初盛行的一个重要教育思想,是指通过对学生及全体国民进行军事训练和尚武精神的教育,以增进国民体质使学生及全体国民具有军人品德和能力,达到寓兵于民,旨在抵御外侮、富国强兵的思想教育运动[25]。军国民教育使“尚武”成为当时最具号召力的符号,体现着教育救国与尚武救国的结合。1906年3月,由学部制定《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并呈请朝廷批准实施,同年光绪帝批准了此奏折,至此,标志着中国教育管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颁布的教育宗旨诞生。该宗旨指出,中国民质之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为“尚公、尚武、尚实”,其中,尚武要求效仿“东西各国,全民皆兵”之制。教育作为政治的附庸,必然凸显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事实,因此,军国民教育主义必寓于中小学堂的各个教科书中。对于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34]。体操一科包括普通体操、兵式体操和游戏,名为体操实际是军事训练。“‘以弧矢戡定天下’的满清统治者谕学堂以舶来体操培育尚武精神”[6],军旅武术同样具备军事和尚武的功能却没有被清政府所采用,虽然提出尚武御侮,但以兵式体操来练习武事。武术被体操所代替不仅与武举制废除有关,亦与当时义和团运动致使清政府对武术非常忌讳相关。
1911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教育会议”(旧称)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会议提案中有2件与体育相关的议决案,《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与《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2个议决案均上奏请示清末政府特颁谕旨,宣布军国民教育主义。两者以培养学生忠勇精神为目的,为达到强国之根本和立宪之基础。在《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中规定军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兵式体操、打靶实习、讲授武学等,特别强调各类学堂一律把体操科列为主课。在《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中,除了有《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的内容之外,还提出初级小学应注重游戏、初级师范学堂应注重体操方法、高等小学以上应兼习拳术,强调各学堂均厉行军国民教育主义之训练。1915年1月,袁世凯在《颁定教育要旨》中进一步阐释尚武的内涵:“尚武之道分之为二:曰卫身;曰卫国。合之为一,卫身即卫国,卫国即卫身也……故今之言国民教育者,于德育智育外,并重体育。”[39]继清末拟定的《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与《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之后,根据袁世凯的《颁定教育要旨》和世界发展趋势,欲使国家强盛,必先厘革体质羸弱,铲除民风不振之境遇。为保障军国民教育贯彻落实,1915年4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民国期间共召开了11届年会(1915—1926)。在会议期间,教育部派人员出席,教育总长、次长多次到会发表讲话。其形成的各项议决案,从来源、审查、通过到执行都有相应的程序来保障,会员所提交的提案要以所代表教育会的名义提出,且须在开会前2个月分送各省区教育会先行讨论。大会所形成的议决案内容均呈教育部,或呈请教育部施行,或由教育部备案存查,或呈请其他政府部门采纳。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会议,提出《军国民教育实行方案》,并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建议,其内容分为教授部分和训练部分两类。
其一“关于教授者”指出,小学生注重作战游戏,师范学校、中等学校或中等学校以上分别学习军事学、兵式枪操、射击、野外运动等。各学校“应添”中国武术,其教师由各师范学校培养。教科书适当列举古今尚武的人物和国耻的案例,与军国民主义有关的材料须特设时间讲授,校歌选用雄武的词曲以激励学生志气。其二“关于训练者”指出,小学生应当养成军国民的气质以及军人的志向。高等小学以上的学生一律穿制服。中等以上各学校管理参考军校管理模式,学生应当具备充当兵役的能力。各学校须注重体格检查,养成辛勤劳动、粗衣淡食的习惯以及雄健齐整的校风。各学校特设体育会,并严格实行各种运动游技。各学校制作国耻纪念物,以促进警悟自省,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讲述其功绩[14]。
清末时期,军国民教育运动的开展,不仅开启了一场身体改造运动,同时将“国家”这个概念塑造成为身体忠诚的惟一对象[12]。将这两个同步发展,体现了社会精英面对国权丧失而提出具体改革主张的一种责任担当。民国初期的学校体育沿袭清末,尚武与军国民教育主义的一致性,使得尚武成为军国民教育的核心。军国民教育以兵式体操为主,内容是军队的整列和列队。兵式体操的引进,实则是对封建社会忽视民族体质和尚武精神的一种反思。在1911年的《定军国教育主义案》中,有“高等小学以上应兼习武术”的规定,并明确指出各地方应自行举办。1915年欧战的炮火和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国人觉得非尚武不足以立国,非图强不足以雪耻。因此,北京体育研究社提出在学校体操科内兼授中国武术,列为必修科,以振起尚武之精神,并向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交《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科案》。同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形成《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法案》,指出“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
从2个议决案中“应兼”“应添”的用词来看,这2项议决案还仅处于建议层面,和“以肄武事”的体操相比中国武术还处在“游离”状态。虽如此,此时期与清末时期政府不事提倡武术相比,已有所改观。即便提倡中国武术仅是为兵式体操训练做辅助,或者说“不过是一种利用,绝不是真正提倡武术”[15],但此时的中国武术在学校教育中其地位合法。
3 兵式体操的废除为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提供有力时机
1914年,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指出:“强国之道,首重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体育不讲,人种不强,国将安赖。”[35]在他看来,学校体育亟需革除兵式体操:首先,兵式体操属于军事方面,国家有专门军队以防御外侮,其训练目的无非攻占杀伐,与学校体操“保存康健”相违背;其次,各学校兵式体操多邀请军人教授,且多为军队中所不齿者,品行不端、文字不识、粗暴之气俗不可耐;最后,中国武术是我国最古最良的体操术,较之东西洋所谓的高等体操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提出“高等小学中学师范亟应添习本国技击一门”。
事实上,在军国民教育主义兴盛的民国初期,西方体育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轻视身体运动的传统,国人开始把身体运动、体魄健康、体育竞争和国家兴亡紧密相联[40]。1913年2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了总成绩第2名,但明显感觉到中国的体育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差距,“试观日本数十年来之体育,何等注重,然较之欧美各国社会体育之能普及者,尚觉瞠乎其后”[26]。之后又因鉴于世界发展趋势,军国民教育已不适合于新教育的潮流,需对学校体育加以改进,于是在1919年10月第4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产生了《改进学校体育案》。该议决案主要涉及减少兵式体操时间以体育代之,并增加体育经费,注重师范学校与女校的体育,改良高等小学校国民学校体育,实行身体检查,改良运动会等。
为使学校体育学科日趋完善,应着重从研究体育旨趣与方法的人才培养开始,北京体育研究社于1919年向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请设国立体育学校案》。该议决案认为,虽然上海体育专门学校、东亚体育学校、体育师范学校、中国体操学校等把培养体育师资作为目的,但是这些学校均属私人团体,绌于款项规模不大,不能成为各校之楷模,又因学校体育关系到国家体育的前途和命运,至深且巨,有必要设立国立体育学校。对于中国武术特别强调“因门户歧见、拳种多样、风格迥异,究之各有所长未可厚非,融会贯通调剂适当,是所望于国立体育学校者”[27]。
“吾国体育问题,素为国人所轻视,全国人口既无明确之统计,其生存死亡率自无切实之比较,然考证事实体察情形,国民体育未能与他国抗衡,盖无可讳。”[26]鉴于此,在1919年第4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形成《推广体育计划案》。该议决案除了涉及体育上的设施和改进事项之外,还提出“提倡武术,发展国人特殊之运动”[26],并在“学校体育”中强调“加授武术”的内容。之后为了在学校体育中“加授武术”这一事项的顺利完成,山东教育会向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案》。中华新武术是马良根据自己多年习武经验从浩繁的传统拳械套路中,抽取武术的基本动作,加以修改和组合创编而成。根据议决案的要求,将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及议案函交付各省区教育厅,由教育厅再转交各中等以上学校的体育教员以供参考,但是当时若干省并未设置教育厅,所以,此议决案并未能完成理想的推广。
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方案》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受美国教育家孟禄的影响,并模仿美国的“六三三”分段的单轨学制而制订。1923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正式把学校的“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并扩大了体育课程内容,规定初中和高中加授卫生学和生理学,还要求小学体育课占总课时10%,初中体育课为16学分(包括生理4学分),高中体育课为10学分(包括健身法与卫生法)。之后,学校体育内容以普通体操、田径、球类、游戏等项目为主,并逐渐代替兵式体操。新学制标志着新体育课程体系的建立,学校体育从此朝着“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28]。在把体操科刚改为体育科时,学校体育虽因破旧立新而处于混乱状态,但是兵式体操的废除为“更多运动项目进入学校体育课程提供契机”[17],当然,中国武术也顺势进入学校体育领域。1924年,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附属小学校向“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提交的《小学校自初级三年级起体育一科应加授国技案》中指出,中国武术刚柔兼备,精力两全,不仅适合于成人练习亦更宜于儿童学习,提议“将三年级以上之体操时间,完全改为武术。同时组织课余武术团”[37]。1926年,在《学校体育应特别注重国技案》中再一次指出中国武术刚柔兼备,精力两全,“各学校体育,均须加授国技,但以不妨碍儿童身体发育为原则”。其实在此之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都曾通过类似的议决案,教育部也曾通令,但推行效果不佳,故在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再加研讨。
总之,自然主义体育与军国民体育相比明显表现出其项目多样化和理论全面化的特性,其锻炼方式和方法更符合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加之“壬戌学制”的制定为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性指导,此时武术被列入学校体育课程与军国民教育对武术的“利用”相比,更凸显为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服务的目的。从上述议决案中的“加授武术”“完全改为武术”“均须加授国技”等这些带有强制性的词语,可见当时国人的用心。在中国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之初,“武术进入的学校多为专门以上高(职)校较多,这些学校多处风气较开的、武术社团组织较为密集的沿海和发达城市”[6],一些偏远的乡村并没有开设武术课程。学校即便开设武术课程,由于武术师资严重缺乏,体育教师难以胜任武术教学,以至于武术在学校体育课程中处于非主课状态。当然,西方体育理论的引进,为武术学科的完善以及演进提供了先进的学理支撑。
4 推动武术成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必修课
进入学校教育之初的中国武术“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16],即武术在学校体育的框架之内仅作为选修课并非作为主课存在。“从体育专业教育机构看,无论大学、学院或师范专科,武术所占学分都极少,且非每学年的必修课程。由于学生所习甚少,又不常复习容易忘却,毕业后成了学而不用的科目。”[36]在历次规定的体育课程标准中都提到过武术,但是仅有的武术教材并没有进行学年划分,教材难易程度未作区分,男女性别以及季节因素没有考虑在内,武术课程形同虚设。
1918年,山东公立农工商法四校在“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上提出《请将中国固有武术加入专门学科案》。该议决案指出,学校教育因倡导三育并重,故学校体操列为专科。虽然全国中学以上学校练习兵式体操用意至深,但是兵式体操适合于团体习练,不适用于个人习练,即便兵式体操行列步伍,严整可观,但在学校教育方面存在诸多缺陷。而中国武术固有拳师名家,与其步外人之后尘不如保固有之国粹。“拟请由部通令各专门以上学校,将吾国旧有武术,择其适用团体教练者,列为必修科,以资练习。庶整齐划一,于军事教育前途裨益当非浅鲜。”[23]此议决案经过会员共同讨论,议决结果为中国武术由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专门以上学校开设,不必列入学科之内。虽然中国武术并未和体操一起被学校列为专门学科,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能有学科意识已难得可贵。1919年,山东会员郭葆珍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上提出《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案》,指出:“武术一项,于身体裨益最多,各校应即切实提倡,以振起国民尚武之精神,而发挥国技莫大之功用。现闻各省中学校已有将武术加入课内练习者,俟将来师资教本均不感困难时,希望全国中学校一律定为必修科,以期体育教育之普及。”[21]中国武术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可以养成强身自卫能力,意义重大,因此在“办法”中提出“培养师资,预备教本,提倡方法”3点建议。
在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张之江针对全国学校体操多采用欧美式训练,既不合国情又不适用,与国术相比实有天壤之别,提交了《请令全国学校定国术为体育主课案》,该议决案被大会决议交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该议决案中提出“通令全国各学校亟以国术一门,定为主课。并普及民众,以资锻炼,可增健全,自强强国,实利赖之”,并在“附件2”的《请提倡我国固有武术案》中制定了5年规划:
“1)最近一年以内,中央及各省区,各设武术专门学校。或于中央及各省区大学内,添设武术系,由大学院联合国术研究馆,共同组织。其教师人选,由国术研究馆介绍专家充任之。学生毕业后,即发充各校军师团营,充武术教员。2)最近三年内,各级学校除前期小学外,均得自由添设武术课程。三年之后,武术教师当已略可敷用,即由大学院修正令各级学校将武术科正式订入课程。届时各级学校当以武术为必修科,无此科者,其学校取消立案,其学生不准毕业。3)最近五月内,大学院须成立武术教育委员会,联合国术研究馆,共同组织之,负责提倡武术。4)五年以后,中央须设立武术学院,罗致武术最高人才,为奖励研究武术机关,兼为研究武术之中心。”[22]
如此强有力的议决案,绝不是仅限于培养学生的“体德二育”,更指出“况强邻环伺,倭人更暴,岌岌不可终日,为御侮雪耻计,提倡国术,更不得视为缓图”。在民族主义的支撑下,民族存亡与国家兴衰成为学校武术教育优先考量的重要目标。在“附件1”的《国术研究与民族强弱之关系》中指出:“国民革命,首先唤起民众;我们要承认武器是有限的,惟有国术这件宝贝,只能普及于民众,力量异常伟大,所以真正要唤起民众,要国民革命成功,便要普及国术。”[41]以国民革命为动机的武术教育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根据北京体育研究社1924年的调查,北京成立的民间体育团体就有13家之多,如北京体育研究社、剑术研究社、中华尚武学社、北京武术体育会、中华国技武术研究社、陶然武术团、四民武术研究社等。天津的民间武术团体有中华武士会、天津武术学会、天津进德武术会、天津道德武术研究会。这些民间体育团体,或以研究国技、传习武术、振兴尚武精神为宗旨,或以研究体育、发展体育为宗旨,或以两者兼之为宗旨,但目的均以健全国民之体格为己任。这些民间体育团体随时代应运而生,有的出于爱国热诚,以私人的力量来推进;有的为实验技击,纠合同志设研究所。但其中也有些体育团体存在“竟别立宗法,以××社的名义大收其门徒,使爱好国术的青年,不信仰统一化的科学技击,而迷离于怪诞不经的自炫稗史”[20]的现象。另外,“这种社团组织,出于无权无位的小民则可,若‘政在掌握’的国术官。尽可以如孔子所云‘君于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了,而现在之私立门派,以扩张个人势力,是何居心?”[20]因此,马良、陈泮岭、刘慎旃、李百龄等人在1932年的全国体育会议上提出《请筹办国立国术专科学校案》,在此议决案中提出筹办国立国术专科学校的理由:一是广植人才普及国术以为国族;二是根据科学方法、武术原则训练国术人才,造就中华式体育。在1940年的全国国民体育会议上,张之江汇报了全国各级学校的武术课程设置情况(统而计之,不过十分之一二,且多作为课外活动)。在张之江看来,中国武术具有强种与御侮的功效,习练设备简单、经济、便利,不仅符合我国当时经济状况,而且适合社会推广,以建立“健勇自卫”基础,实现国民精神总动员,故提交《拟请由部通令全国大中小各级学校列为国术为必修科案》。议决案指出:“请部通令全国大中小各级学校,列国术为必修课,并给予学分,凡考试不及格者,不准升级或毕业。”[42]
虽然在1918年提出的《请将中国固有武术加入专门学科案》最终经过讨论并未将武术列为专门学科,但是从之后的《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案》《请令全国学校定国术为体育主课案》《请筹办国立国术专科学校案》《拟请由部通令全国大中小各级学校列为国术为必修科案》来看,武术在学校教育中逐渐开始从边缘走向主流,从最初的选修课开始向必修科过渡。以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为例,从其1936年的课程安排来看,武术和国术研究仅作为选修课,但在西北师范学院时期(1940—1944年)已经把武术课程作为主课安排在第三和第四学年。1942年,由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体育课程标准》,在该标准中规定体育正课课时安排为“第一二学年各学期每周正课三小时,一小时教授学科、二小时教授术科。第三学年各学期每周正课二小时”[30]。在体育正课中,各个年级武术内容占体育教材的比例为男生10%、女生5%。其实,国民党时期的学校武术教育制度、标准、措施等有的并未进行实施,有的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但把武术作为必修课,并给予学分且与升级和毕业挂钩的举措,把学校武术教育推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5 推动武术师资的培育
中国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首先要解决武术师资问题。“在过去关于国术的教授,完全是依赖私人间的自由教练。其教练方法,并无规则,只不过应用某种模仿的方法而已。”[31]所以,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必须应用教育的原则,而指导教练,在教的人如何教导,学的人如何学习,完全听学校化、教育化,这样才能够使国术迅速地发展和进步,才能够达至提倡国术的奥秘”[31]。然而,“知新教法者,不擅长武术。擅长武术者又不明新教育,故此养成体育师资之不容少缓也”[43]。师资缺乏“教授未易得人”,欲使学生学习中国武术,非有专门教师指导不可。对于武术师资的培养在《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法案》中规定:“于师范学校养成之。”在《推广体育计划案》中指出:“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均设体育专修科,以应各省之需要。”在《请设国立体育学校案》中指出:“国家对于重要学术,莫不设国立学校以培植人才。”在《学校体育应特别注重国技案》中指出:“凡设有体育专科之学校,应加授国技学科以储师资。”在《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案》中对于师资的培养指出:“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添设武术一门以及各省区设立武术传习所。”
针对武术师资议决案的陆续提出,体育社会团体以及师范院校体育系(科)相继以培养武术师资为己任。例如,北京体育研究社附设的体育讲习所(后改名为北京体育学校),其主要目的就是培养武术师资。北京体育研究社虽属民间武术社团,却因以培养武术师资为主要目的而得到教育部的支持,甚至教育部发专文给全国各省市教育管理部门,要求其“所属大、中、小学选派专职人员前来学习(培训),并准允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学校担任专职武术教师”[7],这些武术教师再进一步培养学生。北京体育研究社附设的体育讲习所的入学资格为现为及曾为中小学校体操教员及高等小学校以上毕业生;之后改为北京体育学校,其入学资格为师范学校及中等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即可。体育讲习所的学业年限为一年半,体育学校学业年限为3年,其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
中央国术馆成立以来,其工作集中于培育师资、编订教材、训练民众等事项。在张之江看来,“以培养师资为最重要、最根本”[44]。为了弥补各学校武术师资的匮乏,张之江等人在中央国术馆内附设体育传习所(后改为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以培养专业武术师资。由中央国术馆培养的武术毕业生,以优异成绩留在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的有李元智、张文广、何福生、康绍远、李锡恩、温敬铭、张登魁、胡云华、傅淑云等。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对入学资格有严格规定:年龄在18~25岁之间,身体健康,品行端正。招收对象分三类:高级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者,体育专科学校毕业者,专门军事学校毕业者。学业年限分为3年制和5年制专科两种。另外,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对于学生毕业有严格的考核标准,若有一项考核未通过则扣发毕业证。其武术考核内容包括练步拳、新武术、八极拳、太极拳、摔角、拳击、刀、枪、剑、棍等。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从1933—1949年被合并仅存16年,却培养出武术与体育师资600余人,遍布世界各地,如张震海(美国)、陈玉和(新加坡)、刘景行(泰国)、张文广(北京)、温敬铭(武汉)、王景伯(贵州)、张庆林(江西)等。精武体育会亦注重武术教师的培育,又因学校亟需武术教师,精武体育会定期派会员到学校教授武术,如姚瞻伯、郑灼辰分期赴广东小学,简世铿赴培德学校,王亨利赴庭助小学,郑福良赴爱国女学校,宁竹庭赴山东会馆小学,陈土超赴祟德女校,李志荔赴广肇女校,马信忠赴广肇义学等。此外,还有一些师范院校体育系(科)培养武术师资,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均涉及武术师资的培育。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资格为中学或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则放宽至同等学力者亦可,年龄在18~24岁之间。符合入学资格者可直接向两校报考,并通过入学考试成为正式学生,对于体育学科,则需要增加体格检查和体操测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的武术内容有罗汉拳、少林拳、枪、棍、刀、剑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除了正课开设武术内容之外,暑假期间派学生到民间主要围绕武术名人和武术书籍进行走访和调研。两校均属公办师范类学校,学生不仅享受学费全免待遇,且毕业后学校分配工作,两校毕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前便被一些学校提前预定,就业率极高[18]。民国时期培养出的武术教师,为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 推动武术教材的编订
民国时期,武术突破了镖局、秘密结社、庙会、宗族、村落等原有文化空间而步入新的教育场域。然而,“国术历史既久且长,各家所传,教者仅知其术不明其理,仅知其当然不明其所以然,且椎鲁无文,仅以口述,以致鲁鱼亥豖,真相莫明”[29]。另外,中国武术拳派众多,盘根错节,“数千年以来,除笔记小说偶有记述,大多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32]。在教材方面“多无标准可循,教者就己之所长而教授,学者亦不得不随之而习学”[45]。各级国术馆、体育社团或武术组织、体育专门学校等把武术作为研习或学习的主要内容,并聘请民间拳师传经授技,虽然在《请注重全民体育以救国难案》中规定“各国术馆聘请国术能手、尽量教授,不得有营私居奇秘不公开等情弊”[3],但是仍存在着“知之者不能言,能言者不及知”等疑难,一批武术家归结此原因为“不立文字”。学校教育方面“只因课本未定,练习者诸多困难……致各校普及体操,皆沿用外国操法,但于本国固有之武术,未能发挥其特长,俾成为一种普通之体操”[8],从而提倡武术或者改良武术的途径与方法均在“罗致专门人才,编纂系统书籍”或“厘订课程,依序渐进”等方面践行。在《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案》中明确指出:“请部征集各省武术教材,研究教授方法。并编辑适用教科书。”在《整理国术教材案》中认为,中国武术派别分歧,种类繁多,除有志于武术高深研究者外,如以普及推行及锻炼体育为目的,则武术教材,实有加以整理编订之急需:“1)由教育部聘请专家组织委员会,审定教材纲目;2)审定时以采各派之长,合于科学原理,为一般所能练习,不涉深奥为原则;3)审定后将原有教材依科学方法加以改编,并加教学法说明,作用当时期之实验;4)试行结果圆满者,发给各级学校及民众团体,作为体育教材一种。”[46]在《编定各级学校国术教材案》中指出:“教育部体育委员会聘请国内国术专家,体育专家、教育专家、生理专家以及心理专家,详细研究编定之。”[2]
议决案一经提出,社会各名流或研究武术的各机关、团体积极践行,编撰各类武术教材,致力于武术教育的复振。北京体育研究社“合于体育而无害于生理卫生者为教材”,约集中外名家或通信协商,或集合讨论研究;精武体育会始终遵循着“不争门户之长短、南宗北派并蓄兼收”原则,集各派武术名家的拳艺编写成“精武十套”。中央国术馆“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围绕宗旨展开了武术教学、编辑出版武术专著、创办期刊杂志、举办“国术国考”等工作。1933年,教育部发函中央国术馆编辑武术教材,中央国术馆遵循由柔而刚、按年教授、互相衔接、循序渐进的原则,编订了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四级学校武术课程标准。同时,武术名家也做出了积极性探索,如《国术概论》(吴图南,1939年)、《国术教本》(缪省飞,1935年)、《国术教本》(万籁声,1943年)、《拳术教材》(黄浪僧,1929年)、《国术教范弹腿》(吴志青,1930年)、《十二路潭腿新教授法》(王怀琪,1931年)、《弹腿讲义》(马永胜,1935年)、《拳术教科书》(薛巩初、徐愚忻,1930年)等。在学校武术教育亟需教材的诉求下,1935年,华北国术促进会编纂《大中小学校国术教材标准》, 此标准获得教育部体育委员会通过,并经教育部核准选用施行,通令各省市作为武术教材暂行标准。该标准设置了小学教学目标、中学教学目标、大学教学目标三级目标,并根据教学目标制定了各级教学内容。1936年,国民政府委托北平特别市国术馆依据实情负责编撰了《大中小学国术课程标准》。该标准针对课程目标、教学内容、课时分配、实施方式、要点教授等进行详尽说明。该标准的教学内容借鉴了1935年的《大中小学校国术教材标准》,虽然该标准制定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形成全面的“上行下效”,但是作为民国时期学校武术教育的官方文件,还是对中国武术进入学校教育进行了科学化、系统化的有效尝试,武术教材标准和课程标准的出现促进了学校武术教育发展的进程。
民国时期,诸多的武术著作和武术教材使中国武术的理论水平从“不立文字”逐渐向“著书立说”跨越,促使中国武术由“技”到“术”的衔接,使其逐渐以整体的、统一的面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但是也存在着个人为利益而违背武术本意胡乱编造的现象,“近见有体操专家,以个人之一知半解,窃取拳术中三数无系统的姿式,编为国技体操,徒袭皮毛,全失本意。而卖艺者流,或更加以点缀,谬为粉饰,不问学理,而互相标榜,舍其精华,而拾其糟粕,方自诩为创造家,亦多见其不知量也”[38]。
7 推动武术教育的社会化
“学校体育提倡了数十年,可以说已有相当的办法,但民众体育似尚少有人注意。”[24]“体育之讲究,不仅限于学校学生,人人皆有积极求身体健康之必要,故社会上各种团体皆应谋人民之幸福以倡体育。”[9]黄振华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交《国民体育之振兴及其进行方法案》。该议决案认为:“一国国民中得受体育之训练者惟少数青年而已,社外大多数均在实际社会服务,苟对此大部分之国民,而无相当之奖励与指导,则所论之国民体育,有何意义也?”[13]并提出由大学院派体育专员数名往各地巡回讲演,组织青年体育团,组织体育协会,设置公共体育场等方案。
在1932年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明确说明武术在体育中的地位:“国术实为体育活动之一种,不能因其为我国所固有者而予以特殊之地位,以捐弃他合乎科学及教育之体育活动也。”[10]武术属体育的一种,体育场应有武术的设备及训练,《各省市县体育场应设国术部以资提倡案》指出:“各省市县体育场设国术部。凡国术馆尚未设立之区域尤当从速实行并应聘请国术专门人才充任指导以广造就。”[11]张之江在《全国各省市县亟应限期设立国术教练所,以便推行国民体育案》中指出:“关于国民参政会议所提议‘提倡尚武精神,以固国基’一案,并抄附原办法第八项原文‘省市县均须设立国术教练所,授民众以臂刺,刀剑拳击等技术’。”[47]为郑重其事,促进发展起见,拟请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并转饬在规定时间内成立“国术教练所”。之后由张之江、马福祥、孔祥熙等79人提交《请指定公款限期成立各省市县区国术馆社案》,指出:“凡社会上、私人组织之国术团体,如确为提倡体育起见,政府应与捐资与学者视同一例,优予奖励。”[48]青海省政府教育厅在全国国民体育会议上提交《为适应抗建需要,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应普及国术馆,提倡固有国术,以健强民族体魄案》,认为在古代教育中射御占六艺的三分之一,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当前要健全国民体魄,恢复民族地位,理应从复兴中国武术着手,以期达到自卫卫国。但是各地国术馆设备极其缺乏,武术教师不足,推广设立有赖于政府的提倡。“各省市县应各设立国术馆一处,聘请擅长武术教师担任教授,以期普遍。国术馆设备应力求充实,并确定其经费,边远省份,得呈请中央补助经费。”[33]与此同时,陈泮岭也提交了《发展国术,以普及国民体育案》,在施行办法中从教材编订、内容设置、师资培育、奖励制度4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发展武术惠及民众。李景耀提交《国民体育应切实推行我国固有之射术、拳术、摔角、跳远、举重案》,提出各省市政府令各县乡保,凡年龄在18~45岁之间的男子,均须自觉学习射击、骑射术、拳术、摔角、举重(石担石墩)等项目中的一项或两项。制定项目考核等级标准,每年春季由各县政府分区举行考验,每年秋季由省政府分区派员赴各县区进行省试,中央每2年举行一次全国考试,在县试、省试以及全国考试中合格者颁发相应的等级证书[19]。张之江在《请订定国术课程为国民体育案》中认为,当此弱肉强食之际,国难严重之时,应积极普及武术训练,推广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身中,发挥我大中华民族之精神。在办法中规定“请教育部订国术为各级学校必修课程,并呈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公务员,实行早操,施以国术训练,并于国民军事训练中,添授国术为必修课程”[49]。
民国时期除了学校武术教育之外,社会武术教育主要以民间体育团体为主展开活动。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当属中央国术馆和精武体育会。模仿中央国术馆在各地开办地方性国术馆,围绕中央精武体育会在全国各地开设分会。中央国术馆在推动武术教育的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以教授中国武术以及管理全国武术事宜为主,可见一斑。中央国术馆开设民众练习班,并针对社会民众专门制定了各级武术教程,分为初级教程、中级教程、高级教程。每级又分为4期,一期为3个月。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民国政府参考相关体育议决案的建议,下令全国各省市县设立地方国术馆。据《省市国术馆组织大纲 》《县国术馆组织大纲》《区国术社及村里国术社组织大纲》,各级国术馆均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全国各省市县所设立的国术馆,大都模仿中央国术馆的机构设置。1929年,北京体育研究社模仿中央国术馆的机构设置在北平成立了北平市国术馆,北平市国术馆下设高等研究部、普通研究班、各门专修班和民众练习班。其中,民众练习班其入学资格为“凡本市政学军警工商各界人士有志练习国术,年在18岁以上40岁以下身心健全具有普通知识者均可来馆报名经本馆考验及格后方可入学”。 其宗旨为“本馆遵照教育部颁布国民体育实施方案组设国术训练班以期国术普及民众”[1],其训练科目为国术概论、拳术、器械。训练时间为6个月,每周授课3次,每次2小时。湖南国术训练所成立于1931年,该所采用分门专授,分为民众班、妇女班、儿童组、特别班。每班所学内容有特殊规定,由于采用差异化的训练方式,所以学员无不积极踊跃认真习练。在1932年统计时,其4个班总人数已达到2 047人之多[4]。截止1933年底,全国共有24个省市建立了国术馆,县级国术馆300多个。全国各级国术馆都受上级国术馆和同级政府领导,形成自上而下的国术馆系统[17]。由于全国各省市县及乡村的国术馆馆长由政府官员担任,使得中国武术的社会化普及得以畅通。
另外,精武体育会遵循“并蓄兼收”的原则,集各派武术名家的拳艺编成“精武十套”,该教材编辑成书并辅以真人动作示范图和口令,使学者易于领会和统一传授。在上海精武体育会的带领下,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纷纷定章程、谋注册设立分会,至1929年,精武体育会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开设分会42个,会员多达40万人。精武体育会借助集散效应在全国各地开设分会,利用创办期刊、拍摄电影,组织游艺大会以及宣讲会演说,以精武主义灌输人群,以涤除社会污浊耳的教育方式,推动武术教育的社会化。此外,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出现了大量武术组织,以北京、上海居多。这些武术社团除了个别如北京体育研究社和精武体育会规模较大外,其余规模一般不大,所教授内容也较单一,如北京的通背社仅传授通背拳,上海的鉴泉太极拳社仅传授吴式太极拳,虽然规模小,但均有明确的宗旨、章程和机构,与旧式武馆私人传授相比,逐渐向“公诸于世,团体传授”转变,对武术教育的社会普及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体育议决案提出之后全国各省市陆续建设公共体育场及国术馆,为武术教育的社会化提供施教场所。根据史料统计[5],1929年体育场及国术馆达到1 142个,1934年为646个,1945年多达2 029个。为确保民众体育(武术)的开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分别颁布《社会体育法令》《民众业余运动会办法大纲》《各省市县运动会举行办法大纲》《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体育场规程》《体育场工作实施办法》。为了推行国民体育兼纪念孙中山首次起义,国民党政府设置了从1942年开始每年的9月9日为体育节。此外,凡举办武术以及竞走、爬山、游泳、骑马、划船、赛车、举重、球类、田径等比赛,规定其举办经费正式列入各级行政机关经费预算。
8 结语
民国时期,体育议决案的制定与颁布,反映了清末武举制废除、庚子之变使武术弃而不用,各学术皆仿效欧美的境遇下,社会精英们一改昔日被动状态,以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精神为武术复振献计献策、呕心沥血。各种议决案的提出,使中国旧有的武技借此契机得以复兴,虽然很多议决案并没有达到理想化的实施,甚至有的成为“一纸空文”,但议决案的颁布在中国武术从清末武举制废除之后的衰微,到民国时期硬性的实体支撑(国术馆、学校、武术社团)与柔性的建设(研制课程标准、教材标准、师资培养以及待遇)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性力量。议决案制定的背后,体现着社会精英们把中国武术与时代命题进行关联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反思,为武术教育的发展规避了一些主观障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虽然是借助政治力量使中国武术上升为国家行为,却对其发展难得可贵。
[1] 北平市国术馆民众国术训练班简章[J].体育,1936,4(2):27.
[2] 编定各级学校国术教材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15.
[3] 陈掌谔,沈昆南. 请注重全民体育以救国难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129.
[4] 陈闻经.教务科各班组训练情形[J].国术半月刊(湖南),1932(1):51-52.
[5]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57.
[6] 杜舒书,张银行.中国武术教育的近现代化转型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6,33(6):715-720.
[7] 范克平.许禹生与北平特别市国术馆[J].武魂,2005,(2):38-40.
[8] 郭葆珍.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3.
[9] 各地方宜联络社会上各机关共同组织及推广社会体育案[J].新教育,1922,5(3):535.
[10] 国民体育实施方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94-112.
[11] 各省市县体育场应设国术部以资提倡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117.
[12]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51,46.
[13] 黄振华.国民体育之振兴及其进行方法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73-75.
[14] 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法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5-6.
[15] 林伯原.民国初期学校武术课程的设置状况[J].体育文史,1994,(7):27-28.
[16] 吕思泓.民国时期学校武术考论[J].中国体育科技,2016,52(1):16-23.
[17] 林小美.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96,167.
[18] 李期耀.论中国高等体育师范教育的起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3):93-99.
[19] 李景耀.国民体育应切实推行我国固有之射术、拳术、摔角、跳远、举重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21.
[20] 马步周.提倡国术中之矛盾[J].求是月刊,1936,2(6、7):200-202
[21] 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2-23.
[22] 南京特别市教育局.请提倡我国固有武术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93-94.
[23] 请将中国固有武术加入专门学科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18-19.
[24] 实施与推行组审查总报告[J].体育,1932,1(9):44-45.
[25] 田标.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体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9.
[26] 推广体育计划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6.
[27] 体育研究社提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设国立体育学校案[J].体育丛刊(专件),1924(1):3.
[28] 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05.
[29] 听驼.国术改进之方策[J].体育月刊,1938,5(11):1.
[30] 王增明.近代中国体育法规[M].河北:中国体育史学会河北分会,1988:367.
[31] 王燕谋.关于提倡国术的我见[J].山西国术体育旬刊,1935,2(2):1
[32] 吴绪.北京体育研究社与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J].体育文史,1990(6):34-37
[33] 为适应抗建需要,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应普及国术馆,提倡固有国术,以健强民族体魄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19.
[34] 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M]//舒新城.中国近代史资料(上、中、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217-223.
[35] 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J].体育杂志,1914,(2):1-6.
[36] 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181.
[37] 小学校自初级三年级起体育一科应加授国技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37.
[38] 许厚龙.提倡拳术应保存其固有之真精神说[J].体育丛刊(论说),1924(1):1
[39] 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M]//舒新城.中国近代史资料(上、中、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217-223.
[40] 张晓军.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认识的嬗变(1840-1937)[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41] 张之江.国术研究与民族强弱之关系[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92.
[42] 张之江.拟请由部通令全国大中小各级学校列为国术为必修科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165.
[43] 中学校学生体育应如何从生理卫生上体察施行规律的训练并如何订定运动标准以收实行锻炼之实效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1.
[44] 张之江.为请转呈教育部恢复中央国术馆组织章程内之设置国术师资训练班之条文以利教学而倡导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57.
[45] 中华民国教育部.“令北京特别市国术馆”之“令字第五八七号”文件大中小学国术课程标准[Z].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1938,全宗号:5,宗卷号:15046.
[46] 整理国术教材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14.
[47] 张之江.全国各省市县亟应限期设立国术教练所,以便推行国民体育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18-219.
[48] 张之江等.请指定公款限期成立各省市县区国术馆社案[M]//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24卷.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348-349.
[49] 张之江.请订定国术课程为国民体育案[M]//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31-232.
The Inf l uence of Sports Resolu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educationalists and sports off i cials made suggestions about the present state of spor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and formed a resolution case through the confere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resolution not only map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ports,bu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education. Through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ushu education related sports resolution by sorting and classif ication,general military n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resolution,the resolution of school sports,school of the resolution of wushu education,social wushu education resolution,martial arts teacher training of the resolution,martial arts teaching material compilation of resolution and so 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 research.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ports resol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education inf l uence mainly ref l ects in:for martial arts in the school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rovide legal status;The abolition of military Gymnastics provides a powerful opportunity for wushu to enter th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to promotewushu as a required course in the school’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wushu teachers;topromote the compilation of martial arts textbooks;topromote the soci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martial arts. The enactment of the sports negotiation case ref l ects th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ref l ection of the social elite on the issue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the Republic of China;sports resolution;Wushu education;inf l uence
G812.9
A
1000-677X(2017)10-0032-09
10. 16469/j. css. 201710004
2017-07-10;
2017-10-10
资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TY051)。
刘帅兵,男,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教育与历史,E-mail:328092592@qq.com。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为中心
- 体育科学的其它文章
- 中医运动处方的起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