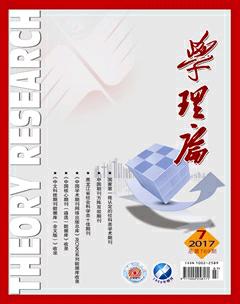国际实践理论与国家行动逻辑
李蓬莉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37)
摘 要: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存在范式分野,而国际实践理论则拥抱范式融合和超越范式取向。实践是人类根本存在方式,是首要社会事项,具有不可化约的本体地位。作为解释变量的国际实践通过培育习惯和建构规范两种路径导向国家行为体的自发行为和自觉行动。
关键词:国际实践;行动逻辑;习惯;规范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69-03
世界是如何维系起来的?这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从结构和单位关系的角度来说,世界的维系方式是指结构和施动者互动的中介。从结构层面来说,这个问题探讨的是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或国际社会的观念分配;从施动者层面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际行为体行动的逻辑,也就是行动的原因机制[1]181-182。
超越范式分野,本文认为,世界的维系方式是国际实践,实践是人类根本存在方式,是首要社会事项[2]103,具有不可化约的本体地位。国际制度和国际行为体行动是物质性和观念性的集合,不能被简化为物质和观念之中的任何一个层面。国际实践理论统合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不能被化约为结构(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和单位(单位的行为和性质)。作为解释变量的国际实践通过生成习惯和培育规范两种路径导向自发行为和自觉行动。
一、国家行动原因机制的多种解释视角及其实践性缺失
关于世界的维系方式有多种解释视角。在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世界的本质是国际体系天然的物质结构,国际行为体被简化为国家,国家被假定为单一、理性和功能相似的行为体。由于国家是单一的,人(决策者、观众和利益集团等)的能动作用被忽视。由于国家是理性的,社会性要素不被考虑。自由制度主义者提出,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理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国际社会并非现实主义所描绘的那样没有秩序;第二,武力和使用武力不是国际社会的独有特征;第三,有形的政府不是维持秩序的唯一因素,制度和权威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因素。建构主义者在更深层次的生成性要素上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是观念结构,也就是文化。身份建构和规范传播,在主流建构主义者看来,是国际体系文化得以生成和维系的主要方式。
通过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国际体系维系方式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一条由物质到理念、由主体偏好和意图到主体间观念分配的连续逻辑线。结构现实主义语境下的国际体系是物质权力分配,是国际体系最表层的物质结构。自由制度主义仍然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中。主流建构主义者一方面通过借鉴互动理论解释了身份的生成,另一方面聚焦建构性社会规范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相比于理性主义者的物质主义视角,建构主义似乎看到了更深层的观念性和社会性要素,从而把国际关系研究从因果逻辑分析带入了适当性逻辑分析。
但是,建构主义的社会化理论却导向另一个问题:规范是如何生成的。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研究规范,前者定义的规范与规则相似,是对行为施加约束的理性的行动准则,而后者研究建构性的规范,是具有给定身份的行为体适当行为的准则。自由制度主义的规范是理性准则,而建构主义的规范是适当性准则[3]。规范传播是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中发展最成熟的一项,以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为代表的研究规范传播的建构主义学者,发展出了较完整的规范的生命周期研究,包括规范的兴起、普及、内化和退化研究。但是这个周期是以规范的传播过程为研究对象,探讨规范传播的因果机制,没有包括对规范生成机制的研究。
此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身份生成机制的研究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以“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这一主张直接批判结构现实主义的天然无政府性的观点。温特借鉴互动论等社会理论,提出身份生成的逻辑。两个行为体,自我和他者,在一个没有共有观念的世界相遇,在自有知识的基础上,经过镜像互动形成相互的意象,意象经过反复的互动稳定下来,完成自我和他者角色身份的建构[4]403-407。此外,行为体互动还建构了观念结构。国家通过彼此的社会交流和互动,形成对于某个问题的“共同知识”,共同知识经过内化、稳定化和外化,形成集体知识。共同知识和集体知识是共有知识的内容相同形式不同的两个方面。国家通过互动建构起来的共有知识就是“无政府文化”[5]140-141。无政府文化是一种观念结构,是世界的本质。出于研究的需要,这个身份生成机制解释突出了观念和知识,淡化了知识的物质载体——行为体行动。温特说社会化不仅包括行为的方面,也包括观念的方面,他侧重研究社会化的观念方面,这说明温特只考虑观念结构,而不考虑其载体,只考虑国家的社会互动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不考虑建构过程发生的时空场所——国际实践。但是脱离了日常行动和实践的观念不但无法产生意义而且无法生成。
因此,建构主义的规范传播和身份建构的逻辑突出了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导向行动的单向因果关系,却在观念的生成的场所和时空条件这个环节的解释上显得有些单薄。因为该理论假定行为体在没有共有观念的世界完成相互建构,这把国际体系/社会的现实进行了简化和还原,弱化了社会的意义体系。相比较而言,把具有社会意义的国际实践作为行为体互动的场所更加接近国际体系/社会的现实,行动者的观念和行为只能从国际实践的过程中产生。
二、实践性在社会理论中的维度定位、概念内涵和本体地位
建构主义对于身份建构和规范传播的研究,产生于对国家利益和偏好的天然单一性假定的怀疑以及对国家意图不确定性推理的质疑。而对于规范和身份生成机制的深层思考,则需要突出国际实践的本体地位。
克里斯蒂安·坎贝尔(Christian Bueger)和弗兰克·加丁格(Frank Gadinger)沿用安德烈亚斯·雷科威茨(Andreas Reckwitz)对于理性主义、基于规范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等三个维度的社会理论的区分。基于工具理性的理论化工作把社会秩序简化为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因而忽略了集体行动的模式。基于規范的理论相比之下更加充分地解释了集体行动和变化,却难以解释规范自身是如何出现和建构起来的[6]451。而文化的方法可以解释规范的建构。文化理论分为三个家族:内在的理念、外在的话语和内外合一的实践。文化的方法不是假定规范指导行动的主体,而是考察秩序如何存在以及为什么存在。正是为集体所共有的知识、符号系统、意义或文化编码,为行动生成规则[7]243-263。
西奥多·沙茨(Theodore R.Schatzki)指出,尽管社会实践理论内部有多种研究路径,但都持有一个基本信仰,即众多人类知识,如人类行为、权力、知识、意义、语言、社会机制以及历史变革都发生在实践的场域中[2]13。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文森特·波略特(Vincent Pouliot)认为,“实践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的行动,这类行动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行动者的适当绩效,同时包含并展现背景知识和话语,并可能物化这样的知识和话语。”而国际实践则“是指与广义世界政治相关的、通过社会组织的活动”[8]6-7。
实践和制度有相似之处。温特说制度(institution)就是一系列相对稳定的身份和利益的结构[4]403-407。制度就是经过社会化而稳定下来的某种结构或过程,而实践也可以被看作社会行动制度化的产物。但是实践不仅是身份和利益的结构,它包括多个层面的内容,表象知识(身份和规范等)、背景知识(主体间预期和性情)①和物质安排(既是载体又是表征)统一于实践本体和当时当下的情景之中。
与主流理论相比,国际实践理论有着更为广义的本体论。聚焦国际实践会导致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围绕图1的中间位置出现:
国际实践理论的研究者假定实践的变化只能来自实践活动的实施,具体来看:变化是社会生活的常态,稳定是实践活动的结果;实践是施动者所为;实践变化的动力不仅来自施动者,而且也来自结构,因为具体的实践活动是互动的[8]19。
三、实践导向行动的路径机制
那么具有本体地位的国际实践是怎样决定行动的呢?实践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决定行为体行动:实践-习惯-自发行为、实践-规范-自觉行动,分别依赖一个可观测的中介变量:习惯和规范。首先,实践包含背景知识,背景知识塑造行事习惯,习惯引导自发行为。其次,退一步来看,实践可以培育规范,规范决定自觉行动。
(一)实践培育习惯,习惯引导行为
习惯是与反思相对的,无意识的行为或行动。泰德·霍普夫(Ted Hopf)区分了实践逻辑和习惯逻辑,认为实践逻辑比习惯逻辑更加具有施动性。霍普夫认为基于习惯的行为不经过理性的和规范性的反思[9]544。如果行为体采取行动(合作或不合作)是因为与自身利益相符合或者相背离,或者是因为对是否符合特定规范的反思,那么习惯就没有发生作用。朱立群使用了“惯习”(habitus)而不是“习惯”(habit)来描述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稳定的行为模式,“惯习是体现在行为体身上的历史”[10],历史就是有意义有意识的活动。因而惯习存在于社会意义网络中,这使它区别于习惯这种无意义的固定行为模式。惯习脱胎于实践,正是实践活动周而复始地发生才演变成为一种惯习,惯习是历史的实践活动,它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
有一些行动遵从了脱胎于反复行动的习惯逻辑,另一些行动则是根植于社会实践模式的更具有社会意义的惯习。或者有一些重复性的行动既有个体习惯的方面,又有社会惯习的方面。这些行动模式在产生之初是出于理性或适当性的目的,但是经过重复和实践,内化为习惯或惯习,经过了内化和稳定化,这些行动模式在以后相似的情景中都会按照它已经形成的模式来进行。比如在A国,乘公交车下车时要对司机道谢,这是一个群体的固定行为模式,从规范和适当性逻辑考虑,乘客对司机道谢是遵从了这个群体的社会规范,这种行为被群体共同认为是适当的,该国人或外国人来到这个社会就要遵从这种规范,否则就不会被認可。但同时,经过反复的行动,对乘客来说对司机道谢的行为已经内化成为习惯,是一个不需要加以反思就会发出的动作。另一方面,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乘客对司机道谢的行为反映了这个群体的惯习,反映了在公共交通这个社会领域,司机和乘客有意识有意义的互动模式。
波略特认为实践中恰恰包含了那些让实践者知道就是要这样去做的不言自明的知识[11]。这种包含于当时当刻的实践情景中的不言自明的知识恰恰决定了实践者如何去做,它们(他们)知道就是要这样行事。实践活动催生自然而然的行动,这种行动表现为习惯/惯习。
(二)实践生成规范,规范选择行动
如前文所述,规范是一种适当性准则,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共有知识。规范如何在实践过程中完成建构?实践的多个组成要素,情景、背景知识(经验)、物质安排方面等,共同启发实践主体对什么是适当的行为的集体认知。适当性表示群体认为我们要如何去做,不必然与正确性相联系。不管是芬尼莫尔的规范教授,还是阿查亚的规范本土化,都暗含规范倡导者和规范接受者的二元对立,规范的传播路径是规范的单向社会化。芬尼莫尔认为规范的传播是因为国际组织的教授。阿查亚提出,行为体在面对国际规范时,既非被动接受,也非全盘拒绝,而是主动地选择与转化。外来规范与本土规范契合是规范传播的关键。他考察了共同安全和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在东盟的扩散,前者由于与东盟的规范结构相吻合,故而被其接受,后者则相反,因为东盟的本土规范结构是强主权的[12]。这是全球性规范向地区扩展的过程,但是可不可以打破倡导者和接受者的对立,而考察规范建构者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比如“强主权”作为一种本土规范是如何生成的?实践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实践过程经过稳定化和外化,成为历史,行为体携带的历史就是其实践的体现。东盟国家的殖民地历史引发了它们对主权和独立的珍视与追求,携带这样的历史和实践的行为体的互动建构的规范一定是强主权的规范。
四、结语
本文在梳理解释国家行动逻辑的不同视角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范式的实践性缺失,因此本文从国际实践的本体地位出发,研究了作为解释变量的国际实践是如何导向行为体行动的。本文认为表象知识(身份和规范等)、背景知识(主体间预期和性情)和物质安排(既是载体又是表征)统一于实践本体和当时当下的情景之中,实践具有不可化约的本体地位。作为解释变量的国际实践通过培育习惯和建构规范两种路径导向行为体的自发行为和自觉行动。本文初步建立了一个解释行为体共同行动的“实践——习惯/规范——自发行为/自觉行动”的简单分析框架。
參考文献:
[1]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
[2]朱立群,聂文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8).
[3]魏玲.第二轨道进程:规范结构与共同体建设——东亚思想库网络研究[D].北京:外交学院,2008.
[4]Wendt,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2).
[5]高尚涛.国际关系理论基础[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
[6]Bueger,Christian and Gadinger,Frank. The Play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15(59).
[7]Reckwitz,Andrea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 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2).
[8][加拿大]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国际实践[M].秦亚青,孙吉胜,魏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9]Ted Hopf,.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0,16(2).
[10]朱立群,聂文娟.社会结构的实践演变模式——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另一种思路[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
[11]Pouliot,Vincent and Cornut,J?伢r?伢mie. Practice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diplomacy: A research agenda[J].Cooperation and conflict,2015,50(3).
[12]Acharya,Amitav.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4,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