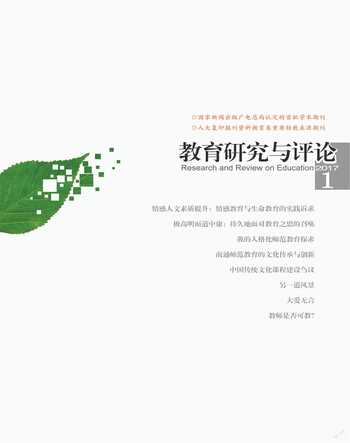常常忆及是师父
因为工作调动,无法和师父朝夕相处已有数年,电话、短信成了最主要的联系方式。每次发短信,打出“师”,屏幕上立刻出现“傅”这个字,每一次,我都是十分执着地用大拇指敲动七八次,向后翻寻自己心目中的“父”。我怎么可以用一个对陌生人都可以称呼的“师傅”,来称呼我那既是师又是父的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人?
还在南通师范就读的时候,看学校橱窗里陈列的优秀校友的照片,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张兴华,著名小学数学特級教师。然后,有一次南通市优课评比,作为通师理科大专班的学生,我们有幸可以听课。随着周围人的指点,我看到一位十分儒雅的学者——张兴华老师,旁边坐着他的徒弟王庆念,心生羡慕,但从不敢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他的徒弟。当时我隐隐约约觉得,当教师我肯定不能像当学生那般成功。因为,被同学唤为“考试机器”的我,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当教师的天赋或潜力:实习时我都不会写教案,十分钟就讲完一节课,因为我“实在没什么可讲的”。随着毕业的临近,我的心情越加灰暗,对未来的茫然和缺乏自信甚至让我放声大哭。
那时,毕业分配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海门每年两个大专生,都是实小、附小各一个。当时我的同班同学,还有普师班几位挺优秀的学生,出于对张兴华老师的崇拜,不约而同都填了实小,我明知没有竞争力,但是真的不甘心啊。面试我相信自己表现得也是一般,谁知最终竟然奇迹发生,实小把我们几个都要下了!事隔多年我才知道,是师父再三去教育局请求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认为第一届理科大专班的学生一定有其过人之处。
工作了,在一群充满活力与灵气的同龄人之中,我一直是毫不起眼的一个。但是,我真的幸运极了!工作两年后,也就是1993年,师父要收我为徒!在之后和师父的交往中,我才慢慢知道了所谓幸运并不来自命运女神的垂青,而是师父两年来默默的关注。
自己的文字能变成铅字让大家读是多令人骄傲的事啊!我便把自己教学中的点滴感悟写下来并投了稿。这件事没人知道,但是传达室偶尔的一封退稿信让师父推断出了!
学生时代的学习成绩早就是遥远的历史了,也无关教师是否当得成功,所以没人会关心这事。在我自己都快忘记的时候,师父却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师范时数学学得很好,我还知道你曾经是全校唯一免考的……”
随着师父的叙述,我看到的再也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我,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有这么多优点。由此,我改变了之前一贯的想法“我再努力也只能当一个二流教师”,重新找回了自信!
和其他师父带徒相同,上课、听课、评课是主要的方式。但是又有些不一样。首先,师父关注的焦点不是公开课,而是每天都进行的随堂课。“每节随堂课都要像公开课那样去上”,这是师父三十年教学生涯的结晶,也是对我们弟子的要求。于是有时,当我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师父已坐在后面了;有时,课已经上了好几分钟,师父却突然夹着一个听课本从后门悄悄地进来了。评课就更不一样了。有人从纯理论角度出发,高高在上,头头是道,但是如何操作仍然是个难题;有人则源于经验或拍脑袋来的灵感,没有什么理由,让你拍手称好的同时却无法领悟。如果说前者是天,后者是地,那么因为长期对数学教学心理学的潜心研究,师父的评课从来都是行走在天地之间。有“是什么”,有“为什么”,有“怎么办”,并且还加上他的示范。那种豁然开朗、悠然心会的感受,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最享受的是听他的“现场直播”——一位教师在上课,我们其他人都围坐在师父身边,听师父小声地对教师的反应做出各种点评。那些都是转瞬即逝的情境啊,如果到了课毕,细节被遗忘之后的交流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对“现场直播”都习以为常,上课教师也并不因之受到影响,礼节不约束我们这个熟悉得如同家人般的群体。
一次数学教师“下水题”考试得了满分之后,我顺理成章接了学校的数学兴趣组。在小升初一律就近入学的年代,数学兴趣小组参加各级竞赛的成绩是关系学校声誉的重大事情。我的一些做法引起了集体荣誉感特别强的老主任的担忧:我非但没有大力动员数学学习好的学生都来参加,还很潇洒地放走了曾经得过奖的学生,让他们参加更感兴趣的田径队,于是全年级只留下8个人。没有量的保证,质的追求谈何容易?学生少得可怜,做题更少得可怜。没有一定的积累,怎么面对全新的挑战?师父一如既往地给了我信任与支持,老教师们不大理解,一次全体会终于真相大白,师父是在透过表面现象深入观察更本质的东西:原来师父曾经多次在自家阳台“偷听”我给兴趣小组的学生上课,我那连续一个半小时不带歇的讲解让他看到了我对数学浓厚的兴趣,这份兴趣他认为比什么都重要。随后他又提出建议,要考虑学生的情况,“看孩子的眼神”,他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分析教会了我“以学论教”。慢慢地,那8人组成的数学兴趣小组战无不胜:南通市数学竞赛包揽了1~6名,省数学竞赛6人得一二等奖——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师父对我们常提的要求包括阅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经常走在路上被师父截住,用他推荐的书中的内容考我们。几个徒弟中我算是最没长性的一个,所以这方面受到师父的教导也最多,用语重心长、苦口婆心来形容毫不为过。渐渐地,一段时间不看点书也会觉得空虚。偶尔去趟图书馆,必能见到师父常向我提起的榜样,更觉惭愧。就这样,我开始慢慢走近书籍。
师父对我的最大影响,恐怕还不止这些。他对名利的淡薄,对事业的执着,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我。他的绝不因为取媚于谁或出于利益的考虑而违背内心这一做人做事的原则,已在我心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坐在电脑前,回忆往事,泪流满面,诉诸的文字又如何表达得了内心的那份感动!
(施银燕,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