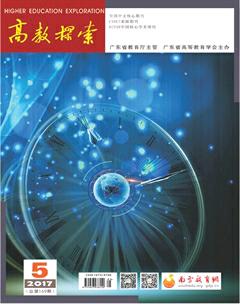科学规训对知识生产形态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塑型
彭静雯
摘要:学科规训是在学科生成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学科功能理论。正是在社会建制的过程中,学科具备了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强制功能,拥有了规训的合法化权力力量。基于知识的权力正发生于科学进入大学时,它是学科规训理论的逻辑起点。科学不仅改变了知识生产的形态,促进了现代学科门类体系的建立,而且以“体制化”的力量给几乎所有的学科都烙上了“科学”的印记。因此,学科规训的实质就是科学规训。一旦科学规训的藩篱套住大学场域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在对个体的形塑上,就形成了以理论知识为中心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纯粹理性的人为目标,强调抽象的观念与确定性的学习内容,并以“可算度性”来评价个体的学业成就。
关键词:学科;学科规训;学科建制;科学规训
在大学这个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制度性场所中,没有任何教育实践可以先天地避免权力的染指,个人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接受一定方式的规训。而学科规训理论在塑造“学科人”上具有较好的话语建构力量。本文试图通过对学科规训理论的重新解读,寻找到学科规训与人才培养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为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为何依循着强劲的科学化的发展路径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进而为教学实践中理论脱离实践的痼疾寻找到改革的可能破解点。
一、学科规训理论的逻辑起点:科学建制
(一)学科规训理论的内涵
早期学者将“学科”定义为“学术的分类”,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其学术属性进行探讨。所以discipline作为一个“舶来品”虽然有很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且本身也兼有学科、纪律、教育、训诫等义,但训诫主要指向的是知识本身对人所发挥的涵育熏陶作用。它既包含学科文化对学者惯常遵守的学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的影响,还包含了对个体精神气质的影响,譬如默顿对科学理性的四种精神气质的概括以及国内的“学问改变气质”等。
直至上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柯(M.Foucault)通过对知识演化的系谱学分析,最先洞悉到了知识体系与权力网络间的对应共生关系,并以“权力制造知识”[1]发掘出了权力的生产性,一语点破了“学科”复杂的社会属性,认为这种基于知识的权力生产了“规范化”的知识与个体。自此,学科作为“规训方式”的社会功能得以彰显,这就为知识与权力的结盟以及规训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循着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这一线索,美国学者华勒斯坦、霍斯金等人着眼于“学科”的字源探索,梳理从18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重建历程,总结了学科“制度化”的实施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学科规训理论,以“disciplinarity”一詞来表征规训使人在学科知识的受教过程中拥有“自主自持(self-mastery)的素质”[2]。因此,只有当学科建制在大学教育中取得合法地位,并以普遍化和规模化的形式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塑造和规范施加影响时,“第一批经由这些新方法训练出来学以致学的学生,正就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始创者”[3]。
学科规训是在学科生成发展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学科功能理论,它的功能指向两方面——知识生产和对个体“同一性”的塑形。正是在社会建制的过程中,学科具备了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强制功能,拥有了规训的合法化权力力量。任何想要进入的个体,必须在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同时,反过来受到其相应准入制度、评价制度、奖励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并形成带有该学科标识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
(二)学科规训理论的逻辑起点
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分类,而是历史化的产物。它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并且恰恰是在学科规训制度的引导下,具有了动态的结构。因为学科规训所关注的既非知识的简单分类,也非学科本身,而是要探讨为何学科知识会呈现出当前的状况,各学术领地的界限和区域是如何被划定的,某一知识门类训练出来的学术传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因此,对学科规训的任何讨论都应该是对学科建制史的分析。此外,规训权力运作对象和工具决定了大学将是其重要的运行场所。霍斯金在分析学科规训缘起的三种手段和三种运用场所时,也都是以大学为背景对教育实践方式进行的探讨,为此,他甚至总结学科规训“本来就是一个教育词汇”[4]。这是因为大学兼具了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两种功能。同时,相较于一般的学术机构,它还具有专门人才的培养功能。这一主要职能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又是紧密相连的,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三者之间的同步整合。学科规训就是在这种统一的社会化同构中,固化了其规范化权力。反过来,学科规训所具备的同一的规范、严谨的逻辑和书写中心主义等特质,在对人的多样性进行规则化和秩序化后,也促使知识能够以更加便利的形式在大学教育中进行传承与传播。
而早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大学通常所设立的四科学院中,学科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建制属性就有所体现,以神学“唯我独尊”的学科地位和对其它学科“无孔不入”式的渗透为代表。它不仅表现于拉丁文的教学语言,而且从教师的讲授方法、讲授内容到对学生的口试考核,也都以解释和论证基督教神学教义为出发点。尽管如此,早期的学科并不具有现代意义的“规训权力”。这是因为,在教会组织对大学知识传播的严密控制背景下,学科知识的合法性标准只在于是否具备对神学权威“顶礼膜拜”的工具性价值功能,而非知识本身,因此,学科所具备的权力与知识性质本身间的关系是十分松散的。而“学科只有形成了学科建制并且这种建制垄断了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才会有基于知识的权力产生”[5]。这种权力在福柯看来,它是交织在人的科学中的,权力关系就像毛细孔现象(capillary form of existence)一般到处存在,且促进了“常规化社会” [6]的出现。因此,学科规训理论的逻辑起点始于科学的建制化。
综上,学科规训理论除了以学科为基点,另外还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与科学有关,一个与大学有关。其中,“科学”是规训权力的来源,而“大学”则作为规训权力的主要制度性场所发挥作用。基于此,为了厘清学科规训和科学进入大学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寻找到学科规训以科学化方式规训人的原因所在,就需要以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科学的发展为追溯起点,梳理科学知识进入大学并取得合法化建制的历史过程,从而对学科规训的实质有更深刻的认识。
二、科学对知识生产形态的“塑型”
通过对科学史和教育史的考察,学科知识在被科学规训的历程中,呈现出分门别类、标准化与规范化的特征。前者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大学中的学科数量,最终促进了现代学科门类体系的建立;而后者则以“体制化”的力量给几乎所有的学科都烙上了“科学”的印记。[7]
(一)科学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形成与知识的分化
以19世纪为分水岭,任何知识想要进入大学,都被纳入到科学研究的对象范畴,并在科学的范式下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树立起各个学科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群体、评价标准和学科规范等学科准入制度,构成各有界域的学科边界甚至壁垒,排斥假知识和非知识。这套规训准则不仅规限了学术传承的基本条件,为所有试图进入该学科领域的学者竖起一道“门槛”,接受该学科长期以来形成的连续性规则体系;而且促使他们对知识分类的内在构成朝着一个更加精细化和集中化的方向发展。
科学虽然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逐渐进入大学,但是一当科学进入大学后,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就迅速地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与神学、法学、哲学等传统学科“并列”的学科。在此过程中,大学的讲座以基层学术组织的制度化形式出现,为促进学科知识的细化和专门化以及学科建制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譬如剑桥大学的第一任矿物学教授克拉克先生,就由于就高级僧侣胸甲上的宝石发表学术演讲而获得了科学学科中最早授予的教授职位。它不仅意味着大学教师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学者在学术分工上被赋予了合法化的职业身份,而且为学术分工制度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因为围绕“讲座”制度,一方面,专业化的学科组织“教授会”(facultas)、专业化的知识交流、传播和分类系统、学科共同体内部的学术评价机制等物化层面的制度也会相应建立起来,以维护学术分工制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些分工制度借助它的奖励系统、舆论环境,对学者的学术行为进行规限,同时为以学术为业的职业性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空间,使他们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人生态度、学术理想和行事方式。学术分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知识管理的专业化,而专业化让知识管理的形态和性质也随之发生改变,以致产生了以管理为业的知识管理人,学术管理活动也在大学中逐步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建构起现代大学的整个专业分科体制。
伴随着大学内部按照学科分类而形成学术组织分工的条件渐趋成熟,科学学科的进一步细化和专门化也有了发展的基础。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知识分化中的学科界限日益泾渭分明,促使社会科学得以有了生存空间,并逐渐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此基础上,现代学科门类的基本框架才得以搭建起来,而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分门别类的知识,学科规训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也就缺乏必要的动力。就像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中提到的:“只要知识一直局限于中世纪早期的‘自由七艺(the seven liberal art),就不会出现大学。”[8]因此,近代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探索世界的领域,形成了知识迅速增长和分化的趋势;现代的学科体系就是科学进入大学的历史产物。
(二)科学促使了知识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科学进入大学后,对知识生产形态的另一种改变是知识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具体而言,就是要让知识内在地具备严谨的理论逻辑体系,同时以类公理化的外在形式呈现。由于它是诉诸于经验归纳而建立的严格且可证实的公理系统,所以很容易获得社会认同的合法化,并通过大学教育向学生传授。
这种“科学”烙印的标识以洪堡对德国柏林大学的改革为起点,并随着自然科学的权威地位在知识领域的确立与提升,不断通过学科建制获得强化。在自然科学的理性的强烈挤压下,非理性的科学知识,只能更多地以被理性修正过的面目出现,成为理性的附庸。体现于在其之前而产生的人文学科那里——由于它通常是建立在纯粹的思辨、主观推理基础上,关注个体的情感和价值判断行为——这些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以致不得不转向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群体或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因果关系与规律;而那些即便研究对象未作改变的人文学科,也力图在研究方法上借鉴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譬如提倡研究者不带个人预设,强调客观地观察、记录被研究对象的表现等——试图以分割的方法机械客观地还原研究对象本身,强调理性精神。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康德等人所创立的思辨哲学曾被诟病为“异想天开的冒险事业”。为了摆脱越来越受到猜疑和冷落的尴尬境地,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加以系统阐述,以使科学能够接受它们——不管科学是将其作为前提原则,还是作为最终结果”[9]。即便19世纪下半叶才进入大学的实用知识,也不得不将自身的个别特性普遍化,以寻求客观规律为目标,甚至不得不以“搭便车”的形式以理科之名来争取狭窄的生存空间。
为此,梅尔茨曾经这样总结到:“这是从德国大学制度中特殊地演化出来的一种观念。在这个制度里,神学、法学、医学和专门的哲学研究全都被拿来做‘科学的处理,一起形成普遍的无所不包的人類知识大厦。这样一种观念、这样一个名字的运用,只能在这样的地方产生和发展,在那里,各个不同事业、各种知识分支习以为常地在同一屋顶下共同生活了许多个时代,它们不断接触,学会彼此看作一个家庭的成员、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德国大学制度的优越性在于精心制定了最宽广的科学概念,规定了最高的、最一般的科学标准。”[10]
总之,大量的自然科学进入大学,通过普遍化的社会建制促使科学按照一个统一的权威来建立学科分立的制度,不仅有助于知识的认知和整理,而且也有助于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因为它以严谨的理论逻辑作为知识选择的基本“底线”,促使学者在学科的逻辑起点上达成了一种共识。这当中,“以书写为中心”的规训手段为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因为书写中心主义的实质是理论中心主义。它以追求知识生产的确定性和可证实性为目标,以实验性、经验性科学方法为路径手段,来让知识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结构性和有序性。同时,还自设了一套报酬累计增强的机制,以对学科地位产生影响。因为通常来说,学科在学科规训的过程中越严格与规范化,其学术地位也越能得到社会的公认;反之亦然。而学科地位上的高低之别,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学科资源的分配、学科本身的地位等等方面。因此,它在加快科学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增强了科学知识在大学中传播和生产的合法化地位;而科学的成功也进一步加快了学科规训的完善与制度化。
三、科学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塑形”
科学进入大学以后,在对个体的形塑上,用科学的体系建构目的观、课程观、教学过程观和评价观,以培养纯粹理性的人为目标,并在对个体进行批量化生产的过程中,强调对抽象的观念与客观的科学知识的学习,形成了以学科理论知识为中心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一)科学塑造了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组织形式
史帝希威(R.Stichwen)在论述学科的缘起与发展时,把学科定义为知识透过归类而形成可教的形式。[11]在学科规训体制影响下,大学被认为是按照学科来管理知识、按照院系来形成学者共同体和组织教学活动的场所。大学按照学科进行专业化教学的模式形成,起源于“考试、书写、评分”这些新的教育实践形式与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教育场所间的结合。
以1760年始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课室(classroom)为例,它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为专业化的教育提供了实践环境,促使传统的百科全书导师指导形式转变为单门学科的方式,教师在知识的传授上更为专门化。这样一来,它一方面不仅为培养专门人才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知识生产专门化的条件下,促进了知识的更加分化以及一些新学科的诞生,就像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过程一样[12]。专业化因此成为科学不断分化历史进程中大学教育形态的必然产物和特征。而1760年间始于德国大学的研讨班(Seminar)、1780年间始于法国高等学府的实验室这两种教育场所进行的教育实践,不仅分别促成了新的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诞生,而且还培养了学科新人。因为,以学科为中心的方式不仅规训了学者当前的学术生活,其更为强大的机制是“控制了学者结束训练以后的职业样式”。“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无论是教学职位还是研究职位,一般都要求拥有博士学位(或具备同等学历),而且大多数职位还要求在某一特定的学科取得博士学位。每个人在组织上都要归属于一个学科;在该学科的正规刊物或半正规刊物上发表论文,被看成是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不光在过去如此,直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也依然如此。研究生还被劝告(而且是很明智地劝告)要在公认的常规学科里拿学位。学者倾向于主要参加他们自己学科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各学科机构给它们的成员罩上一层保护网,唯恐越雷池一步。”[13]
每个人在大学里都被“放逐”到各个专门领域里,他们教授或者学习不同的学科,以接受学科的规训。因此,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变成学科教育专家的研究对象,在学科的知识体系、组织框架、制度规范和思维范式下塑造和建构着自我。
(二)科学促成了以学科理论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
1.在教学内容上建立的以教科书为中心的规训模式。教科书在编写过程中为了讲求效率以及造成知识在时间产生上的连续感,必然会简化甚至扭曲结论产生的历程。正如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到的:“为着一些明显而功能性的理由,科学教科书(以及大部分老的科学史著作)只会提到过去科学家的研究的一部分,也就是那些很容易看成对书中典范问题的陈述以及解答有贡献的部分。部分出自拣选、部分出自扭曲早期的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所遵循的规范,都被刻画成与最近在理论与方法的革命后的产物完全相同。难怪在每一次科学革命之后教科书以及它们所蕴含的历史传统都必须重写。当一些都重写过后,也难怪科学再一次地看来大体而言像是一个累积事业。”[14]如此一来,教科书中到处充斥的是简化了的结论性的理论知识,反而把对启发学生认知结构最有意义的核心认知过程给掩盖了。
2.在教学方式上建立的以确定性知识为中心的规训模式。当所有的课程都按照学科知识的体系来编排,对理论的讲授成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而以理论知识为中心的教学,只可能传授和考查写进了教科书中的确定性知识,学生思维的活跃性、发散性必然受到抑制;其自主判别、选择和评价的能力由于缺乏实际锻炼,也会对那些“没有固定程序”、“没有标准答案”的认知活动感到不适应。即使教师刻意安排了实践性教学环节,但由于它的目的只在于对理论知识的验证和重复应用,并没有突破既定的知识范围,因此通常它们也只作为理论教学的附属地位而出现。
3.在学生学业成绩评价上建立的以可算度性为中心的规训模式,将考试与评分相结合。就考试而言,它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权力行使的机制,使得知识也成为一种可操作的类型,而分数这一可算度性原则下的无形技术则赋予个体学习价值。为此,福柯曾经这样质问:“为什么没有人撰写更普遍、更富于变化、但也更有决定意义的考试的历史——它的仪式、方法、特点、作用、问答游戏、评定和分类体系。要知道,在这种微不足道的技术中可以发现一个完整的知识领域、一种完整的权力类型。”[15]因为为了保证评分的可算度性,考试形式就必须简单化和去情境化,甚至直接转化为对知识掌握多寡的考核,学生利用资源的路径不可避免地就要受到限制。“通过对每次考试(以至一般地对每个独立个体)的表现,做出经常性的监视和计算评断,对学习者强加一種新的‘规训性权力。……分数却不但用来互相比试,而且鼓吹竞争,为的是竞夺那些能显示自我有用之处的流通价值。分数给表现树立客观价值,用数量来设定10分是完美,0分是一败涂地的标准。……就这样,这些新型的学习者变成(懂得)自我规训、自我实现(的重要),是一群惧怕失败、永远追求奖赏的求真者。”[16]
综上,学科规训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其实质就是科学体制化对知识生产和人的规训。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学科规训的实质就是科学规训。科学规训的历史功绩有目共睹,因为它不仅使各门学科走上了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道路,而且使大学教育走上了进步的轨道。然而借助这一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规训制度也在步步包围着大学教育。因为这种以理论和学科为中心的科学教育模式,一味地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对教育模式作出简单量化及去情境化的非法还原,人文知识甚至工程知识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也被分科教育模式分解得支离破碎;它已经沦为了一种单维的追求效率的工具,最后的结果是造就了缺乏创造力、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单向度”人。因此,只有打破传统科学规训的束缚,既以学科为依托又不为其所“裹挟”,才能在人才培养上破解“理论脱离实践”的难题。
参考文献:
[1][15][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9,208.
[2][3][4][12][16][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47,79,73,47.
[5][7]冯向东.关于学科规训与科学进入大学的历史[R].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博士生专题讲座讲义,2011.
[6]Foucault,Michel (1980a)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New York:Harvester Press,39.
[8][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
[9][德]费里德里希·包尔生,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M].张弛,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60.
[10][英]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M].周昌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9.
[11]Stichweh R..Zur entstehung des Modernen System Wissenschaftlicher Disziplinen.Frankfurt am M.; Suhrkamp.:1984:7.
[13][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77.
[14][美]T.S.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M].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193.
(责任编辑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