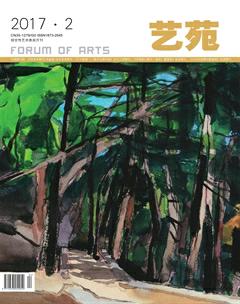“嘴”和“肢体”间的碰撞
皮雨鑫
【摘要】 舞蹈向来被认为是动作的艺术,是肢体言语的表达,但在各种艺术门类融合日益频繁的今天,舞蹈中声音元素的介入已不足为奇,当今舞蹈作品中“声音语言”的出现无疑成为了一种新的舞蹈编创和表演方式,其中也必定有使一些舞蹈编导为之推崇,观众为之喜爱的缘由。本文就将围绕舞蹈与声音间的碰撞,侧重分析不同“声音语言”下给舞蹈带来的不同艺术效果,并从具体舞蹈作品着手,探究其运用的意义。
【关键词】 舞蹈作品;“声音语言”;舞蹈编创
[中图分类号]J7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入“声音语言”的原因
在艺术世界的万花筒中,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早已不是孤独行走的单行线,各门类艺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往往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吸收并且借鉴其他门类艺术的精华部分,吸收自身所需要的“养分”,舞蹈亦如此。即使存在一些舞蹈艺术家们依然强烈表达着对“材料单纯性”的忠诚,只专注于对肢体的无限开发,但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舞蹈作品在各种艺术门类中吸取着舞蹈编创的灵感,寻找着令人出其不意的多种可能性。舞蹈中的唱词、旁白、人声的叫喊等“声音语言”的介入,正是舞蹈从音乐、戏剧中抽离出的部分元素,经过整合、应用后,能“为我所用”地融合成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展现。排斥或脱离多种艺术门类间的融合发展的趋势,实际也变相地在与时代前进的步伐脱轨。
在舞蹈作品的创作中,恰当的“声音语言”的应用不仅为舞蹈本身增加了亮點、看点,更为舞蹈创作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编创思路。当我们在评判一个舞蹈作品是否具有观赏性时,通常会围绕其表现的主题内容、表达的思想情感来赏析,而舞蹈编导为了作品的完整性,在进行舞蹈编创时也不得不追求更明确的主题设定、内容展现以及愈发饱满的情感表达。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如果没有语境,词就没有意义”,而运用得体的“声音语言”往往能在不同的舞蹈“场”中传递具有差异性的艺术传达效果。舞蹈演员利用声音,在不同的舞蹈“场”中任意转换空间的大小,就像由数十根联动轴组成的伸缩球一般,有差别的声音发出形式就如联动轴相互交织产生的不同形态,满足着舞蹈在大小“场”中,灵活改变与观众间距离远近的需求。不仅如此,更有编导利用“声音语言”进行舞蹈调度,以“声音”的发出为线索,往往起到了烘托气氛、推动情节、激发演员情感的作用。舞蹈编导在极力与“肢体”动作较劲之外,巧用“嘴”发出的声音,也能将舞蹈作品的呈现效果得到提升。
归根结底,观众的多元化观赏需求,才构成了舞蹈编创者无止境地寻求新颖而独特的舞蹈表现手法,多样“声音语言”的进入便是最好的佐证。在舞蹈创作不断更新的新形势下,观众也主动或被动地培养出了更挑剔的观赏眼光,一贯传统的舞蹈技巧、循规蹈矩的表现题材,已然满足不了大众对于舞蹈艺术创新的期待,而舞蹈“声音语言”的引入往往能在观众中引发预期的情绪效果和戏剧效果,在不超过观众期待阈限的情况下,刷新他们对舞蹈表现艺术固有的思想观念。
二、舞蹈作品中不同“声音语言”的运用
(一)旋律性的“声音语言”
旋律作为音乐的首要要素,总是在音乐的领域被谈起。而笔者在这里所提到的舞蹈中“声音语言”的旋律性是指:在舞蹈作品中,舞蹈演员在展现肢体动作的同时,还兼顾着用人声唱词配合着的,一种带有明显旋律感的舞蹈表演形式。这无关“音乐是舞蹈灵魂”的争论议题,借助音乐中旋律的概念,不过是为了更准确地划分多种“声音语言”进入舞蹈作品后的不同特征。其实早在中国古代,“诗、乐、舞”原本就是三位一体的艺术,古代《毛诗序》中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实际也就揭示了乐舞间的共融性,其目的也只不过都是为了最简单的抒情达意而已。
孙颖老师创作的汉唐古典舞《相和歌》,其背景音乐采用《诗经·郑风·子衿》为歌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通过人声唱词极力复原汉唐乐舞艺术的同时,向观众准确而直接地传达出了古代女子内敛含蓄的相思之情。舞台上,舞者们一人一鼓,通过脚上多变的击鼓技法、汉唐独有的舞姿风韵,配合上口中的念念有词,不知不觉就使观众在视觉满足的同时,更多了听觉的感官享受。除此以外,在台上演员“舞而优则唱”的表演形式下,台下观众往往被带进了观演情绪的高潮,从而调动起他们深藏于身体内部的“动觉”,在心理学上又被称为“筋肉感觉”,也就是说,“声音语言”的加入,使舞蹈情感的传递变得更加富有张力,配合着唱词的《相和歌》仿佛让观众置身于汉唐盛世,一幅幅承载着古代乐舞文化的画卷随即映入眼帘,以此,便能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就唤醒了观众自身的“内模力”,促使观众也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肌肉敏感和“表现冲动”。这种富有“声音语言”的舞蹈表现形式,让原本以技术动作服人的舞蹈也变得“朗朗上口”起来,使观众在听觉中对舞蹈的形式感也留下了更深刻的记忆。
(二)戏剧性的“声音语言”
戏剧本身就是一门集多种艺术门类元素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而戏剧性是指把人物的内心活动(思想、感情、意志及其他心理因素)通过外部动作、台词、表情等直观外现出来,直接诉诸观众的感官。而笔者这里所提到的带有戏剧性的“声音语言”,实际强调的是舞蹈演员在展现肢体动作之余,直接在舞蹈间隙用嘴相互交谈、向观众讲故事或纯粹自言自语所发出的声音。这时候舞蹈中演员所发出的“声音语言”就绝不再是音乐的附属品,相反,这类声音的发出都几乎自给自足地诉说着或显或隐的故事情节,有时它是帮助观众理解舞蹈作品含义的一把工具,而有时,特别在当今的现当代舞作品中,这种自说自话的舞蹈风格常常也会让观众看得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然而现代舞蹈编导们很少解释“声音语言”与“肢体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或许只是想借助于声音这一形式更好地设定一出“假定情景”,为了拓展舞蹈舞台表现生活的艺术可能性,也便于更好实现既单纯又晦涩的自我表达,又或是想要保持住观众继续关注的新鲜感而已。
其实早在德国表现派时期,皮娜·鲍什的“舞蹈剧场”就时常将这类戏剧性的“声音语言”搬上舞台。她的舞蹈作品常常是一场混合了戏剧台词与行为艺术的综合体。而来自中国宝岛台湾的骉舞剧场与著名香港戏剧导演林兆华合作的舞蹈作品《两男关系》,也将这一戏剧性的“声音语言”充分发挥。舞蹈作品仅由两名舞蹈演员就撑起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表演时长,作品将所要交代的背景,人物的具体关系以接近戏剧的形式传达出来,在口头叙述时,两人不断转换主次关系,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相互描述对方或讲述两人之间发生的各种故事,即在分工合作下,一人极简的肢体动作伴随另一人的口头表述。毕竟无论是从生活还是舞蹈的角度出发,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把握起来很棘手。试想男生间的情感就算是再默契也大多就是心神领会,极少能细腻到像女生间频繁的肢体接触。那么,除了舞蹈编创中“度”的把握,此时“声音语言”的应用就恰当好处地弥补了某种程度上肢体语言的局限性,在舞蹈演员的种种语言口述中,就常常能暗示出舞蹈本身所要传达的深层含义。《两男关系》中两名舞蹈演员的交替诉说,以及在话语来回的抛接间,就叙述了两位主人公之间的熟悉与陌生,依赖与竞争,面对与逃避……编导便是以这样的“声音”介入方式,试图寻找着作品与观众间的共鸣,达到使舞蹈作品实现多重观赏性效果的创作目的。
(三)情感性的“声音语言”
舞蹈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是以人体的动态和内心的情感深刻地折射出人情、人性和人生的真谛,这也是舞蹈的终极目的所在。舞蹈之所以感染人,是因为舞蹈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撞击,舞者不仅仅是一个动作的完成者,而更应是情感的载体。正如罗马著名诗人贺拉修斯所说:“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而富有情感性的“声音语言”正是一种舞蹈情感的厚积薄发,是舞蹈演员在经过前期舞蹈动作语汇的足够铺垫和感情积累,到达情绪顶端后所自然而然迸发出的一种情感宣泄,而这类情感满溢的状态最终以叹息、呐喊甚至嘶吼的声音直击观众的内心,在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戏剧化效果,使观众被“肢体语言”與“声音语言”的双重夹击所深深震撼,观演情绪也随即达到一个高潮,从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海军政治部文工团表演的《八女投江》,是一部根据东北抗日联军女战士冷云等烈士英雄史实创作的舞蹈作品。这部作品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法,把生活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民族女英雄的光辉形象。其中整部作品的后半段,在敌人的步步紧逼与猛烈的机枪扫射下,除了王惠民以外的七名女战士虽仍奋勇抵抗却已在死亡的边缘挣扎,而此时扮演年仅十三岁的王惠民的演员,从舞台最后方以全身蜷缩的状态,一步步端着枪战战兢兢地调度到舞台的前方,只听一声枪响,伴随渲染着紧张气氛的音乐突然戛然而止,“王惠民”声嘶力竭地哭了出来,哭声的动心骇耳似乎释放出了“王惠民”内心极度的恐惧,哭喊出那一刻无助的绝望,又或是叫喊出了女战士们深入骨髓的坚韧。那几秒的哭声使整个剧场甚至连观众的呼吸都仿佛刹那间被凝固,单一的音效却唤醒了观众不单一的心境,让人们无不为之动容。舞蹈编导将这一“声音语言”从舞蹈情节的高潮、演员情绪的尽头以及舞蹈动作的顶峰中压迫出来,是一种人物内心情绪的外化,在动作与动作之间快速连接、连续翻滚、身体重心大幅度转换等丰富的舞蹈肢体动作表现外,“声音”的出现成功地在动作基础上,进一步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在相对简洁的舞蹈呈现形式上,透过“声音”便升华了作品的主题内涵。
三、对舞蹈作品中“声音语言”应用之思考
随着舞蹈表演形式多样化的出现,尤其是现代舞蹈编导们求新求变的创作思维,导致参与到舞蹈艺术门类中的元素逐渐增多,他们不断尝试着突破原有的舞蹈编创方法,使标新立异的舞蹈呈现方式令观众耳目一新。在创作空间无限放大的今天,舞蹈中的“声音语言”可以随意地按照编导自身对作品的要求去添加、去运用,这种“声音语言”可以成为舞蹈中的“添加剂”,起到为舞蹈本身润色提亮的作用,甚至在少数现代舞蹈作品中,音乐都可以忽略不计,完全以声音的发出作为舞蹈的主体也未尝不可。
首先,在舞蹈主题的诠释上,“声音语言”往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题看不见摸不着,观众只能通过编导在整个作品中铺下的层层线索,去反复体会和思考,此时“声音语言”的插入通常能够使观众在第一时间就获得信息,锁定目标,按照编导所给予的方向去理解舞蹈所要表达的内容。例如:王玫的现代舞剧《雷和雨》,在一个圆的调度下,舞剧人物依次变换位置,分别进行简短的独白,“声音”的运用使得编导不费吹灰之力就已经交代好了故事的主要人物,透过声音还奠定了舞剧的整体基调,同时映射出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其次,在舞蹈情节方面,“声音语言”的出现往往是在整个作品的某一个重要情节的节点上,而这个节点又往往承载着作品的核心看点,于是这里“声音”的出现应是符合情节发展的脉络,离不开情感的延续与波动,是具有一定逻辑思维的,何况情节的发展都是情绪推动的结果,是在量变下引起的质变,如上文中提到的舞蹈《八女投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次,“声音语言”的恰当应用,对于烘托、渲染舞蹈环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即使在现代舞蹈创作中,运用服装、道具、灯光等各种先进的舞美设计就能够达到目的,但有不少编导仍选择用“声音”的手法,试图依靠演员自身就实现其交代舞蹈环境的功用,这也体现了那些舞蹈编导,想要极力挖掘出人体自身在舞蹈艺术中的无限可能性。执着于人体本身的艺术理念。舞蹈《相和歌》的唱词就使舞蹈描述的环境氛围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服饰和乐器只能将观众引领至汉唐繁华景致的大环境,而歌词可以让观众领会翩翩少女们真正的内心所思之小环境。总的来说,活跃在舞蹈作品中的“声音语言”对舞蹈主题、舞蹈情节、舞蹈环境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当然,从当前舞蹈作品创作中,不得不直面一种现象,那就是大量的舞蹈作品开始融入“声音语言”的“跟风”创作。在近年的某舞蹈大赛中,甚至有将近一半的作品都出现了演员现场喊叫的情节,大赛评委也表示:“现场喊叫原本是少数民族舞蹈的一个特点,融入当代舞无可厚非,但太多的舞蹈运用现场喊叫就失去了舞蹈原本用肢体表达情感的意义,达不到真情实感表达的效果,违背了舞蹈肢体语言表达情感的基本原则和艺术规律。”(1)这一席话实际也就为舞蹈中“声音语言”的盲目运用敲响了警钟。要明确的是,舞蹈中的“声音语言”绝不能成为一种追赶新潮的舞蹈编创方式,或者用以充填舞蹈内容的空洞,更不能成为编创者为了掩盖其作品主题不够鲜明、思想不够深刻的借口。“声音”进入舞蹈的前提是真切需要,真正需要“声音”来强化作品主题内容、真诚需要“声音”来释放内心满溢的情感、真切需要“声音”来达到与观众忽远忽近的“对话”效果。因此,合理恰当地使“嘴”与“肢体”发生必要的接触,才能碰撞出绚丽的火花,使舞蹈艺术“陌生化”,给观众出其不意的舞蹈呈现效果,否则只会弄巧成拙。
当声音语言越来越多地介入以身体动态为表现形式的舞蹈艺术时,也衍生出一些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面对各艺术门类间愈来愈多的融合交流,舞蹈今后该如何发展?舞蹈的未来究竟在哪儿?如何实现对舞蹈本体的追求?舞蹈的编创是迎合观众还是坚持舞蹈本身?……这里所谈论到的还仅仅是“嘴”和“肢体”间的碰撞,随着一部分舞蹈编导家不断寻求舞蹈样式的多样化以及多媒体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那些能与“肢体”间碰撞出火花的元素,定会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但无论如何,舞蹈艺术终究是一种人体动作的艺术,是经过提炼、组织和美化了的人体动作,她以人的肢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继而才运用舞蹈语言、节奏、表情和构图等多种基本要素,塑造出具有直观性和动态性的舞蹈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等。即使时代变化、艺术发展、审美更迭,舞蹈的本身特性必然不能也不会被任何“舞蹈”以外的形式所替代、吞没。
注释:
(1)摘自《北京青年报》2014年11月24日 B08版。
参考文献:
[1]刘建.舞蹈身体语言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欧建平.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高鑫.舞蹈作品中的“声音语言”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