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潘小松:译之无文,行而不远
文/孙永庆
对话潘小松:译之无文,行而不远
文/孙永庆
编者按:潘小松,1962年出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曾赴美国波士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译审。译有《海明威书信集》、本雅明《莫斯科日记》、亨利·米勒《宇宙哲学的眼光》、斯特林堡《神秘日记抄》、库佛《公众的怒火》等十余种,著有《书梦依旧》《书国漫游》等随笔集。下面是教师、作家孙永庆与潘小松先生的对话。

孙永庆:我在您的《书梦依旧》一文中读到:“一些不十分重要的外国作品在国内拥有众多读者,而一些真正的世界名著倒没引起广泛的兴趣,我觉得原因多半在译文上。”我们就从这个问题谈起吧。
潘小松:这个问题涉及汉语翻译文本的被接受程度,也涉及译者的文学表现力。通过母语接受外国文学,大抵会面临这个问题。有机会最好读原著。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是翻译中失去的文本。
孙永庆:我记得季羡林先生也说过:“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读原著当然好,但世界上的语言非常多,谁也不能通晓所有语种,能读懂原著的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需要翻译。中学语文课本里也收入了多篇翻译作品,如泰戈尔的散文诗,是作家郑振铎翻译的。可不可以这样说,译者的文学功底深厚,其翻译作品的水平就高?
潘小松:译本的高下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字的掌控能力。会写诗的译诗,会写散文的译散文,会写戏剧的译戏剧,这就比较理想。好的文学翻译当然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翻译者比原作者使用母语更得心应手,甚至能做到译本比原著更出彩。只是,在文学翻译上更多的情况是化神奇为腐朽,因为会创作的译者毕竟是少数,能有文学大师手笔的译者更是极少数。殷夫是诗人,所以他译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即便不十分忠实于原文,也是优秀的翻译。另外,文学翻译的好坏有时取决于译文传播的广泛程度,而不是其科学运用语言的程度。
责任编辑:吴新宇
孙永庆:我知道,您比较喜欢戈宝权翻译的《海燕》,它也是语文课本里的传统篇目。
潘小松:《海燕》是我读到过的真正好的文学翻译:“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这些读后不忘的译文,多半是翻译家再创造的结果。优秀的翻译家都不会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出彩。译之无文,行而不远。我读过的上佳的译文,阅读感觉比读原文更好。可见,文学翻译的确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孙永庆:您在谈阅读时说:“时尚阅读是基础阅读的补充,这就好比古典风格的时装加上当下的元素。如此阅读,就不会呆板甚至刻板。时尚信息无须精读,泛览即可。需要精读的仍然是经典的语文文本,这是阅读的语言艺术对我们的要求。”请您具体诠释一下。
潘小松:这里说到的是文学接受的时代感。时代感涉及当下,但文本的价值仍然依赖语言。语言表达是区别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标准。人类的文本阅读如今不限于文字和书本。通信的便利、视频的迅捷让人可以很直观地进行知识获取活动,产生审美愉悦。所以,我们提倡的阅读更偏向于传统典籍。因为,这些典籍经过时间的筛汰,被证明属于可靠的文本。可靠的文本有如橄榄,值得咀嚼和回味。对经典作品的阅读构成一个人读书的底子。有了这个底子之后,我们就容易形成阅读见解和选择主见,不易被时尚所左右。
孙永庆:如何确定翻译作品的经典性——不仅是原著的经典性,还有翻译的经典性?现在重译的版本太多了,有很多是蹩脚的译作,让人无所适从。
潘小松:印刷成本低廉,以及文本的商业化运作,是蹩脚文本滋生的主要原因。这个现象并不只存在于译作,非译文的文本同样有这个问题。我自己40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基本原典如《诗经》《楚辞》,虽然不容易通晓,但常读常新,受益是终生的。一个人的阅读品位要由这样的经典来构建。19世纪以后的文学作品贴近生活现实,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比更为久远的古典文学更有审美价值。人类在语言文字上的建树,并不表现得如科技进步那样日新月异,或者说,不一定就能后来居上,比如汉语文本的白话文学品种就不一定比古文高明。这也是现代人阅读面临的两难处境。我个人认为,经典文本的价值除了动人心弦之外,文字本身的铿锵韵律和内在节奏,是读之弥新的保障。我常想,一个文本何以令读者回头再看,文字的美是主要原因。经典文学家的魅力,就在于他们把日常琐碎的事情进行了艺术处理,让读者不觉得琐碎。
孙永庆:草婴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李健吾翻译的《包法利夫人》、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等,仍是很多读者读译著的首选吧?
潘小松: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择。或许,以后的人们会有自己的标杆。
孙永庆:想起翻译家冯亦代的一段话:“翻译一位外国作家的作品,除了要熟悉每篇特定的作品外,还需要多多少少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多看几本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熟悉他的风格。”汝龙先生是我国翻译契诃夫作品的专家,为此花费毕生精力,充分译出了契科夫作品的“文气”。请谈谈您的看法。
潘小松:喜欢并熟悉一个作家的文体,是翻译家的加分值。不过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莎士比亚生平材料几无,却不影响朱生豪优美的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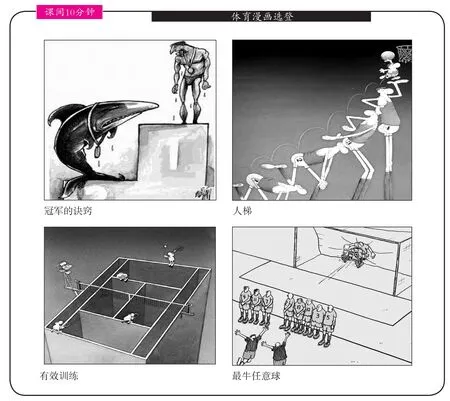
孙永庆:您阅读了大量的外文原著,翻译了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亨利·米勒的《宇宙哲学的眼光》等著作,请谈谈读翻译作品和读原著的不同感受。
潘小松:一般来说,阅读原著的语言享受,是翻译文本不能替代的。翻译能传达信息,但未必能表现原著母语的美感。当然,好的译本同样有其自身的魅力,译者的语言功底、文化涵养以及对原著的理解,至关重要。
孙永庆:很多家长往往愿意让孩子读中、英文对照翻译的书,您如何看?
潘小松:对于初学外语的孩子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