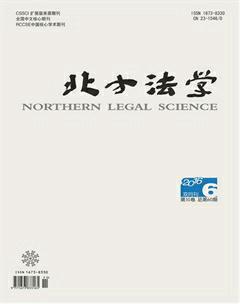“意思”的诞生
赵毅
摘要:基于罗马法教义学的考察显示,“意思”的发现是罗马合同法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早期罗马法到古典罗马法,在社会变迁的推动和法律解释技术发展的双重合力中,意思经历了一个从潜伏到破茧的诞生过程,而在要式口约、正式免除、嫁资口约和要物合同中,意思缺失会或多或少影响合同效力,对意思解释和错误问题的教义学探讨由此肇端。
关键词:罗马法 意思 合同
中图分类号:DF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6-0073-14
“意思(volonta)”作为一个法律(特别是私法)教义,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专门针对“意思”的研究,在汉语学界还是空白。山在意大利,里科波诺(Riecobono)教授最先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后又有学者专门从法哲学和私法的角度对这一重要法学概念的价值进行了提炼。对罗马法原始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意思的发现是罗马合同法发展的重要标志,而在要式口约、正式免除、嫁资口约和要物合同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意思这一合同要素在发生缺失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学者们常说:“在人类的法律文化史上,正宗法律科学之发育肇始于罗马社会,而在古近东国家以及古希腊社会,并不能发现法律科学之痕迹。”毫无疑问,罗马法学家对合同中“意思”的发现与价值提炼,正是罗马法律科学的表征之一。
由于古今合同观念不尽相同,笔者首先简要阐述罗马人对“合同”的理解,再详细分析与缔约有关的“意思”教义在罗马法中的发现及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一、罗马人对“合同”的理解
现今一般将“合同”一词与拉丁文“contractus”相对应,尽管该词及其动词原形“contra-here”在罗马法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较晚,且罗马法在其漫长发展历程中创造出了各种迥异的词汇,以表达其丰富、多元的“合同”观念,但由于“contractus”一词在后世得到了更为普遍的使用,考察该词在罗马法原始文献中的表现,对于理解罗马人的合同观念仍然是有意义的。
(一)作为债的发生原因的“合同”
D.46,3,80。彭波尼:《昆图斯·穆丘斯评注》第4卷。以什么方式缔结的合同,也应以什么方式解销。因此,如果我们是通过交付物订立的合同,该合同应通过交付物来履行。如果我们做了借贷,应偿还同样数额的金钱。如果我们通过言词订立合同,该合同可通过交付或言词解销。以言词解销,有如债务人得到了正式免除允诺的情形;以交付解销,又如债务人给付了他所负欠之物的情形。同样,如果有买卖或租赁,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单纯的协议订立,它们也可通过具有相反效果的单纯的协议解销。
这段法言揭示了三种具体的合同分类,即要物合同、言词合同、合意合同,由此,“合同”成为一个属概念,具备了抽象性。法言存在添加——这在涉及有关债的消灭的法言中十分常见,且非彭波尼之原创,因为彭波尼在谈论债的消灭问题时,惯于采用的是另一种思维模式。可以判定,法言的核心思想事实上来自公元前2世纪的法学家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他也被认为是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合同(contractus)”一词的第一人。谢沃拉的这一贡献在确定罗马人“合同”观念的时间坐标上尤为值得铭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古典时代早期,就已经存在着有关“合同”的抽象性观念,同时,“合同”与债这两个概念也第一次联系起来。
现有文献显示,直到盖尤斯生活的公元2世纪,合同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及其自身之内在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在盖尤斯对市民法的体系化建构中,债法是物法的一种,“合同(contractus)”则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在盖尤斯看来,债涉及一人对另一人所涉之义务,这种义务或者来自不法行为,或者来自一方对他方之许诺。由此,合同和私犯被法学家逐渐区分并被类型化为两种债的发生原因。接下来,盖尤斯依据合同成立的方式列举了各种会产生合同上义务的原因,包括要物合同、言词合同、文书合同和合意合同(Gai.3,89)。盖尤斯在债的框架下讨论合同,后者毋宁是“使债之关系得以发生的其中一种可能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合同类型,但却无一个一般性的合同概念。
(二)作为双方行为的“合同”
谢沃拉——盖尤斯——优士丁尼一脉对“合同”之理解并不能代表罗马人的全部。在谢沃拉以后盖尤斯之前,亦有法学家开启了对“合同”予以定义的努力:
D.50,16,19。乌尔比安:《告示评注》第11卷。拉贝奥在其《内事裁判官告示评注》第1卷中做了如下定义:有些事的实施是“行为(agere)”;有些事的实施是“执行(gerere)”;有些事的实施是“订约(contrahere)”。确实,“行为”是个一般的术语,不论某事是通过言词实施的还是通过交付物实施的,前者如要式口约,后者如借贷,都被这一术语包括。但合同是某种涉及到双务之债的东西,希腊人称之为“交换(Synallagma)”,例如买卖、租赁和合伙;“执行”指某事不通过言词实施。
本段法言摘录了公元1世纪初法学家拉贝奥的论述,他是普罗库鲁斯学派的奠定者。从字面意思出发,拉贝奥将“合同(contractus)”一词定义为“某种涉及到双务之债的东西(obligatio ul-tro citrogue)”,行为(agere)则成為统摄各种法律关系的上位概念。由于法言中的这一合同定义在罗马法原始文献中找不到其他旁证,故被认为价值不大,拉贝奥对合同的定义更被认为是伪造的。抛却有关添加的争论,即使这一法言为真,“合同”的内涵也因局限在双方行为范围内,从而被限缩颇多。有学者指出:“拉贝奥仅强调合同的双务性,而不强调合同的合意性,这是对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的忽略。”的确,概念之抽象和体系之建构是这段法言希望展示的最大目的,但对意思的忽视也是明显的。
(三)作为意思合致的“合同”
D.2,14,1,3。乌尔比安:《告示评注》第4卷:协议(conventio)是一个属概念,它适用于并来源于一切为缔结或谈妥交易在行为人之间达成同意的事情。因为正像从不同的地方被召集并来到一个地方的行为被说成是汇合(convenire)一样,从不同的内心动机出发就一件事情达成了同意,换言之,达成了一个意见的行为也是如此。而且协议的要求非常具有普遍性,故佩丢斯合乎逻辑地说:本身不具有协议的活动,不论是以交付物还是通过言辞达成的,不产生合同,不产生任何债。因为以言辞达成的要式口约,如果没有达成合意,也是无效的。
这一法言中的“协议(conventio)”一词也有学者译为“合致”,它与“合意(consensus)”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协议指双方当事人对行为内容看法的一致,双方无主次之分;而合意指一方对他方意思的附合,双方有主次之分。尽管如此,在对意思内容同一性之强调上,两者实质又是殊途同归的。乌尔比安是古典晚期的法学家,法言体现了他对“合同”概念的鲜明立场:合同之基础是当事人意思之合致,如无这种意思之合致,则不会产生合同。
乌尔比安引用了佩丢斯(Pedius)的论述,这是后者在《学说汇纂》中留下的唯一印迹。在佩丢斯看来,合意不仅是合同之核心,而且是债之核心,甚至要式口约中也必须满足此项要求。显而易见的是,古典时代已经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意思”因素开始侵入强调形式性的要式口约中,由此,“合意”成为要式口约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法律要素——这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上的要求:“没有形式的合意无效,反过来,没有合意的形式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当然,要式口约中的“合意”与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合意合同中的“合意”还有差距。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佩丢斯的这一合同观念对前述作为债的发生原因的合同观念构成了挑战。按照前述观念的两分法,合同和私犯构成债的发生原因,而在佩丢斯看来,合同就是债的全部,私犯显然被排除在这一框架之外。
二、罗马人对合同中“意思”的发现
对上一部分三个法言的考察证明,自古典时期始,罗马法逐渐开启了对合同一般性理论的探索,这种探索既有对抽象性概念之界定,也有体系上的建构。尤其是,第三个法言展示出的以意思合致为基础的“合同”观念体现出了鲜明的对“意思”之尊重,已经和现代人对合同的理解非常接近。我们可以看到,佩丢斯——乌尔比安的合同学说与之前的学说具有根本差异,“受到了个人主义与人格主义的深刻塑造”,而“意思”显然就是它们的助推器。新的问题就是,与缔约有关的“意思”教义是如何在罗马法中勃兴的呢?
(一)“意思”于早期罗马法之潜伏
1.明线:“要式”之束缚。在《十二表法》时代,还远未出现类似于古典法学家们所理解的合同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罗马人无法从事交易行为。在《十二表法》中,罗马人用多处条文规定了形式不一但皆具“要式”束缚的法律制度:
Ⅻ Tab.1,5。福尔特斯人、萨那特斯人,同样享有债务口约权或要式买卖权。
Ⅻ Tab.6,1。实施债务口约或要式买卖的,按宣告的言辞具有法律效力。
Ⅻ Tab.6,6b。拟诉弃权与要式买卖,各自具有法律效力。
这些条款涉及债务口约(nexum)、要式买卖(mancipium)和拟诉弃权(in iure cessio)三种交易形式。Ⅻ Tab.1,5和Ⅻ Tab.6,1将债务口约与要式买卖并行规定被认为是“重言法(pleo-nasmus)”之运用,按照德国学者普弗吕格的观点,“nexum”与“mancipium”实为同义词,皆指“约束”。“约束”意味着束缚,意味着自由意思的表达受到了严格限制。
在Ⅻ Tab.6,6b中出现的拟诉弃权则是罗马人发明的另外一种物权变动方式,该方式不仅适用于要式移转物,还扩及略式移转物,作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市场交易行为,它对应着一种虚拟的法庭审理程序。其中,当事人之意思合致也非移转标的物之有效要件,由此可见,买卖合同是否存在对于交易之达成并非不可或缺。
2.暗线:“意思”之潜伏。在《十二表法》中,还有两种简化了形式要求的交易形式:
Ⅻ Tab.1,6。如当事人达成了简约,则实行之。
Ⅻ Tab.2,1b。在根据要式口约主张债权时,可提起要求承审员之诉。
简约(pactum)亦称为无形式简约(nudum pactum),是当事人采用法定形式之外的方式所达成的协议,它既不移转权利,也无任何以它为根据的诉讼,所以有人说,简约是且“仅仅只是”一种同意(accordo)或是协定(convenzione)。可见,简约是最早的自然之债,因为对其之履行完全取决于当事人之自愿和诚信,而并无法律强制性的要求。
要式口约(stipulatio)虽名为“要式”,但由于其在订立上既不需要若干证人,也不需要长官出席,实质是简化了形式要求的交易形式。与简约相比,要式口约是一种正式的交易形式,具有显而易见的庄重性和完备的形式要求。立约人和受约人皆需到达缔约现场,通过特定的套语经问答订立合同,比如,立约人问:“你答应给我一百个币吗(spondes mihi dare centum)”?受约人回答:“我答应(Spondeo)”。很明显,提问和回答应当是相互完全吻合的,“颇类似于承诺必须重复要约的内容”。
正是从这两种简化了形式要求的交易形式中,我们可以发现与缔约有关的“意思”教义在早期罗马法之潜伏。在简约中,尽管双方之意思合致无法受到法律之保護,但这并不妨碍其所生协定在人类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伦理束缚。戈德雷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即使当事人已经知道,在一方没有遵守约定时法律不会给予救济,人们也已经在从事买和卖了。他甚至断言,在法律产生之前,罗马人仍然在过着一种比较有秩序的伦理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了物质上的交往——受到伦理规范的调整,这意味着,即使处于一种前商业社会,也存在着意思合致。相较简约,在要式口约的实施过程中,首先会涉及对要式口约之拟定,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对即将履行的合同的实质内容予以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即表明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协议。要式口约本身要求使用形式上一致的语词,它们由此表征着双方在交易事项上达成的心灵契合,尽管这种心灵契合通过严格甚至僵化的形式传达给对方,但它恰恰也是保证语词的内涵不会发生歧变的最可靠方式。
D.2,14,1,3表明,佩丢斯和乌尔比安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要式口约中的意思合致因素。这说明,到古典时期,在缔约中一直处于潜伏地位的“意思”要素终于即将破茧。
(二)“意思”于古典罗马法之破茧
1.“意思”破茧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合同缔结上施加的严格“要式”要求在地域狭小的农业社会中较能发挥作用,但随着罗马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和商业交往的频繁发生,“意思”破茧而出的土壤已经成熟。在罗马共和早期,随着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加深,交易开始大量增长,交易效率逐渐提高,偶尔会出现一些形式上的些微欠缺。比如,订立要式口约时,以前要求家父必须亲自到场,但由于地理空间变大导致的路途遥远,以及交易愈加频繁导致的家父无法分身,渐渐也允许派家子或奴隶到场订立要式口约。这使形式在合同中的地位日渐衰落,新的合同观则呼之欲出。这种崭新的合同观就是意思主义。到了共和晚期,随着公地私有化完成和罗马历史上商业时代的到来,罗马法的重心由物权法向契约法转移,意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取代也日渐成为可能。一方面,人的思辨能力在逐步提高,在自由和理性精神的滋养下,苛严的“要式”坚冰逐渐融化,“意思”日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因子而脱离于形式;另一方面,由于外贸之扩张,外国商人不熟悉罗马法的要式要求,主张订立无形式的合同,这意味着,罗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她的法律也需要具备一种世界精神”。毫无疑问,商业化社会之成形为“意思”提供了一个最大的舞台。
2.从法律解释技术中勃兴的“意思”
在古典法中,相较于早期罗马法,无论要式口约还是简约都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就要式口约而言,在万民法的影响下,形式的严格性减退了。就简约而言,裁判官通常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提供诉权对某些简约提供一定的保护。特别重要的是,通过法律解释技术之运用,蕴含在两者中的“意思”要素被发掘出来,成为罗马合同法独立考察的一项内容。
首先,在“言词”与“意思”的对立中,“意思”正式被赋予了超越言词的效力。就此,有帕比尼安的表述为证:D.50,16,219。帕比尼安:《解答集》第2卷:人们确定:对于协议(Con-ventio),与其考虑缔约人的文句,不如考虑缔约人的意思。
法言意在确立判定交易双方共同意图之标准。很明显,对“意思”的强调胜过了外在的“文句”要求,这表征着意思主义对表示主义的胜利。法言中的“缔约人的意思”既非立约人之意思,也非受约人之意思,而应是当事双方的“共同意思”。对于解释者来说,审查双方这一“共同意思”将是合同解释的首要目的。
其次,在无法审查上述“共同意思”或是意思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时,应以受约人的意思为准。D.34,5,26(27)。杰尔苏:《学说汇纂》第26卷:在要式口约中,如果对双方当事人的意思产生疑问,对模棱两可的解释应不利于立约人。D.45,l,38,18。乌尔比安:《萨宾评注》第49卷:在要式口约中,当就口约内容产生疑问时,应当作不利于立约人的解释。
类似的法言还有D.45,l,99pr.、D.45,1,41,1、D.50,17,34、D.50,16,125、D.45,1,106、D.45,1,12、D.45,1,109、D.45,1,83,3、D.45,1,126,2等。古典法学家们一边倒地倾向于受约人的态度是深思熟虑并经过利益衡量的产物,从诚信的要求出发,古典法学的一般观念要求,行为人要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也即所谓的自己责任原则(autoresponsabilita)。既然“市民法为勤勉之人而设”(D.42,8,24),且“蒙受了自己的过失造成的损失,不认为是遭受了损失”(D.50,17,203),那么,在诚信的双边行为中,对于要式口约内容明晰化的义务,显然只能由立约人承担,正如杰尔苏在D.45,1,99pr.中假设的那样,“立约人比受约人具有更大的自由,以给予言词更宽泛的含义”。而根据自己责任原则,由此造成的言词含义不明的责任,显然也只能由立约人自己承担。
可以发现,由自己责任原则导致的受约人意思对立约人意思之优先是对双方共同意思进行代替的不得已之举。以下两个法言更清楚地阐释了这种代替的条件和原因:D.18,1,33。彭波尼:《萨宾评注》第33卷:如果买卖契约中这样写道:“引水道及排水道维持现状”,但契约并未写明哪条引水道或排水道,则应首先考察当事人是如何约定的。如果这一点并不清楚,则应做对出卖人不利的解释,因为契约的词句含混不清。D.18,1,21。保罗:《萨宾评注》第5卷:拉贝奥写道,协议的含混不清所损害的应该是提出协议的出卖人,而非买受人。因为出卖人在契约完成之前,本可以更清楚的方式表达他的意愿。
D.18,1,33阐明了对出卖人意思不利解释的条件:契约的词句含混不清。这意味着,买卖双方的共同意图无法查明。法言第一句强调,在此之前,必须进行“考察当事人是如何约定的”这一工作,因为如果能够通过考察确定共同意思,则还是以共同意思优先。D.18,1,21则清楚地解释了在出现协议含混不清的情况下,为何应做不利于出卖人之解释的理由:“出卖人在契约完成之前,本可以更清楚的方式表达他的意愿”。这意味着,出卖人在表达自身意思的时候,负有使之明晰的义务,否则造成的不利后果由自己承担。
再次,简约同样采用受约人意思优先的解释规则。
D.50,17,172pr.。保罗:《普劳提评注》第5卷:在缔结的出售中,对模棱两可的简约,必须作不利于出卖人的解释。D.2,14,39。帕比尼安:《问题集》第5卷:早期法学家认为,内容含混或书写不清的简约不利于卖方和出借方,因为他们在起草简约时本应该书写得更为清晰、明了。
D.50,17,172pr.与D.18,1,33类似,阐述了在简约中作出不利于出卖人解释的前提条件:简约内容模棱两可。当然,这同样意味着,简约双方的共同意思无法查明。D.2,14,39则与D.18,1,21完美对应,论证了为何制定这种不利于出卖方的解释规则之因由。整体上看,对简约的意思解释规则同要式口约并无不同。
总之,与缔约有关的“意思”要素于古典罗马法之勃兴意味着罗马私法一个新的时代来臨,在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意思瑕疵问题自然而然走人了古典法学家的视野。
三、意思瑕疵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现今人们非常熟悉的作为意思瑕疵的错误、胁迫、欺诈之三分法在罗马古典法时期并未形成体系,它们是在优士丁尼时代建构的结果。在罗马古典法时期,欺诈和胁迫主要作为不法行为而出现,既未与“意思”或“意思瑕疵”产生关联,也与行为或交易的效力无关。与行为之心理内容产生联系的意思瑕疵主要是错误。贝蒂认为,意思瑕疵在古典法中是被置于对法律行为解释的框架下予以讨论的。由此,我们可以在古典法学家对附加了要式要求的口头合同(包括要式口约、正式免除、嫁资口约)和要物合同的解释中,发现罗马法对意思瑕疵问题浮现后的各种解释学尝试。
(一)要式口约
1.意思解释规则
要式口约是缔约当事人通过特定套语经程式性问答而订立的合同。如果要在要式口约中进行意思解释,必须以缔约人之意思发生模棱两可为前提:D.32,25,1。保罗:《内拉蒂评注》第1卷:如果文句中无模棱两可,不应允许提出意思问题。
这一法言展示了意思解释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它意味着“意思问题”之出现须以文句发生模棱两可作为先决条件。文句发生模棱两可则意味着需要通过解释重构双方当事人之“共同意思”。
由此带来争论的是下一法言:D.45,1,32。乌尔比安:《萨宾评注》第47卷:当就要式口约的标的物达成了合意而仅仅是搞错了所要给付的奴隶的名字,我们认为要式口约有效。此处,要式口约缔约双方皆未发生意思的模棱两可问题,双方对要式口约标的物之认知是同一的,并无分歧存在。故而,对“所要给付的奴隶的名字”发生的错误只是言词表示与双方真实意思之分离问题,而根据D.50,16,219,意思显然比表示具有更大的效力。
下一法言则出现了意思的模棱两可问题:D.45,1,106。雅沃伦:《书信集》第6卷:如果几块土地都是同样名字,当有人通过要式口约就其中一块进行交易时,所说的这块地并无特定指征,此时,要式口约之标的物就是不确定的;这也就是说,通过他所立之要式口约,受约人可以选择性地挑取土地交予他。然而,受约人的意思将一直处于未定之状态,直到他所选定之土地已交付。法言讲的是不确定的要式口约(stiulatio incerta)。由于几块土地皆为同样的名字(即有共同的族名),自然在立约人的表意过程中会发生意思的模棱两可问题。此时,根据自己责任原则,意思解释倾向于受约者,他有从相同族名的土地中自由挑选的权利。可见,通过意思解释技术之操作,本来发生语义模糊的要式口约,可以最终顺利缔结和履行。
2.要式口约中意思问题的本质
在要式口约中,还会出现一些意思的模棱两可情况,经过意思解释规则之操作后,可以发现双方在意思上呈现出明显的不一致。就这些在意思上出现的不一致之本质,原始文献呈现出的理解并不相同,有“不合意”和“问答不符”两种观点。
一方面,一些法言明确宣称,只有通过合意,要式口约才能够缔结,不合意的要式口约无效:D.45,1,83,1。保罗:《告示评注》第72卷:如果以斯提库斯为标的物订立了要式口约,我想到的是这个斯提库斯,你想到的是那个斯提库斯,不发生任何交易行为。阿里斯托认为这种情况也要审理。而更好的意见是原告想到的人被视为被要求的人。要式口约确实根据双方的合意生效,但也可违背某人的意志作出判决,因此相信原告更可取,否则,被告会总是否认他作出了同意。D.45,1,137,1。魏努勒留斯:《要式口约》第l卷:在我和你就一个奴隶缔结的要式口约中,如果我想的是一个人,而你所想的却是另一人,要式口约不会成立;事实上,要式口约只有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才能缔结。
另一方面,也有片段明确显示,要式口约中错误的本质是“问答不符”:I.3,19,23。如果要式口约的提出人指的是一个物;债务人指的是另一个物,不缔结任何债,完全如同提问没有得到回答一样,例如,某人通过要式口约买奴隶斯提库斯得到你的允诺,而你指的是你认为被叫作斯提库斯的庞菲鲁斯的情况。
对这两种观点的考察,需要分别进行。先看前两段法言。D.45,1,83,1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实体上的,包括第一句和第四句的第一分句,核心观点是要式口约以双方合意为成立前提,否则将不能成立。第二层意思则是程序上的,包括第二、三句和第四句除了第一分句之外的其余部分,重心在于借阿里斯托之口阐明裁判官对意思解释享有的裁量权。此处,阿里斯托不仅认为发生了不合意的要式口约也可能生效,而且采纳的是支持立约人利益的立场,由此使得第一层之实体意思和第二层之程序处理出现断裂,这可能也正是保罗与阿里斯托观点之对立——保罗显然是第一层意思的支持者。
保罗的立场则可能来自魏努勒留斯。D.45,1,137,1显示,后者对前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将这一法言与D.45,1,83,1中的第一层意思进行对比,两者不仅观点一致,所举之事例亦几乎相同。两人所用的皆是非常肯定的语气,前者断言“要式口约确实根据双方的合意生效(stipulatioex utriusque consensus ualet)”,后者坚持“要式口约只有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才能缔结(nam stipula-tion ex utriusque cortsensus perficitur)”。显然,在两人看来,要式口约中错误之本质是合意缺乏。
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I.3,19,23,这一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片段进行了与D.45,1,83,1和D.45,l,137,1完全不同的表述。I.3,19,23并未提到要式口约之成立以合意为前提,而是强调,如果立约人之提问没有得到守约人之回答,将不会缔结任何的债。这里的问题是,要式口约因为“不符合时代要求”,在公元427年已被列奥皇帝废除,那么为何在公元6世纪编写的《法学阶梯》中,还存在着对这一历史概念之表述?徐国栋教授作出的一个推测值得注意,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了要式口约作为古典时期罗马合同法一般规则承载体的作用,由于拜占庭法学家之懒惰,他们在进行法典编纂时并未根据变化了的时代“另起炉灶”,而是依托要式口约予以打造合同和債的一般理论。这就恰恰反映出,这一片段是真实的,反衬了古典时期法学家对要式口约之理解。
I.3,19,23之理论来源是盖尤斯《法学阶梯》,在Gai.3,102中,盖尤斯谈道:“如果某人对于被询问的话未做回答,要式口约也是无效的,例如:我在要约中让你给付10塞斯特斯,你却回答给5塞斯特斯,或者我提出的是简单要约,你回答时却附加条件。”这再次证明,“问答不符”这一观点,可能并非来自优士丁尼时代法典编纂者的添加,而至少是某些古典法学家的真实看法。
与诞生于优士丁尼时代的I.3,19,23真实反衬出古典法学之原貌正好相反,有趣的是,披上了古典法学家著述外衣的D.45,1,83,1和D.45,1,137,1却被证明是添加的产物。无论是前者所声称的“要式口约确实根据双方的合意生效”,还是后者所坚持的“要式口约只有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才能缔结”,它们皆是来自于法典编纂时期的产物。在古典法学时期,就合同错误问题,还未能产生出不合意导致合同错误的一般性理论。
但这样一来,如何解释D.45,1,83,1和D.45,1,137,1与D.2,14,1,3呈现出的相互印证之效?在D.2,14,1,3中,乌尔比安借佩丢斯之口说道:“本身不具有协议的活动,不论是以交付物还是通过言辞达成的,不产生合同,不产生任何债。因为以言辞达成的要式口约,如果没有达成合意,也是无效的。”学者们的考证承认,D.2,14,1,3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如果说D.45,1,83,l和D.45,1,137,l中对“合意”的提及是添加之产物的话,那么为何又承认在D.2,14,1,3中出现的“合意”表述?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D.2,14,1,3强调的并非合意,而是内在于要式口约中的“协议(conventio)”,它的重心不在合意上,而是债的效力问题。的确,D.45,1,83,1、D.45,1,137,1与D.2,14,1,3所讨论的问题域完全不同,前两者讨论的是要式口约中的错误问题,而后者是在力求建构一个一般化的“协议”或是“合同”概念,与错误问题无关。
由此笔者认为,要式口约中意思问题的实质是“问答不符”,它准确而真实地反映了合同错误制度在形成时期的原始性,由此与要式口约基于外在形式所体现出的特质相符合。当然,双方内在意思之不合致潜藏于“问答不符”的外在形式下,但此时还并未抽象出不合意导致要式口约(它就是那个时代的“合同”)无效的一般性规则。
(二)正式免除
D.46,4,6。乌尔比安:《萨宾评注》第47卷:在已缔结了几个要式口约的情况下,受约人如果想对其中之一要求正式免除,其辞曰:“余与汝所约之物,汝曾受领否?”如果这里双方清楚指的是哪一个要式口约,就可单独处理该项要式口约的正式免除事务。如果所指并不清楚,所有要式口约皆被消灭。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牢记,如果我意在对一项债务予以正式免除,而你要求的是对另一项债务之正式免除,正式免除无效。
正式免除(acceptilatio)是古典罗马法中撤销债务的要式行为,它表现为一种虚拟的清偿。与要式口约通过问答方式创设债务相同,正式免除通过问答方式消灭债务。详言之,即受约人问立约人曰:“余与汝所约之物,汝曾受领否(Quod ego tibi promise,habesne acceptum)?”立约人答曰:“余已受领焉(Habeo)”。如此,则债务完全免除。
本段法言涉及正式免除的意思解释和错误两个问题。前三句讨论的是正式免除的当事人出现意思模糊时的解释问题。在法言给出的案件中,由于要式口约的数量为复数,此时应对“余与汝所约之物,汝曾受领否”这一言词之所指为何予以解释,以获得双方之共同意思。如果通过解释能够确认双方之真意,且这种真意达成了合致,此时,对其中一个要式口约的正式免除就是有效的。但如果无法通过意思解释找出双方之共同意思,此时作扩大解释,视为对所有要式口约皆正式免除。
法言的最后一句则涉及错误问题:如果受约人问立约人的是一项债务,而立约人之回答所指实为另一项债务,此时由于“问答不符”,正式免除无效。有意思的是,与上述D.45,1,83,1、D.45,1,137,1和I.3,19,23类似,本段法言同样反映的是物之同一性错误问题,但与上述三个法言中的物为有体物不同,本段法言是对无体物——债——发生的错误问题。
(三)嫁资口约
D.23,3,46,2。尤里安:《学说汇纂》第16卷:在父亲误认为其欠女儿一笔嫁资,并许诺支付给她,父亲将受此嫁资口约的约束。D.12,4,9,1。保罗:《普劳提评注》第17卷:假设某人在其女要求下,错误地许诺给其女未婚夫一笔金钱,以为他付的是女儿的嫁资,随后,其女与该男结婚。他不能适用诈欺抗辩,尽管其女婿是基于自身的交易收受的金钱,但他并未实施欺诈。他不应该让其女婿失望,使后者被迫带走一个没有嫁资的妻子……
作为一种典型的古典法上的制度,嫁资口约(dotis dictio)也称为嫁资声言(dictio dotis),是一种设立嫁资的行为,通常在订婚时发生,表现为女方的家父或女自权人之单方口头许诺。嫁资口约既可能发生在家父与女儿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家父与女婿之间,还可能发生在作为自权人的女人与其夫之间。D.23,3,46,2即第一种情况,D.12,4,9,1则是第二种情况。事实上,作为一种单方的要式行为,在嫁资口约中,债之约束在一方许诺时即产生,故而其在形式上并不具有协议性,也不存在考虑意思的合致问题。
由此,就可以理解在上述两段法言中,为什么即使父亲的允诺发生了错误,他也将会受到约束的原因,因为此时债已经形成,这正体现了要式行为的机械性和形式性之本质。另外,罗马人常基于政策考虑“认错为对”,此处有保护女性的政策考虑。D.50,16,219规定的意思优于文句的规则在此处并不适用,因为这里并不存在“协议”。
但即使如此,如果一方意思出现模棱两可之情形,对意思之解释仍然是必要的。在D.50,16,125中,普罗库鲁斯谈到:“当有人通过以下言词允诺嫁资:‘在我有能力之时,我将付你100阿斯的嫁资。我认为对此应进行合适的解释。因为在有人使用模棱两可言词的时候,他对其内心之表达应通过其使用的言词来理解。”这一法言展示的问题是:何为“在我有能力之时”?普罗库鲁斯选取的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模式——“通过其使用的言词来理解”。实际上,“在我有能力之时”更像是一种随意条件(condizione potestativa)之运用,这里并不存在有何模糊之处。D.23,3,79.1选取的是另一种解释模式:“父親在其有能力之时支付嫁资,以使其不会陷入不名誉或破廉耻之境地。”显然,这是一种社会伦理解释模式。
最后,如果要对上面两个法言中的错误情形进行定性的话,家父之错误实属动机错误,即“误认为其欠女儿一笔嫁资”。可以看出,与前述要式口约和正式免除中的错误情形相比,动机错误与它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主要表现为一方当事人的心理活动,从而既与“问答不符”或意思上的不合致相距甚远,也与物之同一性无关。由于嫁资口约完全不具备“协议”的特征,可以预见,动机错误将与正趋日臻完善的罗马合同法渐行渐远。
(四)要物合同
要物合同产生于古典法学时期,消费借贷(mutuum)是其最重要的一种类型。消费借贷是一种单务的实物契约,标的物为可替代物,一般是货币。债之产生以物之交付为前提,如果并未发生所有权转移,则不产生消费借贷。需要注意的是,要物合同之所以被称为“合同”,是因为双方当事人在一定目的下对物之交付达成了意思合致,这种目的作为物之交付的原因而存在。以消费借贷为例,双方当事人基于借贷目的产生的意思合致是行为成立的前提条件,而金钱交付行为之履行则意味着合同成立。
在杰尔苏的法言中,可以发现一个有关消费借贷中出现的错误问题的记录:D.12,1,32。杰尔苏:《学说汇纂》第5卷:如果你要求蒂丘斯和我借钱给你,我命令了我的一位债务人完成此事。你在和他缔结要式口约的时候,相信他是蒂丘斯的债务人。你因此会对我欠有债务吗?我的立场保持不变,的确,你并未和我缔结合同,但我认为你仍然对我负债。这并不是因为我借了你钱(因为除非双方达成合意,否则这并不现实),而是因为我的钱进入到了你的手中,因此,你应还钱于我,这是基于公序良俗的要求。
由于这一法言据说是古典法中关于当事人错误(error in persona)导致合同无效的唯一一份孤证,相关文本数量极少,故而在学说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撇去从代理角度对法言进行的分析和对文本最后部分关于返还诉(condictio)的讨论,学者们的考察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法言本体的分析,核心是消费借贷合同是否成立。由此,学者们被划分为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多数说持否定的态度,但亦有少数学者坚持消费借贷成立。第二即所谓的当事人错误问题。从第一种立场出发,自然得出当事人错误影响合同效力的结论;但如果少数说的观点为真,就可以推测,当事人错误其实并不具有影响合同效力的重要性。
先看第一个问题,即消费借贷合同是否成立。持多数说立场的学者们似乎并未站在一个相同的思维层面上讨论。比如,在沃奇看来,消费借贷关系应该发生在借用人和作为被代理人的“我”之间,但由于借用人错误地相信了钱来自蒂丘斯,故而在借用人和被代理人之间的消费借贷合同并不成立。沃奇完全没有提及代理人——即“我”的债务人——与借用人之间是否成立消费借贷合同的问题。但在泽莱蒂的一个学说综述中,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学者们都承认在代理人和借用人之间的要式口约有效,但却否认代理人与借用人之间存在着消费借贷合同,原因是错误或不合意。”泽莱蒂完全忽略了对借用人和被代理人之间关系的考察。
笔者认为泽莱蒂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同时笔者也赞同沃奇在此的结论,因为法言已经清楚地申明,作为借用人的“你”与作为被代理人的“我”之间并未缔结合同,原因则是双方之间不存在合意——虽然“我”意图借钱予“你”,但“你”却认为在向“蒂丘斯”借钱。当然,这样一来,也需解释清楚法言中的“但我认为你仍然对我负有债”这一表述的真实含义。这一表述并非意味着“我”与“你”之间仍然存在消费借贷之债,如果这样理解,将是荒谬的,因为前一句已经清楚申明两者之间并无消费借贷合同。那么,“债”从何来?劳利亚对此进行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考察,在他看来,此处使用的“债”是一个技术性术语,用来指称市民法所确认的在诉讼程式中必须进行的给付。四故而,基于公序良俗之要求,被代理人可以因此而向借用人提起要求返还之诉。
更值得探讨的是代理人与借用人之关系。这里,笔者并不赞同泽莱蒂的说法。笔者认为代理人与借用人之间既成立了要式口约,也因此而成立了消费借贷合同。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最后一句中出现的“我的钱进入到了你的手中”这一表述,“进入”这一动词在法言的拉丁原文中为“per-venit”,一贯用来表示物之交付,而非单纯的占有关系。这说明,在本段法言中,作为标的物的金钱已经被交付到借用人之手。由于前述Gal.3,90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消费借贷合同以物之交付为前提,显然,“我”的代理人和借用人已經缔结了消费借贷合同。当然,这一合同之缔结是通过要式口约的外在形式完成的。要式口约之双方当事人同样是借用人和“我”的代理人。在金钱的交付过程中,该两人分别的要式口约显然达成了就借贷为目的的合意。尽管债务人在缔结要式口约的时候错误地相信对方是蒂丘斯的代理人——而非“我”的代理人,但这显然与交付导致的消费借贷合意无关,错误是外在于这一要式口约的。
由此再审视第二个问题,即这一法言是否真的建立了所谓的“当事人错误导致合同无效”理论。笔者认为这同样是不成立的。首先,在被代理人与借用人之间并无消费借贷合同之存在,这一点所有人皆无异议。但需要注意的是,“合同之不存在”与“合同无效”完全是两回事。从借用人的角度看,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和被代理人缔结合同,他所想的合同缔结对象一直是另一人,即使他之所“想”是一种错误,但这种错误与他和被代理人之间所不存在的消费借贷合同完全无关,更不存在这一错误会使一个本就不存在的合同无效的问题。事实上,在借用人和被代理人之间,一直横亘着一个代理人,就算可以把借用人在借贷对象上的误解描述成所谓的“当事人错误”,但这一错误的作用范围也是有限的,并不能跨越代理人而直接作用于其与被代理人的关系。其次,再来看当事人错误是否对代理人和借用人之间的消费借贷合同产生影响。显然,借用人是对代理人的身份——而非代理人本身——发生了错误。从借用人的角度来看,他对交付人本身的认定是可以确认的,只是他错误地以为交付人代理的是蒂丘斯,而非“我”。如前所述,这一身份之错误并未影响到消费借贷的效力,由此可见,身份错误并不具备重要性。
结论
以上的文本分析尽管不能完全反映出“意思”在罗马合同法形成时期的全貌,但毫无疑问已经在特定向度上展示了罗马人对意思教义多元性的思考。可以发现,从一开始,意思问题就和解释问题与错误问题紧密相缠。正是在对交易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进行的解释学尝试中,罗马法学家们逐渐产生了对错误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为意思瑕疵制度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我们还可以发现,罗马法学家们通过决疑法提炼的意思瑕疵问题皆发端于有形式要求的要式行为——要式口约、正式免除、嫁资口约皆属典型的要式行为,D.12,1,32所讨论的消费借贷合同也是通过要式口约缔结的。由此可见,在古典时期,对行为的“要式”要求已经不像罗马法早期那么苛刻,意思主义逐渐取得了对表示主义的胜利,由此腾留了意思解释和错误问题的探讨空间。当然,罗马法学家从未试图在私法或者合同法领域建构一个普适的“意思”、“意思瑕疵”亦或“意思表示”观念,它们作为抽象法律教义的出现,将是千年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