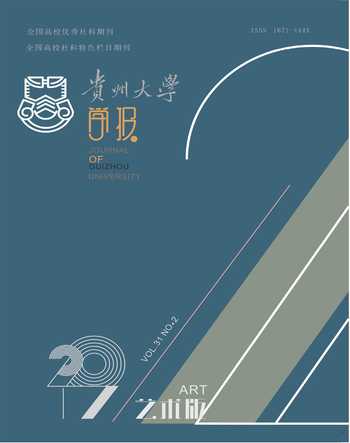两汉音乐机构与鼓吹乐互动关系研究
赵倩
摘 要:本文第一部分探讨了西汉时太乐与乐府的职能及其所掌音乐的性质,对汉武帝“重立乐府”及哀帝“罢乐府”两个历史事件及其意义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西汉自高祖制定宗庙、朝会礼乐,到武帝“重立乐府”,再到哀帝“罢乐府”,这从“立”到“破”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帝王对于礼乐制度的重视,更体现了西汉帝王对“功成作乐”理念的沿袭,是对“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强化步骤,是维护皇权“正统”性的必然之举。第二部分,主要对承华令的设置进行溯源,探讨其与东汉鼓吹的关系,并认为东汉的音乐机构建设,体现出“并官省职”及其“礼乐合一”的特征,而鼓吹则是由承华和黄门两机构共同管理。通过对两汉音乐机构的变迁与鼓吹乐隶属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探讨,反映出汉代礼乐制度背后的政治逻辑。
关键词:汉代;音乐机构;鼓吹乐;皇权;礼乐制度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7)02-0076-14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7.02.014
汉代较为统一的政治环境,使从宫廷到民间出现了异常繁荣的音乐活动,其中音乐机构在音乐活动的实施、生产及協调等环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太乐、乐府以及黄门,作为音乐机构,是两汉国家礼乐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在由汉室执掌中原政权的400余年间,其兴衰演变、存废取舍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紧密地关联着两汉政治、经济背景、礼乐关系、帝王的审美趣味等因素。而对于鼓吹乐在两汉的机构归属问题,学界也多有讨论,只是存在界定不够清晰或论据不充分的情况,本文则希望对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解读,提出较为清晰的界定。
一、西汉音乐机构与鼓吹乐
(一)太乐和乐府的职能
西汉的太乐和乐府官署,均承秦制。《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宫令长丞,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1]726“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监,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1]731《通典》云:“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及丞,又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2]695
上述文献清晰地说明了汉代掌管乐舞的音乐机构——“太乐”和“乐府”,分别隶属于“太常”和“少府”。关于“太乐”和“乐府”掌管的音乐性质,历史上,王应麟曾说:“太乐令、承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3]当代学界也有不同的讨论。如刘兴珍认为:“太乐”主要掌管宗庙礼仪中的祭祀乐舞,“乐府”则是掌管供皇帝及其亲贵享受的俗乐舞演唱教习机构。[4]25许继起则通过对秦音乐机构的设置,论述汉代对秦音乐机构的“继承”关系:“秦代音乐机构设有乐府、太乐。乐府有乐府令、丞,乐府丞分左、右乐丞,丞下亦各有属官。秦代乐府的功能是汇集当时异国宫廷音乐,主要用于宴饮娱乐,也可参加郊庙祠祀礼仪,这种方式影响了汉以后乐府机关的管理职能及其乐府音乐的社会功能。太乐有内乐、外乐之职,前者掌房中、宗庙、宴飨用乐,后者则掌南北郊、四望、山川、五祀、五神及各地方祠庙用乐。在乐府音乐和太乐音乐同用于郊庙、出行、宴飨时,由礼仪之官奉常及其属官太祝令统一调配”[5]39,“从音乐技术角度讲,古代宗庙、郊祀之乐,多法后王,重改作,甚者其乐仪、乐节、乐歌大致不改,因此太乐机构对音乐技术的要求相对降低。即太乐之乐主要为娱神之乐,尚‘朱弦疏越,娱人之乐则重‘繁手淫声,显然二者对音乐技术的要求不同,这样决定了太乐、乐府教授的内容、方式等各有侧重,不能一概言之。”[5]18虽然诸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对汉虽承“秦制”,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却仍有差异的事实,则有统一的认识。西汉时太乐和乐府两机构之职责是各有分工的,两汉礼乐制度的完善,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汉书·礼乐志》载:
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干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1]1043-1044
孝景帝时,定制宗庙乐舞: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集解】: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执干戚。文始舞执羽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见礼乐志。”【索隐】:应劭云:“礼乐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袭。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乐总象武王乐,言高祖以武定天下也。既示不相袭,其作乐之始。先奏文始,以羽钥衣文绣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执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6]436
可见,汉初时,在沿用前乐的理念下,高祖先创“宗庙礼乐”,即为太乐所属,到景帝时的乐舞创制,也是用于宗庙,自然也归太乐管理。此外,从“制氏”的身份而言,“太乐机构的功能也有保存、传授、传播先王之乐的功能,显然与乐府之职能相区别。”[5]42河间献王以为宗庙乐已无雅正之乐,因而献雅乐,被立于“大乐”中,即文献所载之:“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大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1]1071-1072
到了武帝以后,不同于汉初帝王的“崇祖”、“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6]14的观念,在将神学化了的儒家思想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型态后,“郊祀”便更加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即如《汉书·礼乐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干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1]1045
可以认为,“重立乐府”并创制“《郊祀歌》十九章”的目的,是服务于郊祀之礼,与此同时,乐府的功能有所扩大,其人员也得到了大幅扩张。西汉时之太乐和乐府所分别执掌的用乐功能可进一步解释为:前者主要是“宗庙乐”,后者则是“郊祀乐”。但由于西汉又有“哀帝罢乐府”之重大历史事件,将原属于乐府的部分乐人——“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归入太乐之内,使两者的职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换,那么太乐的地位无疑又得到了提升。因此,萧康达认为,汉代太乐令、丞的职能为:“一、掌管先朝留下的雅乐。二、哀帝即位之后,还职掌郊庙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声者。”而乐府令、丞的执掌范围分别为:“一、监造乐器;二、职掌郊庙祭祀与古兵法武乐;三、职掌郑卫之声(俗乐);四、采集民间歌谣;五、配乐。”[7]5-8
俞士玲依据二者使用场合的不同进行功能区分:
则太乐、乐府职掌的音乐分别运用于不同场合,它是划分两者职能的主要标准。(中略)西汉设立司乐官署,首先着眼于用,即用于什么场合。太乐署主要为宗庙祭祀等提供音乐,乐府为郊祭、朝贺、娱乐等提供音乐。[8]
除此之外,西汉时期太乐和乐府在功能上的交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学者对此现象进行研究,认为两者可能是一个机构,如黄祥鹏认为从历代职官的演变看,唐代以前的“太乐”和“乐府”几乎没有同时在一个时期内出现,“有‘太乐则无‘乐府,有‘乐府则无‘太乐,也可证明二者是同一个机构。”[9]170
总之,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太乐和乐府所掌音乐的性质的准确界定和认识。
(二)汉武帝之“重立乐府”
關于“乐府”的生辰,学界已有定论如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1期。音乐界近年出版的音乐史著述中,也有较为清晰的论述,本文不再重复。,即“乐府”起于秦而非汉武帝时。武帝的“乃立乐府”实则是“重立乐府”。且看文献对于“重立乐府”一事的记载和简评:
《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干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1045
《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1]1756
《汉书·武帝纪》赞曰:“典太季,修郊祀、改正朔,定磨数,偏音律,作铸祟,建封植,被百神,绍周俊,镜令文章,焕焉可述。”[1]212
具体而言,武帝在乐府官署及其功能上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扩大乐府的官职设置及其职能范围:由令、丞各一,变为三丞[1]731,通过“采诗”保存了许多不同地区的音乐,并将秦楚赵代各地之音乐用于郊祀仪式中,乐府乐人除了参加宫廷内各种燕饮仪式外,还要参加郊祀仪式的音乐表演;二是令司马相如等作诗、李延年为之度新声,以备郊祀乐舞之用等。除了上述内容,张永鑫还认为武帝时期大规模的乐舞活动还包括:把输入异域乐舞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和开始扩增乐工的工作。[10]
把乐府职能的变化,放在西汉武帝时期的背景下分析,其体现出的音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便呈现在我们眼前:
其一,礼乐关系的生动再现,它是王者“功成作乐”的具体行动,是统治者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班固的《白虎通义》是针对由汉明帝组织的围绕《周礼》仪式用乐讨论的政治性会议笔录,其中便有对“制礼作乐”的记载:
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饥寒,何乐之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乐言作、礼言制何?乐者,阳也,阳倡始,故言作;礼者,阴也,阴制度于阳,故言制。乐象阳,礼法阴也。[11]
其二,是武帝时政治权利布局思想在音乐分配上的表现。武帝“重内轻外”的思想,使其把内廷的各方面建设摆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也是为了限制外朝的权利膨胀,因此他能够将原属于太乐的“分内事”揽在“乐府”麾下,并且导致“郑声满堂”而最终遭罢。
其三,武帝立乐府将郊祀礼乐纳入其内廷乐府的管辖,是其神学观念在其大一统的政治建构中的必然反映。利用各地音乐来娱乐山川鬼神等神明,以强化对于臣民的思想控制。汉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伺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1]1045。由此可见,宗教祭祀中在以“礼乐献天神”的“幌子”下,所隐藏的是怎样一种政治的目的。
其四,武帝立乐府之举,又可以看出,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以及追求奢华享乐的观念。乐府属于少府,而少府则是统管皇帝宫廷的一切事物,那么,乐府的功能就主要是面对皇帝及后宫在宫廷中的各种礼仪性的或娱乐性的音乐活动。同时,据赵敏俐研究,正是在宗教神学“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思想的影响下,汉代帝王的享乐观念又是一种对待“生命意识”的关怀和抒发。[12]
其五,所谓“采诗”,即“观民风”之举,实则是通过所采民歌监视地方诸侯。汉代在政治上,虽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帝国,但是仍然延续了分封制,为了加强中央政权对于地方诸侯王的监管,“采诗”便是一种较为“平和”的监察方式,同时又能以“新声”献于天地、五帝等,可谓“一石二鸟”。它不仅表明了统治者对于各诸侯国音乐的重视、甚至地方风俗之于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性外,更体现了在“大一统”的观念下,汉代帝王通过音乐制度所体现出的政治思想,正如许继起也认为支配武帝“采诗”制度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制度与地方势力间的内在张力:
汉代宗族观念的加强,是两汉对同姓诸侯几位重视。采择地方歌诗、风俗、歌谣,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势力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中央政府监督地方势力的一种手段。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每年由刺史循行天下,采择风谣,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地方势力的监督与控制。[5]87
其六,武帝立乐府,亦体现了汉代音乐(礼乐)观念的转变。上文提到,王应麟认为乐府执掌“郑卫之乐”,即武帝通过“郑卫之乐”的引入,以郊祀乐为“试金石”,改变了古经典雅乐的音乐风格,依许继起研究,汉武帝的乐府在“礼官”和“乐官”的结合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而核心就是“协律都尉”的设立,使得西汉的礼乐制度建设,即注重礼之仪式性,又注重音乐性。[5]172-173
总之,新乐府的职能与其用乐规范的建立,在音乐史和文化史上,都是意义重大的事件。此外,客观上讲,武帝重立乐府在满足统治阶级宗教性礼乐制度的建构需要外,同时也利用国家的力量,丰富和推动了汉代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发展,促进了汉代乐府诗歌的繁荣,是一举多得之举。
(三)太乐和乐府音乐的性质
从学界对于太乐和乐府职能的争论看,其实质与两者所掌管的音乐性质有关。王运熙曾总结说两者的音乐性质可以用“雅”“俗”两类来区分:
汉魏两晋南北朝音乐,一般可分为雅乐、俗乐两大部分。雅乐歌诗为郊庙、燕射等歌辞,俗乐歌辞则以清商曲为大宗。二者因性质用途不同,职掌的乐官也常区分开来。从西汉讲起,西汉乐官有太乐、乐府二署,分掌雅乐、俗乐。[13]
根据王运熙的总结,及上文的描述,西汉太乐所掌音乐的性质是雅乐,当无疑问。即从高宗开始就以“宗庙乐舞”为主,在音乐的表演上主要是以歌(乐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表演形式,即中国古代之“乐”。
不过,若谈及西汉乐府,尤其是武帝“重立乐府”以后,少府所辖乐府的性质,就与其所掌音乐的主要使用场合产生了矛盾:武帝重立乐府后,便“采诗夜诵”,所采之乐歌乃秦、楚、赵、代等地的歌曲,从性质上说,当属“郑卫之音”或“新声”,依礼,此类音乐需禁,更不应出现在雅乐场合。虽说,少府之职为“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即负责皇帝、宫廷的一切事务,那么,乐府的功能自然主要以皇帝、宫廷的娱乐燕饮等仪式场合的用乐为主,但武帝所采的“新声”却并未直接用于内廷,而是施于重立的“郊祀”仪式场合,因此这也就是矛盾所在,使得我们不能准确界定乐府所用音乐的性质。
又,三代郊祀之禮,有乐舞的存在,《史记·封禅书》载:《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1]1357秦汉多依周制,文献中也可见乐舞也为郊祀中必需之音乐形式,而乐舞的表演,又不仅是乐府独自完成,乃协同太乐共同实施,即如许继起所言:“从祀祠用乐的角度来看,西汉郊祀之乐多用地方音乐,受汉初祠祀制度的影响。其郊祀之鼓舞乐事,盖由巫祝之官、太案官共掌。”[5]43而且,武帝时期,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负责郊祀用乐,其中便又存在着矛盾:李延年是俗乐的行家,但是所参与的事却是用雅乐的场合。
因此,对于西汉太乐和乐府所掌音乐的性质的界定,就不能以雅乐、俗乐进行简单的对应定义,而需要将其使用场合的不同功能作为考虑因素。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关于汉以后音乐的总体评价,可以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夹漈郑氏曰:“有宗庙之乐,有天地之乐,有君臣之乐。尊亲异制,不可以不分;幽明异位,不可以无别。按汉叔孙通始定庙乐,有降神、纳俎、登歌、荐祼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乐,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黄门鼓吹之乐,天子所以宴群臣也。鸣呼!风、雅、颂三者不同声,天地、宗庙、君臣三者不同礼。自汉之失,合雅而风,合颂而雅,其乐已失,而其礼犹存。[14]
可见,汉代武帝以后,先秦《诗》用以区分不同功能之乐的“风”、“雅”、“颂”等概念已经界限模糊了,混同而用的现象已经在宫廷中逐渐蔓延开来。因此,正是由于“风”、“雅”、“颂”之区别不明,故河间献王刘德才要献雅乐,以正国之“视听”,《汉书·礼乐志》云: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1]1070-1071
可以认为,西汉的太乐主领宗庙祭祀乐,后期又统领宗庙和郊祀乐等,它是《诗》之“雅”“颂”。而乐府则因为职能的扩大,将本属于各地之“风”的音乐(俗乐),用在了郊祀、皇宫之宾燕、娱乐场合,又使其音乐具有雅与俗双重品格,直到哀帝罢乐府后才有所改观。有学者认为,西汉乐府中的“郑声”虽然被用在郊祀等场合,但是当时并未被认可为“雅乐”,因此,才有河间献王“献雅乐”之举,而到了哀帝罢乐府时,这些“郑声”,才改变了身份,跻身雅乐行列。[15]
雅俗之争,是中国音乐史学界乃至大文化界长期争论的课题。萧涤非将汉代乐府音乐分为四种:“雅声、楚声、秦声、新声。雅声为雅乐系统,新声为胡乐系统之经过改进者,楚声、秦声则是中土原有的民间音乐。”[16]黄翔鹏先生曾对“雅乐”和“俗乐”进行过研究,认为:“汉魏以来,无论从音乐的管理机构上说,还是从音乐活动中作品的使用来看,雅乐和俗乐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差别。不像宋人那样把二者分得那么泾渭分明。”[10]171黄先生的研究以整个中国音乐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雅俗”之乐,但是对于汉代不同音乐机构所领音乐的性质,也没有明确的界定。然而,可以说明的是,我们不能用后世所探讨的“雅俗之辨”去套用汉代不同音乐种类的功能和性质。
此外,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的一段话,又似乎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郑卫之音与广义的雅乐的关系: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6]3073
如果“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先奏郑卫之音,结尾时则演奏雅乐,可以看作是武帝为了化解郑卫之音之入乐府、郊祀用乐产生的音乐性质上的矛盾而采取的折中作法,以使郑卫之音获得正式的名分,那么,可以认为,武帝以后的乐府在用乐比重上,是以郑卫之音(俗樂)占绝对优势地位的,这也与武帝“立乐府”的初衷相一致。
综上所述,至少在两汉时,太乐、乐府所掌管的音乐,是随着不同帝王政治思想、宗教信仰及音乐观念的变化而变迁的,同时它们在功能上又存在一定的交叉,在隶属上存在着先后的更替。严格的“雅乐”和“俗乐”之别,并不能作为性质上的合理划分,或者说,雅乐和俗乐的称谓本身并不在同一性质的评价标准上。由于“雅乐”和“俗乐”已经成为用于指代宫廷礼仪用乐和民间音乐的一对约定俗成的概念,因此,在涉及“太乐”和“乐府”音乐性质的问题上,暂可沿用“雅乐”和“俗乐”的概念,但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做到因“地”制宜,需要将礼乐的使用场合、功能及其占有的比例作为判断其性质的参照项。
(四)哀帝之“诏罢乐府”
关于哀帝“诏罢乐府”一事,是事出有因之举。
汉武帝以后,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几任帝王均善音律,在这样的语境下,用于统治阶级享乐的乐舞或女乐表演也越来越“繁荣”,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达到非减罢不可的地步了。如《汉书·张汤传》载:“知男子李游君欲献女,使乐府音监景武强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贼伤三人。又以县官事怨乐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缚束长吏子弟,斫破器物,宫中皆犇走伏匿。莽自髡钳,衣赭衣,及守令史调等皆徒跣叩头谢放,放乃止。”[1]2013可见,此类“郑声”俗乐已经极大地撼动了雅乐的地位,汉王室的统治也会被动摇,而又逢哀帝不爱好音乐,因此,其即位以后,便在公元7年正式下诏,罢去乐府。
具体的执行细则,见于《汉书·礼乐志》:
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彊、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皇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三十五人,兹邡鼓员三人,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外郊祭员十三人,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给事雅乐用四人,夜诵员五人,刚、别柎员二人,给《盛德》主调篪员二人,听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钟工、磬工、箫工员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竽工员三人,一人可罢。琴工员五人,三人可罢。柱工员二人,一人可罢。绳弦工员六人,四人可罢。郑四会员六十二人,一人给事雅乐,六十一人可罢。张瑟员八人,七人可罢。《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十九人可罢。沛吹鼓员十二人,族歌鼓员二十七人,陈吹鼓员十三人,商乐鼓员十四人,东海鼓员十六人,长乐鼓员十三人,缦乐鼓员十三人,凡鼓八,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楚四会员十七人,巴四会员十二人,铫四会员十二人,齐四会员十九人,蔡讴员三人,齐讴员六人,竽瑟钟磬员五人,皆郑声,可罢。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其七十人可罢。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奏可。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坏于王莽。1073-1074
上文已经谈到,武帝扩大了乐府的人员和职能范围、使采诗制度成为常态、将郑卫之音引入乐府,这在汉武以后大一统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中,无疑造成了后世帝王享乐观念的膨胀,促使宫廷宴饮、娱乐发生了巨大发展。虽然史籍对于此并没有过多的记载,但是从哀帝“诏罢乐府”这一事件,经过了昭、宣、元、成四朝的发展,我们即可以看出,西汉中期乐府机构的大致状况。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哀帝罢乐府的基本原则即为“去郑声,存雅乐”,凡属于“不应经法”的“郑卫之乐”皆罢,凡郊祀用乐、“古兵法武乐”皆归入“大乐”(太乐)官所掌。同时,从上述材料可知,因为黄门倡乐、散乐是引起“罢乐府”的原因之一,那么,可以认为,黄门所辖之乐人应与乐府之乐人有重合,两个机构在功能上应是互相交叉的,而哀帝所“罢”之乐,应包含郑卫之乐(“朝贺置酒”之乐)以及黄门倡乐。
根据上述存罢的举目来看,哀帝之前西汉乐府的规模可谓庞大、乐人职能可谓详细、用乐层次可谓分明。其中的乐人职责分类,约有专职鼓员、乐器演奏员、百戏员、歌手、乐器制作员等五类;从演出的礼仪场合看,则有南北郊、外郊、朝贺燕饮等;从乐人的身份来看,则有刘氏宗族乐人、地方乐人等。总之,这场罢免运动,使原来掌管郊祀、皇帝朝会等礼仪场合的“乐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使乐工由829人,减少441人吉联抗研究,实际减罢人数为451人。详见吉联抗编《秦汉音乐史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留388人。“乐府”中的地方音乐“郑卫之乐”也改变了身份,被纳入“雅乐”范畴。同时,从乐人的身份分析,可以看出,西汉乐府的音乐以晋、楚为主。同时,“太乐”的职能得以扩大,共掌郊庙等礼仪雅乐和宫廷燕饮娱乐的俗乐。
为了明晰西汉乐府的乐人及用于情况,笔者试以表1、表2形式予以说明。
通过对汉武帝“重立乐府”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一幅音乐对于政治的象征性的表达:乐府所领的乐舞,不是单纯的声音和肢体语言的集合,而是代表着帝王的政治话语的支配力。同样,哀帝罢乐府,不仅是由于郑卫之音撼动了国家礼乐体系,也同样体现了皇权与地方政治力量的博弈。正是因为武帝时对于民间郑卫之音的开放态度,导致了哀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淫侈过度,与人主争女乐”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实则体现了地方外戚权力的膨胀:宫廷的礼乐的权力象征性被泛化,敢“与人主争女乐”,则更是无视帝王权威的表现,等等。西汉末,政治上的“外戚专权”已形成规模,因此,哀帝“罢乐府”,实则是维护皇权的必然之举。
如果说哀帝“罢乐府”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那么就其结果而言,他却并未改变国家礼乐体系僵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融入太乐之后的俗乐的本质性质,只是用乐的礼仪场合又发生了改变而已,也说明了雅俗的界限变得模糊。但是,从音乐机构的职能上看,“乐府”原有的职能划归“太乐”,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后汉所实行的“并官省职”的作用,使汉代国家礼乐的管理趋于统一化,这样一来,对于后世音乐机构就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并且,对鼓吹的管理机构也有重要影响,至魏晋之际主要服务于宫廷、官员、军中仪仗中的“鼓吹”乐趋于定型,且建立了专门的“鼓吹署”予以管理。
总之,西汉自高祖制定宗庙、朝会礼乐,到武帝“重立乐府”,再到哀帝“罢乐府”,这从“立”到“破”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帝王对于礼乐制度的重视,更体现了西汉帝王对“功成作乐”理念的沿袭,是对“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强化步骤,是维护皇权“正统”性的必然之举。而音乐机构所掌管的各种音乐形式,无疑是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表征。
(五)西汉“鼓吹”的隶属机构
关于西汉“鼓吹”及其官署,凡有所论及的记载,如《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等,多见于后汉或魏晋以后史家之手,直接出于西汉的史家的记载,目前只有刘向在《说苑·善说》中所提到的“鼓吹乎不测之渊”[1]3214,而西汉司马迁作《史记》,虽言及西汉之世,但是却未有关于鼓吹之记载,不知原因何在,目前,我们只能依据上述后世文献来推测西汉“鼓吹”的存在及其型态。如《西京杂记》中有“黄门前部鼓吹”及将军鼓吹[17];如《汉书·叙传》又载:“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1]4197《汉书·韩延寿传》载延寿:“衣黄纨方领,驾四马,傅总,建幢,植羽葆,鼓车、歌车。”孟康注曰:“如今郊驾时车上鼓吹也。”[1]2907《汉书·霍光传》载昌邑王:“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内召太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1]2940等。又如《北堂书钞》卷130引《晋中兴书》曰:“汉武帝时南平百越,始置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仓梧凡七郡,立交州刺史以统之。以州边远,山越不宾,宜加威重,七郡皆假以鼓吹。”[18]《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王范《交广春秋》曰:“交州治羸县,元封五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诏书以州边远,使持节,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镇。”等等。书载之“鼓吹”是涵盖多种型态的多元复合的音乐概念,并非单指某一音乐型态。那么,据文献载,基本可以认为鼓吹之概念应产生于西汉武帝以后。至于其隶属机构,则有两种认识。
其一,学界认为西汉即有黄门令官,属少府,所配置的各种人员几乎负责皇帝近前一切大小事务。而“黄门鼓吹”则是作为“鼓吹”之一种形态,因而命名为黄门鼓吹,而且黄门中又有倡乐和诸多懂得音乐的乐官的存在,故而认为,西汉的“鼓吹”隶属于专门的“黄门乐署”,属黄门令管理。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汉代鼓吹乐机构的研究,如王运熙在《说黄门鼓吹乐》中认为,黄门鼓吹在西汉时当由“乐府”管理,至东汉则为黄门乐署管理。[19]许继起在《汉代黄门乐署考》中,也认为两汉鼓吹乐的管理机构是“黄门鼓吹乐署”,进而认为:“两汉时期黄门乐署均为独立的音乐机构,西汉倡监是西汉黄门鼓吹乐署的重要职官。”[20]22孙尚勇在《黄门鼓吹考》中,认为西汉时的鼓吹隶属于黄门,由黄门冗从仆射所掌。[21]黎国韬在《汉唐鼓吹制度沿革考》一文中,认为西汉的黄门鼓吹还不具备“乐署”的资格,故而不赞成王、许之论述,认为鼓吹应属于黄门令掌管。[22]后三人均对“黄门”的由来、职能进行了解释,探讨其与音乐的关系,进而证黄门鼓吹乐管理机构在西汉存在的可行性。
黄门中人,本是负责皇帝各种事物的内侍人员,即如亲信人员,在皇宫禁门之内活动。如颜师古在《汉书·百官公卿表》注中所言:“中黄门,奄人居禁中在黄门之内给事者也。”而蔡邕所言之“黄门鼓吹”的职能为皇帝的近前服务,即“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23],那么黄门令掌黄门鼓吹似乎也讲得通。另外,黄门中也确有诸多善音乐之人才的存在,如《汉书》所载:宣帝时有小黄令焦延寿令为京房之师,显然也是善音律的黄门官。刘向给事黄门,也善音律。元帝时还有陈惠和李微二人(据后汉服度注云:“二人皆黄门鼓吹也。”)。此外,《汉书·张放传》中提及的乐府音监景武[1]2655,在《汉书·礼乐志》中则说他富显于世:“是時,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1]1073这就更加说明了黄门与乐府乐官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重要人物李延年则更是由黄门转变为乐府官的特例。《汉书·佞幸传》载:“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悦之,及入永巷,而如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神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配二千石印,号协声律。”[1]3725-3726他先是给事狗中,后因善歌舞,善制新声,而任官比九卿、秩两千石的协律都尉,总掌郊庙歌诗配乐与宫廷之游宴之乐事。
但是,上述材料,也只能证明黄门中的官员具有掌管“鼓吹”的条件,并不能证明“黄门鼓吹”是由上述黄门各人员演奏,或一定就有专门的“黄门乐署”负责音乐的操作。
其二,再次考察西汉“乐府”的职能,则发现“鼓吹”由它管理或教习、表演,实则更具操作性。据上文对西汉武帝时乐府职能及汉哀帝罢乐府等音乐事件的考察可知,西汉乐府体现了汉代礼乐制度建设中的新的变化,是重要的转折点,它在汉武帝以后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音乐机构,它采民间郑卫之音充于宫廷,用于郊庙祭祀、朝会、飨燕以及帝王私燕等礼仪场合,使地方音乐融入国家礼仪性的用乐场合。可以说,它是西汉宫廷音乐的主要管理和实施机构。且据《汉书·张延寿传》《汉书·东方朔传》《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所载,汉代乐府令之下的音乐人员还有“音监”、“游徼”、“守令史”、“长吏子弟”、“官寺”、“乐府钟官”、“倡监”、“发乐府乐器”等人员[24]。另哀帝罢乐府乐人的行为,则又从客观上告知,西汉乐府的实际服务生涯当直至西汉末期,部分朝贺置酒场合的音乐及黄门倡乐、百戏等都属于其管理。若据蔡邕《礼乐志》所言而论,更可证明西汉部分“朝贺置酒”场合所用之音乐,当与“黄门鼓吹”有密切关系,其中“宴乐群臣”的乐舞表演即是“黄门鼓吹”乐的表演内容,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认为,西汉之鼓吹应隶属于乐府的管辖范围。
此外,在描写西汉鼓吹的文献中,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也认为鼓吹在乐府中:“至于轩岐鼓吹,汉世铙挽,虽戎丧殊事,而并总入乐府……”[25]。虽然刘勰以文学家的眼光来看汉代兴起的乐府诗,但是,他是首次在探讨文学创作的著述中论及鼓吹,而且,在他的描述中,汉代丧葬所用之挽歌,也在乐府之中。乐府不仅是一个音乐机构,自汉武帝重立乐府后,广采郑卫之歌诗,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乐府”命名的诗歌体裁,而被历代文学大家所关注、记录和仿制。那么,乐府中原有之音乐型态如“鼓吹”,自然也在其关注之列。刘勰为南朝梁人,其据汉代未远,因此,其言可信度较高。后世郭茂倩在编辑《乐府诗集》时,也同样将鼓吹和横吹之“曲辞”作为重点的辑录对象,并对鼓吹和横吹的产生和流变进行了追溯,这同样说明了汉代鼓吹作为音乐型态与乐府的关系。而且,从西汉官职设置而言,哀帝所罢之乐还有属于黄门所管理的黄门倡乐、属于西汉乐府管理的郑卫之乐。综合这些文献,则证明了西汉的鼓吹与黄门官署之间是有联系的。
另,少府所辖的黄门职官与乐府职官,共同主宫中出行卤簿、郊庙、朝会、游宴等事,因此,二者在音乐上与职能上存在交叉。但是因为黄门不同于乐府,是非专门的音乐机构,其职能主要是主“事”,而非主“乐”;而乐府因其音乐机构在人员和功能上的庞大,从音乐上具备从事专门的音乐活动的客观条件。
因此,笔者认为,西汉时,乐府与黄门对黄门鼓吹都具有一定的执掌功能,不过在具体的分工上有所不同。进一步而言,如果乐府具有执掌鼓吹的权力,那么它与黄门倡监的关系就证明了汉代依旧承袭了古代乐教的“掌而不教,教而不掌”的特点。此外,也可以说明,鼓吹被乐府和黄门所共掌的起始时间,应是武帝大兴乐府和黄门职官及其功能扩大之时期。
二、东汉音乐机构与鼓吹乐
(一)太乐
东汉时期,光武帝重整汉室大业,在职官的设置上实行“并官省职”[26]3555的政策。其太常的设置,大体依西汉末之制,有太常卿一人、丞一人。《后汉书·百官二》载: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刘昭注引卢植《礼》注云:“如大乐正”。]本注曰: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丞一人,比千石。[刘昭注引卢植《礼》注云:“如小乐正”。]本注曰:掌凡行礼及祭祀小事,总署曹事。其署曹掾史,随事为员,诸卿皆然。[29]3571-3572
又永平三年,明帝为应图谶,“改太乐为大予乐”,《东观汉记·孝明皇帝纪》载:
永平三年……秋八月诏曰:“珑矶铃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会明帝改其名,郊庙乐曰太予乐,正乐官曰太予乐官,以应图徽。[26]57
蔡邕在其《礼乐志》中,将汉代音乐分为“四品”,其“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30]159可见,大予乐的主要功能是负责郊庙乐和食举乐。
而《后汉书·百官二》也记录了大予乐令的职能:
大予乐令一人,本注曰: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刘昭注引卢植《礼》注云:“如古大胥”。]丞一人。[刘昭注引卢植《礼》注云:“如古小胥”。][29]3573
卢植为东汉顺帝时人,官至北中郎将,与郑玄一同师从马融,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其注可以作为东汉的可信史料。那么,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东汉之太常卿要比西汉之太常卿,多出部分音乐层面的职能,且与其属官——大予乐令、丞有分别,即如“大乐正”“小乐正”与“大胥”“小胥”之区别。关于“乐正”,许继起将其与太常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具有一致性,如表3所示:
而关于“大胥”与“小胥”的职能,《周礼·春官·大司乐》则解释为:
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春入学舍采,合舞;秋颁学,合声。以六乐之会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乐官,展乐器。凡祭祀之用乐者,以鼓征学士,序宫中之事。
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27]
可知,东汉的太乐——大予乐依然执掌和教习国家礼乐层面上的音乐表演,只是在功能上比西汉的太常有所增加。
(二)承华令与鼓吹乐
1.“承华令”溯源
关于东汉之乐府机构,通常认为自西汉哀帝罢乐府后,东汉的少府不设乐府职官,而承华令的设置则接替了西汉乐府的部分职能,主要是对于黄门鼓吹和百戏散乐的管理。《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条中载:“后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人。晋遂置鼓吹令、丞,属太常。元帝省太乐,并于鼓吹;哀帝又省鼓吹,而存太乐。”[28]《通典》中对“承华令”的功能也有辑录:“鼓吹署:《周礼》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后汉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属少府。晋置鼓吹令、丞,属太常。元帝省太乐并鼓吹,哀帝复省鼓吹而存太乐。”[29]
上述兩部典籍作为叙述我国典章制度演变历程的重要著作,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其引文可以看出,后出的《通典》在成书过程中,应是对《唐六典》有所抄录,他们均将承华令归入“乐官”,认为“承华令”出于东汉,属于少府,其职能是“典黄门鼓吹”,但二者此说源自何处,则不见著录。
追溯“承华令”的源头及其功能,可见“承华”最早见于西汉,归属于太仆卿管理。《汉书·百官公卿表》在: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騊駼、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菀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马挏马,初置路軨。[1]729
上述可见,太仆是职掌皇帝及皇太后之卤簿乘舆车马的,而“承华丞”也是其中一员。
而同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水衡都尉”也出现了掌管着厩马的官员: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输四丞,御羞两丞,都水三丞。禁圃两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厩官。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1]735
如淳注引《汉旧仪》云:
天子六厩,未央、承华、脑聆、骑马、格转、大厩也,马皆万匹。据此表,大仆属官以有大厩、未央、格羚、驻瀚、承华,而水衡又云六厩技巧官,是则技巧之徒供六厩者,其官别属水衡也。[1]736
“水衡都尉”职责所掌之上林苑,乃皇帝之“离宫”,主要是皇帝的祭祀、朝会、游宴娱乐等礼仪之事。那么,对比上述两则文献,说明在西汉时,承华令也归于“水衡都尉”管理,他作为主乘舆车马的令官,即需要服务于皇帝之大驾或法驾卤簿,还要服务于皇帝在上林离宫中的各种燕饮、娱乐等活动,应该说是这种“兼职”的功能,体现了西汉承华令与皇室之卤簿、燕饮娱乐所用之间的关联。我们也看到了承华令对太仆卿和水衡都尉的从属关系。
至后汉,在《后汉书·百官志》“太仆卿”属官中曾一度不见“承华令”之踪影,只有太仆卿及其属官沿袭着负责皇帝“乘舆车服”功能:“太仆,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车马。天子每出,奏驾上卤簿,用大驾则执御……车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诸车。丞一人。未央厩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及厩中诸马。长乐厩丞一人……有本注曰:“旧有六厩,皆六百石令,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御马,后或并省。又有牧师范,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但以羽林郎监领。”[1]3582由《百官志》“太仆”条“中兴省约”可知,掌管车马的太仆卿所辖的官署中,分掌不同马匹的令丞在东汉光武帝“并官省职”下历经了多次存废、并省,而“承华令”也有较大的可能被并省掉了,关于此,司马彪却并没有言明。司马彪曾做《续汉书》,南朝宋范晔之《后汉书》出后,前者便逐渐被遗弃,但是其八《志》却被吸收进了《后汉书》而得以存留。
不过,通过查阅文献,可知,早在顺帝之前,仍有承华厩令,负责乘舆马车,它出现在张衡(78-139年)的《东京赋》中:“驸承华之蒲梢,飞流苏之骚杀”,李善注曰:“承华,厩名也。言取华厩之蒲梢,以为副马也。汉官仪有承华厩。善曰:後宫蒲梢汗血之马”。[东汉]应劭撰、[清]孙星衍校集:《汉官仪》,载[清]孙星衍叙录、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张衡《东京赋》载:“驸承华之蒲梢,飞流苏之骚杀。驸,副马也。承华,厩名也。言取华厩之蒲梢,以为副马也。汉官仪有承华厩。善曰:後宫蒲梢汗血之马。流苏,五采毛杂之,以为马饰而垂之。续汉书曰:驸马赤珥流苏。挚虞决疑要注曰:凡下垂为苏。騷杀,垂貌。”([东汉]张衡:《东京赋》,载阴法鲁审定《昭明文选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蒲梢马,乃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所带回之西域汗血宝马,见《汉书西域传》:“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第3928页。张衡所言之事是皇帝“祀天郊,报地功”之九九八十一乘之大驾卤簿,因此,此处之“承华”,若依西汉之制应属太仆卿。但《后汉书》中并未记载顺帝之前的承华厩令,其明确记载的“承华厩令”设置时间和地点,是在汉安元年(142年),见《后汉书·顺帝纪》中载:“秋七月,始置承华厩。其注引《东观记》曰:‘时以远近献马众多,园厩充满,始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29]272而这里仍然没有说明其隶属太仆,还是少府。从东汉的职官建制看,它多依据西汉之制,那么,如果建立承华厩,设立了承华令,也应属于太仆卿和水衡都尉所辖,而与少府无涉,但却为何《唐六典》及《通典》中,都认为“承华令”属于少府呢?这里还需要借助东汉“水衡都尉”隶属关系的改变来予以解答。《后汉书·百官志》载:“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别主上林苑有离官燕休之处,世祖省之,并其职于少府。每立秋貙刘之日,辄暂置水衡都尉,事讫乃罢之。”[29]3600
原来,受东汉“并官省职”的影响,东汉的“水衡都尉”被并入了少府,而据前文可知,其属官应与西汉一致,仍有“承华令”,那么,承华令也就随之被并入了少府。因此,也就有了“东汉之承华属少府”之说。据此还可以进一步认为,“承华令”之属少府,应早于顺帝之“置承华厩”的时间,应该始自光武帝刘秀,至安帝时仍然存在。而顺帝时见之于《百官志》的“承华厩”应仅指其于顺帝朝的设立时间而言,所谓“秋七月,始置承华厩”,则是因为彼时远近献马众多,而又在顺帝时重新设立了“承华厩”[29]272。
2.承华令与鼓吹
上文简要梳理了承华令一职的缘起及其变迁。关于承华令与鼓吹的关系,则是东汉音乐机构变迁的重要内容。
关于“黄门鼓吹”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的文献中,为蔡邕《礼乐志》中所载明帝“四品乐”之一,即“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宾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30]159王运熙认为,四品乐中,“第三第四两品为俗乐,由黄门乐署掌管。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依据王先生的观点,汉乐四品之第三品为“黄门鼓吹”,第四品为“短箫铙歌”。而根据上文的梳理,“典黄门鼓吹”的是承华令,该如何辨别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从文献来看。
《后汉书·梁节王刘畅传》载明帝之子刘畅因言语有僭越而自我忏悔,送还所受之乐人,其书中即有关于鼓吹与少府或太仆厩马的记载:“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自选择谨劫奴脾二百人,其余所受虎责、官骑及诸工技、鼓吹、仓头、奴脾、兵弩、厩马皆上还本署。”[29]1676由此,可以看到东汉前期诸侯王也有其品级的卤簿及鼓吹。
《后汉书·安帝纪》的记载,也可以作为佐证,说明太仆、少府所掌之承华令与黄门鼓吹之间的关系:
(永初元年<107>九月):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其注引《汉官仪》曰:黄门鼓吹百四十五人。[29]208
分析这段文献,可以知道:一是安帝初年在国家政策上,也体现“并官省职”与“节俭”的政策;二是所减“黄门鼓吹”用卤簿乘舆车马,太仆所掌也同为卤簿乘舆车马,黄门鼓吹乐人在卤簿中所用之马匹需要太仆卿所管辖,二者在这一点上有重合,那么随着它们之间进一步的联系,“承华令”能够典“黄门鼓吹”则成为可能。
另据许继起研究认为:
东汉考工由少府转属太仆,少府监制乐府之器的职能由太仆令接替,这间接地反映了太仆职能的变化—具备了管理部分乐府音乐的职能,同时也反映了它在管理机制上已具备了掌管黄门之乐的条件。[23]
至此,我们为《唐六典》所记载的“后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之说找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还可以对此做以补充:后汉太仆、少府皆掌之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用于卤簿、燕饮娱乐中。但,在实际的音乐表演中,承华令在东汉并非独典黄门鼓吹,因为东汉时黄门官署不仅存在,而且在人数和数量上有较大增长,其黄门令官的职责应是主掌黄门内音乐的表演,那么所谓的黄门鼓吹也当在其职掌之下,与其他乐人共同实施宫廷音乐的表演,因此,以从属关系来看,东汉时的黄门鼓吹,应是由承华令和黄门令两官共同管理。
或可做如下解释:黄门鼓吹在汉代被用于大驾、法驾卤簿与皇帝之私燕娱乐等场合,与东汉太仆和少府共掌的“承华令”在场合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它们之间——太仆、少府和黄门鼓吹,就因有着诸多的共同性。而使得少府所领的“承华令”典黄门鼓吹具有可操作性。而“承华令”归入少府,无疑加速了与掌鼓吹的黄门署令在职务关系上的交叉。
另据《后汉书·百官志》可知,黄门内的职官分属太常、少府和大长秋[29]3606,主要有:太常卿所辖“中黄门八人,从官二人”,少府所辖“黄门侍郎”、“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黄门御史”[29]3594,大长秋所辖“中黄门冗从仆射”、“给事黄门”。他们的职责范围几乎囊括了宫廷天子身边的各项事务,他们也多由宦者充任,在政治力量上,也得到了增强。这与后汉帝王重内轻外而在职官上多使用“宦者”有关,但是其直接的影响则是汉末宦官外戚的专权和权力斗争。总之,后汉的黄门系统在继承武帝的基础上,更加健全,他们对于黄门内各种音乐的表演的执掌,联系自然就更紧密了。
综上所述,如果说西汉鼓吹管理机构承华和黄门共同管理,体现了周代乐教“掌而不教,教而不掌”的职官管理模式的证据还不够确凿的话,那么,东汉鼓吹的隶属关系,则能为这一模式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如许继起所说:“东汉黄门鼓吹员应分属少府、太仆二卿。西汉时期,由乐府、黄门二署对卤簿鼓吹乐人进行音乐上的训练;东汉则由太仆卿属官承华令、黄门署令垂取而代之。我们认为两汉音乐职官在管理职能沿袭了古代音乐教育中‘掌而不教,教而不掌的管理模式。”[23]
3.承华令的意义
首先,承华令的设置,反映了随着后汉政治统治意识的增强、权力的收缩、黄门职官的增多,以及黄门侍(宦)者势力范围的扩大,诸官之间的兼容性随之而增强了。水衡都尉和承华令在职能上的整合即是基于此。如前所述,承华令,首先是典黄门鼓吹和百戏师(《唐六典》《通典》),这从和熹邓皇后罢鱼龙曼延和在她的实际操控下减黄门鼓吹乐人即可看出。
《后汉书·安帝纪》载:“十二月甲子……罢鱼龙曼延百戏。”[29]205其后,又有罢黄门鼓吹之载:“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29]208
上述文献所载,均是后漢安帝在和熹邓皇后的操纵下,因为国家经济的困难而做出的“并官省职”之举,而安帝所减黄门鼓吹的原因,在邓皇后看来却是因为:“黄门鼓吹,曷有燕乐之志。”[26]205那么,在进一步证明了“黄门鼓吹”之用于专用于“燕”的事实。
其次,从所减之乐人的去向——入羽林士,则可以认为:一是黄门鼓吹中的特定乐人,与羽林士具备同样的护驾“素质”——如上文提到的“鼓吏”。二是黄门鼓吹之“燕乐”的力量在减弱,而用于乘舆卤簿的功能在增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于仪仗功能的凸显。鼓吹乐人一部分需在卤簿仪仗中吹奏笳、角等乐器,主要是需要乘马,因此使用承华令等掌管这一综合性的音乐类型及其乐人。而从它监管黄门鼓吹和百戏师来看,随着东汉社会经济的衰弱,才产生了汉安帝时在邓太后的影响下,减黄门鼓吹入羽林士,而羽林士正是骑乘舆驾左右的内卫。
最后,后汉见诸于天子臣下之仪仗或丧葬用鼓吹的记载的增多,正是后汉时“鼓吹”的仪仗性增强的主要体现,也可以作为“承华令”执掌鼓吹以后,鼓吹使用功能的转型。
那么,综合上述三点,对于“承华令”设置的意义,是否可以认为:这体现了东汉“鼓吹”乐内涵和功能由初期的典“黄门鼓吹”和“百戏师”时期在宫廷飨宴场合表演,逐渐向乘舆仪仗性发展?在现有文献论证下,笔者先作此假设。
东汉的音乐机构建制上,体现出“并官省职”及其“礼乐合一”的特征[5]172。这也从制度和功能上,促使东汉的音乐型态逐步向细致化发展,功能性也愈加明显。虽然没有了“乐府”的名称,但是少府总的职能没变,相应的音乐行为依然在实施,只是稍有变化,东汉整体音乐机构的变化较之西汉,在功能上有着较为明确的区分,太乐所掌之功能比西汉有所扩大,“鼓吹”在东汉也从服务于天子燕饮与王公、诸侯、将军等身份的郊庙、丧葬、出行等各种卤簿仪仗等两种型态,逐渐缩小化和单一化为专指卤簿,并且对后世鼓吹产生了较大影响。在魏晋以后鼓吹、横吹和短箫铙歌逐渐统称为“鼓吹”,即是基于乐署机构的改革及其在所属音乐功能的认定。而黄门鼓吹在朝会、宴饮置酒等场合中的功能则被分流至他官。
小 结
在两汉音乐机构的变迁上,武帝“重立乐府”,主要体现了“开放型政策”,这从其“重立乐府”所带来的在政治和音乐上的影响即可看出。但是,如武帝好大喜功,在职官的建设上设置较多,使隶属关系不够清晰,同时又因西汉时期音乐类型较多,也使得其归属及施用场合也多有混淆。东汉时,则是“紧缩型政策”,即“并官省职”,这里一方面与东汉经济的衰落有关,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原因,即吸取前代经验教训,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性和权威,这一点从西汉末哀帝时的“罢乐府”事件就已经表现出来,东汉则更为明显。但是,“并官省职”的政策,却使得礼乐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音乐类型的隶属关系趋于清晰,即如鼓吹,在功能和隶属关系上趋于单一化,这对魏晋以后鼓吹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通过对两汉音乐机构及鼓吹乐管理机构的简要分析,可以再次说明,在两汉相对“大一统”的政治、经济等局面下,统治阶级音乐机构的变迁始终围绕着礼乐制度的建设,其实质是维护皇权至高无上地位,确认刘氏政权的合理性与正统性。而在礼乐制度建设中,作为其重要音乐型态的“鼓吹”乐,作为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无疑在完成其音乐性功能的同时,也担当起了对象征和维护皇权、贵族等阶级身份和地位的功能、作为音乐产品而体现的娱乐性功能。而了解两汉音乐机构的变迁、功能的转化及鼓吹管理机构的变化等,则有助于逐步阐释两汉“鼓吹”型态、种类、功能及其历史动因。
参考文献:
[1] (东汉)班固.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唐)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8:695.
[3]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4] 刘兴珍,李永林.中华艺术通史·秦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5.
[5] 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02.
[6] (汉)司马迁.史记[M].(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63.
[7] 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5-8.
[8] 俞士玲.西汉太乐、乐府职能考[J].中华交史论丛,1980(02).
[9] 黄翔鹏.乐问[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0:170.
[10] 张永鑫.汉乐府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69-80.
[11]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3)[M].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98.
[12] 赵敏俐,等.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3-240.
[13] 王运熙.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A]/乐府诗论丛(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185.
[14]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2)[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51.
[15] 付林鹏.雅俗之争与汉代音乐机构之变迁[J].乐府学,2009(04).
[16] 蕭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7-31.
[17]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33.
[18]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2:43.
[19] 王运熙.说黄门鼓吹乐[A]/乐府诗述论(增补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25.
[20] 许继起.汉代黄门乐署考[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04).
[21] 孙尚勇.黄门鼓吹考[J].黄钟,2002(04).
[22] 黎国韬.汉唐鼓吹制度沿革考[J].音乐研究,2009(05).
[23] (东汉)刘珍,等.东观汉记校注[M].吴树平,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159.
[24] 曹贞华.西周至唐宫廷雅乐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
[25]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03.
[2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3555.
[27]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A]/十三经注疏(标点本)[G].李学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02-607.
[28]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406.
[29] (唐)杜佑撰,王文锦,校点.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