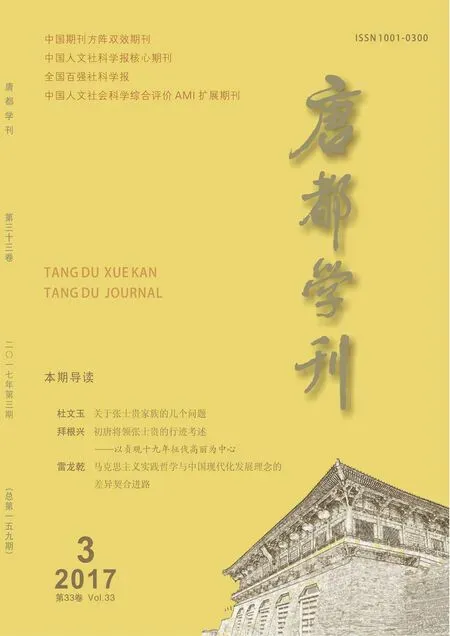天宝末年的阿倍仲麻吕及相关诗文研究
——以名号和官职为中心
靳成诚
(北京大学 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
【汉唐研究】
天宝末年的阿倍仲麻吕及相关诗文研究
——以名号和官职为中心
靳成诚
(北京大学 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
唐代是东亚各民族间交往空前频繁的时代,也是中华文化大规模对外输出,对周边民族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中日文化交流是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赴唐留学生的杰出代表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在华居留超过五十年,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成为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缩影。但关于这位中日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有诸多问题依然晦暗不清,或者不如说关于他的在华经历已经形成了一套陈陈相因的叙述话语,从而遮蔽了许多有价值的细节。以天宝末年晁衡与日本遣唐使团的事迹为研究的切入点,以这一期间的相关诗文为具体研究对象,围绕着晁衡的名号和官职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力求还原出当时中日交流中一些历来为人所忽视的因素。
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晁衡;秘书监;中日交流
一、第十二次遣唐使团的相关背景

以上就是对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团行迹的简要介绍。阿倍早年在东宫任职时,诗人储光羲曾有诗相赠,题为《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阿倍第一次请归时,友人赵骅有诗相送,题为《送晁补阙归日本国》。而在这次使团来华前后流传下来的与阿倍仲麻吕有关的赠答诗和悼亡诗还有四首,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送日本使》之外,另外三首为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李白《哭晁卿衡》。阿倍仲麻吕为答谢友人作有汉诗一首:《衔命还国作》。另外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这首诗之外,还写有一篇五百余字的骈文相赠。这些诗文便是本文的基本研究对象。
关于遣唐使,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首先,任何国家派往唐朝的使节都可以被称为遣唐使,只是目前学界习惯于用这个词专指唐朝时日本的来华使节而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中日关系在后人眼中的重要性。第二,关于遣唐使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依据评判标准的不同,有二十次、十九次、十六次、十二次等多种说法。本文称天宝十一年抵达的日本使团为第十二次遣唐使,采用的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中的说法。*参见王勇、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第3章第1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将评判标准放到最宽后的结果,也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唐代中日官方往来情况的必然要求。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只要是有当时日本政府的正式任命,且以当时唐政府的辖境为目的地的使团都应该算作是遣唐使。因此四次有任命而未成行的不该被排除在外,护送唐朝使臣回国的送唐使团和迎接滞留唐土的前任大使回国的迎入唐使团也应该被包括在内。比较有争议的是天智天皇六年(667)护送唐使司马法聪回国的使团。这次使团来回用时仅两个多月,由此推断,他们可能只达到了朝鲜半岛便返回日本。有些学者,例如王仲殊先生在《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一文中,便据此认为这次使团不能被称作“遣唐使”。[3]61但是实际上这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均已被唐军攻灭。唐朝政府在高句丽故地设立安东都护府,在百济故地设立熊津都督府,实行羁縻统治。司马法聪出使日本,便是受镇守熊津的唐军将领刘仁轨派遣,而他当时的职务,正是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4]273所以即便此次护送司马法聪归国的使团只达到了朝鲜半岛,他们所抵达的也应该是在唐朝政府管辖下的熊津都督府。终唐一代,其管辖范围始终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只要我们坚持用当时当地的观点来看待唐代疆域问题,就必须承认这次的使团也应该被称为遣唐使。
二、“阿倍仲麻吕”与“晁衡”
在二十次遣唐使中,最后成行的有十六次。随着这十六次使团,大约有五千到六千人抵达了唐境。[5]64这其中能以学识闻名中土的只有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两人。正如《续日本纪》所载:“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按:指吉备真备)晁衡二人而已。”[6]78两人之中,阿倍仲麻吕的学识造诣更显突出。他在华时间更长,能够在唐朝宫廷中担任左补阙、仪王友这样需要深厚的文字和学问功底的职务,而且还与当时的许多文人,包括李白和王维这样的大诗人都有交游。可惜对于这样一位在中日交流史上颇为重要的人物,我们对他的了解却很肤浅。虽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而且入朝为官,但是因为他品秩不高,又身为异邦人,所以中国的史书没有专门为他立传。两《唐书》里关于他的记载,都只是《东夷传》中日本条下的只言片语而已。也正因为他一生都远离故国,日本史料对他的记载也很匮乏。《续日本纪》《续日本后纪》等与阿倍生活的时代比较接近的日本史书上对他同样也是只言片语。因而后来的研究者需要到其他史料和文学作品中去寻找蛛丝马迹,才能大致勾勒出阿倍仲麻吕一生的轨迹。然而这样做有两个风险:一是这些从其他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找到的材料很零碎,去伪存真的工作非常不好做;二是一旦由这些零碎的材料形成了一套关于阿倍仲麻吕生平事迹的系统的叙述话语,就会在不断被征引的过程中获得某种权威性,其中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往往会被后来的研究者不假思索地沿袭。
在这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中,首先便是阿倍仲麻吕的名号问题。阿倍本身是日本贵族出身,入唐之后又改汉名。两种文化的交织和冲突使得他的称谓问题显得特别复杂,各种史料和文学作品中对他的称呼有十几种之多。不过这些称谓虽然芜杂,但并非没有规律可循。我们可以将其分成日本名号和中国名号两个大类来加以考查。
“阿倍仲麻吕”是现在这个人物的日本名最流行的写法。当时日本贵族对姓氏的理解与我们今天不太一样,“阿倍”并不是他的姓,而他所属氏族的名称。阿倍仲麻吕这个名字的日语发音是あべのなかまろ(abe no nakamaro),在族名阿倍(あべ)的后面要加一个表示所有格的助词の,意思相当于“阿倍家的仲麻吕”。在嵯峨天皇弘仁六年(815)编成的《新撰姓氏录》里这个氏族的名字写作“阿部朝臣”,《日本书纪》卷4孝元天皇条则写作“阿倍氏”,而在《续日本纪》中更是有“阿部氏”“阿倍氏”“安倍氏”三种写法。但这并不意味着阿部氏分化成三支,因为在日语中阿部、阿倍、安倍的读音都是あべ,它们只是用汉字来记日语固有词的读音所产生的不同写法而已。
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用来解释“麻吕”的问题。在《古今和歌集》和《小仓百人一首》等日本文献中,仲麻吕这个名字又被写作仲麿。麻吕和麿在日语中读音一样,都是对日语固有词まろ的汉字记音。まろ是日本飞鸟、奈良时代贵族男子常用的称呼之一,翻看当时的日本史书,会发现无数名叫麻吕、麿的人物。至于麿这个汉字为什么会被用来记まろ这个音,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古时从上至下的书写顺序所致。在传抄的过程中,麻吕两字连写在一起就变成了麿。而在中国的史书中,对阿倍的称呼则是朝臣仲满,满字大概是中国人用来记まろ的音时所用的汉字。
既然“阿倍”不能简单地被当成阿倍仲麻吕的姓,那么他到底姓什么呢?从两《唐书》中的记载来看,显然是把朝臣当作了他的姓。这其实是一个中日之间微妙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误会。朝臣确实是当时日本的“八色姓”之一,但是这里的姓并不等同于中国文化中的姓,而更接近于一种爵位的名称。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氏是按照血缘、职业等纽带集合起来的家族集团,而姓则是主要由大和朝廷颁赐的贵族身份的标志。这与中国秦汉之前“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的情况正好相反。日本到大化改新之前,已经出现了“臣”“连”“直”“首”“造”等姓。从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开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笼络、抑制豪族势力,又按照与天皇家族血缘的远近,制定了八色姓的制度:“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祢,四曰忌寸,五曰道师,六曰臣,七曰连,八曰稻置。”[4]306阿倍氏正是在此时和其他五十一个氏族一起,获得了朝臣之姓。[4]307所以阿倍的全名应该是阿倍朝臣仲麻吕或者阿倍朝臣仲麿。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这首诗中的“晁巨卿”应该是“晁臣卿”之误。大概是由于臣、巨两字字体相近,加之中国文人不熟悉日本文化,导致在传抄的过程中出现讹误。宋人编辑的《文苑英华》中这首诗还写作《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臣卿东归》,而到了明清时期,《唐诗品汇》和《全唐诗》里就都写成了“晁巨卿”。现在一些文章在提到阿倍仲麻吕的汉名时说“巨卿”是他的字,就更是以讹传讹了。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争议。当时日本贵族中有“朝臣”这个姓的人数量不少,天宝十一年来华使团中的副使吉备真备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吉备真备归国时也有唐朝政府授予的官职,完全可以称之为卿。日本学者杉本直治郎便认为包佶这首诗实际上应该是写给吉备真备的,其论证也自成一说,本文在此处提出以备感兴趣的学者深入研究之用。[7]201-209
当时日本贵族男子这套复杂的称谓系统,是与日本社会相对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封建文化高度发达,早已实现了姓、氏的合流。如果顶着“阿倍朝臣仲麻吕”这么个绕口的名字在中国生活,肯定会有诸多不便,于是阿倍入唐之后,便很自然地取了个中国名字,这个中国名字在中日两方的史料中都有晁衡、朝衡两种写法。据唐代史料记载:“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1]5341;“其副使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为朝衡”[8]6209。而在与阿倍仲麻吕有关的赠答、悼亡诗中,则是晁、朝混用的。有写作“晁”的,如赵骅的《送晁补阙归日本国》、李白的《哭晁卿衡》;也有写作“朝”的,如储光羲的《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日僧真人元开撰写,记载鉴真东渡事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则把他称作“安倍朝臣朝衡”。[9]83从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中日双方的材料在称呼阿倍的汉名时,“晁”和“朝”是通用的。
晁、朝两字在古籍中确实有通假的关系,但只有在读陟遥切(zhāo)的时候这个通假才成立。晁字的古文写作“鼌”,本义是一种蛙类。《说文·黽部》:“鼌,匽鼌也,读若朝。从黽从旦。”[10]680朝字的本义则是早晨,《说文·倝部》:“朝,旦也,从倝舟声。”[10]308从字音上看,鼌字属定母,在宵部;朝字属端母,也在宵部。两字属于音近通假。从字义上看,两字在通假时,朝是本字,鼌是借字,意思是早晨、早上。例如屈原《九章·哀郢》:“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鼌吾以行”;扬雄《羽猎赋》:“于是天子乃以阳鼌,始出乎玄宫”;宋代王明清《挥麈前录》卷4:“明清弱龄过庭,前言往行,探寻旧事,鼌夕剽聆”。[11]1080晁则是鼌的俗字。因为晁字作为姓氏比较常见,而且把“朝臣”一词中的朝字读破也很能自圆其说,于是鼌、朝之间的通假关系便逐渐被人忘记。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于将朝臣、晁衡、朝衡这三个词的第一个字都读成cháo。实际上根据汉字的通假关系,来源于日本八色姓的朝臣一词中的朝应该读zhāo才对。这一点从日语的读音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在日语中,朝字读あさ(asa),臣字读おみ(omi),朝臣一词的读音则是两字的连读あそみ(asomi),日语中的朝字正是早晨的意思。因为中文里朝、晁互通,晁又是一个常见的姓氏,所以中国人常把朝衡写成晁衡,接着便顺理成章地把晁当作是阿倍的汉姓了。
那么衡字又是从何而来呢?杉本直治郎在《阿倍仲麻吕传研究》中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衡字来自仲麻吕的仲。[7]180此说颇有启发意义。古时仲、中两字音、义相通,《说文·人部》说:“仲,中也”[10]367,而《说文·丨部》上对中的解释则是:“中,内也,从口丨,下上通也”[10]20。日语里仲字读なか,意思也是中间、居中。这属于日语另外一种利用汉字的手段,即用汉字的义来记日语固有词的义。而衡字的本义则是拴在牛角上,防止伤人的横木。《说文·角部》上说:“衡,牛触,横大木”[10]186。后来引申为居中,公正,不偏袒之意,例如《礼记·曲礼下》:“天子视不上于袷,不下于带;国君绥视;大夫衡视。”《荀子·致士》:“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12]1202两字在字义上确实有相通之处。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断,即阿倍仲麻吕入唐之后所改的汉名也许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姓加名的中国名字,而只是取朝臣的朝字和与仲麻吕的仲字含义相近的衡字组合在一起而已。关于“朝衡”这个汉名的来历,中日双方的史书有不同的说法。从两《唐书》的记载看,似乎是阿倍仲麻吕自己改的名;而《大日本史》中收录了一条史料说是唐朝政府赐的姓,“按《古今集钞》曰:唐朝赐姓朝,名衡,字仲,未知孰是”。[2]325唐朝赐姓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赐国姓李氏以表恩宠,也有赐外戚之姓的。也有赐他姓的,其中很多都是对异族复姓的简化,所赐之姓依然与原来的姓氏有关。例如唐太宗时出身突厥的将领阿史那忠:“忠以擒颉利功,拜左屯卫将军,妻以宗女定襄县主,赐名为忠,单称史氏”;[1]3290又比如武宗时回鹘国相爱邪勿:“丁丑,赐嗢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13]7965可见即便“朝衡”是唐朝所赐,这个汉名脱胎于其日本名这一点还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三、关于秘书监的迷思
唐人称呼阿倍仲麻吕,往往还将他的名字和官职连在一起。而关于阿倍在中国所担任过的官职,除了史书上的记载之外,最主要的依据就是相关诗文了。例如阿倍担任补阙一职的经历,唯一的依据就是赵骅的诗《送晁补阙归日本国》;阿倍担任校书郎一职的经历,唯一的依据也只有储光羲的《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综合中日史料和相关诗文,到第十二次遣唐使团归国前,阿倍仲麻吕在华担任过的官职有以下几种:左补阙、仪王友(两《唐书》、赵骅诗)、校书郎(储光羲诗)、卫尉卿(《唐大和上东征传》)、秘书监(王维诗及文)等。这些职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官员的文化修养水平要求很高。这其中又以秘书监一职后人论述最多,因为中国古时的秘书省掌管天下文物典籍,地位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化外小邦,从这个国家来的一个留学生居然能够当上掌管整个大唐图书事业的秘书监,总是一件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有些学者以此立论,称赞阿倍仲麻吕在秘书监任上为中国的图书文化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例如张白影《晁衡任唐代秘书监史迹考》说:“晁衡为唐代图书事业致力躬亲尽心尽职,做出卓越贡献。”[14]33
实际上这种说法很可疑,因为阿倍仲麻吕担任秘书监一事,与他担任其他官职的事迹一样,其史料依据十分薄弱,只有王维的那首《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及文而已。但是后世注家和研究者因为缺乏对当时官制的了解,往往也只好因袭这个证据十分薄弱的说法。例如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这是现行最好的王维集注本,《古诗文要籍叙录》中称赞他的注“不仅引征详赡,而且由于赵殿成本人对唐代礼俗、地理、官制、名物等都有很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所以往往注解得清晰准确”。[15]263可即便是赵殿成对秘书监这个职务当时究竟如何也不甚了了,他在笺注里说得很简略且有讹误:“唐书百官志,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二品上。”[16]221而《新唐书·百官志》中的原文是:“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监掌经籍图书之事。领著作局。少监为之贰。”[8]可见少监是监的副职,可是在赵殿成那里,副职的品级反倒比正职要高了。至于秘书省这个机构的具体职能,赵殿成根本没提,《新唐书》说得也比较简单。根据当代学者张国刚在其著作《唐代官制》中的解释,唐代的秘书省掌管经史子集四部图书的抄写贮藏与校勘刊布,下又设著作、太史两局。不过太史局在天宝元年(742)就已经独立出去,后来改名为司天台,成为国家的天文气象机关。[16]108-109所以在王维写作此诗及序的时候(天宝十二年),秘书省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图书档案机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秘书监之衔的阿倍仲麻吕就掌管着全中国的图书典籍,因为唐代秘书省有自己特殊的机构沿革和职能变化过程。总体来说,秘书省在整个唐代的地位都不是很高,所执掌的权责也不能与前代相比。之前历代著作局一直兼领的修史功能,在唐初就因为设立了专门的史馆而从秘书省中剥离了出去。到了天宝年间,掌管天文立法的太史局又独立了出来。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唐代各种文馆兴盛,秘书省仅剩的掌管图书典籍的职能又被许多新设的文馆所占据了。尤其是开元年间设立的集贤殿书院,“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1]1852,几乎取代了秘书省的所有工作,在阿倍仲麻吕和王维两人主要活动的开元、天宝年间,秘书省的地位可以说处在一个空前的低谷,*参见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第1、2章,齐鲁书社,2007年版。只是一个“清而不要”,甚至可以说是有名无实的机构。
正因为如此,阿倍仲麻吕秘书监的头衔到底是实衔还是虚衔都很值得怀疑。既然在王维写作《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及文的时候,唐朝的秘书省正处在一个衰败凋敝的时期。那么玄宗皇帝会不会只是把秘书监作为一个荣誉职位授予有才学之士,而并不要求受职者从事实际工作呢?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来提出这个疑问,因为历代都有将秘书监作为一个虚衔授予的做法,而且在唐代的史料中,这类例子尤其多,授予的对象也不局限于文人学士。例如唐睿宗曾经封自己的儿子李业为秘书监,“睿宗即位进封薛王,加封满一千户,拜秘书监兼右羽林大将军。”[1]3018宪宗时更曾经将这个职位授予异族政权的首领,“(元和)八年春正月乙卯朔庚午,册大言义为渤海国王,授秘书监,忽汗州都督。”[1]444渤海国远在辽东,大言义作为一国之主也不可能长期待在中国。如果这个秘书监是实衔,那么唐朝政府的这个决定岂不荒唐?不仅如此,历代还有将秘书监作为官员死后追加的荣誉职位的做法,两《唐书》中这类例子也不少。例如高宗、武后时的名臣朱敬则便享受了这一待遇,“虽天诱其衷,亦敬则启之。于是追赠秘书监,谥曰元。”[8]4221最有趣的例子莫过于王维本人,在他一生担任过的官职中,品秩最高的尚书右丞也只有正四品下。王维去世后,肃宗又追赠了他一个官职,这个官职正是从三品的秘书监,“(王)缙在凤翔,作书与别,又遗亲故书数幅,停笔而化。赠秘书监。”[8]5765再者,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第十二次遣唐使团在准备归国时,使团里许多人都有唐朝政府册封的官职,“日本国使大使特进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大伴宿祢胡麿,副使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吉备朝臣真备,卫尉卿安倍朝臣朝衡等,来至延光寺”。[9]83由此可以推断,阿倍仲麻吕之所以获得秘书监的官衔,很可能是玄宗皇帝在他即将回国之际对他多年在御前侍奉的褒奖,而且可能还有平衡在华多年的阿倍的心态的意思。因为两位副使都有两个头衔,在华为官多年的阿倍仲麻吕不能只是一个卫尉卿,这样会显得唐朝政府鄙薄外人,不重才俊。这条记载也可以进一步佐证唐代秘书监这个职务经常被当作虚衔授予,因为唐朝政府不可能同时任命两位国家图书馆馆长,再把他们都送回日本。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阿倍仲麻吕确实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也许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大,尤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个秘书监的官衔而夸大阿倍在当时唐朝的地位和作用。可惜这个说法实在流传太广,许多学者都习焉不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注,原文对使团成员官职的记载已经留下了足够的线索让人怀疑阿倍秘书监的官职到底成色几何了,但是中国学者在注释时却没有提出任何疑问。汪向荣在解释“安倍朝臣朝衡”时写道:“安倍朝臣朝衡,就是阿倍仲麻吕,当时正担任唐秘书监兼卫尉卿”;[9]84另一位注者梁明院的解释也大同小异,“(朝衡)历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秘书监兼卫尉卿。工诗文,与大诗人王维、储光羲、李白等友善”。[18]98细究起来,阿倍这个人物虽然确实与当时一些文人友善,但是所留下来的诗文大多是私人唱酬之作。唐人如果真的把阿倍仲麻吕当成日本国的代表,那么所写出的东西就是另外一番味道了。
我们可以从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这篇文章一窥当时唐人对中日往来的真实想法。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今天常将这篇骈文称作王维此诗的序,其实并不准确。今天保存下来最早的王维集宋蜀刻本中,这篇骈文收在第二卷,题为《送朝监还日本国序》;诗则收在第9卷,题为《送秘书朝监》。*参见《王摩诘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今人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也说:“此篇序与诗诸本多不相系属,分载于文及诗中,唯底本、《全唐诗》将序跋置诗前,今从之。”[19]320这样的编排容易让后世读者忽视这篇文章中一些有价值的细节,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王维的这篇骈文到底写了些什么:
舜觐群后,有苗不服;禹会诸侯,防风后至。动干戚之舞,兴斧钺之诛。乃贡九牧之金,始颁五瑞之玉。我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广运,涵育无垠。苦垂(按:一作若华)为东道之标,戴胜为西门之侯。岂甘心于笻仗,非征贡于苞茅。亦由呼耶来朝,舍于蒲陶之馆。卑弥遣使,报以蛟龙之锦。牺牲玉帛,以将厚意;服食器用,不宝远物。百神受职,五老告期。况乎戴发含齿,得不稽颡屈膝。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与天子。司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居蛮夷之邸。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弛禁。上敷文教,虚至实归。故人民杂居,往来如市。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聃,学诗于子夏。鲁借车马,孔子遂适于宗周。郑献缟衣,季札始通于上国。名成太学,官至客卿。必齐之姜,不归娶于高国;在楚犹晋,亦何独于由余。游宦三年,愿以君羹遗母;不居一国,欲其昼锦还乡。庄舄既显而思归,关羽报恩而终去。于是驰首北阙,裹足东辕,箧命赐之衣,怀敬问之诏。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方鼎彝尊,致分器于异姓之国。琅邪台上,回望龙门;碣石馆前,夐然鸟逝。鲸鱼喷浪,则万里倒回;鹢首乘云,则八风却走。扶桑若荠,郁岛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苍天而吞九域。黄雀之风动地,黑蜃之气成云。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都之故旧,谒本朝之君臣。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恢我王度,谕彼蕃臣。三寸犹在,乐毅辞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归魏而逾尊。子其行乎,余赠言者[16]219-220。
文章开头到“晁司马结发游圣”这么一大段都是在以唐朝政府代表的口气说话,不像是私人赠答之作,中间还把玄宗皇帝的尊号全称抄了一遍,更是让人觉得蹊跷。要解决这个疑惑,可以从考察王维当时所任官职入手。后代常以“王右丞”之号来称呼王维,这是取其生前所担任过的最高官职而言。根据赵殿成所做的右丞年谱,王维担任尚书右丞的职务要迟至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天宝十二年(753)时王维的职务是文部郎中。[16]555-557所谓文部,就是以前的吏部,天宝十一年三月丙午,“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其部内诸司有部字者并改”。[1]225《旧唐书·文苑传》中记载王维在服完母丧之后官拜吏部郎中,天宝末年又为给事中,天宝十二年位于这两个时间点之间,此时王维的官职应该就是吏部郎中,那么这个吏部郎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
根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解释,吏部下有四司: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其中吏部司有郎中两员,“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其告身、假使;一人掌选补流外官。”[8]1186似乎两人有所分工,一人掌管文职官员“阶品、朝集、禄赐”,颁发文官任职的凭证(告身),管理文官请假、出使等事宜;另一人掌管外地官员的铨选。但是在唐人杜佑所撰的《通典》中,对这两位官员的职能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划分,“掌选补流外官,谓之小铨,并掌文官名簿、朝集、禄赐、假使并文官告身,分判曹事。”[20]633吏部是尚书省第一部,吏部司又是吏部四司中的第一司,掌管人才选拔、调动,位置十分重要。其他三司都只有一名郎中,而吏部司设两名,很可能是因为事务繁杂,不一定这两位郎中之间就有明确的分工。不管怎样,王维既然在吏部郎中任上,就必然要参与到吏部司所负责的工作中。这条资料很重要,因为这可以解释王维为什么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这首诗之外还要写一篇五百多字的长序。阿倍仲麻吕的秘书监之职也许只是一个虚衔,但是他确实在唐朝担任过校书郎、左补阙等文职,因此当他请求随遣唐使团东返的时候,正属于吏部司郎中的职责范围之内。本来唐代就有文臣代做国书的传统,例如玄宗时名相张九龄就写过《敕新罗王金兴光书》《敕突厥登利可汗书》《敕日本国王书》等文章。晚唐时的另一位名相李德裕也写过《赐回鹘可汗书》《与黠戛斯书》等。大诗人白居易在朝中任职的时候也有《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书》《与回鹘可汗书》等作品。*此处所引唐代文臣代做国书的例子均据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而中国文人在友人出使或赴外地当官时以诗文相赠更是司空见惯,加之王维又素来以诗文见长,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王维此诗及序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好友之间的私人赠答之作,而很可能是他以吏部郎中之职,受玄宗皇帝之命,代表唐朝政府写给即将出使的官员的。所不同的是这位官员本身是个外国人,而现在正要代表自己的所任职的异国出使自己的母国,而他与王维本人也有交游。
阿倍仲麻吕这个复杂的身份使得王维写给他的这篇文章既兼有外交文书和私人赠答之作的双重性质,又在遣词造句上体现了十分矛盾和暧昧的态度。首先,从文章开头到“人民杂居,往来如市”这一段完全是在以国家和皇帝的口吻在说话。其中从“舜观群后”到“得不稽颡屈膝”这一小段恩威并举,宣扬中华上国教化远人,不宝远物的博大气度;从“海东国日本为大”到“人民杂居,往来如市”这一小段则赞扬了日本遵从教化的态度,并列举了唐朝政府因此对日本使团的格外开恩之举:“司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居蛮夷之邸”。如果《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真的只是友人之间的赠别之作,那么这一大段文字就显得很奇怪。但是只要想到这可能是一篇政府官员的受命之作,一切便豁然而解。王维此时是在代皇帝和唐朝政府发言,自然会将对话上升到国家层面。
其次,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唐朝政府和唐代文人对异邦的态度未必完全是一派祥和——即便是写给在华为官数十年的旧友,即便这位旧友来自“服圣人之训”的日本,王维还是要在文章开头提到防风氏的典故,以示对异邦的威服。但是另一方面,在谈到阿倍仲麻吕本人的时候,王维却极尽溢美之词,甚至拿孔子做比,“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聃,学诗于子夏。鲁借车马,孔丘遂适于宗周;郑献缟衣,季札始通于上国。”王维在这里对晁衡的恭维算是罕见的高规格了,其中涉及的三个历史人物:孔丘、子夏和季札,都是儒家极为推崇的圣人或君子。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颇为令人疑惑,不过如果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还是可以给出一个大致可信的解释。唐朝与外族的关系也一直是有战有和的,在有些时候,例如王维作此文的天宝中晚期,唐朝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的关系就相当紧张,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说得正是当时的事。当时唐朝政府与周边诸民族有一系列攻伐之事——天宝八年哥舒翰攻克吐蕃石堡城,但伤亡甚重;天宝十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攻南诏,大败亏输,仅以身免;天宝十年七月又发生了著名的怛罗斯战役,唐军又遭惨败。*以上事见《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以及《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而只有在东方日本这个方向,自白江口一战之后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往来。不仅如此,日本还多次遣使来朝,积极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这无疑极大地满足了在军事上逐渐陷入被动的唐朝的虚荣心。王维此文既将日本作为唐朝立威的异族,又盛赞其慕化来朝,更希望晁衡回国之后能够“恢我王度,谕彼蕃臣”。这种又打又拉的做法,可能正是玄宗皇帝和唐朝政府此时复杂心态的折射。
[1]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德川光圀.大日本史[G]∥孙锦泉,周斌,粟品孝.日本汉文史籍丛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3] 王仲殊.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J].考古,2006(6):60-65.
[4] 日本书纪[G]∥孙锦泉,周斌,粟品孝.日本汉文史籍丛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5] 王勇,中西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6] 续日本纪[G]∥孙锦泉,周斌,粟品孝.日本汉文史籍丛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7] 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研究[M].东京:育芳社,1941.
[8] 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1]冯其庸,郑安生.通假字汇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张白影.晁衡任唐代秘书监史迹考[J].高校图书馆工作,1987(3):33-37.
[15]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6]王维著,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17]张国刚.唐代官制[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
[18]真人元开著,梁明院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M].扬州:广陵书社,2010.
[19]王维著,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0]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 王银娥 朱伟东]
Study on Abeno Nakamaro During the Last Yearsof the Tianbao Period and Relevant Poetry and Prose——Focused on his Name and Title
JIN Cheng-cheng
(InstituteofComparativeLiterature,DepartmentofChinese,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Tang Dynasty witnessed frequent and unprecedented culture exchange among the Eastern Asian nations as well as the massiv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st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Japan. Abeno Nakmaro, also known by his Chinese name as Zhao Heng, the most outstanding of all Japanese students who ever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stay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50 years, making his own legendary life an epitome of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t that time. However, many questions about this key figure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remaind unclear, or it might be safe to say that a set of rigid discourse had been formed about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casting a shadow over many valuable details. This paper builds its research upon the deeds of Zhao Heng and the Japanese missions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of the Tianbao Period, and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poetry and prose as the main subjects of study, and centers around his name and title, hoping to restore some long forgotten facts of the Sino-Japanese culturel exchange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diplomatic envoys to Tang; Abeno Nakamaro/ Zhao Heng;MiShuJian; Sino-Japanese exchanges
I209
A
1001-0300(2017)03-0017-08
2016-12-26
靳成诚,男,安徽六安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