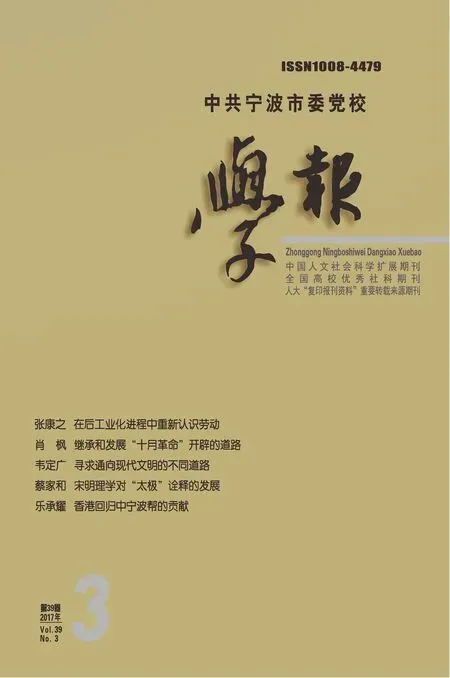社会网络结构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安徽省S县的调查
朱慧劼 姚兆余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社会网络结构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安徽省S县的调查
朱慧劼 姚兆余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基于在安徽省S县的问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和网络结构因素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收入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网络规模越大,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网络经济异质性越大,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差;网络经济地位越高,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在路径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社会网络结构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作用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社会网络结构本身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
社会网络结构;经济因素;精神健康;路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关于健康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健康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和健康社会学/医学社会学是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健康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关注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而健康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随着公众对精神健康的关注,这两个领域对精神健康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健康经济学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健康经济学对精神健康的研究基本上沿袭了健康经济学对身体健康的研究,在收入被证实对精神健康有着显著影响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因素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获得广泛验证[1~5]。对经济因素与健康的分析中较为透彻的是封进、余央央,他们指出人均收入、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跨层次效应(收入效应)对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非常重要[6]。越来越多的论证使得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获得普遍认可,健康经济学和健康社会学在健康不平等的研究领域引入了囊括收入、职业和教育程度三个因素在内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很快被证实对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但经济学研究对因素的影响路径的关注往往不及社会学研究。
健康社会学关注的是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整合[7]、社会流动[8]、生活方式[9]、教育[10]等。迪尔凯姆较早地关注到精神健康问题的重要性,他在《自杀论》中,指出了社会整合程度对自杀的影响。随着社会学领域计量统计方法的流行,社会整合程度这一空泛的概念被社会支持、社会参与等概念代替。大量研究证实了社会网络对健康的显著影响。社会网络是影响疾病认知、疾病处理、就医行为、健康追溯和疾病治疗的关键因素之一[11],社团参与数量、亲密网络规模及社会交往频度三个要素构成的结构部分社会资本对健康显示出负面的作用[12]。对社会支持的关注并没有使社会网络受到关注,反而使社会网络被纳入了社会资本的研究范畴。社会学传统中,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在个人社会关系网中的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和信任[13]。对社会资本与精神健康的研究离社会网络与精神健康的研究初衷越来越远。尽管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社会资本理论中多数将社会网络看作是资源联结的媒介,并没有关注社会网络结构本身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加之社会资本与精神健康的关系也受到了质疑和验证。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14],Norman Daniels等人则指出,收入不平等通过阻碍社会资本形成而影响健康[15]。因此,分析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路径就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已有文献表明,学术界对社会网络对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和经济因素对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的关注相对较多,但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的关注相对较为缺乏。在精神健康研究的已有研究中,对农民工、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关注相对较多,关注全体农村居民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对精神健康的测量标准有待优化。对健康的测量往往采用自评健康的方式,或采用自设问卷的方式,缺失较为细致的测量准绳,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心理学在精神健康测量方面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例如简明症状量表(Brief Symptom Inventory)、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生活质量量表(SF-36)等量表值得借鉴。第三,在社会网络对健康的研究中,社会网络被纳入社会资本概念之中,侧重于参与和支持等行为方面的因素,而对社会网络的静态结构缺少关注。海因斯等人提出:在健康研究中,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是彼此独立的元素,社会支持反映的是个人通过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构所获取的资源,而个人的社会网络则是对这种社会环境和结构的描述[16]。因此,关注社会网络结构对精神健康的研究需要从社会支持中剥离。第四,尽管社会经济地位对精神健康的影响获得广泛的例证,但是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受到质疑,例如Andrew Leigh等就指出,健康不平等的经验研究被不平等的低质量数据和家庭收入影响健康的观点的普及影响[17],反思经济因素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就显得有必要。另一方面,对内在路径进行探讨的研究也相对较为缺乏。
本研究通过在安徽省S县开展的问卷调查,试图论证经济因素和社会网络结构因素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并通过路径分析来探究经济因素、社会网络结构因素和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关注的是社会网络结构本身的功能。以往研究强调社会网络作为资源的传递渠道,对健康产生积极作用,主要还是强调资源对健康的影响,但对精神健康来说,社会网络结构因素可能会存在更为细致而微观的影响,因为精神健康比身体健康更加具体而微。
关注社会网络结构因素涉及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和测量技术为理解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网状结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测量工具[18]。随着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发展,社会网络分析的类型包括主体网(ego-centered networks),例如网络规模;整体网分析,例如位置;关系分析,例如关系内容、强度、亲切度[19]。本研究测量的社会网络结构因素有3个:网络的规模(size)、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位置(position)。
本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和网络地位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如研究假设1。这一假设在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可见一斑。林南在其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一系列命题,其中“地位强度”命题、“强关系”命题、“位置强度”命题与社会网络结构的功能有关。地位强度命题指的是初始社会位置(position)对好的社会资本的获取和使用有正面影响,反映了工具性行动的结构效应;关系强度命题指的是同质或异质性(heterogeneity)对获取和使用社会资本有正向的影响,反映的是行动效应[20]。
网络规模对精神状况的作用是一种可能的倾向:一方面,网络规模越大,农村居民就越可能获得较多有利于精神健康的资源,例如社会支持;另一方面,网络规模越大,农村居民就越可能拥有自我优越感或归属感,从而促进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因此得到假设1a。网络的异质性反映的是个体所属群体特征、行为等方面的异质性情况,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中,群体特征和行为上的异质性会促进社会行动的异质性,减少冲突,从而促进居民的精神健康,因此得到假设1b。网络地位涉及到资源的分布,但是它关注的仍然是表现为静态结构的资源。在假设居民在相同网络资源的情况下,网络地位较高,能够产生较高的社会阶层定位,也可能提供更多的有利于行动和健康的资源,也就可以认为网络地位越高,居民的精神状况就越好,因此得到假设1c。
研究假设1: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1a:网络规模越大,农村居民的精神状况就越好。
研究假设1b:网络异质性越小,农村居民的精神状况就越好。
研究假设1c:网络地位越高,农村居民的精神状况就越好。
以上假设部分获得过验证。如赵延东指出,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对精神健康起着积极作用,“核心网络”对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个人在网络中的相对地位对精神健康起着积极作用[21]。
社会网络结构在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路径是本研究试图探究的第二个问题。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借鉴,影响的中介变量主要有生活方式、社会资本和邻里社区环境等。例如Lisa F.Berkman较为全面的描述了社会网络因素对健康产生影响的机制:从社会结构性环境到社会网络,再到心理社会机制的影响路径[22]。这一研究主要考虑的是身体健康,且尚处于理论假设阶段,未得到实证研究的验证。在实证研究中,被证实为经济因素影响精神健康的中间变量有:生活方式、社会资本、邻里社区环境等。
回到社会网络结构并不是完全撇开社会支持或者资源,而是将社会网络结构的多种可能纳入到考察中来。社会网络结构受到社会行动和经济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在多数研究中忽视了这一点。考虑到经济因素对网络结构本身的影响,研究提出假设认为社会网络结构是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这种影响路径中包括两种影响:既包括经济因素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也包括经济因素影响到了网络结构因素的作用而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社会网络结构因素既与所传递资源有关,其本身也对精神健康发生作用,即为研究假设2。
研究假设2:社会网络结构因素既对精神健康单独产生影响,又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对精神健康发生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使用的数据是2015年在安徽省 S县的问卷调查。S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抽样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式,首先,根据县政府公布的财政数据,分别选取3个不同发展水平的乡镇;其次在选取的乡镇中列出所有村庄编号排序,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在3个乡镇各抽取1个村;再次在选取样本村的村委会开列的门牌号编号,按照等距抽样的方式选取家户的门牌号,按照门牌号进入家户进行问卷调查;最后在进入家户时按照生日离调查日期最近的家庭成员进行调查。在每个村发放问卷为120份,共计360份问卷,以现场填答或以结构式访谈的形式回收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34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4%。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二)指标测量与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精神健康。心理学领域对精神健康的测量有较好的成果,所以研究对精神健康的测量借鉴了简明症状量表[23],该量表在国内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例如何雪松等人曾用于测量移民的精神健康。该量表包括心理问题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24],共有53个题目。由于该量表过于冗长,存在影响调查效度的可能,而且针对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农村居民,BSI-53显然题量过大。Derogatis将其简化为3个方面内容:心理问题躯体化、焦虑和抑郁,各对应6个题目[25]。在实际调查中,考虑到部分问题的敏感性,笔者对BSI-18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例如将“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修改为“想换个地方生活”。调查将量表对应项的分值加总分别获得心理问题躯体化指数、焦虑指数和抑郁指数,并通过加总获得精神健康指数GSI,GSI指数越高,精神健康状况越差。经过对调查数据的信度分析发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42,表明量表的信度较高。
2.自变量
本研究核心的自变量是社会网络。本土社会网络的测量受到较多的争议,主要的测量媒介有拜年网[26~27]、讨论网[28]和最大宴席网[29],有的学者在研究中甚至采用了多种测量方法,例如邹宇春和敖丹曾用拜年网、讨论网和饭局网比较自雇者与受雇者的社会资本差异[30]。在这些研究中,社会网络的测量手段的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笔者认为这些测量手段只适合部分对象,从已有研究来看,饭局网对城市在职人员的社会网络有较好的适用性,拜年网对城乡居民有较好的适用性。考虑到本研究测量的是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本研究采用拜年网来进行测量,正如王卫东指出的,拜年网是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测量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本的有效(可能是最有效的)工具。
常见的社会网络的测量方法有两种:定名法和定位法。定名法通过设定特定情境询问调查对象想起、试图求助的和讨论的人的名字,这组成了调查对象的重要关系网络,然后按照名字依次询问重要关系网络中的人的经济社会特征,从而来测量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定位法则通过测量个体社会网络中的个人的职业声望来衡量个体的社会网络,这一方法有赖于统一的职业声望测量手段,这也是定位法被诟病的地方。这两种方法的测量手段较为繁复,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测量上依然存在困难。研究采用拜年网这一媒介来测量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通过询问去年带礼物到家中拜年的人数、拜年的亲戚数量、拜年的朋友数量来测量网络的基本结构(规模),通过询问拜年网中经济收入高和收入水平差不多的人数以及声望高和声望差不多的人数,来获得网络的异质性、网络地位和网络存量。
在实际的测量中,网络规模(size)是去年带礼物到家中拜年人数n。网络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分为经济异质性He、声望异质性Hr。其中,经济收入高的拜年人数为n1,经济收入相当的拜年人数为n2,经济收入较低的拜年人数为n3,声望高的拜年人数为n4,声望相当的拜年人数为n5,声望较低的拜年人数为n6。

网络地位(stratum)是用于测量不同网络结构中的农村居民在网络中的地位。研究将网络地位分为网络经济地位Se和网络声望地位Sr。网络经济地位是经济水平较低的人数除以收入水平较高和收入水平相当的人数的乘积,在网络经济地位指数中,经济水平较低的人数越多,其网络经济地位就越高,经济水平较高的人越多,其网络经济地位就越低,经济水平相当的人数比例越高,其网络经济地位就越低。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经济因素。性别转换为男性;文化程度由于调查时未考虑到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过多(占到58.2%),因此转换成一个变量处理,即小学及以下虚拟变量。职业由于过于分散,将其整合为六类,即务农者、本地务工者、外出务工者、公共服务人员、无业或退休和其他,本地务工者包括乡镇企业管理者、乡镇企业职工、私营企业主、农村私营企业工人和农村个体户,公共服务人员包括农村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农技推广人员等)和村干部。经济因素采用去年家庭支出来进行测量,分析中对家庭支出以对数形式呈现。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收集到的数据通过社会统计软件SPSS20.0进行分析。研究中因变量为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精神健康采用量表的形式得到总体精神健康状况(GSI),为定距层次变量,因此采用一般线性回归。一般线性回归的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精神健康状况,Xi为第i个自变量,i为与自变量Xi对应的回归系数,i表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Xi,Y就增加一个单位的i,为截距,为回归误差。一般线性回归通常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OLS估计),OLS估计的基本思路:是每个样本点与回归线上的对应点在垂直方向上偏差距离的总和最小[31]。
为了辨别经济因素在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路径之间的影响,研究采用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的分析方式。路径分析是多因分析和详析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用以分析因果网变量间复杂关系的分析方法[32]。在路径分析中,一个内生变量对应一个回归方程,每个回归方程都会有一个确定系数,它表示相应内生变量的方差中能够被该方程所揭示的比例,而1-R2就表示剩余的部分[33]。那么,对应于所有内生变量的残差,对于有P个内生变量的模型,能够计算出这样一个指数:

该指数表示由模型能够解释的广义方差占总广义方差的比例。根据该测量值,可以计算出一个统计量W:

其中n为样本量,d为简化模型中所删除的路径数目,通过这一统计量可以对多个模型进行比较。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描述分析
表2为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精神健康自评为3.35,没有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精神健康非常差。总体来说农村居民自评精神健康状况良好。BSI-18量表的结果显示,精神健康指数GSI为11.99,精神健康状况良好,比精神健康自评能够更好地呈现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

表2 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
按照BSI-18量表得到的三个精神健康指数分别为:焦虑指数为3.80,抑郁指数为3.07,心理问题躯体化指数为5.12,可以看到焦虑、抑郁和心理问题躯体化症状并不明显,抑郁症状最轻,其次为焦虑症状,心理问题躯体化症状最为明显。可能是这一部分问题涉及到的是否感到浑身疼痛等问题与身体健康状况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心理问题躯体化症状表现得较为明显。
(二)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一般线性回归
为了更好地探究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建立了3个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模型1只纳入了性别、年龄、职业等控制变量,模型2只纳入了社会网络特征变量,模型3综合了模型1和模型2的变量。从模型拟合情况来看,模型1的决定系数(Adjusted R Square)为0.26,模型拟合情况一般,模型2的决定系数是0.25,模型拟合情况也较为一般,综合引入模型1和模型2自变量的模型3决定系数增加到了0.35,有较好的解释力。
从模型1可以看到,小学及以下、务农者、外出务工者、公共服务人员等虚拟变量和家庭支出对数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有显著的影响,表明文化程度、职业和经济因素都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居民的GSI指数越高,精神健康状况较差;经济收入越高,农村居民的GSI指数越低,精神健康状况就越好;显著的职业虚拟变量中,务农者的精神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外出务工人员和公共管理或技术人员的精神健康状况相对较好。可以看到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都是正向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都有积极作用,而农业劳动者的精神健康状况普遍偏低,公共管理或技术人员以及外出务工者的精神健康状况相对要好,表明就不同职业的农村居民来看,农业劳动者的精神健康状况相对较低,被誉为农村社区的“典型的精英群体”的外出务工者,精神健康状况要比农业劳动者的精神健康状况要好;公共服务人员多是乡村教师、医生和村干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都相对要高,所以精神健康状况相对要高。从社会人口特征变量进入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中看到,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影响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状况的关键因素还是社会经济地位,研究假设1获得验证。
模型2中仅放入了社会网络结构因素,从一般线性回归的结果来看,网络规模、经济异质性、关系异质性和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都有显著影响,声望异质性、网络声望地位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没有显著影响。网络规模越大,农村居民的GSI指数越低,精神健康越好;关系异质性和经济异质性越高,农村居民的GSI指数越高,精神健康越差;网络经济地位越高,农村居民的GSI指数越低,精神健康越好。可以看到,网络规模、经济异质性和网络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
模型3中结合了模型1和模型2的自变量,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模型1中的个体特征变量的显著情况没有发生差异,模型2中社会网络结构因素中网络规模、经济异质性和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仍然有显著影响,关系异质性、声望异质性、网络声望地位等变量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没有显著影响。

表3 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状况的OLS回归
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OLS回归发现,影响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个体因素有文化程度、职业和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和收入三个变量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提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三个部分内容,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影响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因素有网络规模、经济异质性和经济地位,假设1获得验证。经济异质性和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显著影响,表明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有着显著的影响。
(三)社会网络、经济因素和精神健康的路径分析
研究建立了4个方程来探究经济因素在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影响的路径中的影响。方程中变量的选取参照了 OLS回归分析结果。分析结果显示,四个模型的决定系数均在0.2左右,因果结构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无需添加新的变量。

第一个方程中网络规模、经济异质性和经济地位三个显著的社会网络结构因素和家庭支出对数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回归方程。结果发现,家庭支出对数(sig.=0.000)、网络规模(sig.=0.000)、经济异质性(sig.=0.045)和经济地位(sig.=0.007)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经济因素和社会网络结构因素对精神健康的独立影响显著。

图1 路径分析图
后三个方程分别是家庭支出对数对网络规模、经济异质性和经济地位的回归方程,以家庭支出对数为自变量,网络规模、经济异质性和经济地位分别为因变量。分析结果发现,网络规模、经济异质性和经济地位中,家庭支出对数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395(sig.=0.000)、-0.311(sig.=0.000)、-0.241(sig.=0.000)。
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而社会网络结构因素是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的中介变量,它是经济因素影响下精神健康不平等的表现之一。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在S县的调查,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良好,抑郁和焦虑症状并不明显,但心理问题躯体化相对较为突出。心理问题躯体化指数相对较高可能与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就医行为相关,农村居民(或早年)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慢性病多发,但其就医行为往往会延误就医时机,从而导致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受到慢性病的困扰。这一现象表明,农村居民的精神状况在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一定程度上受到身体健康和就医行为的影响。
第二,社会网络结构因素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与赵延东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收入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网络规模越大,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网络经济异质性越大,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差;网络经济地位越高,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网络规模和网络地位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但异质性不利于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异质性与精神健康的反向关系可以看作是农村居民对“陌生人社会”[34]的反抗。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农村居民阶层分化的不断深入,不仅仅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异质性的增强,更加会使得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结构的异质性有所增强,从而使得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三,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社会网络结构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既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社会网络结构本身又对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更多的是基于学理上的探讨,它区分了社会网络结构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和经济因素影响下作为中介变量的社会网络结构因素对精神健康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指出了社会网络结构在健康影响中的多重角色,它既作为资源传递的渠道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指示物,又在心理-社会的微观机制上有加强社会交往和增强归属感的可能性。这一研究结论对同类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那些被忽略的微观结构因素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并不排斥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到分析和研究中来。
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缺陷。调查仅选取了安徽省S县,样本量也受到研究经费制约,研究结论的推广范围受到质疑。因此,大范围的抽样调查能够为本研究相关议题提供更有力的证据。另外,本研究只考虑了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精神健康的影响,要明晰经济因素对精神健康的影响路径,需要不断纳入多元的变量,从而更好地审视社会因素在精神健康不平等中的影响路径。
[1]John E Ataguba et al.Socioeconomic-related health inequality in South Africa:evidence from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s[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2011(10).
[2]Oanh L.Meyer,et al.Determinants of Mental Health and Self-Rated Health:A Model o f Socioeconomic Status,Neighborhood Safety and Physical Activ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4,104(9).
[3]解垩.与收入相关的健康及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研究[J].经济研究,2009(2).
[4]齐良书,李子奈.与收入相关的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流动性[J].经济研究,2011(9).
[5]马超,顾海,韩建宇.我国健康服务利用的机会不平等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4(2).
[6]封进,余央央.中国农村的收入差距与健康[J].经济研究,2007(1).
[7]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8]王甫勤.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J].社会学研究,2011(2).
[9]王甫勤.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J].社会,2012(2).
[10]聂伟,风笑天.教育有助于改善身心健康吗?——基于江苏省的数据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5(1).
[11]Pescosolido,Bernice A.Illness Careers and Network Ties:A Conceptual Model of Utilization and Compliance[J].Advances in Medical Sociology,1991(2).
[12]胡康.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13]Coleman,J.D.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M].Cambridge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4]EderstadtN.Health and theIncome Inequality Hypothesis:A Doctrine in Search of Data[M].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2004.
[15]Norman Daniels,Bruce Kennedy,Kawachi Ichiro.Is Inequality Bad for our health?[M].Boston:Beacon Press,2000.
[16]Haines V.&J Hurlbert.Network Range and Health[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92,33(3).
[17]Andrew Leigh,Christopher Jencks,Timothy M.Smeeding. Health and Economic Inequality[A].W.Salverda,B. Nolan&T.Smeeding.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Inequality[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张文宏.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特征——兼论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的联系和区别[J].江海学刊,2007(5).
[19]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0]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1]赵延东.社会网络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J].社会,2008(5).
[22]Berkman L F.Social support,social networks,social cohesion and health[J].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2000,31(2).
[23]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锤.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0(1).
[24]Derogatis,Melisaratos.The Brief Symptom Inventory: An introductory report[J].Psychological Medicine,1983, 13(3).
[25]Derogatis,L.R.BSI Brief Symptom Inventory:Administration,Scoring,and Procedure Manual(4th Ed.) [M].Minneapolis,MN:National Computer Systems, 1993.
[26]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3).
[27]王卫东.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J].社会,2009(3).
[28]梁玉成.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J].社会学研究,2010(5).
[29]陈云松,边燕杰.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J].社会,2015(1).
[30]邹宇春,敖丹.自雇者与受雇者的社会资本差异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5).
[31]Caroline Ashley,Diana Carney.Sustainable Livelihoods:Lessons from early experience[M].London: Russell Press Ltd.,Nottingham.1999.
[32]李沛良.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3]张文彤.SP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4]风笑天,林南.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路 曼
C912.64
A
1008-4479(2017)03-0075-09
2016-04-05
朱慧劼(1991-),男,安徽宿松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姚兆余(1965-),男,安徽庐江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