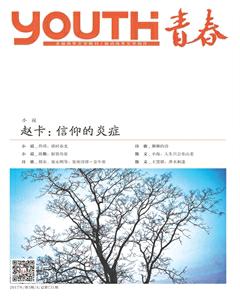萍水相逢
王慧骐
之一
那天去中医院取药,坐了他的车。三句话一聊,便认了老乡。他是江都昌松人,我年轻时在江都工作过几年,那个乡我去过,不大,倒有些历史。乡名是为纪念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两位烈士而取的。
他说自己开车有年头了,早先在扬州替一个私人老板开车,钱拿得不少,但人没自由,一天到晚跟着,老板谈生意打麻将泡澡堂子,他都得鞍前马后地一边候着。干了几年拜拜了。后来到江都街上租了个门面,经销红木家具,从苏州的蠡口进货来卖,那几年这生意好做,赚了不少。还在县城买了房。
有一个儿子在南京读大专,毕业后留了下来,在一家蛮大的公司干水暖工程。媳妇是江都的。后来有了孙子,就留在江都让他们老两口带。如今孙子七岁了,上小学了,被爹妈带南京来了。孙子打小便同他腻着的,一下子不见了,不习惯,就跟着也来了。在水西门那儿买了一处二手房,大头他来出,小头让儿子媳妇办了按揭慢慢还。到了南京不能总闲着,过了年也才五十六,身子骨还硬朗着哩。得,老本行再捡起来,开车吧,弄个二驾干干。但他并不匆忙上阵,先把地形熟悉起来。找了部电动车,大街小巷地转,转了有个把月,主要区域的什么街什么路七不离八了,这才上手。八九个月跑下来,俨然一个南京通了。问他一個月能苦多少钱,他笑笑:不多。我干的白班,早6点到晚6点,给一驾每天缴一百一,再加加气什么的,一天落个两百,没啥问题。中午这一顿在外面打打游击,晚上回到儿子那儿,喝杯小酒。主要是天天能看到孙子,这比什么都强。
说江都的那个红木家具店暂时还没关门,老伴在那盯着,生意不咋的。昌松乡下还有几间老屋呢,可惜没人,空关着。往深里想,人再能折腾,还不就是睡一张铺嘛。
他车技好,说这些事儿,全没耽误他拉活。我也是光顾着听了,竟忘了问其尊姓。不过那张脸倒还记得,活络里透着几分乡人的精明。
之二
在天泉小镇有些许凉风的初秋的一个傍晚,我们在一家名为“小鱼村”的饭店门口,拉了张店里的桌子,放露天里点菜,吃饭。门前站了好几个村中老少,他们已早早地吃了晚饭,聚拢在一块吹吹风说说闲话。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汉子,听说我们从南京来,便饶显热情地凑上来唠一点家常。
说他已故的父亲早年也在南京干的,单位在中央门一带,那时候不叫园林局,叫苗种场,负责城市绿化的。不过他爸不栽树,是给那些栽树和修剪苗木的工人专业磨剪刀。还有一手不赖的铁匠手艺,能打制各种大号铁剪,裁剪树枝的那种。做这份营生有十好几年,后来因故回去了,在村里支了爿铁铺,制作用以打鸟的火枪。枪管里装上铁砂,几十米内可命中目标。那时候这边山林多,常有竹鼠、野獾、獐子、黄鼠狼出没,大大小小的鸟类就更多了,不少人靠捕杀这些猎物出售为生,因此他们家父子几个凭这门手艺能有碗饭吃。后来不行了,生产火枪被明令禁止。没几年,老爷子也死了。兄弟几个里算他活劲些,去了村上的排灌站,农忙的时候给各家田块送水,平时要对水渠水坝做些维护。近几年一家大型的酒店集团来这儿开发一个面对都市市场的养老项目,当地政府也参与了,把他们住的那几个村子全都征用了土地,而后在这里建了座小镇,统一建房安置他们这些移民。
说现在的小日子过得还行,属羊的,六十一足岁了,在农村算年纪不小了,但还没退,有一份活在干着——在一处隶属于养老项目的水处理厂做门卫,每月还有靠两千的钱拿着。日常也没啥钱好用,四季的蔬菜自家地里长着;逢到3、6、9号镇上有集好赶,要买点荤的,村口坐一块钱的中巴就到了,挺方便。两儿一女都已成了家,兜里有几文也都花在了孙辈身上。
说话间,天色渐渐暗下来,他摁亮手机照明,又朝我们吃饭的小桌指指:不跟你们韶了,菜都凉了,我去那头转转,活动两下筋骨。
这老汉个子不高,嗓门不低,我问他怎么称呼,他脆脆地撂一句:百家姓里排第一,免贵姓赵。
之三
在长寿之乡如皋小住了几日,宾馆附近有一处“骐记小炒”,是做快餐的。见店名与自己的名字相同,不由生出几分亲切,腿便迈了进去。店堂里坐了不少人,供应的品种有盖浇饭,面点,和各式小炒。特点是价格低廉,二三十块解决问题。我带了瓶小劲酒,慢悠悠呷着。一阵的热闹过去后,老板娘方才有闲空坐下。是那种好客且健谈的类型,没费太大的劲,其来龙去脉也就知晓一二了。
她姓薛,原在一家化工企业做仓库保管,嫌工资低,遂主动请缨去了生产一线。因为企业间合作的关系,早几年她还去过内蒙、新疆,在那儿一呆就是半年。技术上有两把刷子,给人家当师傅那是绰绰有余。重要的是去边远地区还可另拿一笔外勤补贴。她说干化工对身体总有些妨碍,五十岁一到赶紧办了退休。下来后却又觉着在家闷得慌,便找到这家店里打起工来。先前的老板是外地的,干了几年走人了,她就把这个店盘了下来。想想大厨也不用请了,家里就有现成的,是她老公。年轻时就爱捣鼓饭菜,烹蒸烧炒,还都像那么回事。老公姓仲,和她同年,也才五十五,还在一家企业上着班哩。但工龄长了老资格,岗位也不是顶重要,所以每天只要上、下午去点个卯,其他时间便可自由支配。于是一大早去单位露个面,而后便自驾车去了菜场,把一天里小饭店要用的菜肴就全都买了。中午和晚上,这里热气腾腾的锅灶上他便大显身手了。
两人有个儿子,也三十出头了,在当地一家4S店搞汽车销售;媳妇是电影院的售票员,工作蛮轻松。小孙子已七岁了,放了学跟着爸爸来店里玩。爸爸替奶奶当下手,小家伙嗤溜嗤溜地店堂里转,时不时还见他帮爸爸端两只客人吃剩的盘子哩。
这一对勤快的夫妻忙了这多年,在县城置下了三处房产。有两处对外出租,最大的一套房留给自家住。老板娘言语里溢满自豪:我们是四世同堂,我的婆婆七十六了,也跟我们一块住。每天干活累,早上起不来,总是婆婆来叫我;待我洗漱后再去把儿媳妇唤醒。一家子有老有小,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这小店我连着去了两回,发现老板娘不光生意做得井井有条,还待客周到,人善心好。有两位操北方口音的老人进店问她有无粥卖,她先回说没有,后又追出去叫住老人,让他们进来坐着,自个儿跑出街去买了玉米糁,不多大功夫两碗热粥捧上了桌。
之四
在“骐记小炒”用餐时,还遇上了一个长相清秀的小伙子。听说他家在无锡的东亭镇,太太心下一喜,过后说很想找这位小老乡聊聊。打听到他就在不远处开一家洋快餐,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寻了过去。
小伙子其实不是无锡人,家在安徽六安,父母亲都是农民。他生于1980年,姓刘名辉,说朋友们都叫他阿辉。有一兄一妹,他是老二。由于家境贫寒,他17岁读完高一就辍学了,跟着乡亲去上海崇明打工。建筑工地上给人搬砖拎灰桶做小工,还在一家木板厂干了两年,这以后又漂泊到了东亭,在一个机械企业干装配。江南的这处富庶小镇成了阿辉生命中的福地——来这儿不久他便认识了来自河南固始的打工女孩小燕子,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且有了个男孩。小两口在东亭镇上租了房子,边上班边养育后代。本想把孩子送回安徽老家让父母带的,殊料家中遭遇了天大的灾难:先是不到50岁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仅仅隔了两年,生身母亲又被另一起车祸夺去了生命。那时候阿辉还才25岁不到。
接下来的这十多年,没了爹妈的阿辉自我成长的速度无形中得到了加快。在南京浦口打拼的哥哥通过努力成为一名婚庆主持人,好学的阿辉后来也入了这一行。这让他慢慢有了点财富,脑子也越来越快地跟上了时代的节拍。他在东亭镇办了十年期的按揭,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同时还在隔江的如皋、南通等地,以小额投资的方式加盟了几处快餐连锁店。
他坐阵其中的一家,参与店内的经营管理,因此较多的时间人就待在如皋。十三岁的儿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则由妻子领着在东亭生活。好在两地相隔不远,也就两小时的车程便可让他坐拥妻儿。作为兼职婚庆主持人,他和多家公司建有一种松散型合作关系,平时好几个微信群里都有互动,有合适的活儿他便西装笔挺地出现在大江南北的婚礼现场。
之五
无锡上马墩,是一处颇具人气的老城区。这对小两口在菜场门前租了间约十多平米的门面房,专做熏鱼生意。他们来自苏北宿迁乡间,小伙子二十九岁,女的小他两岁。说来这儿快三年了,之前是在上海做的,好几个亲戚都在那干这行。上海人爱吃熏鱼,甜甜酥酥口感好,又富营养。无锡人口味与上海接近,所以他们这小店一开张便一炮打响,有时忙得连抽支烟的功夫都没有。门面房选在菜场门口,那是小伙子的精明。活鱼不用自己养了,人家的池子替你养着,空气泵每天侍候着,那鱼自然活劲,新鲜。这边有人要买了,几个箭步进去便捉了活鱼来,活蹦乱跳的,现杀现弄。剖肚刮鳞分段,再切成薄块,刺和肉不能分家。小伙子刀功不错,案板前常围了人看他手艺。女的则负责站油锅,火候也把握得恰当,一把带网的大勺在她手上使得起落有致。客家倘要稍嫩些的,早点起锅便是。
不只熏青魚段,还炸小鱼。我买来吃过,连头带刺全炸酥了,咬咬全吞了。下酒是只好菜。还以为这小鱼不好打理,女的说容易的,手一挤细细的鱼肠就出来了,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做好的熏鱼盛放在大小不同的塑料碗里,论碗卖,中碗15元,大碗20元,价格不算贵。
中午、晚上饭点前后,小伙子还腾出手来,做那种带汤料的酸菜鱼卖。20元一盆,比饭店便宜。菜场里卖菜的,周边药房、超市的售货员都来买去吃。他们没空送,要吃的自己来。丢五块钱押金盆子拿走,还盆时将押金取回。一个中午有几十盆生意好做。
问了小伙子,说已有了两个孩子,大的女孩快5岁了,小的男孩已2岁半。没在身边,是乡间的爷爷奶奶带着哩。他们在附近租了一处房,一天十多个小时忙下来,回到屋里已是人困马乏,洗洗弄弄要紧睡觉了。
之六
在沙家浜穿行于芦苇荡的一条竹筏船上,认识了五十七岁头发有点花白的老严。他是景区为游客提供水上服务的若干船工中的一个。这天是周日,他特别忙,刚从另一处工作现场匆匆赶来——沙家浜景区为吸引游客,近年开发了一个大型实景剧,叫《芦荡烽火》,把京剧《沙家浜》的剧情作了提炼。专门辟出一块很大的水域,并搭起供演员表演的舞台,对面便是可容纳几百人观看的半露天剧场。郭建光、阿庆嫂、胡司令等一众人物悉数出场,文、武戏全有,文则让一些著名唱段饱你耳福,武则船艇枪炮,火光四起,水柱冲天,好不热闹。
老严在这场实景剧中也是开船的,是艘挂了膏药旗的鬼子的船,在水上追逐,对速度有很高的要求。戏演了四十分钟,老严忙乎了一头热汗。那边一结束,赶紧蹬了辆车,赶回这边的码头。好在这里的游艇不用人工撑篙或摇橹了,发动机电闸一推,船就嘟嘟跑了起来。我给他递了支烟,“短平快”地问了一些情况。老严干这活快八年了,算是景区的正式工。却非多劳多得,而是拿基本工资,一个月也就两千上下。这几年红色旅游升温,来景区的客人猛增,节假日、星期天常常会被安排加班。加班日的工资是翻双的,可以拿到一百六,但人也忙到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早先是在外东跑西颠,跟着工程队在江南一带造桥,但那份活累人,年纪慢慢大了,腰吃不消了,快五十岁那年便回转来。正好景区要招聘一批船工,他就应聘来了。
老严家在横泾乡下,弄船使橹那是从小就练就的童子功,只不过如今重新捡起罢了。有一个儿子也在景区工作,三十五了,之前干过导游,现在坐办公室了。“他不比我,我没什么文化,他是大专毕业,新东西学得快,所以钱也拿得比我多。”谈起儿子老严有几分掩饰不住的骄傲。又说到孙儿孙女都有了,大的快十岁了。那一刻清楚地看到他两边眼角溢出的笑。
之七
到阳澄湖边看望一位老友,被安排在临湖的一处宾馆住下。透过落地窗见一八角亭建在水中,亭子里有两位神情专注的钓者。阳光下见他们手中的鱼竿不时地高高提起,那上钩的鱼儿扑闪扑闪地被他们捉放到脚边的水箱里。于是按捺不住地出房,跑过一段不长的小桥,上前和他们搭讪。
两位都已退了休,原在上海一家机电公司,是玩得好的同事。周五上午9点多,开车从家里出发,两小时车程便到了这儿。这一片水面的主人和他们是朋友,来这儿垂钓不向他们收钱,只要钓得着,无论大小拿走就是。一问才知所有的渔具都是品牌货,连衣服、帽子一身行头皆正规军模样。此处来过几回了,熟门熟路,中午一到车停妥,两个先至湖边把窝子打好,而后抓紧去旁边的饭店把肚子填上。人吃饱了,精神头来了,鱼竿儿上上下下也就不乱章法了。鱼饵是专业商店配好的用几种粉揉捏而成的粘粘的团儿,粉红色的,挺诱人。可水中敏感的鱼儿不是回回咬钩的,十次有八次是把你钩上的那点饵食吞了,自己却不上来。因此可见二位频繁地把钩子拎上来,重沾饵食后再抛入水中。
不过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们的战绩也颇让人眼热的了。小鲫鱼小鲹条已有了三四十条,还有一条近三斤的鲤鱼被装在另一只篓里,复又小心翼翼放置湖中的活水里养着。小鲹条也就手指粗细,出水不久便没了声息。他们拎到饭店请厨师加工,用油烹炸,撒些椒盐,晚上便用它下酒。这哥俩倒也并不贪杯,一瓶绍兴女儿红两人平分。喝完了趁着月色,还想再钓一会。却不料夜风起了,水下估计也有几分凉意了,鱼往深水里去了,再香的饵食不来问津了。于是他们只好鸣锣收兵,说歇着吧,明儿一早再来。
人家钓鱼不好老打岔,一些事儿也不便多问。只晓得这哥俩是同年同月生的,虚岁六十三了。一个祖籍南通,另一位生在南京溧水,打小跟父亲去了上海。次日下午三点他们便打道回府了,几条大一点的鱼美滋滋带回去与家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