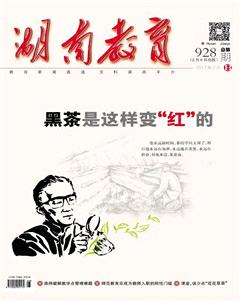时光里的经典
原野
多年前,《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成功地把茨威格挡在我喜爱作家的黄线外,而后,他挤在尘埃掩埋的阴暗角落,像冷宫里的嫔妃,经年来沉默如铁。好在老天仁慈,三五好友轮番向我推荐《昨日的世界》。于是,年初的某个日子,茨威格走出旧书橱,抖抖身上终年的积尘,在经历长久的沉默岁月后,一开口就让我如闻天籁,又如遭雷击:
“一个人在孩提时代,从时代的空气中吸收到自己血液中去的东西,是无法排除的。”
茨威格的孩提时代,世界,或者说奥地利帝国,还是一个唱着欢乐歌谣、跳着康康舞、不知忧患的老贵族,人们的生活像童话一样宁静而优美。茨威格把这个昨日世界命名为“安稳的黄金时代”。我想,正是这个时代流入茨威格血液里的养分,让他在战争的车轮碾碎生活的自由时,依旧能够保持自己的高贵与独立。
是的,高贵。这个词是我读《昨日的世界》最强烈的感受。不仅仅因为茨威格让我明白语言所能抵达的高贵、优美与智性,不仅仅因为在战争风暴中他与友人高岸深谷般的情谊,更因为它带我深入人类的苦难,深入人性的隐痛。在历史血肉模糊的伤口处,那些高贵的人们强忍着痛苦,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完整……这是一段痛彻心扉却让人滋长力量的阅读,整个过程于我却心如澡雪。很多时候,身旁无人,我会大声诵读书中段落,庄严而虔诚地诵读。我希望把这高贵更长久地留存在唇齿间,并最终进入我的身体。
1942年2月,世界还是一片黑暗,《昨日的世界》已然完成。一个寻常午后,茨威格与妻子从容吞下大剂量安眠药,告别这个———曾赐予他希望,也塞给他绝望;赐予他名声,也塞给他苦难;赐予他思想,也粉碎他自由的世界。这个被战争折磨得“力量已消失殆尽”的苦难灵魂,留给世人最后的话语是充满哀伤的祝福:“愿你们经过这漫漫长夜后,还能看到彩霞满天!”当我读至此句,眼淚不禁簌簌而下。
年初是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后,我随即把他的《三大师》《自画像》《与魔鬼作斗争》《精神疗法》找来,大过了一把思维与智性挑战之瘾),之后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谢宗玉的《时光的盛宴》,然后到了岁末的叶芝。
尽管此前对这本“美得让李健自发地写书评”的书有过各种幻想,但当阿啃老师把《寂然的狂喜》递给我时,我的心仍禁不住微微一颤。
叶芝的诗与回声。封面是洁净的白,却是凹凸的肌理。也许,这才是诗歌的质地———纯净,却绝不简单,在那起起伏伏的凹凸中深藏着艺术与美的玄机。书中每一首诗都有国外绘画大师的配画,叶芝的诗则写在小幅象牙黄纸间,正面是叶芝的母语,背面是中文。
这样的书,我只觉美得如同一束月光。
书名取自书中诗句,“A longly impulse of delight”,诗中翻译为“寂寞的愉快冲动”,用于书名,化为“寂然的狂喜”。这真是太天才的翻译!把阅读时那风暴般的激动、秋水般的宁静诠释得淋漓尽致。
我一直认为,读诗是一种高尚、奢侈的生活内容,它较之其他精神活动,更能带来一个人精神的追寻与确立。可惜,叶芝的诗此前读得不多,但那首《当你老了》深入骨髓。相对书中“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爱你渐衰的脸上那缕缕忧伤”的翻译,我更钟情老翻译家袁可嘉的版本:“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我觉得“朝圣者的灵魂”与“痛苦的皱纹”才是这首诗歌的深沉与力量所在。这也许是因为我为文喜欢用力,也许是因为我的岁月尚长,众多苦难还等在前途,未来得及爬上脸庞。我想,当我老时,或许就会喜欢这个“缕缕忧伤”的版本。诗歌配图是一个熄灭了的壁炉,旁边一把椅子,却人去椅空,极具意境与想象力,倒是与“渐衰的脸上那缕缕忧伤”的淡然相匹配。
茨威格和叶芝是同时代人,青年茨威格在都柏林求学时,还遇见过叶芝,并对其诗艺深为折服。生活在同一世界、同一时代,两人因为各自祖国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也截然不同:身为奥地利帝国国民的茨威格始终处于战争漩涡的中心,终身颠沛流离,其作品仿若别在人类苦难身躯上的哀艳花朵;而中立国爱尔兰的诗人叶芝,则在为民族独立运动奔走呐喊之余,更有富余的精力去追求田园牧歌的浪漫。苦难与浪漫对承受者本人而言,有地狱与天堂之别,但它们培育出的文学,对后世的阅读者皆是福泽无边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