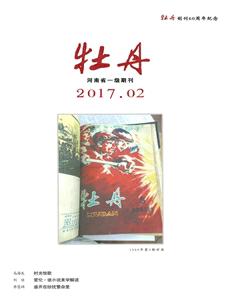《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诗性隐喻
吴悦茜
“隐喻”常见于一切的话语模式中,在英文中“隐喻”一词为“metaphor”,它源自希腊语“metaphora”,意为“由此及彼”。胡壮麟先生在《诗性隐喻》中指出:诗性隐喻是诗人通过个体思维的努力对所直觉的现实关系进行概念和经验上的建构、整合和重现。《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的代表作之一,哈代作为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具有“跨文体”的特征,其小说中的诗性隐喻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天使和魔鬼
一般而言,诗歌语言与宗教语言密切相关,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用隐喻来解释概念,这也不难解释诗歌中的许多宗教原型的出现。要理解《德伯家的苔丝》的诗性隐喻特征,需理解其中的人物设定是以《圣经》为原型的。
(一)天使与魔鬼的传统解读
传统的分析中,“天使”与“魔鬼”分别指克莱尔与德贝维尔。《德伯家的苔丝》男主人公的名字叫“安琪儿”(Angel)为“天使”之意,对于苔丝而言,安琪儿智慧而优雅,是理想爱人该有的模样;而引诱苔丝失贞的德贝维尔则如引诱夏娃吞食禁果的撒旦一般,在苔丝看来,生活中所有的不幸都是由德贝维尔引起的。但是,这种解释的方式有不完善之处。
首先,克莱尔与德贝维尔的形象都不是扁平化的,二人是“虚伪的天使”与“真实的魔鬼”。安琪儿对苔丝的爱看似天真炽烈,但当苔丝坦白了自己过去,安琪儿的态度却陡然转变,充分说明这个人物的虚伪性,他所爱并不是苔丝,而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另一女人”——是他自己的幻象;相比之下,德贝维尔的形象反而真实了许多,他迷恋苔丝是由于苔丝的美貌,于是他想方设法占有苔丝,他只忠于自己的欲望,但德贝维尔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恶魔,他也有过真诚的忏悔,且在苔丝家落魄的时候予以他们帮助。第二,苔丝与夏娃的形象也有出入,夏娃吞食禁果,蛇只是一个诱因,吃与不吃是夏娃自己的选择,但是,苔丝的失贞则是被迫成分居多。第三,如果说作为“魔鬼”的德贝维尔给予苔丝的伤害是身体上的,那么,作为“天使”的安琪儿给予苔丝的则是心灵上的重创,在苔丝给安琪儿的信中,可以看出其心理变化,从“因为你不在我这儿,所以光明已经不再吸引我了”,到“你待我这样无情无义啊!这是我不应该承受的呀……我只好尽力把你忘了”。“天使”并没有给苔丝指引,反而使她更加迷茫,甚至最后苔丝所得到的快乐与救赎并不是因为安琪儿,而是因为她对安琪儿的爱情本身,正如诗歌的意象或符号具有复杂性一样,它的能指与所指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因此,人们不能将安琪儿与德贝维尔看作“天使”与“魔鬼”的化身。
(二)天使与魔鬼的原型新解
事实上,“天使”与“魔鬼”的设定具有双向性,不仅是安琪儿与德贝维尔之于苔丝,更是苔丝之于这二人。苔丝的身上同时具有“天使”与“魔鬼”的特性。
对于安琪儿而言,苔丝是“天使”,起初安琪儿眼中的苔丝从身体到灵魂都是一个不受尘俗污染的完美女人,是一个“美神”的形象:
“他爱苔丝,完全是为了苔丝自己;为了她的灵魂,为了她的心性,为了她的本质——而不是因为她有奶牛场里的技艺,有读书的才能,更不是因为她有纯洁的正统的宗教信仰。她那种天真淳朴的自然本色,无需习俗的粉饰,就能让他喜欢。”
安琪儿糊涂之处在于从未跳出旧有观念的束缚。安琪儿出身于牧师家庭却不愿意担任教职,因为他虽然对教会有着很深的感情,但是依然为“她(教会)还没有把她的思想从奉神赎罪的不堪一击的信念中解放出来”而痛心,虽然表面上看安琪儿是叛逆者,但在苔丝坦白过去的经历时安琪儿仍然显得世俗和麻木。好在后来,安琪儿明白苔丝的爱对他而言才是真正可贵的,于是请求苔丝原谅并得到了她的宽恕,在苔丝杀死德贝维尔以后安琪儿与她一起逃亡,终于使苔丝获得了最后的自由与平静。某种程度上,苔丝是安琪儿的拯救者与引导者,安琪儿在苔丝死后娶了苔丝的妹妹——“一半是少女,一半是妇人,完全是苔丝的化身”也寻找到他的平静和自由。
另一条线索中,苔丝之于德贝维尔才是真正的“魔鬼”,德贝维尔眼中的苔丝永遠有着“冬青浆果似的”娇艳的嘴唇,苔丝对他而言也是危险和诱惑,使他永远都不得不在自己的情欲面前低头。阿力克戏称苔丝为“你这个亲爱的而又是冤孽的巴比伦女巫”。《启示录》第十七章记载“巴比伦女巫”:“那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身穿朱红色的衣服,在她的额上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在苔丝控诉德贝维尔骚扰她时,德贝维尔这样说明苔丝对她的影响:
“你说你没有骚扰我?可是你一直在骚扰我呀!你的影子老是在我心里,赶也赶不走。刚才你那双眼睛用恶狠狠的目光瞪着我,就是你的这种眼神,无论白天黑夜都在我面前。苔丝,自从你把我们那个孩子的事告诉了我,我的感情以前一直奔流在一股清教徒式的激流中,现在仿佛在朝你的那个方向冲开了一个缺口,立刻从缺口中奔涌而出。从那时起,宗教的河道干涸了,而这正是你造成的呀!”
“其实你只是保持了你美丽的容貌并没有做其他的……我相信,如果那位独身的使徒……也会受到你这幅美丽的容貌诱惑的,他也会和我一样,为了她而放弃他的犁铧。”
苔丝的美原本是无罪的,在德贝维尔眼里却成了致命的诱惑,从而导致他的罪恶与最终的毁灭。小说写德贝维尔之死:“长方形的白色天花板和中间,有一个红色小点出现在上面,看起来就像一张巨大的红桃A。”霍桑的《红字》中也提到字母“A”。“A”是“通奸罪”(Adulitery)的第一字母,红色最有危险和罪恶的意味。这印证了《圣经》摩西十诫中的“你不可犯奸淫”。
德贝维尔的罪恶导致了他自身的死亡,然而这何尝不是杀死德贝维尔的苔丝的罪恶呢?在她纯洁的天性中也有危险的面目,采取最极端的方式反抗使得苔丝的形象也具有了“天使”与“魔鬼”相结合的二重性。
胡壮麟在《诗性隐喻》中认为;“诗性隐喻”的重要特征是其义域具有“跨越性”和“扩展性”。两个不同义域的概念放置在一起,就体现出作者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读者的思绪也可以在作者所营造的艺术境界中飞驰。显然,“天使”与“魔鬼”的原型人物的设定拓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二、生存和毁灭
《德伯家的苔丝》中还有一对对立的概念——生存与毁灭。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提出: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在奋斗中扫清这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在苔丝的一生中,总是充满着造化弄人和命运无情的悲剧性,面对命运,哈代将其描述为“众神之王对苔丝的戏弄”,面对无常的命运,苔丝可以选择生存,也可以选择毁灭,生存与毁灭的主题本身就是一重隐喻。苏珊·朗阁在《艺术问题》中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家所表现的是人类共有的深层次的情感,运用艺术直觉捕捉艺术形式与生命的逻辑形式之间的“象征性联系”。对于苔丝被捕的场景,哈代这样描写:
“天越来越亮了,所有的人都在那儿等着,他们的脸和手都仿佛镀上了一层银灰色,而他们身体的其他部分则是黑色的,石头柱子闪耀着灰绿色的光,平原仍然是一片昏暗。不久天大亮了,太阳的光线照射在苔丝没有知觉的身上,透过她的眼睑射进她的眼里,把苔丝唤醒了。
……
‘现在可以走了。她从容地说。”
明明是在奔赴刑场以前,却有希望的光照在苔丝的脸上。哈代创作的时期正是“印象派”绘画发展的时期,受到“印象派”的影响,哈代在刻画具体的场景时也总描绘光与影的对比变幻,从而营造出一种诗性的意象与氛围,是毁灭也是生存,是结束也是开始,至少在结束一生的前一刻,苔丝是平静,自由而幸福的。
通过释放出“魔鬼”,彻底反抗命运,苔丝灵魂深处的那个“天使”终于生存下来,哈代将整本书的副标题定位“一个纯洁的女人”(A Pure Woman),当委曲求全的生存变成了一种顺从的懦弱,毁灭何尝不能作为一种成全。面对命运,苔丝最终选择了最危险的道路,杀死了德贝维尔,从某种程度上便是成全又毁灭了那个“魔鬼”的自我,她终于可以最终“像羔羊一样将最终自己献祭给永恒的爱情,让希望之光照亮她的死亡”。从这一角度来看,哈代站在了更高的视点上将隐喻指向命运,使作品的主题有了悲剧性的崇高意味。
(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