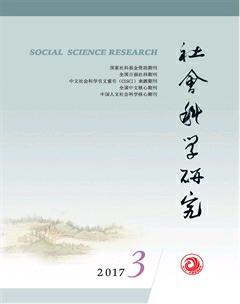列宁哲学研究的一个崭新起点
鲁宝+张义修
在十月革命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2016年,日本世界书院出版了张一兵教授的《回到列宁》〔1〕日文版,引发日本学界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该书的出版将成为“新时代列宁哲学研究的起点”(大下敦史语)。9月15-17日,日本《情况》杂志社在京都和东京举办了《回到列宁》日文版专题研讨会。来自日本中央大学、东京都立大学、明治学院以及中国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回到列宁》的独特研究视角和“构境论”等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回到列宁”的理论旨趣与当代意义
《回到列宁》致力于反思传统列宁研究中的理论遮蔽,彰显列宁思想的当代意义,获得了与会学者的强烈共鸣。大谷浩幸指出,在苏联解体已经25年后,不少人认为,列宁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感与闭塞感日益增大,思想的迷惘不断加剧。在这一背景下,《回到列宁》日文版可谓为日本左翼思想界吹来了一股新风。世界书院社长大下敦史指出,日本学界的列宁研究经历了近30年的沉默期,《回到列宁》引起如此大反响,正是因为该书“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列宁形象”。
福富健进一步指出,《回到列宁》深入批判了斯大林教条主义、前苏东马克思主义的偏颇与不足,具有划时代意义。过去的列宁研究总是倾向于以完成的形象,从革命领导人的身份来理解列寧。而《回到列宁》使人们熟悉的列宁形象面临一个大转换。该书分析了列宁研读黑格尔,进而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进程。这一进程过去不是被忽视就是被主观地解读为“计划构想论”,而在西方“列宁学”那里则被简化为从唯物主义走向唯心主义的过程。由于受强制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列宁“哲学笔记”的文本过去并没有被真正打开过。
南京大学张传平教授认为,《回到列宁》潜在地包含两个批判对象。其一是俄文第5版《列宁全集》在编辑上的重大缺陷。这种编排过度抬高列宁早期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忽视或贬低列宁1914-1915年“哲学笔记”的理论价值,没有认识到笔记本身所具有的非同质性。《回到列宁》的另一个“靶子”就是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凯德洛夫逐篇地研究了列宁的笔记,但并未真正回到列宁的思想语境之中,所谓“辩证法体系”的构想是一种明显的主观性判断。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回到列宁》破除了前苏东研究模式的列宁形象,对列宁研究具有启蒙性和解放性意义。正如大下敦史所言:“此次日文版《回到列宁》的出版,对处于低谷与困境中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巨大的促动,书中提出的全新视角、全新方法与全新问题激发并拓展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思考空间,为深化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与动力。”
二、列宁哲学的全新分期与“哲学笔记”的重新认定
对列宁哲学的全新历史分期是《回到列宁》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该书提出,列宁哲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94-1906年),在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哲学观念主要依附于普列汉诺夫等外部权威;第二阶段(1906-1913年),通过深入研究唯物主义,成为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第三阶段(1914—1916年),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专题研究,获得哲学思想的飞跃,自主掌握了实践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2〕这种历史分期引发了日本学者的热烈讨论。
寄川条路认为,张一兵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分期是与前苏联教条主义的一次诀别,彰显了一种独立、真挚面对经典文本的态度。福富健指出,列宁在其思想发展的初期,在哲学方面“动辄依赖他性的东西”,外在地依赖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的某些结论。通过在“伯尔尼笔记”中与黑格尔哲学进行“苦斗”,列宁最终在唯物主义的层面上理解了辩证法的意义。加藤在指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实践诠释为变革对象世界,这种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也是列宁后来才理解的辩证法的实质性内涵。
《回到列宁》中与历史分期紧密联系的是对“哲学笔记”文本性质的重新认定。张一兵提出,列宁的“哲学笔记”并不是一本书,而只是后人整理、编辑出来的列宁在20多年间写下的读书笔记、心得的汇集。所谓“哲学笔记”中的不同文献不是同质性的。这就颠覆了传统对于“哲学笔记”的基本认定。〔3〕对此有日本学者提出,过去日本的研究也都认为“哲学笔记”是一本完整的、同质性的著作,是为写作一本系统的辩证法著作而作的计划纲要。这种观点长期统治人们的头脑,导致人们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认识停滞不前,同时也是列宁哲学在当代失去了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重新认定“哲学笔记”的文本性质,特别是重新解读其中的“伯尔尼笔记”,对于实现列宁哲学思想的“再发现”具有启发意义。
三、“伯尔尼笔记”与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新认识
“伯尔尼笔记”是《回到列宁》的一个新提法,它是指1914-1915年间列宁在瑞士伯尔尼系统研究黑格尔哲学所留下的摘录笔记。作为列宁哲学发展第三阶段的核心文本,“伯尔尼笔记”过去被放在“哲学笔记”的名下,其哲学内涵往往被低估和错认。而《回到列宁》主要就是要重新研究这一部分的思想内容。〔4〕
大部分日本学者肯定了《回到列宁》对“伯尔尼笔记”的创新解读。榎原均认为,列宁为了将辩证法颠倒过来而研读《逻辑学》,起初留下了将观念与物质替换的评语,后来逐渐提高了认识,将实践作为主体与客体的交错点,得出了实践基础上的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三者同一”的结论。寄川条路指出,列宁在开始做“伯尔尼笔记”时,依靠普列汉诺夫等的观点来面对黑格尔哲学,随后态度发生转变,逐渐向黑格尔靠近。当他形成新的思考立场后,又重新热衷于马克思,在研读完《逻辑学》以后,继续阅读黑格尔的其他著作,继续建构新思想。
也有学者对《回到列宁》关于列宁“伯尔尼笔记”的论述提出了不同意见。稻叶守认为黑格尔并未将其整个逻辑学统称为“辩证法”,而只是称为“思辨的方法”,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思辨方法总体性地改造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未试图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总体构架加以转换,他所提到的辩证法只是针对黑格尔逻辑学的个别环节,不足以被提升到“实践辩证法”的总体性高度。因此,《回到列宁》中列宁以“实践辩证法”理解黑格尔“思辨的方法”的观点,还需进一步论证。
四、“构境论”的理论意义与列宁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在《回到列宁》中,张一兵教授正式提出原创性的“构境论”思想,这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以此为基础,《回到列宁》在文本研究层面首次使用思想构境的解读方法,拟现出列宁的思想演进的异质性轨迹。在本次研讨会上,“构境论”及其在列宁研究中的运用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焦点。
寄川条路认为,张一兵的“回到”并不是新康德主义的“回到康德”的意思。要回到的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事物自身”;不是纯粹的客观文本,而是作者的思想構造情境。“回到列宁”并不是回到列宁的文本,而是回到对列宁的哲学思想重新进行建构的场面。因此,作者否定单纯对文章进行解释的做法,解构了文本原意的客观直达性。“构境论”解读不是原初文本意义的复原,而是思想的重新建构,由读者给文本带来新活力。福富健指出,“思想构境论”的解读方法广泛吸收了以拉康的“他性理论镜像”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在文本研究的层面开创了新的局面。此书对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广松哲学、柄谷行人等的丰富论述,充分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理论挑战精神。
还有学者指出,以“构境论”面对列宁研究,对于增强列宁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具有重要意义。过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从客体或直观出发,西方“列宁学”则是单纯地从主体或主观出发,都没有站在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辩证法的立场上。“构境论”在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而超越了过去列宁研究中的解读模式。中野英夫指出,后现代的马克思理论已经很常见,但《回到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一种后现代式的列宁理论,这或许在世界上都是首创。该书不仅消除了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象,而且以全新的视角,对文本和历史事实进行了主客体相互作用之中的构境论的再现。这是《回到列宁》最为精彩的创造。
《回到列宁》问世以来,斯拉沃热·齐泽克、特瑞·卡弗、凯文·安德森等国际知名学者对该书的理论价值予以积极评价,孙正聿、王金福等国内专家学者也围绕《回到列宁》的若干问题做出了深刻剖析。此次《回到列宁》日本版研讨会的举办,将围绕该书的讨论再次引向深入,也表现出中日两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种共同思考和期待:积极吸收当代思潮的有益资源,创造性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深化思想史研究,为理解和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参考文献〕
〔1〕〔2〕〔3〕〔4〕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8,9-10,22.(责任编辑:颜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