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说异见,别样风情
——读《舞文詅痴》
何文斌
异说异见,别样风情
——读《舞文詅痴》
何文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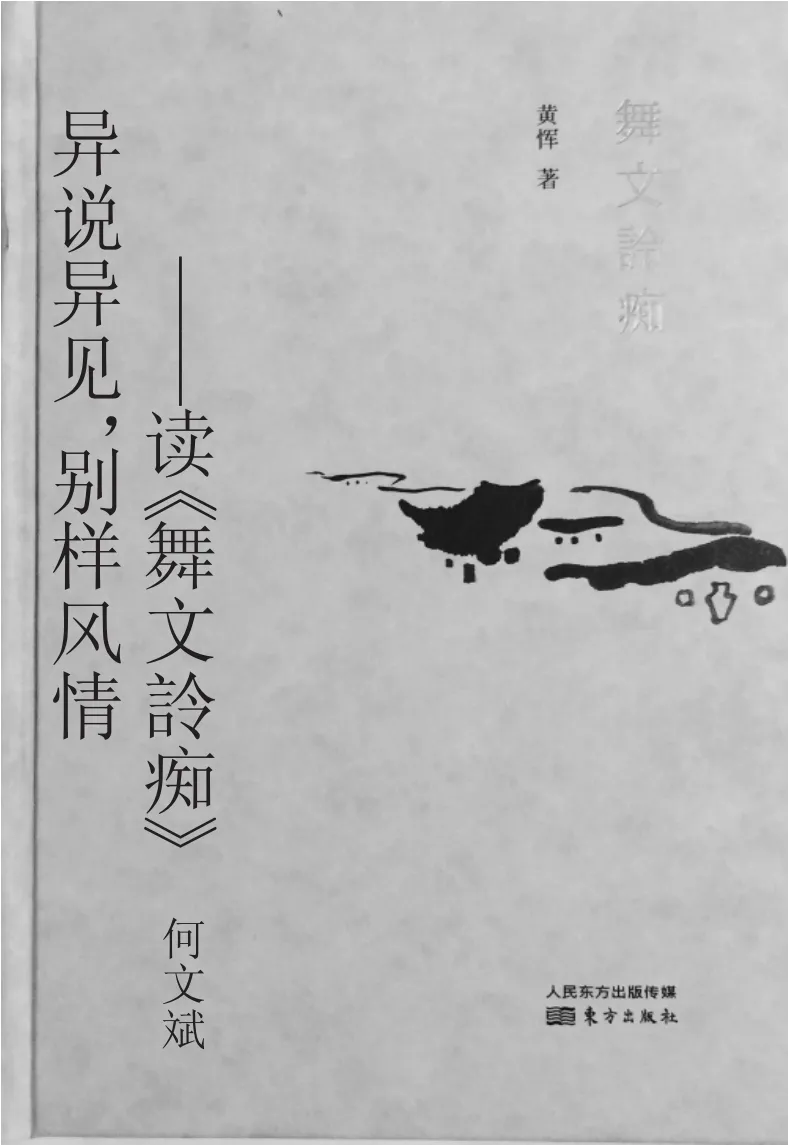
“我本是不会写文章的人,却慢慢弄成以编文章和写文章为生,真是做梦也没有梦到。”这是黄恽先生《舞文詅痴》序言开头的话,也是作者自谦的话。作为读者,我们已经等待了两年半了。
从最早《蠹痕散辑》开始到这一部近著《舞文詅痴》,依然是以四个字作为书名,这是黄先生著作的一大特点。作者引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通读全书,自然明白是一位学者的谦辞。化用成语、典故,却又是他自己的独有表述手法,令人耳目一新。清代的黄丕烈在他的藏书上题写的文字后人冠以“黄跋”的称谓,沿袭这种风格,黄恽先生的书名不妨可以称为“黄氏表述法”。同样,他的文章也是如此。
很多人(尤其是网上)把黄恽先生这样的作品归为掌故传统,比较有代表的是《储安平传》的作者韩戍先生,他在《接续晚清民国掌故传统》的文章里说:“黄恽作品继承的,实际是中国文史写作中说掌故的传统。晚清民国时期,有很多热衷于讲故事、说段子、说掌故的老辈,通过各种随笔、札记来记录掌故、品评人事,许多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对于我们这一代读者,提到掌故的第一印象就是郑逸梅先生,纸帐铜瓶室主人写了七十多年掌故,被誉为“补白大王”。在我看,黄恽先生早期的文章的确受到郑逸梅先生的影响,巧合的是郑的著作也常用四个字作为书名。
黄恽先生并不局限于郑氏风格,从掌故的框架跳脱出来,进而向到文载道、金克木、刘衍文等文史大家学习。近几年的文章尤为突出,渐渐自成面目,风格清晰,可辨性极强。这本《舞文詅痴》便是最好的证明。书分为“如梦记”“烟云录”两辑,讲的都是人或者书的故事。好看与有料相结合,读来不犯困。
黄先生的文章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趣味性,二是具有史料性。能把枯燥乏味的长篇资料化为自己的文字,把表述的内容立体呈现出来,好像一部连续剧,吸引我们不断往下看。苏州的说书先生,一把扇子一张嘴可以演化成千军万马,可谓是声情并茂。不过黄先生为文的生动却不是演义。他有丰稔的知识储备,这源于二十年来收罗的大量民国书籍和报刊,并且潜心于民国小报研究,熟悉大量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曾用五年的时间一字字地输入纪果庵的著作,还搜集了大量民国报纸、杂志上尤墨君的遗文。这才有了傅斯年先生说“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长于分析、慧眼独具,而且绝不胡乱猜测,与当下“大师清流”“南渡北归”这样流行的轻奢历史随笔,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本书第一篇:《1927年苏州易帜中申听禅的遭遇》,作者用了大量当时的报纸信息,那时小报记者的报道常用半文不白的文字,有时候还酸不拉几地掉几个书袋,阅读容易错过信息,而在黄先生的一支妙笔下,犹如手术刀解剖一般为我们微显阐幽,渐渐把申振刚的曲折遭遇展现出来,很有画面感。这样的行笔颇为不易,把前人文字化开,转化为通俗的文字却又高于时下,在文字里体会出一点无奈、一点苦涩。这一篇是黄先生“追踪申听禅”的又一力作,可与《古香异色》中的文字衔接,为我们了解申氏其人增添了更多的信息。《金性尧谈苏青》《北京〈中华周报〉中的张爱玲的消息》等篇可作为“张胡研究”专著《缘来如此》的延续。
常写易流于无趣而媚俗,能写常趋向专业而艰涩。有的人写文章,见到一则史料或者趣闻,开始天马行空、漫天想象,好像在古人头顶装了摄像头,这样的文字经不起推敲,往往贻笑大方。有的人写文章,把稀少的资料不加分辨全部引入,最终出来的文字又臭又长,展读几页便哈欠连连。对于学者而言,或会觉得是资料汇总,而普通读者却实在无福消受。会写则融合了这两方的优点,既让普通读者感兴趣、能读下去,也可以让专业人士从中萃取养分,继续深入发掘和研究。会写如黄先生,其文字方有如此的魅力,这也是一种“黄氏表述法”。比如书中有一篇《陈白尘被枪击事件》 ,既引用了常见书《我家的故事》——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女士的“讲述”,也用了稀见杂志《青年电影周刊》的报道。又利用了1947年的《民治周刊》以及柯灵编辑的《作家笔会》(海豚出版社2013年6月新版),将几方的记载和看法放在一起作比较,并在黄先生鞭辟入里的分析下,种种不同说法都归聚到了一个结果,读者会心一笑、完全明了。如果没有黄先生的妙笔,或只读江苏凤凰文艺版的“讲述”,自然疑窦丛生,不辨真伪了。事实上这一本海豚版的《作家笔会》我早先已读到,而我却只知道一位署名殷芜的作者写了枪击事件。
又如谈刘文典,总喜欢说刘的学问,然后絮叨一番刘文典与沈从文、刘文典与蒋介石的故事,沈、蒋总是跟着“躺枪”,用来用去不过是炒冷饭而已,而黄先生写了一则不为人知的轶事:《失去了儿子的刘文典》 ,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大学师生之间的善意与诚挚。纵观全书,提到了太多尘封已久的人和书,一幕幕往事好似展开的银幕、立体的长卷。如周作人的日本女粉丝阿部淑子、项星耀这个大众陌生的作家、《纯常子枝语》这部稿本等等,都是如此。
对于黄先生的文章,研究者有两个误区,一是常常被认为是民国掌故,本书的封底的上架建议还打着“民国掌故”的字样便是明证。这样的文字如果只是归结为掌故或者民国,属于局限的看法,不妨称为读书随笔,都是文史研究的范畴。第二个误区是,人们常把写这类文章认定为借古讽今,为前朝粉饰。这好像是一道魔咒,也是当今研究者的浅薄。《深圳晚报》有一个对黄恽先生的专访,题目叫做《民国热很可悲:民国是个很糟的年代》。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搜索一下。当下或许不尽完美,民国何尝是人间桃花源?!黄先生保持着一贯的清醒。
视角独特,观点新颖,为我们解读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面目,也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常读常新。作者在《吕思勉谈〈古文观止〉》一文中提到:“通识俗见,众口一词,人云亦云,往往凡庸;异说异见,虽或不免偏执偏见,却经过自己个性化的思考,是打上个人烙印的知见,即使不一定准确,也必能给予别人启迪。”吕思勉先生是如此,黄恽先生也如此,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