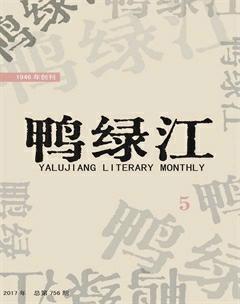懵懂少年的一次远行
王张应
1
近几年来,只要见到我的堂弟先成,我总会想起一件事。我就会对他说,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那户人家,尔后我俩一起过去,回访那一家人,向人家表达谢意。
我说这话时,需要感谢的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事情发生时,我和堂弟先成都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先成,跟我同年,比我小月,同宗同姓也同辈分,而且还一直是同班同学,从小学同到初中,再同到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我们又同时从事着教师职业。我俩是一对未出五服的堂兄弟。
事情源自我和先成兄弟于懵懂岁月里的那一次远行,一次十分果敢却又非常盲目的远行。当然,那次出行,拿现在的眼光看来,根本不算回事,也绝对谈不上远行。但在几十年前,在那一对十二三岁的小兄弟的眼里,那次出行就该算是一次远行了。这对小兄弟,在那次出门之前,都还没有离开过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名叫黄土岭的村子。这次远行的目的地,是县内一个名叫王河的区公所所在的集镇,路程大约三十多公里。如今,从我们村子坐车去王河镇,大概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吧,但在那时,这段路程全靠了兄弟俩的步伐来丈量的,两双还不够粗壮有力的腿脚,努力地向前跨去,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把整个路程测量出来,留存在了自己的记忆里。成年人走完这段路,怎么说也得六七个小时吧,何况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步伐小,耐力弱,走起来时间就更长了。所以,我现在把这次出行界定为远行,应该还是有道理的。
从地理位置上讲,我们村子在县域版图上中部偏北的地方,王河则是在县域版图的南边,东与邻县怀宁交界,南离太湖县境也不远了。自家里出发,前往王河,中间需要经过县城梅城。从家里到梅城,这一段路程大约有十六七公里。从梅城到王河,原以为很近,紧挨着。后来,走过了梅城才知道,梅城到王河虽是紧挨着,也不近,足有十七八公里呢。甚至,比从家里到梅城的路程还要远。
兄弟俩出行的时候,是在暑假里,立秋过后,8月下旬。当时,白天的气温还是蛮高的,两个少年都是穿着短裤短褂出门的。
那天,我们吃过早饭,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出的门,除了身上的一套短裤短褂外,我们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带上。那会子,我们年少心粗,遇事不会多想,出行说走就走,根本不会做任何准备。无知无畏,应该是对当时的两个少年最真实、最恰当的写照。不过,对于年少的人来说,无知无畏不见得就是坏事,从某个角度看,它也是好事。正是因为无知无畏,两个少年对自己才有了太多的信心,他俩相信凭着自己的一双腿,足以远走天涯,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
2
走出家门,这一对小兄弟,简直如同久居笼中的小鸟,突然被人给放了出来,一时间天高地远,世界空旷无边,两个少年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快乐。兄弟俩在村道上一路小跑,很快就到了人民公社所在地的小集镇,那个名叫老岭头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踏上了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马路。那条路当年还是105国道呢,是一条国家级的交通要道。不过,在那个时候过往的车辆并不多,路面不够宽,两车相会时,车子几乎都要停下来才能彼此通过。当时还不是柏油马路,路面是用沙石铺就的,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路面上空立刻腾起一股灰白色的尘雾,顺着汽车驶去的方向,拖曳得老长老长,久久不能散尽。
新鲜感最能够给人鼓劲。一开始,兄弟俩几乎是一阵小跑着前进。好像王河就在眼前,只要跑一跑,马上就到了。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这兄弟俩而言,王河离他们的心里固然很近,真正走起来还远着呢。少年人的新鲜劲来得快,去得也很快,耐力不能持久。兄弟俩在马路上小跑了一阵,就觉着累了,跑不动了。气越喘越粗,越喘越快,感觉那颗小心脏都快蹦到嗓子眼里了。
兄弟俩不再奔跑了,慢下脚步,最后停了下来,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歇息一会儿。一旦歇了下来,就不单单是累的问题了。仅仅累了,歇一歇,也就可以了,很快就会恢复过来。在路上奔跑时,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人的心脏都按捺不住了,总想伺机朝外蹦出来。这样的剧烈运动之后,人最强烈的反应是口渴,想喝水。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当时的两个少年却不明白。
搁在现在,口渴了,自然不成问题。如今的人出门时一般都不会忘记带水,年纪大的人出门,都习惯带个大茶杯,最好还是保温杯,里面装满了茶水,随时随地都能喝上一口热茶。年轻人的习惯不一样,他们出门时不愿意带个茶杯,觉得那是老土。他们大都喜欢带上一瓶矿泉水,喝完了水,找个适当的地方就把那只塑料瓶子扔掉了,很方便,不累手。但在那个年代,人们都还没有这些习惯,当然,也不具备这个条件。少年兄弟俩出门之前,就根本没有想到走在路上会口渴,还需要喝水。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总是在冥冥之中眷顾着那些有难处的人。就在兄弟俩口渴难忍的时候,一抬头,兄弟俩几乎同时发现,前方不远处,路的东边有一口池塘。兄弟俩一个对视之后,没有说话,立即起身,快步往前赶,来到了那口池塘边。这是一口山野间的池塘,附近没有人家。不大的水面,三面环山,一面毗邻稻田。水很清冽,人站在池塘边上,能看见山边树的倒影,也能看见兄弟俩在水底的人影,就连那一群群十分欢快的小鱼儿,在水里跑来跑去飘忽不定的身影,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兄弟俩蹲在水边,弯下腰去,将脸面贴近水面,双手并在一起,把池塘里的水小心谨慎地捧起来,慢慢地送到嘴里,一次又一次,一直喝到小肚子鼓圆鼓圆。
歇息好了,水也喝足了,兄弟俩继续赶路。沿着沙石马路一直往南走,不久,来到了一个小集镇,名叫余家井,是當时的余井区公所的所在地。在集镇上,两个少年没作停留,继续向南走。出了集镇,没走多远,就走到了余井大桥。站在桥上,把那条传说中桀骜不驯的余井大河踩在了脚底下。余井大河,其实就是皖河,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皖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所谓传说,指的是1954年和1969年两次大洪水,摧垮了河堤,一次又一次把原本坐落在河边的余井小集镇夷为一片沙滩平地。两次灾后重建,余井老街基本上没有了,小集镇就逐渐地被迁移到了离河边较远的小山冈上了。1954年的那次洪灾来时,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呢。十五年后,1969年再次暴发洪灾时,我还年幼,没有能力亲自跑过去看到当时的灾情。所以,对于余井大河,我最早的记忆,只是来自这两次有关水灾的传说了。
余井大桥,这座横跨在皖河上的公路大桥,是两个少年平生见到的最大的一座桥。在少年的心目中,天下最为雄伟壮观的桥,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了。但两个少年没有到过南京,当然也就无缘见识南京长江大桥。见到了余井大桥,两个少年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南京长江大桥,心中没有由来地涌起一股自豪感。
在这以前,兄弟俩都还没有见过那么长的桥,也没见过那么宽阔的河流,从北岸到南岸足有三四百米吧。见到了那条河,看着河里水流湍急,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样子,一个少年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当年一首非常有名的电影插曲——《一条大河波浪宽》,另外一个少年也紧跟着哼唱起来。两个少年都很兴奋,都很忘情,他俩连蹦带跳,在桥上奔跑,跑一会儿,又停下来,趴在栏杆上朝着河面上望去。随后,把目光从远处的河面上收回来,放到脚底下来。少年发现桥很高,该有四到五丈的高度吧,人站在上面都有些脚杆子发软的感觉。桥下是宽阔的河面,河水很丰满,覆盖了整个河床。水质很清澈,在浅水处,能看见水底的石头,甚至还能看见嬉戏于鹅卵石间的鱼虾。水深处,绿茵茵的一片,深到望不见底。如今,再去余井大河,当年站在桥上的这些所见所感,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早已不复存在。虽然,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桥,但这里的桥早已经不是当年那座桥了,这个地方的桥梁都不知道重新修建过多少次了。现在的桥不像过去那么高了,是因为河里的沙石越积越多,导致河床一直在抬高,渐渐接近着桥面,桥,自然显得矮了下来。河水已不再丰盈,一年比一年更加消瘦。大桥下面是大片裸露的沙石,水流如线,在沙石铺就的河床上缓慢游走。据说,这些年,在河的上游,修筑了一座又一座水库。本来就已经越来越少的河水,还有一部分河水平时不再往下流了,躺在水库里面睡大觉呢,这就难怪河的下游来水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如果没有少年时代的那次远行,我对家乡的这条河流,知道的,甚至说相信的,也就仅限于今天眼前所见的现象了,无法如同我现在这样,能够了解到一条河流的前世和今生。现在回想起来,就冲这一点,我也觉得少年时代的那次远行,真的没有错,很值得。正是那次远行,让少年学会了观察,给少年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那天,兄弟俩在桥上逗留了很久,玩耍了很长时间,直到兄弟俩心中的新鲜感完全过去,才离开大桥。过了余井大桥,天已近午,问题又来了。两个少年几乎同时听见了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地叫着呢。他俩这才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人出门在外时,总是有一个不能回避、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人得吃饭。兄弟俩在这个时候,什么都不会多想了,他们想的就是能够得到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没有菜也行,哪怕只是一碗白米饭。没有白米饭也行,哪怕只是一枚蒸熟了的红薯。可是,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平生第一次来到的完全陌生的地方,到哪里去弄这样一碗热腾腾的饭菜呢?就连一枚蒸熟了的红薯也无法想象。面对现实,对于那种热腾腾的饭食,兄弟俩想都不去想了,两个少年的目光一直在路边的菜地里打着转,一遍又一遍地在那些藤藤蔓蔓中扫瞄着,搜索着。
那个季节,正是蔬菜换茬的时候,黄瓜和葫芦,还有豇豆,那些藤类的蔬菜已经过了鼎盛期的枝繁叶茂,正在一天天地衰败下来。尤其是黄瓜,衰败得最快。那些缠绕在竹木菜架上的黄瓜,叶子已经发黄,打卷,甚至焦枯,不时地随风凋落下来。原先茂密的叶子渐渐稀少了,架子上裸露出了长满毛刺、青筋绽露的黄瓜藤。两个少年的目光,顺沿着那些衰败的黄瓜藤慢慢爬行,细细搜索,终于在焦枯的黄叶间,发现了几只很小的老黄瓜。那可是一些十分少年老成的小黄瓜哟,估计是被主人遗漏了或者根本就是被主人故意遗弃的黄瓜。从个头上看,似乎还是个小孩,块头很小,没有长大,没有发开。从面目上看,却又像个老者,脸色枯黄,长满了皱纹。这样的黄瓜,从长相上说实在有些对不起它的主人了,被主人遗漏甚至遗弃,想来也是必然了。可是,两个少年见到了这些被它们的主人不屑一顾的黄瓜,却亲热得不行,像是流浪在外的弃儿见到了久别的亲娘似的,少年的双手捧起了黄瓜,将黄瓜渐渐抬起,贴近嘴唇。少年以最快的速度,亲吻了那几只皱巴巴的蔫黄瓜。尔后,风卷残云,被亲吻过的老黄瓜就不见了,碎成了一抔黄瓜泥,沉淀在黑暗幽深的那两个不大的胃的底部了。
3
这几只意外出现的老蔫黄瓜,给这两个饥饿疲惫的少年兄弟,鼓了一把劲,加了一股油。兄弟俩又出发了,继续向南行走,步步逼近两个少年心中向往已久中的“大码头”——县城梅城。那个时候,两个少年并不知道,这座县城为什么名叫梅城,他们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想过为什么,也是对头的,何必要想那么多呢,天底下哪来那么多的为什么。当然,后来他们都知道了,这座县城在历史上还是挺有名的。它不仅是一个古老的郡县,而且还曾经是一个有名的诸侯国,国名叫“皖”。对于这个字,人们一定不会陌生,它不就是如今安徽省的简称嘛。是的,很早我就认识这个字,但我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我曾经自作主张地把它理解为“明亮”和“美好”,因为它左边是“白”,右边是“完”。现在,我知道了,除了“明亮”和“美好”,还应该有个“清爽”的意思在。因为“白”,除了“明亮”,还有“清白”。后来,我还听说,县城梅城的“梅”字,与三国时期曹操军队行军途中望梅止渴的典故还有关系呢。在梅城的历史上,还曾经有过国色天香的大乔和小乔,她们风华绝代,曾经是名垂千古的风流人物呢。当年,那一对少年兄弟并不知道梅城的这些历史和典故,他们对大乔和小乔都还不感兴趣。他俩只知道,梅城就是县府的所在地,在兄弟俩心目中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他们正在途中急切行走,紧追快赶,希望早一点到达梅城。
两个少年到达梅城的时候,天色已经向晚,太阳快要落山了。兄弟俩原本打算在梅城那个“大码头”“大地方”,好好耍一耍,玩一玩。回去以后,也好跟小伙伴们显摆一下,我们到过梅城了,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抬头看看天色,时候不早了,少年只好作罷。在梅城没有停留,兄弟俩继续赶路,两个少年没有忘记,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梅城南边的王河。那个时候,两个少年只知道王河坐落在梅城的南边,却不知道王河是在离梅城多远的南边。关于王河的地理位置,少年只有过听说,没有其他途径进行了解。搁在现在,翻翻手机,看看地图就知道了。但在那时,要看地图,在地图上找出类似于王河这样一些小地方的位置,那就不啻于天方夜谭了。两个少年就沿着那条穿城的公路一直往南走,很天真地以为只要出了县城梅城,也就到了王河。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从梅城到王河还远着呢。王河距离梅城,不比我们村子到梅城近。换句话说,两个少年从家里出发走到了梅城,还没走完一半的路程呢。可是,那时的我们却一点都不知情,我们总以为快了,很快了,马上就会到达我们心目中的王河了。
于是,在那个傍晚时分,兄弟俩像夸父逐日那样,追赶着那一轮距离西山之顶越来越近,眼看就要落山的日头,奔走在夕阳的余晖里。在两个少年的身后,地面上拖着两个长长的身影。不知道是从某一时刻开始,天色悄悄地暗淡下来,两个少年拖在地上的影子不见了。可能是两个影子也已经累了,再也走不动了,就偷偷地停留在身后的某个地方,正在歇息呢。
兄弟俩走得离梅城也越来越远了,在两个少年的心目中,这该是离王河越来越近了,似乎王河就在眼前了。其实,在梅城的南边,紧挨着县城的,是一个名叫罗汉的公社,那还不是王河。罗汉公社还是属于梅城区,王河则是一个与梅城区接壤的另外一个区。那天,天黑之前,两个少年并没有走出罗汉公社,也就是说,他俩还在梅城区的范围内。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兄弟俩真的有些焦急了,甚至,还有一股恐惧感,如同无边的夜色一般,从天边渐渐收拢过来,把两个少年包围起来,淹没于其中。两个少年许是想起了从课本上学过的那些英雄的事迹,心里面都会居住着一个英雄,这个英雄一旦现身,少年的胆子就渐渐地壮了起来,一股勇敢的豪气,自脚底生成,冉冉上升,直奔头顶。很快,兄弟俩十分顺利地战胜了焦急和恐惧。虽然天色已暗,但少年的心里却是亮堂的,兄弟俩的心里面都亮着一盏灯呢。这盏灯就是一种信念,是一定要到达王河的这种坚定信念。少年凭借着心中的亮光,在苍茫的暮色中摸索着前行。
走到一处坡道时,兄弟俩实在不知道应该往哪走了。也许,人在年少的时候,辨别方向,做出取舍,总不是一件容易事。少年面前的那个地方是一处三岔路口,一处朝东,一处朝南,朝北的则是兄弟俩的背后,是来路,因而不会是去向。兄弟俩要去的王河,到底是向东,还是向南呢?兄弟俩一会儿想应该这样,一会儿又想应该那样,如此这般地争论了一番,到最后,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了。实在拿不定主意时,一个少年提议可以去问问别人。似乎就在那一时刻,我陡然想起了小时候听奶奶说过的一句话,你要记着,以后出门在外,路就在你的嘴巴下面。意思是说,你不知道面前的路该怎么走了,也不要紧,只要你开口,去问问别人就会知道路该怎么走了。切不可自作主张,想当然地盲目乱走。
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路上好长时间都不见有行人过往,找人问路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兄弟俩站在路口,东张西望,希望能够从四周黑乎乎的夜幕中突然走出一个人来。而且希望那人还是个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况,他能够告诉我们,此去王河,应该选择哪条道,还有多远的路程。最好,他也是去王河,好让我们跟在他的后面一起走到王河。那个时刻,兄弟俩的胆子也算够大了,在那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又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两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少年,竟然能够站在夜幕下的马路上,等待着过往的行人,借机向人问路。
当晚,兄弟俩在那个路口处等了好久,却没有等到一个人影出现。站在路口,一动不动,要想时间长久,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过了一会儿,兄弟俩都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需要另想办法。在我的家乡大别山东麓、长江北岸的那块地方,立秋过后,白天虽是暑热难熬,到了夜晚天气就明显地凉快了。兄弟俩穿的是短衣短裤,露着胳膊光着腿脚,秋后的夜风,吹在身上,初始感觉凉爽,非常舒服,时间一长,竟觉寒意难以抵挡了。再加上還是早上在家吃的饭,中晚两餐粒米未进,人就难免有些虚弱了,凉风吹过,身上遍起鸡皮疙瘩,嘴巴里面,上下两排牙齿不由自主地打起架来。我终于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干耗下去了,一定得想想办法寻求帮助。我说,兄弟,咱这样下去可不行,不能继续这样傻傻地往下等了,万一这一个晚上都不会有一个人过来呢,我们这样等下去会有用吗?不行,不能等了,咱得主动去找人。不去找人,咱俩就只能在这路边过夜了。即使不至于饿死、冻死,也很有可能成为过路的某个豺狼野兽的一顿美餐呢。
4
在那样的夜晚,主动去找人问路,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又是在那样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方,我们能去找谁呢?上哪儿去找?我们兄弟俩想来想去,没有头绪,感到非常无助。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一次发现,到了关键的时候,总是老天爷在暗中助人。就在我们兄弟俩四顾茫然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去哪儿找谁的时候,在路口的东边不远处,突然亮起了一小点微弱的亮光。起先,我们兄弟俩对着那个豆大的光亮,还有些怀疑,担心它会不会是狼的眼睛。因为我们从小听说过许许多多有关狼的故事,知道狼的眼睛在夜间是会发光的。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一个有关狼的故事,还见过故事里的主人公。原来,在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女人幼年时曾经遭遇过狼害。论年龄,她该是我们的长辈了。我对她的记忆,就是一个孩子对大人的记忆。我至今还记得,她的那张脸上,只有半边是完好的,她的那双眼睛仅剩下一只了,另外的半边脸,包括另外一只眼睛都成了一大块十分难看的紫红色的伤疤。据说,那女人在一岁多的时候睡在摇篮里,大人仅仅离开了一小会子,她就被藏身于屋边茅草丛里的狼趁机舔了一口。狼,并没有咬摇篮里的那个孩子,它好像想跟那孩子亲热一下,不过,狼的这种亲热是非常残忍的。狼用它那带有倒钩利刺的粗糙舌头,只是在她那张粉嫩的小脸上轻轻一舐,她的一只眼睛顿时就没有了,半边脸蛋上已是一片血肉模糊了。所以,小的时候,在村子里一见到这个女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会立刻想到了狼,大伙儿都对狼有一种恐惧感,总觉得狼离我们很近,似乎狼就躲在我们的身边,稍不留神,人就有可能被狼“亲热”。
想到了狼,再去看那个如豆的亮光,我就有些不寒而栗了。待我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又觉着不对,认为那个小小的亮光应该不是狼的眼睛了。因为,狼的眼睛是一双,亮光就该是两点,而不是一点。再说了,咱兄弟俩都发现了那点亮光有些忽远忽近、明灭飘逸的感觉,很像是煤油灯火被风吹拂过的那种飘忽情状。那年头,农村人家点的还是煤油灯,而且,煤油很紧张,只能凭票限量供应,有钱也不能多买。人家的灯也只好省着点,不能点得太亮。太亮了,觉得浪费,让人心疼。至于电灯,那还是个稀罕物,只有城里才有,离乡下还远着呢。把那个亮光的问题想清楚之后,我对堂弟先成说,不对,那不可能是狼的眼睛,那应该是一盏灯,一盏煤油灯。黑夜里的行人,突然发现前方有灯光,人会感到十分惊喜和胆壮。有灯光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人家。走,我们过去,去找找那户人家。
在黑暗中慢慢地摸索着前行,大约走了十多分钟,我们终于靠近了那户人家。站在那户人家的窗户跟前,可以清楚地看见窗户里面摇曳的煤油灯火,还有围坐在灯下吃饭的那一家老小。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之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叙话,一边吃着晚饭,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让人好生羡慕。平时,天天在家里享受了那种幸福,我为什么浑然不觉呢?
想到这些,我忽然想家了,我想掉头回家,不去王河了。我恨不得一步跨到家里。王河是什么地方?就算那里是天堂我也不想去了,我只想回家。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从家里出来,已经整整走了一天。现在要回家,同样,少不得还要走上一天。那一瞬间,我陡然觉得我的眼窝子有些热乎了,还有些潮湿感。我吸溜了一下鼻子,稳了稳自己的情绪。这时,屋子里饭菜的香味都已经从窗户里飘了出来,被我深深地吸进了鼻腔里。堂弟先成也已经被屋里的饭菜香味所打动,好像他的嘴巴里在偷偷地吃着什么东西,喉咙里不时地发出“咕咚咕咚”的吞咽声。其实,哪有什么东西可吃呢,先成吞咽的是自己的口水,那些很不听话源源不断冒出来的口水。兄弟俩这才强烈意识到,我们迫切需要一顿晚饭了。可能,是我们在窗外吸溜鼻子、咽吞口水的动静过大,惊动了屋子里面的人。也可能,是屋子里面的人偶然一抬头发现了窗外的人影,受到了惊吓。屋子里,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突然放下饭碗,十分紧张地对他妈妈说,妈,你快看,窗外好像有人。他的妈妈扭头朝窗外一望,大吃一惊地叫喊,谁在窗外?女人的声音明显地带着些颤抖,估计,她被窗外两个模糊的人影惊吓得不轻。
有一句话说,你在明处,人在暗处。从这句话里,你可以领悟关于明和暗的某种关系。人从暗处看明处,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若是从明处看暗处,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总会模模糊糊,甚至觉得暗处是些魑魅魍魉,让人胆怯。比如这户人家的女主人。这事,完全不能怪人家胆小,怪只怪两个无助的少年过于莽撞了。黑夜里,忽见窗外站着人,谁遇见了这等事,谁都会受到不小的惊吓。在吾乡人的心目中,大夜晚上,不在家里睡觉,却站到了别人家的窗前去,一定不是好人,不是鬼,便是贼了。那时,两个少年还不明白这些道理,若是知道这些,他俩绝不会不声不响地站在人家的窗外。至少,会主动地喊上一声“大爷”或者“大娘”。然后,开始向人家问路。
很快,背朝着窗户坐在桌边闷头吃饭的男人,他该是这户人家的男主人了,起身离开了饭桌。这个男人还算冷静,没有一点惊慌失措的表现。他端着饭碗出了后门,绕到窗户外面,站到了两个少年的面前。他一看,他面前站的是两个半大的孩子,男人的表情更加放松起来,丝毫没有被惊吓的痕迹。
此刻,兄弟俩完全是一副做错了事的模样,见了那个男人半天不说话,不敢抬头看他。这个中年男子,态度很和蔼,一看他就是个很有善心的人。他问兄弟俩,你们都是谁?怎么会在这里?话音未落,堂弟就急急忙忙地用手指头直捣我的后背。我当然知道堂弟的意思,他是在催我赶快说话,别等人家下了逐客令,把我们赶走。那样,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们可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其实,堂弟不催,我自己也会急的。黑夜里,顺着一点亮光找到这里来,见到了这一户人家,容易吗?我很清楚,这样的机会,在那样的夜晚只有这一次,不会还有第二次。于是,我就顺着中年男人的问话回答说,大爷,我们俩兄弟不是坏人,都是学生。我们路过这里,是要去王河的。天黑了,我们迷路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离王河还有多远呢?中年男人显得很吃惊,对兄弟俩说,你这两个学生娃,胆子也太大了。天都这么晚了,还要去王河?那地方可远着呢,足有二十里地!咱这里是望虎墩大队,属于罗汉公社,还在梅城区呢。啊?离王河还这么远呀?我还以为快到了呢。我的语气中透露了自己的意外和无助。中年男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十分友善地说,进屋里说吧,别站在外面了。
进了屋子,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也就是刚才被惊吓的那个中年女人,放下手上的饭碗,立即起身离开饭桌,去倒了两碗茶水,一手一碗,端了过来,递给我和堂弟。我和堂弟早已又饿又渴,一碗热茶到手,已经顾不得什么叫斯文、什么叫客气了,端起碗来,一口气“咕咚”了几下,就让那只很大的茶碗见底了。女主人见状,看了男主人一眼,于一瞬间,夫妻二人好像对了一个眼神。就在那一瞬,我发现这位女主人的眼神里面充满了仁慈和爱怜。接着,女主人轻声细语说,哎哟,这两个小兄弟还没吃晚饭吧?咱锅里还有饭呢,我这就给你们盛去。
女主人转身去了厨房。很快,她就从厨房里回来了,手里端了兩碗饭,还是一手一碗。是那种蓝边陶瓷碗,碗里的饭装得满满的。碗很大,原本应该是用来装菜的,并不是用来盛饭的碗。那情景,让我们兄弟俩感觉既迫切又非常不好意思了,我心里头还想着要谦让一下,但根本没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出来,我和堂弟就立即同时站了起来,伸手去接过了女主人手中的饭碗。两个少年异口同声说,谢谢大爷大娘!
饭没还送到嘴边,我就先闻到了一种特殊的饭香,是那种菜饭合煮的香味。低头一看,饭的颜色呈浅紫色,饭米粒中间夹杂着一些淡红色的豇豆皮,还有一些紫红色的豇豆籽。我立刻明白过来,那是一碗豇豆煮饭。是用大米和一些成色很老、结了籽粒的豇豆一起烹煮出来的。煮熟之后,将米饭和豇豆拌匀,用锅铲子反复擂捣挤压,直到把豇豆捣烂,只剩下一些小块头的豇豆皮和豇豆籽,均匀地拌在饭米粒里面。这样的饭食,我以前在家里也吃过好多次,妈妈也喜欢做这样的饭食,吾乡人把它叫作菜饭。那年头,一般人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只得多种点蔬菜凑一凑数,帮着填饱肚皮。煮一锅菜饭,比起一锅白米饭来,毕竟会节省不少大米。而且,还省时间,又省柴火,饭和菜一锅煮熟了,多省事。习惯于这样做饭的人,在那个年头,必定都是一些很会过日子的人家了。不过,这在当时,也是被形势所迫,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好办法。
那晚,我和堂弟面对着那碗豇豆煮饭,根本没有多想,端起碗来就扒,三下五除二就扒完了。好像都没使用牙齿,只用了舌头的来回卷动,很快就全吞到肚子里面去了。当时,我只觉得那顿晚饭吃得格外香,吃得特别爽,比以前在家里吃的妈妈煮的豇豆饭,还要香,还觉得好吃。那碗菜饭的味道,让那两个少年感觉到从未有过地好吃。后来,在家里,我还多次央求妈妈做过那种豇豆煮饭,虽然也很好吃,但是,吃起来味道还是不一样,根本不是那户人家那顿晚饭的味道了。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在那户人家那顿晚饭的味道,于我来说,不仅空前,而且绝后了。甚至,在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多少往事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水,不知道流到什么地方去了,记都记不清楚了,更是无法找回。唯独,我对那碗豇豆煮饭的味道,一直记得一清二楚,仿佛就是昨晚的事情。
吃完饭,那家的男主人发话了。他端着一副长者的腔调说,两个学生娃,你俩今晚不能走了。路途遥远,天又黑了,你俩走在路上不安全,我们不放心,还是等到明天天亮以后再走吧。今晚,你俩就在俺家歇一宿,跟咱小虎子睡一张床。说完,中年男人拍了拍那个和我们一般大小、长得很敦实的小男孩的肩膀,正是那个小男孩首先发现了站在窗外的兄弟俩。那个小男孩就是这户人家的儿子,名叫小虎子,一顿饭的工夫,小虎子就和我们熟络了,眼睛里流露的不再是惊恐,而是友好,是亲热。他的父亲说过之后,小虎子朝着我们兄弟俩看了一眼,莞尔地笑了,脸腮上露出了两个很好看的小酒窝。尔后,小虎子对着他父亲点点头。他点得很有力,点得幅度很大。这时,我们兄弟俩又一次异口同声地说,谢谢大爷大娘!
5
第二天清晨,兄弟俩早早地起了床,谢过大爷大娘这两位恩人,又和小虎子紧紧拥抱,三个少年相拥在一起,抱成一团,久久不愿意分开。之后,兄弟俩重新上路,照着恩人指点的东去的方向,快步前行。有了那一顿喷香的晚饭,再加上那一宿的睡眠休整,兄弟俩的体力完全恢复过来,步行的速度如同头天出门时那么快。几乎是一路小跑了,路上很少歇息。大约是在半上午的时候,我和堂弟终于赶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王河。那个地方,虽说王河是区公所的所在地,集镇并不大,随便问了个人,就找到了我们需要找的那个人。
对了,前边说了这么多,该是说清楚了两个少年是怎样到达王河的,但是,我还没有说这两个少年为什么要去王河。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交代一下。否则,会让人产生错觉,觉得这两个少年,简直是疯了,性子也太野了吧,竟然毫无目的地满世界乱跑。
其实,还真的不是那么回事。那次去王河,兄弟俩真的是有事情,而且还算是个正儿八经的事情。
我们兄弟俩有一个共同的堂叔,他原先在部队服役,后来退伍了,在王河区供销社工作。有一次,堂弟先成于无意中听堂叔说,他们那里有个书店,就在王河供销社的隔壁。书店里有很多书,他和书店里的人很熟悉,一有空他就去书店里翻翻书,有时还借了书回来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堂弟在羡慕堂叔的同时,当场就有了自己的主意。他想,一定要找机会去一趟堂叔那里,越快越好,让堂叔帮忙买几本书回来。堂弟怕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大,不足以说服他的父母给他放行,于是就拉了我入伙,让我跟他一起去。
恰好此事正合吾意。他跟我一說,我只说了一个“好”字,再没说其他一个多余的字。兄弟俩真的是一拍即合了。那年,我们都是刚刚上初中,看到别的同学有课外书籍看,心里痒痒的,觉得能有一本好看的课外书捧在手里,真是太幸福了。所以,有了买书的机会,我们当然不会错过,兄弟俩当即约定了出行的时间。年少的人总归就是这样,遇事说干就干,不能等待,似乎一刻也不能拖延。
放行非常顺利。那天,我们回家分头去向家里大人报告情况时,家里大人也觉得出去买书是件好事,家里不反对。何况,又是兄弟俩一起出门,一路上有个伴,而且还是去王河找自家的堂叔。虽然路是远了些,兄弟俩也都还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两家的大人们还是表示放心,愿意让孩子出去闯一闯,就准许了两个少年一起出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的家乡虽不富裕,但大人对孩子念书的事从来都是看重的,甚至被看成了头等大事。有了这样的背景,关于孩子提出了有关书的话题,大人一般不会说不。
在王河供销社的大院里,堂叔意外地见到了这对兄弟俩时,他一下子完全惊呆了,他是彻底愣住了,好久回不过神来,好像不认识这对兄弟似的。过了半晌,堂叔才问兄弟俩,你们怎么来了?应该说,两个少年这趟远行,完全是冲着他们的这位堂叔来的,一路上又饥又渴又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兄弟俩只要想到了“王河”或者“堂叔”这些相关的字眼,兄弟俩总感到热血沸腾,信心百倍。果真到了王河,站在了堂叔的面前,这对少年兄弟俩又突然扭捏起来,只是低头傻笑,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堂叔已经从惊讶情绪中完全走出来了,他表现出来的完全是长辈的关心和爱护,开始对兄弟俩问长问短。堂叔问一句,这兄弟俩才回答一句,挤牙膏似的,挤一下,冒一点。堂叔终于知道了,这兄弟俩还是在昨天早上出的门,全凭着两双腿走到了王河,而且,半路上,还在一户陌生的人家吃了一顿饭,借宿了一夜。堂叔又是心疼,又是后怕。他用略微带有埋怨的口气说,你俩要来王河,我是欢迎的,但也该提前跟我说一下,好让我回去带着你们一道来呀。你们看看,两个小孩这个样子跑过来,要是在路上出了个什么闪失,我可怎样向我的哥哥嫂嫂们交差呢?这样吧,来都来了,就不说了。你们从这里回去的时候,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心任由你俩再走着回去了,我得把你俩安全护送到家。
堂叔留了这对少年兄弟在王河住了两宿,让兄弟俩在小集镇上玩耍了一圈,还带着小兄弟俩到了隔壁的书店里,为兄弟俩各买了两本图书。到了第三天,堂叔果真请了假,还找好了一辆过路的顺风车,是一辆前高后低装货的平头大卡车,车厢是空的,我们叔侄三人一起搭车回家。那年代,能搭乘汽车,真是一件快活事,哪怕只是一辆载货的卡车。来时,我们兄弟俩曾经用脚步苦苦丈量了十几个小时,还在一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家里借宿了一夜。回去时,搭上了顺风车子,还不到两个小时就到家了。
当年堂叔给买的那两本书的名字叫什么,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那年头,书店里也不可能卖出什么能让人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书。那时的书,内容上无非大同小异,甚至还会千篇一律。
我始终牢记的,是那个黑暗的夜晚,在那个陌生的三岔路口,我突然发现的那一点如豆的亮光。还有,收留我们过夜的那户人家仁慈善良的男女主人,那个接纳我们跟他同眠一床的少年小虎子。尤其是,我们饥渴难忍时,那一碗让我们一饮而尽的热茶,那一碗装得满满的,吃起来特别香的豇豆煮饭。
6
人就是这么奇怪。发生在少年时代的事情,人在青春少年时,往往不以为然,甚至习以为常。只有人到中年了,回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某些往事,人才会想到,有一些心愿需要做个“了结”,而且十分迫切。
几十年后,这种想做“了结”的心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所以,每次见到了堂弟先成,我就不能不想起少年时代的那次远行。我多次嘱托堂弟,让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望虎墩的那户人家。我和堂弟先成约好,一起过去回访那户人家,好好地感谢人家当年的关心爱护和救助之恩。尤其,我非常想念那个小虎子,他应该和我们一样,也是早已人到中年了。可是,他在我的心目中还是当初的少年,一副虎头虎脑的模样,憨厚可爱。我好想再次见到他,再喊他一声好兄弟,然后,再像当年的三个少年那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也不分开。
这些年来,我曾托过不少人,去打听住在望虎墩那家恩人,反馈回来的消息都让人失望。后来,我还是想到了堂弟,我就把找到那户人家的希望,寄托在堂弟的身上。我很早就离开了家乡,几十年来,辗转在江淮平原上,漂泊在异地他乡。堂弟比我过得安稳,他一直生活、工作在家乡,家乡的人,他熟悉的一定比我多很多。所以,我想他肯定比我有办法,一定会找到那户人家。
懵懂少年的那次远行,陌生之地黑夜里的那一点亮光,恩人赐予的一碗热茶,一碗喷香的豇豆煮饭,三个少年同眠的一张木板床,给了我不灭的记忆,永远的回味,一生的牵挂,让我感恩终生!
等待,耐心等待。我一直在等待来自堂弟先成的那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2016年4月3日写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