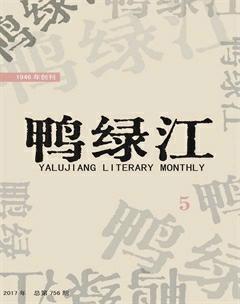乌兰以西
李万华
1
如果从高处去看,会看到大地上的色彩与色彩之间,存有鲜明界线。一种色彩如何结束,另一种色彩如何开始布局,似乎都有安排。然而站在大地之上,色彩之间这些清晰界限何以接替呈现,会时常忽略。有时正沉浸在一种色调当中,认为世界将会始终如此,无以改变,蓦然抬头,发现眼前景况已经变幻。有时,甚至连这种显而易见的变化都看不到。人走进这种变化之中已经多时,脑际徘徊的,依旧是先前风光,仿佛大脑也在遵循惯性运动。乌兰以西,接近德令哈时,草原如何被荒漠接替,便是如此。
或许是路边花朵让人注意到这种改变。此前路边还开着半卧狗娃花,这些喜欢干旱和阳光的菊科植物,有着细长叶子和淡蓝色花瓣,有蓬大而金黄的花蕊。我曾在河湟谷地一些极度缺乏水分的山坡看见另一种阿尔泰狗娃花绽放,在那些尘土足够覆盖鞋面的地方,它们大丛生长,植株高到一尺以上,叶子稀疏,覆有尘土,但是小小花朵清爽秀丽,惹人欲去采摘,又不忍采摘。在乌兰以西的公路旁边,我见到这种菊科植物,植株已经矮小到只有五寸左右,花丛变小,有时只是单独一两株,勉强开出单薄花朵。我曾下车,以微距方式拍下这些花瓣,只为简单存念。等到发觉路旁狗娃花被一种红色匍匐植物取代时,才发现远处草原,已被荒漠替换。这种悄无声息的变化,仿佛因为歉疚和惭愧,而不敢放声喧哗。可是,大地上发生如此鹰化为鸠的变化,居然无人察觉,一时又让人觉得无比怅然,这不该是大地惯常的做法。狗娃花倏忽遁去,草原植物被一些色泽不够明确的荒漠植物取代,仿佛瞬间换了一个星球。
这些荒漠植物为了减少水分蒸发,已将叶片变得窄小细长,有些叶片,甚至已经成为针形。无法越过高速路上的护栏,只能从远处去猜想它们,它们或许正是常见的那些荒漠植物:柴达木猪毛菜,驼绒藜,唐古特白刺,沙拐枣,梭梭……有人说,它们属于人工栽植,为了固沙防沙。是否果真如此,不得而知,但这种说法先入为主,当我仔细去看,它们果然如同刚刚布局的棋子,一丛一丛,在广漠的大地上分布均匀,从无拥挤或者大范围遗忘的情况出现。它们的色彩,也和大地一样,浅褐,或者枯黄。我猜测可能是时节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因为裸露的地面太多。我对这些地方,并不熟悉,也不曾多次往返,得以窥见人们劳动的场景。若只依靠想象,断然想不出人们是怎样以栽种植物的方式去度量如此广袤的土地,只能偶尔现出一些劳作的身影,然而那身影,又只是米勒画作中那些永远躬身面对土地的人。
以为水从此便在这里消失,再不肯光顾,哪怕只是以雨的形式,以露的形式,以雪花的形式和冰的形式,以及,以蒸汽的形式,可是,在靠近遠山的地方,湖水又突然出现。水为何总会和山一起出现,偶一发问,答案即显,因为山无处不在。这块高原原本是水的高原,后来才又变成山的高原。乳白的,浅蓝和深蓝的水,一汪,或者一线,仿佛一声微茫的呼唤,穿越荒漠上的热气和耀白光线而来,让人扭转脖颈,暗自欣喜。待到凝神,它却又不管不顾,抽身离去,仿佛与刚才无关。扒着车窗户,看那些现出又远离的水,依稀明白世间诸种出现,只为离去,存在只是一个微细过程,匆忙,而且慌乱。
2
很多时候,我会想起那些山,那些满是褶皱的山。起初见它,曾有视觉和概念上的强烈冲击。我惯常见到的山,已经有定势存在,它们如何出奇,似乎都逃不脱山的概念,然而在走向德令哈的路上,这些概念一一被摧毁。车子向前,路两边迅速闪过的,那些山体的色泽,无法一下看穿,只能凭眼力判断,是深黛、暗褐还是浅紫,似乎都是,又都不是。起先以为是暗褐,但是太阳光线一转,暗褐亮丽起来,成了浅紫,若说那就是浅紫了,沟壑部分的色彩却又黑起来,仿佛是深黛,又带点苍黑。如此迷乱,无法做出肯定,只得改变关注点。脱离色彩,眼前所显,全是褶皱。那么多的褶皱从山脊披离下来,密集,并且显得酣畅,仿佛干草搭在墙头,刚刚被雨水浇透,又仿佛,有大手,将那些山坡折叠起来,压出印痕,然后像一柄扇子那样撒开。后来,我将那些褶皱想象成外星人脸上的皱纹。然而若说它们是山的皱纹,历经漫长岁月,渐渐形成,又不尽然。因为那些山峰,并不显得苍老,它们耸立在近处,仿佛有人正在将它们揪起,像揪起一堆带着褶皱的深色丝绒布。
要知道,对一件事物的描写,若用尽各种比喻和想象,并力求新颖奇特,那只能说明,描摹者并无多少能力,能直接对这一事物做出恰如其分的描写,他只好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依靠和借用一些不确定,来模糊这一事物的形态和特征。这一种表达方式,看上去似有讲究,显得典雅柔婉,但实际上,表达不过似是而非,大致若是。
那些山似乎与任何生命无关,尽管我看见那些褶皱中,隐藏一些深色植物,但那些植物或许已经干枯。那些山只与时间有关,那并不仅仅是过去的时间,还包括未到的时间。但是我们明白,时间不过是一种概念,它只与物质的变化有关。兜来转去,那些山,实际只与它自己有关。它如何出现,怎样运转,何种变化,无人看得清楚,便是前人后人轮流去看,也不过是盲人摸象,只有局部。它的存在始终孤单。尽管如此,我还是会记下它们的名称,宗务隆山和牦牛山,它们依旧是祁连山这庞大山脉中段的南北两个分支。
我同时会想起那些骆驼。那不是羊群那样以群出现的骆驼,而只是几只。便是几只,也非随处可见。大荒原上,总是行走很久之后,才出现那么几只,在那些同样看不清色泽的草棵之中。它们在那里,除去低头啃食那些荒漠植物,再无事可干,有时也会抬头一望,望向山野和荒原。那引颈一望的姿势,显出旷古忧伤。但在更多时候,它们显得闲淡放任,不关心任何事情。我从一旁望去,倒是种种担忧。夜晚归向何处,碰到袭击者如何逃脱,是否被人饲养,如果不用来载重和骑乘,它们的生理结构是否会改变……
我还会想起那一群黑色的大鸟。那只是偶尔见到的一群,一路之上,也只是见到一次。它们大约从荒漠起飞,飞到高处,忘却方向,只好来回往复。它们并不旋转,排除掉乌鸦的可能,它们扇动翅膀的样子,如同海鸥。它们的背景是那些带着褶皱的山脉,底色单一,从远处看去,它们如同一些缥缈无际的念头。
有人说,人心只是一堆念头的来来去去。但那只是被习气熏染之后的情形,我们的初心,如同平静之后的浩瀚大海,偶有一些念头,也不过是那平面之上的些微涟漪。
3
阳光不仅有斑斓色彩和多种形状,而且拥有气质。荒漠上的阳光,直率果敢,胆汁质那样,形状也是固定不变,大片摊开在地面上,单一到让人惋惜。进入德令哈市,阳光瞬间沉静起来,带些寂寥。其实,太阳还是那旧日的一轮,天空也未曾变更,若说事物有何鲜明的不同,也不尽然,但某种变化还是显而易见。
高速公路向右一拐,路旁有大棵白杨树栽植。这些挺拔树木神情严峻,似乎始终都在提高警惕,想来也是一种喜欢自律的树木,不懂嘻哈世间,不懂逍遥风尘。若说白杨果真如此寡淡乏味,又有例外。如果白杨长得足够高大,夏季叶片手掌一般撑开,一阵风过便是一片银光之外,树叶会在风中发出萧萧之声,那时若如静坐窗前帘后,很有江南夜雨唐宋边塞的萧瑟之意,有时,甚至会有“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的悲凉。与白杨一同挺立的,还有路灯。若在以前,路灯杆子通常低矮,间距较大,夜晚到来,灯光一缕昏黄幽暗,人在街头走过,很有聊斋的鬼魅味道,有时让人怀旧。但现在,这样的路灯再难见到。
德令哈的阳光,并非为这些蓦然出现的白杨树和路灯而改变,我从它们身旁经过,发觉阳光在那里依然显示着简单直率的一面。之外,便是那些大型建筑,是否是它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同样从它们身旁经过,那些以灰色和象牙白为主调的高大建筑,显然精心设计,在竭力体现个性风格的同时,注重端然大方和凝重庄严,这种强调,明显突出与四周环境的和谐与默契。矿业部门,会议中心,体育中心,学校,研究院,名曰“蓝天白云”的大酒店,以及各种宾馆和住宅楼,它们端坐在这块名曰德令哈的大地上,长时间沉默。因为是新建城市,有些建筑尚未有人进驻,大门紧闭,绿化带植物长势旺盛,一些野草,依墙披离。
后来,我终于明白,让阳光显得沉静和寂寥的,并非那些植物和硬性设施,并非阳光它自身,而是人。
坐在步行街前面的小广场上休息,正是傍晚时分,太阳已经西斜,白日太阳的烘烤早已消减。如果在其他地方,日暮前的时刻,步行街一定嘈杂,人们忙着采购,忙着回家做饭,买者卖者,都会高声大气,饭馆也会顾客盈门,车辆拥塞。但在此处,一派萧疏。我坐在沙枣树下的椅子上,看人们来去,然而在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内,只有寥寥数人路过此处。他们多是回家的中学生,穿着校服,塞着耳机,也有老人结伴,躬身而行,年轻的夫妻,专注于话题。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冷清,风过时,沙枣树发出大的声响,零星叶子旋转而下。
在体育中心,我看到人工布置的花坛上有“激情柴达木,魅力德令哈”几个大字,可能是某项活动刚刚结束。亦有零时搭建的大型帐篷,里面摆满书籍,原来正在开展读书月活动。走进帐篷,兜转于各个书摊之间,试图淘得一两本,然而此处依旧如同其他书店那样,摆放的书只以学生的各种辅导资料为主,也有营养保健、烹饪和一些畅销书,文学书籍以青少年版世界名著为主。终于找到一本图文本《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卷数不全,只有下册,算是诸多书籍中的另类,决定买下。
夜晚很快到来,这应该是德令哈无数清寂夜晚中普通的一个。正是中秋,在如此空旷广漠的地域上赏月,该是难得的机会。然而云层一直密布在东部天空,丝毫没有退去的迹象。眼前的大街,只是清阔,街边树木在路灯晕染下,是庞大漆黑的一团,树影斑驳,风过时,影子在地面跳荡,仿佛一群来自春天的小兽,偶有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当街而过,车轮带起的,是一缕无可名状的草木清香,片刻沉寂后,依稀有乐声自远处传来。
4
怀头他拉,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种音韵学上的美感,抑扬顿挫。原是蒙古语,意思是西南的庄稼地。想必很久以前,此处也曾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然而,那会是多久之前呢,在怀头他拉几幅岩画前,我发现已经无法用惯常的方式去理解时间。岩石之上,是一些拙朴的刻画和描摹,来自动植物,以及人类。腰线细长、正在疾驰如飞的狼或雪豹,犄角锐利、身型健壮的野牛和马鹿,温顺的羊正在低头啃食青草,三马架套、志在必得的猎手,飞矢划出精美弧线,相依相偎的阴阳鱼,骑马之人,神情专注的男子和女子,后来出现在佛陀胸部的“卍”字,某种沐浴在阳光下的强劲植物,狩猎,放牧,追逐,休憩,舞蹈……千年前的种种存在,被观察,被记忆,并在坚硬的岩石上,由另一种石器仔细磨划。那些场景,构图精简,寥寥数笔,但是活泼,泛出神采。
岩石之前,时间自今而昔。想那定是天空明澈、陽光温煦的一些时日,高大山脉在远处连绵,山顶积雪发散幽微蓝光,风从山顶披拂而下,漫过原野,翻动草木,掀起阵阵凉意。大地苍茫寥廓,丰茂植物正在生长,草色之中,蓝色湖泊如同珠宝镶嵌。另有一些河流,正在缓慢流淌,静谧水面银光泠泠似有声响。一场狩猎在远处进行,静伏,呼喊,奔腾突围,健壮男子裸露肌肤,阳光已给他们镀上某种金属光泽。近处,女子、孩童和老人守着生活营地,炊烟熄灭,然后升起。母系时代早已过去,女人从某些繁重劳作中解脱出来,开始纺织烹饪。石纺轮,牛羊毛,植物纤维,烧制的粗陶器皿,采撷和种植一些果蔬,编穿珠贝,沿着河谷找寻彩色石子,这些细微,足够忙碌一个整天。老人并不太老,仍旧躬身劳作,孩童赤足,嬉闹之中种种模仿学习……时间缓慢,如同从大麻上剥下纤维,每一件事情都认真对待,话语可以和笑声一起传到远处,夜晚到来,天空被篝火映红。
如此想象,如此关注这些穿越时间却依旧烂漫的画面,我似乎也是其中之一:没有过度文明熏染,没有无以名状的偏执和奢望,一些习气尚未形成,太多烦恼亦未生起,没有过去之心,也不在乎未来之时,注重当下刹那,明白错失便是永久。劳作,爱,安眠,死亡……时间到底是何事物,我伸出手,可以触摸亦被他们触摸的岩面,可以感受他们曾经的愉悦和惊奇,以及强大持久的想象力,但我们的心,为何早已如此不同。
何为逝去,再不相逢,何为永存,亘古常新,一念而东,一念而西,刹那变幻,总成万年。这样的迷局,早该破解,然而沉陷太深,任谁都逃脱不掉。考古资料说,这些岩画创作时间是北朝后期到唐朝时代,那正是任意随心,却又简单纯真的年代。
可鲁可湖畔,我同样被时间迷幻:我所面对的湖水,并非千年之后,而是千年之前。当是千年之前的中秋节气,秋气并未凛冽,但是秋风早已瑟瑟,云在天空,已经散成絮状。雪也已经降临,罩着远处山头,仿佛杨絮层层堆积。湖畔芦苇已经黄去。这些芦苇,曾经青葱年少,曾经芦花似雪,现在,它们成为另一种色泽,仿佛换了一套思想体系,与昔日旧有彻底决裂。巴音河自东南而来,缓缓注入湖中,仿佛一条游鱼,湖水又从西南流出,进入另一湖泊(托素湖)。风偶尔凄紧,但是湖水依旧平静,依旧清明,天光云影,倒影其中,另一层芦苇,正在向湖底生长。我似乎一直坐在湖畔,风不曾吹乱黑发,湖水也不曾打湿双脚。曾经有人捏着木叉来湖中捕鱼,他们赤脚,俯身湖面,静无声息。也曾有其他女人,来到湖畔,用陶罐汲水。她们结伴而来,似乎并不急着汲水回去,她们将陶罐放置一边,临水梳妆。也有孩子,跑来嬉戏,蓄养的牛羊,曾来湖畔饮水,黑颈鹤和斑头雁曾在天空低翔。只是这一时,他们都已归去。鸟归巢穴,牛羊回到草场,孩子或许已经熟睡……湖畔静谧,再无其他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