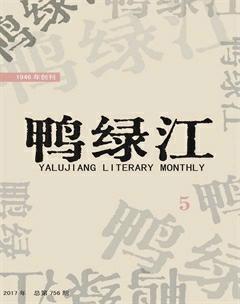邮寄版错觉
陈艾昕
在爱情的事上如果你考虑起自尊心来,那只能有一个原因:实际上你还是最爱自己。
——《月亮与六便士》
1
差不多在十六岁零三个月,小艾姑娘迷恋上毛姆这个“二流作家”的同时,也发疯似的喜欢上了一个学长。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荷尔蒙爆炸的年纪,曾经的“花季雨季”形容都似太过单薄直白,可女生的单纯爱恋却依然那么傻气,期待着别人知晓后暧昧的调笑,又害怕他们口无遮拦闹得人尽皆知。
进退维谷,举步维艰。
每个念头都百转千回,半遮半掩,像是一个熊孩子,依仗着你抓不住他,在你本就脆弱的神经上玩着蹦极。
所以毛姆说,爱情是一种疾病。艾姑娘捧着心口幽幽地对我们复述。
一见钟情大抵是绝症了,但好在她有我们,就像武侠小说中出现的世外高人,总是在主角要死的时候,给他来个绝处逢生。然后继续期待着他下一次垂死,以此来刷个镜头感。
就这样,凭借着我们搜集来的二手、三手等等不知到底是几手了的消息,艾姑娘渐渐拼凑出来了在他容貌以外,那个她所未知的他。
艾姑娘的玛丽苏之魂熊熊燃烧着,在看过他一眼之后,就已经脑补出来他们俩将来孩子的模样。粉红色泡泡一个接一个从没了大脑的她的身上迸发,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糊到我们身上。
听说学长英语次次是第一,近乎满分。外教课就是他和外教两人的相声表演。
只是为了能有一种离他很近的错觉,只为了那好像可以沿着他的脚印向前的错觉,艾姑娘每天抱着新概念四啃啊啃。
她明明在原地自我燃燒,却固执地觉得自己在追逐太阳。
而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看着艾姑娘和学长每天在食堂刻意地偶遇,然后跟着人家,继续在小卖部刻意地偶遇,接着顺理成章在男生宿舍楼下照章复习。
那时我们不知道学长是不是真的知道小艾姑娘的存在,会不会反感她对于他近乎骚扰的接近。其实这些对于当时的她来说,好像都不重要。没有人去点破,或者说,大家也被这近乎偶像剧男主的光芒闪成傻叉了,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直到那天。
晚自习上到一半,艾姑娘神神秘秘地叫我到走廊。出去之后,我看见美晨站在内侧窗台那里写着什么,仔细看发现“扑倒学长攻略”几个大字用荧光笔加大加粗地在A4纸的页眉上飘着,欢喜得要飞起来。
我难以置信地问艾姑娘到底要干吗,她眨了眨眼,开心地说:“我要去找他借他不用了的CAP笔记!然后顺便介绍下我自己。”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学长的CAP学的是线性代数,而艾姑娘二次函数都还没算明白。可事实上我的意见对她来说毫无用处,她一向只听取和自己想法相符的意见。
我叹口气,“好吧,那你注意些,别表现得太过热切,那样的话……”
她转身和美晨兴致勃勃地讨论开场白,没在听我讲话。
我转身回教室,想继续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里,可还是回头看向她。
于是,世界就这样没了声响。
光从四面八方反射过来,冷厉的白炽灯光和绒绒的月光交杂编织成网,罩住她,松松垮垮地束缚。
那是我对百分百纯粹快乐的艾姑娘最后一个印象,她背对着我,看着窗台上的大玻璃,掐着腰对着那漆黑的外景抑或遥远的路灯笑得春光灿烂,映出她的脸轮廓模糊,边缘几乎和黑暗融在一起,暧昧地过渡,光影蔓延向虚无的观众席。
我依稀听到了掌声,也许马戏团的红鼻子会喜欢这种掌声。
但谁能说,马戏团的红鼻子就会比哑剧演员演得更烂呢?
“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 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她喜欢的毛姆。
2
第二天,我和美晨陪着她去找了学长,远远地看着。他支着手肘倚在走廊窗台上,背对着窗,微微侧着头看向艾姑娘,艾姑娘身子朝向窗户,但却扭着头盯着人家看,从脖子根向上均匀地红着,像一只煮熟的软脚虾,我又担心起她一会儿就化成一汪春水,瘫在地上被保洁阿姨用拖布给拖了个干净。
我终于明白她昨晚为什么盯着夜空看,因为她想把星星都吸到自己的眼睛里,然后在和他面对面的时候,全部点亮。
回去的路上她却很沉默。到教室之后,她看看我们,诚恳地说:“我们只考虑到他可能不借我,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他从来不记笔记这种事呢?我又错失了一次还笔记的见面机会。真是失策。”
这第一幕出场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演得勉勉强强还算成功。心中埋下的种子生根发芽,然后破土而出,长出来个男主角。这幕戏,总算不再是酸倒牙的独白了。
艾姑娘继续开始心照不宣地偶遇,每天她掐着时间跑食堂,排在学长后面打饭,看着学长吃什么,她就大声对打饭阿姨喊:“下一份要一样的!”
等一系列套路进行完,她端着盘子跑到我们早就给留好的位置——学长邻桌邻座,硬生生凹造型。
把锅包肉吃成菲力牛排,蛋花汤喝成82年拉菲。
终于有一天,美晨受不了这辣眼睛的场面,瞄着她小声说:“人都没看你,你做作个什么劲?”
艾姑娘昂着她高傲的头,标准的央视微笑。美晨和嘟嘟说:“哈!你看那个熊色啊!”说着说着,学长那桌突然安静了,四个男生有三个盯着小艾看,只有学长,沉默着微笑,看着他的不锈钢餐盘。
我又听到了掌声,但这次是真真切切响在耳边的。
他们在鼓掌,而学长只是说了一句:“行了啊,走了走了。”
小艾的身子板板的,僵直得如同死去多时的猫。我们都想看小艾的表情,但她只是侧着脸,目送学长远去。半晌之后,回过神来,她看向我们。
癫狂了。
美晨和嘟嘟拍着桌子乐,艾姑娘撒欢地敲盘子。
我安静地看着她,试图微笑,可那笑容像水一样,泼在脸上还没被眉梢挂住,就支离破碎地顺着眼角滑落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艾姑娘来说,是高中生涯里最快乐的时光,学长的朋友们她都混熟了,她每天都可以和学长见面,可在她浓烈的欢乐之下,我感受到了她刻骨的自卑和疲惫的不安。
在学长面前,她只是一副灵动的画皮。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只是时间,过后,还是时间。显然艾姑娘不这么想,她如今就是一个糖做的蜜罐,碰到什么东西都是甜的,梅雨季不再是诗人的心事,是她看见他之后紧张又兴奋的心绞痛;烟灰色的雾霾不再是城市的马赛克,是他清俊身影上加的虚化背景;时间自然也就成了香脆的薄饼,椰奶味的,几下吃完,然后带着满口的甜腻,去收拾掉了一地的碎渣。
“‘生活是单调的,灰色的,而快乐是珍奇而稀有的。我们的死亡是漫长的。你看,文化人就是不一样,连无聊都可以形容得这么性感。”午休时候她略带忧郁地和我重复这句话。“你知道么,快高考了。就是……他们快离校了。”我看着她,秒懂。“所以……要聊聊吗?”我问。
那天下午我翘了两节自习课,陪着她坐在二楼回廊的窗台上。
偷偷地打开窗户,我们把腿伸出窗外,晃晃荡荡。
天空在我们这个老牌重工业城市忽然蓝得出其不意,云软得想让人撕下来当枕头,北方的夏初见端倪,风从学校附近的公园吹来,沾染着湖面暖湿的水汽绕过我们双腿,撩起了校服裙角;喧闹的街道上各种人声混作一团,天上的阳春白雪全都被揉碎,丢下来成为我们、他们、她们。隔着一条街的大型商场的音响超大声放着陈奕迅,过了一会儿又切成了五月天,可都是模模糊糊的让人听不清具体。
“有没有那么一首诗篇,找不到句点,青春永远定居在我们的岁月……”
“也许我们这代人,受了太多电视小说少女漫的荼毒,所以一切都在脑海中彩排得如此戏剧化,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代入感。我用了两个礼拜才说服自己,哦,原来他可能是江直树,但我真的不是袁湘琴。”
“但实际要命的从来就不是自卑感,我知道你看出来了,别装傻。”她扯了下嘴角,马尾辫吊得太高,发梢和风在她脖子上跳探戈,艾姑娘抬手松了发绳,头发华丽丽地披下来,被风吹得散乱。洗发水的清爽气息短暂地弥漫开来,转瞬即逝。
我笑开,想这气味会不会就像,我们永恒的爱慕。
“有一种灼心的感觉,让我贫穷又脆弱的自尊很明显,不堪一击。我痛苦的到底是什么?你相信吗,理智上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他在一起。”
“我不该爱上太阳的,尤其是当自己还是个太空垃圾的时候。连月亮都只是默默围着它转,太空垃圾怎么可能。太阳那么美,不该属于任何人。”
“做人的确应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开口,“所以你想说什么。”
“我……最可悲就是,我知道,知道自己的可笑,可我还是希冀拥有太阳。‘感情有着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
我和他现在,就像守着一地的玻璃碎片,在上面缓缓移动,我只能弯下腰,跪在地上窥视有关他的吉光片羽。
可暗恋之所以暗,因为恋它是在闭着眼。然后去走钢丝,云中漫步。摇摇欲坠,千钧一发。我恐高,不敢睁开眼,但又舍不得下面的风景。
“你可以明确地表示你放下自尊放下脸只是因为放不下那个人,可是啊,你想想,这自尊和这脸,都说放下就放下了,它能值几个钱?”
“我听明白了,你就是纠结,不敢上还不甘心。”她快哭出来了,我赶紧打断她逐渐语无伦次的絮语。她却坚定地摇头,“不是的……不是的。”接着喃喃道:“我得做點什么,他要走了。”
我看向她,她低着头,手指在大腿上乱弹钢琴。
然后突然抬起头,灿烂地笑了一下:“哎!不给我加个油啊!”
3
艾姑娘的表白最终没成功。
因为,是学长先开的口。
“他说,这种事情怎么好让女孩子说出口呢。我说,又没说让你当我男朋友,我就是夸夸你,真够不要脸……然后他就说,啊,那刚好我也觉得你还成,所以我让你当我女朋友,成么?”已经异化成粉色桃心怪的小艾姑娘托腮含情脉脉地说。
“他认真了啊!”美晨嗷嗷叫。
“那,中午我就和他一起吃饭去啦。”艾姑娘笑眯眯,像化开的香草冰激凌,不仅腻人,而且黏糊糊的。
我们本以为,事情会这样圆满地结束,从此王子和灰姑娘在城堡里没羞没臊地过上了开心的生活。
可上帝随手丢下的果核,随随便便砸碎了一只蚂蚁的幸福泡沫,刚好,她就是艾姑娘。
高考结束后没几天,学长带着艾姑娘在星巴克补数学的时候,一条匿名消息弹了出来,艾姑娘打开手机,发现是几张聊天记录的截屏。
“这种事情怎么好让女孩子来说呢?”
“做我女朋友吧!”
这熟悉的台词,到底是换过了几个对手戏的演员啊。
“你还想继续看吗?我这里还有呢。”
“喜欢他这么久,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我们形容你的吧。他说,你是他高中生涯里,最有意思的一个笑话。”
“你知不知道他有好多女朋友……我真的很可怜你。”
扣过手机,她抬眼看向学长,他正在改刚刚她漏洞百出的几何证明。
“哗——”一声,热咖啡有几滴溅到她手背,她从学长头上收回手,甩下杯子。收拾收拾东西,拎起书包转身离开。
“喜欢上一个人,除了一直自欺欺人,似是而非,徒增失落与自卑外,并无卵用。一见钟情更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我是被荷尔蒙控制的人偶,在自我欺骗中找寻爱人的感觉。”艾姑娘说。
“我只是爱上一种错觉,这错觉让我暗淡的生活有了些许光亮,我有了存在的感觉。”她接着说。
“当初一见到他就迷得无法自拔,事实就是,连对他外貌的喜欢都是一种错觉,就这样,开始了自我欺骗——他为我脑海中朦朦胧胧的爱情,塑造了一个真身。长着他的脸的,我的爱情。”
“于是而后他所有行为,都强行被我代入那个我心中学长想表达的意思,起初态度不清的确他很垃圾,可是如果我没有给自己希望的错觉,一遍遍加深‘他喜欢我吧!这种错觉,我又怎么像现在这样难过?”
“喜欢人很累,原因也许就在于此。这似是而非的错觉啊,每个暗恋的姑娘,都是特一级的自我催眠师。”
在我以为艾姑娘睡着了的时候,她忽然乐了:“诶,你说,如果我喜欢他一分钟便是个笑话,那他有开心六十秒吗?可能,我还不完全算是彻彻底底的错觉吧?”
那天晚上,艾姑娘微笑着抱着膝盖,侧卧在床上向我倾诉,宝蓝色的床单皱皱巴巴在她身下起了一层层涟漪。
她看起来像是一片海洋,浮在世界上,温柔但不可征服。这才是我所熟知的艾姑娘。
睡前她说:“世界上最大的折磨莫过于在爱的同时又带着藐视了。可是我不爱他,我只爱我想象中的那个学长。晚安。”
4
闹钟响了。我挣扎着从玫瑰色的梦境中爬出来。
昨晚挑了本毛姆看,太久不看书,居然枕着一页书睡着了。
然后我梦见了高中时代的艾姑娘,和那个学长。
艾姑娘在高中一毕业便又有了男朋友。
那段青涩又乱七八糟的时光就这样被随随便便丢掉,沉在岁月的长河里,我们每个人驾着生命船帆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我仔细读了读枕着的那页,上面写着:认为青春是快乐的,这是一种错觉,是那些失去了青春的人的一种错觉。
我认真回想,艾姑娘当时的感觉,其实很快乐,当全心全意生活在一个自己编织的谎言中,那么你便是这世界的造物主,一切都按着自己的心意发展。
只要谎言不被揭穿。
爬下床去洗漱,在晨曦的映照下,我在镜子中看见了艾姑娘的脸,和我的重合。我们一模一样。
这么多年过去,我早忘记当时的一些细枝末节了,没想到今天在梦境中一一浮现。
可这已无从考证真假了。
反正梦里开心的一直是她,不开心的是我。
可能……学长就是个错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