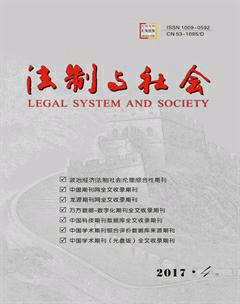论我国对被告人供述中隐蔽性信息的认知误区
于春洋+卢雨晨
摘 要 现代法治的发展要求对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力进行严格的限定,但当依据被告人供述中的信息提取到隐蔽性很强的证据或被告人供述中的信息与经调查发现的案发现场的隐蔽细节高度一致的情形出现时,庭审裁判者往往在内心确信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一般而言,这种判定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我国更是通过司法解释确立这一补强规则。但从近年来被曝光的部分错案中可以发现,对隐蔽性信息的认知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误区,而这对保障司法公正和被告人权利都将具有极大的消极影响。本文拟对这种误区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反思这一规则及其运行的司法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隐蔽性 信息 被告人供述 刑事错案 认知
作者简介:于春洋,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方向:证据法学;卢雨晨,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4.280
一、被告人供述中的隐蔽性信息
(一)强化被告人供述证明力的特殊补强规则
随着现代法治观念的普及和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口供不仅褪去了“证据之王”的光环,还普遍成为法治国家在刑事司法中重点警惕和审查的对象。一般而言,对口供审查的重点是其自愿性和可靠性,而口供的补强规则即是对其可靠性进行检验的一种方式,也是对其证明力进行限制的一种方式。“……根据自由心证原则,口供作为一项证据,其证明力应当由法官依据理性自由加以判断……但是根据口供补强规则的要求,只有口供是不能給被告人定罪的。这实际上是要求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情况下,否定口供的证明力,这就对口供这种证据的证明力加以了法律限制……” 以我国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意味着,我国在法律层面同样对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条件进行了限制。
但与大多数证据规则对口供证明力的限制和削弱不同,通过口供中的隐蔽性信息及依该信息获取的其他证据来确认口供可靠性的规则实质上起到了强化口供证明力的作用。我国2013年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这基本沿用了2010年6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这一规则的表述。这说明,通过对被告人供述中隐蔽性信息的运用,以 “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来对被告人的供述进行补强,并在该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之后,“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且这一规则已经拓展至死刑案件以外的全部刑事案件。鉴于“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之表述较为强烈的定罪倾向性,这一规则将在实质上作为强化被告人供述证明力的特殊补强规则而存在。
(二)隐蔽性信息对定罪的影响
所谓隐蔽性信息,是指被告人供述中蕴含的很难为案外人察觉而通常只有作案人才能知悉的案情信息,比如发生在隐秘环境中的非常态作案细节,尚未被人发觉的作案工具的埋藏地点等等。单从我国对被告人供述中的隐蔽性信息及依此获取的隐蔽性很强证据的规定来看,遵循的是“先供后证”的原则,即被告人供述出的信息尚未被侦查机关所掌握,侦查机关依据该供述获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书证、物证,再由这些实物证据对供述进行补强从而确定供述的可靠和真实性。有学者在解读这一规定时将通过隐蔽性信息获取的证据定义为隐蔽性证据,并为这一类证据总结出了多为细节性的间接证据、通常具有独特性、不易被发现或猜到、独立性强这四个特点 。但在现实中,被告人归案后在交代罪行时如果其供述与案发情况高度吻合,则其供述中的细节信息也足以使侦查机关确认其为作案人,这一效果在案件的审理者处同样适用。
因此,对隐蔽性信息的认定不宜简单的按照法条的规定去理解,而是结合现实,将包含隐蔽性信息的供述拓展至包含侦查机关已经掌握但尚未公开的、除作案人外其他人很难猜测的案件信息的供述在内。而在现实层面,被告人供述中一旦出现隐蔽性信息,往往成为所有审视案件的人在内心确信其为“真凶”的重要甚至主要依据。以聂树斌案为例,案发现场遗留的被害人的一串钥匙始终没有出现在法院认定的案件凶手聂树斌的供述中,却出现在另案疑犯王书金的供述中,这成为许多人认定王书金系该案真凶的重要依据 。
但对隐蔽性信息的运用并不总是能帮助我们看清案情,一些冤假错案之中同样出现了蕴含隐蔽性信息的被告人供述 ,而这些隐蔽性信息所形成的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往往被侦、检、审三方机关视为铁证,成为阻碍冤假错案平反的重要障碍。在历时十余年才最终于2016年改判无罪的陈满案中,其一审法官在曾接受采访时称“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案子没有任何错误,百分之百不是冤案。”而让他能如此坚持的重要理由是“陈满的口供与勘察笔录中某个重要细节非常吻合,这个重要细节一般人在现场走三四遍也不一定能发现。” 这说明,运用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认具有重大影响的隐蔽性信息是一件蕴含着重大风险的事情,但我国目前对被告人供述中隐蔽性信息的认知却存在着明显的误区。
二、认知误区:供述出隐蔽性信息只能是真凶
作案人之所以能对案件细节等隐蔽性信息作出供述,源于其对案件的相关信息具有非作案人无法了解的亲身知识。以证人作证资格中对亲身知识,即“凭借自己感官觉察的结果” 的要求作为参照,供述中出现隐蔽性信息往往意味着供述者对该等信息具有亲历性,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角度讲这属于直接经验。这也是隐蔽性信息具有较高的证明力的原因,即源于非亲历者无法掌握相关事实的基本逻辑。但认为隐蔽性信息只能来自于真凶从而认定在供述中存在隐蔽性信息的被告人即为罪犯的观点却是不严谨的,因为被告人供述中的信息可能并不隐蔽,或者其获知的隐蔽性信息并非来自于亲历亲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隐蔽性信息的来源问题提高认识,对隐蔽性信息的泄露问题提高警惕。严格来讲,掌握案件隐蔽性信息的人按照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可以分为两类:
(一)直接从案件及现场中获取信息的人
1.案件的亲历者:案件的亲历者一般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受害者和目击证人。在不同的案件中,三者的存在情况、比例等都有所不同。比如,在犯罪现场较为隐秘的案件中,很可能不存在目击证人,强奸案件中常常形成被告人、受害人的“一对一”证言即是如此。而在一些杀人案件中,隐蔽性证据的作用之所以十分凸显,往往在于此类案件既缺乏目击者,死去的被害人也无法开口说话,作案人成为侦办机关之外唯一了解犯罪现场细节的人,其供述而出的隐蔽性信息也就有了极高的证明力,甚至成为定案的关键。这一类人所掌握的案件信息往往与案件的犯罪经过直接相关,尤其在某些不引人注意的细节上高度契合,但在某些看似可以较为准确的认知上又可能比较模糊甚至错误,比如强奸案中被害人指认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 。
2.案件的调查者:在刑事审判中作为重要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等来自于案件的侦查机关。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案件的调查者是直接参与调查的刑警或相关工作人员,对嫌疑人进行审讯的刑警也可能并没有参与过现场调查。但侦查机关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其分派给不同工作人员进行的现场勘验、询问证人、物质检测等等工作是在确定统一的规则下执行的,其收集、运用的各项信息也是在内部相互流通的,出于本文的写作目的,可以将其视作一个整体的案件调查者来看待。这一主体掌握的案件信息主要是通过事后的勘验、检测、讯问而得出的,虽然没有亲历案发经过,但由于了解时间的周期性而非即时性、了解范围的全面性而非片面性的特点,其所掌握的案件信息往往比案件的亲历者更为精确。
(二)对案件信息具有间接经验的人
现实中,在案件未公开时即了解到案件信息的情况比较复杂,比如,与案件完全无关但从作为办案人员的亲属口中得知细节的人。基于本文的写作目的,仅选取特定范围作以介绍和分析。这一特定范围的标准是获取了案件的细节信息、该信息在侦查机关看来属于隐蔽性信息且获取该信息的人被视为嫌疑人或成为案件的被告人。结合现实中的案例,较为典型的情况有三种:
1.自愿的替罪者——信息来源于作案人: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金钱的因素,替人顶罪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意味着替罪者很可能从作案人的口中了解到案件发生的经过和细节,而如果作案人对此是支持的甚至本身就是通过买通的手段找人顶罪的话,那么替罪者所掌握的信息很可能十分准确,并在侦办机关看来隐蔽性极强。这种案件的问题在于:首先,案件已经发生,需要追查作案人,尤其是在“命案必破”等政策的导向下,需要有人对案件负责;其次,存在一个积极的要对案件负责的“嫌疑人”,如果认定其不是案件的作案人,不仅使得案件无法终结,还有遭遇上级机关和被害人方的压力;最后,即便对顶罪的情况有所怀疑,就现有的证据来看,无法认定被侦、控、审三方怀疑的人有罪。这类案件在现实中往往被按照“疑罪从轻”的思路解决 ,不仅是对人权和法治的践踏,也是对法律权威的削减。
2.被叨扰的邻居——信息来源于被害人:“如某盗窃案中,被告人供述四次作案,时间、数额、藏钱的位置等隐蔽性细节都得到了失主的证实,其口供似乎很可信。但后来查明,被害人失窃后,在家吵、对外讲,嫌疑人与被害人是邻居,借此了解到案件情况。” 严格意义上来讲,案件中被叨扰的邻居在被讯问中供述出的案件信息来源于被害人,而从“在家吵、对外讲”的描述中可以推断,这些信息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失去了隐蔽性。但问题在于,侦察机关对这一情况的了解具有滞后性,而在审讯的压力之下,这位邻居并不必然能将信息获得的方式解释清楚,其解释甚至可能被认作狡辩。同样的情况可发生在任何对案件信息具有亲身知识的人周围,成为“被叨扰的邻居”。
3.被诱供的无辜者——信息来源于審讯者:如前所述,作为案件调查者的侦查机关,其所掌握的案件信息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作案人所掌握的更为精确和全面,而其几乎必然与嫌疑人进行接触和交流,这使得侦查机关最有可能成为隐蔽性信息的泄露者。
有意的泄露即是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指供诱供的问题,在办案的压力、对被告人翻供的担忧等种种可能的诱因下,一些办案人员通过声调提示、诱导性讯问等方式,使得本来不了解案情的嫌疑人供述出了隐蔽性信息,使其成为“被供述”的无辜者。比如,在对呼格案进行重新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其案卷记载的供述存在诱供嫌疑,被认定为在黑暗封闭的公厕内实施强奸行为的被告人,居然连被害人穿牛仔裤,皮带向左插并由两个金属扣子之类的细节都能供述的清清楚楚 。虽然严格执行讯问的程序、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可以基本规避这一问题的发生,但这些规则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其实并不理想。比如,讯问过程中的选择性录音录像、全程录音录像的选择性播放等问题都较为突出,甚至出现了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功能的异化 。
另一种出于无意的泄露则情况多样,审讯者使用讯问技巧中诈唬的方式时、听到嫌疑人的回答流露出相应的表情时,甚至是审讯间隙无意的交流中,都可能使嫌疑人对案件信息有所了解,从而做出更符合案件事实的描述。
(三)对被告人供述中案件信息的隐蔽性审查
所谓对信息的隐蔽性进行审查,其实是对被认定为具有隐蔽性信息的供述进行再次核查。这种核查的关键在于两个部分,一是该等信息是否具有隐蔽性,二是该等信息出现在供述中的理由是否有除了供述者为作案者外的其他可能性,比如是否属于“先证后供”的情况。这一核查旨在防止对“隐蔽性”的误认。
当然,这种审查某种意义上是需要由审查者依据经验理性作出判断的,被审讯者的心理素质、表达能力、思维逻辑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解释的说服力。但这并不是说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将这一审查完全交给审讯者的理智和良心,而是要明确审查后核查的程序和审查后对解释的记录。首先,应当针对被认定的隐蔽性信息对被告人(侦查阶段的嫌疑人)进行讯问,并允许其对信息的获取方式作出说明(侦查阶段应对该说明记录在案);其次,应对其作出的解释和说明进行核查,不能主观臆断的定性为狡辩;最为重要的是,需要保证询问过程录音录像的完整性,并由案件裁判者对首次出现该隐蔽性信息的供述作出检查,以防止指供诱供的出现。
三、反思隐蔽性信息的认知
隐蔽性信息的认知方面出现的误区,并非仅只由对隐蔽性信息的认识不足引起的。更多的,更为重要的,其实需要对审查判断隐蔽性信息的整个司法环境进行反思。
(一)对“合经验性”的警惕
特文宁在《证据分析》中写道,“论证由证据、假设和称为概括的陈述组成,概括用以证明证据与假设之间联系的正当性。” 而从被告人供述中蕴含隐蔽性信息到被告人对案件具有亲身知识,是作案人之间,其实也是一个通过概括进行推论的过程,同样是“必要却危险”的。而与其他推论不同的是,在对隐蔽性信息进行运用的过程中,其概括往往简单而直接,因此审理者将之视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未能注意到概括的风险所在。比如,知道凶器隐秘埋藏地点的不一定是凶手,也可能只是一个恰巧经过的路人。换言之,在对一些不确定的概括知识库进行怀疑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对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推论的警惕。
这种对“合经验性”的警惕并不是要求陷入怀疑主义,要求一切案件都要达到排除怀疑的绝对为真的标准。而是当我们通过被告人的供述对其定罪时,不能因为其中蕴含的隐蔽性信息是合经验的就忽视了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忽视了对被被告人供述的可信性、可靠性和自愿性的质疑。
(二)“程序正义”的去口号化
隐蔽性信息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并能在刑事司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我国一以贯之的重视实质正义的理念是分不开的。如果能够在内心确信被告人确实施行了犯罪,那么审理者宁愿牺牲程序正义,也不愿意将“真凶”放纵。换言之,我国对程序正义还只是一种口号化的追求,而未能真正将其视作被告人应当受到保护的程序性权利,非法证据排除难、瑕疵证据补正轻率都是这一理念的反映。而将隐蔽性信息这一对审理者而言关乎案件事实的内容纳入“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体系中去,其实给了审理者将依据实质正义定罪转化为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皆实现的外在表现。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利用被告人供述中的隐蔽性信息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否则将违背认识规律,也不符合当下人类的认知水平。需要强调的是,在认知、审查都存在误区的情况下,所谓的实质正义也可能是虚假的;反之,只有坚持程序正义的切实实现,隐蔽性信息指向实质正义的功能才能得到保障。
注释:
毛建平.论口供补强规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28-31.
秦宗文.刑事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法学研究.2016(3).174-192.
案件细节参见胡永平.央视推“聂树斌案”十年调查 首次披露诸多细节.中国网,网址:http://legal.china.com.cn/2016-12/10/content_39890252.htm.最后访问于2016年12月8日.
例如,在杭州张氏叔侄冤案中,办案人员聂海芬“调取案发当日的水文资料”,印证了二张的口供中“在抛尸地点听到水声”的说法。参见丁阳.女神探如何制造张氏叔侄奸杀冤案.腾讯评论.第2385期.
马世鹏、刘旌.一审审判长曾称陈满案“没任何错误,百分之百不是冤案”.转引自秦宗文. 刑事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法学研究.2016(3).174-192.
[美]罗纳德·J·艾伦、理查德·B·库恩斯、埃莉诺·斯威夫特著.张保生、王进喜、赵滢译.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10.
兰跃军. 被害人辨认错误及其防范.证据科学.2014(5).557-566. 注1.
陈卫东、程雷、孫皓、陈岩.“两个证据规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侧重于三项规定的研究.证据科学.2012(1).76-87. 注14.
陈正清.发现疑点不放过,查无实据不定罪.人民司法.1986(4).16.转引自秦宗文. 刑事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法学研究.2016(3).174-192.
张建伟. 从呼格吉勒图案看刑事诉讼中诱供之害.刑事司法论坛.2011(00).218-226.
王超.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异化——以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选择性录制与播放为视角.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3-72.
[美]特伦斯·安德森、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著.张保生、朱婷、张月波,等译.证据分析 (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