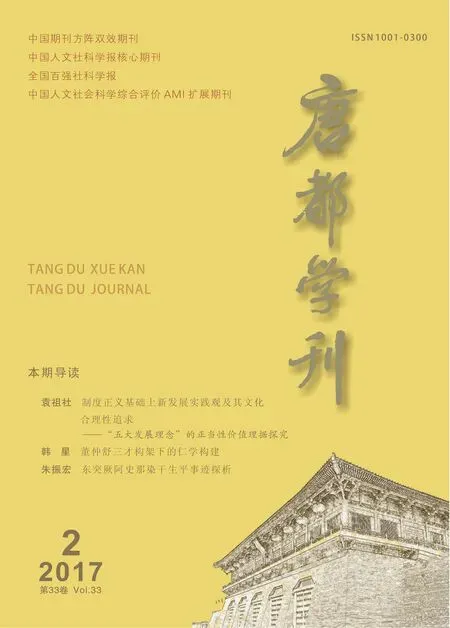明清关中士人的文社活动及其影响
常 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关中历史文化研究所/人文学院,西安 721065)
【关学研究】
明清关中士人的文社活动及其影响
常 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关中历史文化研究所/人文学院,西安 721065)
士人结社与文学关系的问题在当代明清文学研究中是一个重要问题,它揭橥了自唐以来文化权利下移及士人群体扩大的史实及这一现象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明清文人集会与结社的情况比较复杂,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特征,到清代基本延续了这一趋势。受经济与文化地域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因素影响,明清的士人集会与结社同样呈现出地域间的不平衡,集会与结社主要集中在政治中心的京师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关中士人参与集会与结社也主要在这些地区展开。但同时受到士人集会与结社风气的影响,关中也存在士人的集会与结社,这些文社对明清关中文学的发展、关中士人及其文学作品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清;关中士人;文社活动;关中文学
朱彝尊指出:“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1]文人的集会与结社和同一个时代的风尚、士人的交游、士人的心态及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密切相关。结社的士人尽管不一定是官僚阶层,但他们大都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产生于其间的集会与结社加强了士人之间的学术交流,激发了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激情,更重要的是为士人们编织了一个学术社会关系网,在关系网内部通过士人的相互介绍和赞誉,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士人的学术影响力及其作品的传播。考察文人集会,更关注集会中的诗歌创作,将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紧密地关联起来,既立足文学本位,又赋予其以广阔的文化视角,尤其是把结社作为诗歌发展史上一种传统性的文学现象予以重视,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一、明清的文学结社
明代三百年间,京城诗文集会活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和文化现象,它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京城诗文集会风气的变化,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明代诗文的发展变化历程,也对地方的文学集会有着风向标的作用。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称:“元季国初,东南士人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乃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2]这是元初东南士人的诗文结社。
文社以作文为主,尤以作科举文为主,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进士舒璘有《请汪解元书》略云:“窃以学之不讲,士失趋向,则知道者鲜矣。国有学,郡有庠,邑有序,正所以讲明此道,使人不昧,某也不才,岂宜滥居斯职?然自壮岁游学,蒙师友之启发,粗知途径,亦希文会之开,朝夕切偲,不负讲明之意。”[3]可知文社之起,实与书院讲学之兴关系密切。文社的真正盛行,是明代万历之后的事,陆世仪《复社纪略》卷1云:“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举艺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4]这就清楚地说明,文社兴盛的主要社会原因就是基于文人士子研究八股时文、谋取科举功名的迫切需要,当然也有不求科举功名,专以读书作文为务的文社。
元代诗社的组织形式,较之宋代更为严密。《明史·张简传》云:“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钜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则有厚赠。”[5]明代是文人结社的鼎盛期,明代的诗社特征有三:第一,文人结社除了娱情悦性、诗酒酬和之外,往往有着鲜明的实用性。明以前的文人结社,多为诗词吟咏,文酒风流,或怡老崇雅。而明代崛起的文社,在结社之始,每每只为制举业,以仕进为目的。第二,明代文人结社的活动方式,较前代更为丰富多彩;第三,明代文人结社的纷争繁剧,也为前代所罕见。范景文《范文忠公文集》卷《葛震甫诗叙》云:“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今则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嚣,莫辨谁是。”[6]
文社在弘治间的出现,是明代文人结社史上值得关注的新迹象。陆世仪《复社纪略》将明末复社崛起归因于文社之兴,而文社之兴则追溯到弘治间昆山顾鼎臣等人的邑社,曰:“粤稽三吴文社最盛者,莫如顾文康之邑社,社友十一人,如方奉常、魏恭简辈,后皆为名臣,可谓彬彬者矣。”[7]因此,邑社往往被视为明代文社之始,弘治间兴起的文社,一开始就在科场获得佳绩,华亭之钱福、昆山之顾鼎臣皆成为状元,顾清、李希颜、方鹏、魏校等无不扬名科场,一时传诵。而两地本来就是人文昌明之邑,故文社所带来的影响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当地文人结社的风气,对整个明代中后期各地,特别是东南一带文社兴盛产生极大的刺激作用。据顾炎武的记载:“万历末,士人相会课文,各立名号,亦曰某社某社。”[8]时人杜登春亦有过描述:“盖社之始,始于一乡,继而一国,继而暨于天下。各立一名以自标榜,或数千人,或数百人;或课才艺于一堂,或征诗文于千里。齐年者砥节砺行,后起者观型取法。一卷之书,家弦户诵;一师之学,灯续薪传。”[9]
播迁以后,社会政治发生很大变化,士子暂时中断了科举的路子,吟诗倡和,抒发亡国之痛成为甲申以后文社活动内容之一,杨凤苞《秋室集》卷1《书南山草堂遗迹后》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甬上,三吴则松陵。”[10]10其时,不仅大江以南,就是大江以北,乃至黄河以北,也多有结社之举。清初文人结社既隐含着复明的政治目的,其内部又不免党同伐异,流弊滋生,于是朝廷有禁社之令。顺治九年(1652),由礼部题奏,刊卧碑于太学,严禁生员立盟结社。顺治十六年(1659)六科给事中杨雍建疏论,欲禁朋党和社盟,顺治当即颁旨:“士习不端,结订盟社,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甚为可恶,着严行禁止。”康熙四十一年(1702)再申旧令:“招呼朋类,结社立盟,如此之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11]虽然清廷一再严加禁止,但有清一代社事却始终不曾禁绝。屈大均说:“自申、酉变乱以来,士多哀怨,有郁难宣,即皆以蜚遁为怀,不复从事举业,于是祖述风骚,流连八代,有所感触,一一见诸诗歌。故予尝与同里诸子为西园诗社,一追先达。”[12]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一文也记录过播迁后惊隐诗社聚会的情形:“岁于五月五日祀三闾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征士,同社麋至,咸纪以诗”,“诸君子各敦蛊上履二之节,乐志林泉,跌宕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亦月泉吟社之流亚也,后之续遗民录者必有取于斯也夫。”[10]10-11所以申、酉以后,各类文社、诗社的诗文创作颇为普遍,社中遗民通过社集倡和,抒发愤懑,构成宋元以来遗民诗创作的又一个高峰。
结社读书是一种有利于集思广益,增进交流和活跃思想的学习方式,文社之兴促使一部分士人形成博学苦思的精神和扎实稳当的学风,并为朝廷输送了大量的举人、进士,在培养各类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复社、几社、求社等皆以输送科举人才而著称。从及第者诸如袁氏兄弟、张博、吴伟业、陈子龙等人来看,这些八股取士制度下的佼佼者,不仅是制义能手,同时也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名家,而他们的成长都离不开结社这一环节。文社还促进了八股文风的变化,给散文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散文的创作繁荣之地往往即为文社活跃之处。
二、关中士人京城结社与文学活动
文人集会与文学流派密切相关,且集会的中心一般为国都、州县的置所,集会的召集者往往是一些具有一定文学声誉的士人,甚至是文坛领袖。考察明清士人的集会与结社所创作的诗歌,可以发现无论是诗歌内容,还是创作数量,均在明清诗歌创作史上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这种创作对诗歌的流派、文学的观念等方面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前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李梦阳是京师文人群体的轴心人物,乐群好游,雅集结会,是李梦阳文学生涯的重要特点。史载李梦阳“居燕中,社集四方名士,兴复古文词,与信阳何景明互旗鼓,时人称李何”[13]。李开先也记“(李梦阳)始除户部主事,寻迁员外郎,以豪雄不可下之气而为闳肆不可遏之文,薄书有暇,即招集名流为诗会”[14]。早在弘治十五年(1502),李东阳主文柄,康海中进士后入翰林院。“独不之”,与李梦阳、王九思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从文中看,李、王与康海等人的文社只是一种文人聚会性质团体,与举业无关。李梦阳本身脱胎于茶陵派,参加李梦阳京师结社倡和者无不出自茶陵派领袖李东阳门下。弘、正前后,群星璀璨,人才鼎盛。京师、南京、吴中、闽中等地尤其胜流如云,河东、关中不乏才俊,从而为全国性文人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可能[15]213。
“七子”为弘、正间京师文坛的代表人物。如“文学”倡导者王守仁早年爱好古文词,即为这一潮流的重要人物。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说:“已末登进士,观政工部,与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璘、徐祯卿、山东边贡诸公以才名争驰聘,学古诗文。”[16]另外在京城与李梦阳结社、倡和的还有陆深、赵鹤、刘麟、杭济、杭淮、何孟春、杨子器、朱应登、都穆、秦金、钱荣、陈策等。可见,当时在李梦阳周围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文学团体,气象之盛为有明以来所少有。
据《明史纪事》戊签卷12载,关中士人刘储秀“为部郎时,与僚属薛采君、胡承之、张孟独倡和为诗社,都下号‘西翰林’”[17]。所谓“西翰林”指的是刑部,因刘储秀、薛惠、胡侍、张治道皆为刑部同僚,结为诗社,故称西翰林诗社,这一诗社中还包括韩邦奇、韩邦靖二人,“(正德中)一时名流,如石邦彦、乔白岩、储柴墟、邵二泉、王阳明、韩苑洛、五泉皆与(王云凤)倡和。”[1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德间西翰林诗社是一个有鲜明复古倾向的文学社团,成员张治道被钱谦益认为是附北地而排长沙最为得力的人,“极诋弘治之诗”[19]318。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中明确指出:“模效窃仿”李东阳诗文成为一时风气,与康海等结社形成新的文学集团后,以“复古”抵制“仿今”,李东阳由此“衔恨,予以打击”[15]225。
清初满人虽然在政治上形成了相对的稳定局面,但文化因素中的夷夏之辨未能消解,在诗坛体现为在仕的文人与在野的文人相对立的态势,在野文人中的翘楚大都是一些明代的遗民,除过道义之外,他们有着较为崇高的文学声誉与影响力。相较这些士人而言,此时京城在仕文人文学的影响力与文学声誉有限。尽管有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曹溶、周亮工诸名家,但由于他们降清的尴尬角色,使其未能取得朝野诗人的普遍推崇。至康熙年间,这一局面逐渐得到改观,此时新晋进士王士祯、陈廷敬、施闰章、宋琬、宋荦、王又旦等居官京师,他们的遗民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薄,同时整个社会逐渐接受满人问鼎中原的事实,这使得这批新晋的士人在文坛被接受且其影响愈来愈大,其佼佼者为王士祯。他主盟京师诗坛之后,鼓扬风雅,提携后进,逐渐形成了诸如“佳山堂六子”“燕台七子”“金台十子”等文人团体,成为这一时期京师诗坛风云际会的代表人物。
这一时期驰骋文坛的关中士人主要有李因笃、李念慈、王弘撰、孙之蔚、王又旦等人。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云:“关中名士,予生平交善者,如三原孙豹人枝蔚、韩圣秋诗、华阴王无异弘撰、富平李子德因笃、郃阳王幼华又旦、富平曹陆海玉珂,皆一时人豪。”[20]557朱彝尊《王崇安诗序》云“予求友于关中,先后得五人:三原孙枝蔚豹人、泾阳李念慈屺瞻、华阴王弘撰无异、富平李因笃子德、郃阳王又旦幼华。五人者,其诗歌平险或殊,然与予议论未尝不合也。”[21]乾隆年间的王鸣盛亦云:“三秦诗派,国朝称盛,如李天生、王幼华、王山史、孙豹人,盖未易更仆数矣。予宦游南北,于洮阳得吴子信辰诗,叹其绝伦。归田后复得刘子源深诗,益知三秦诗派之盛也。”[22]在以上诸关中士人中,唯有王又旦在京城居住时间较长,有机会处于政治和文学中心地位,与以王士祯为首的山左士人结“十子社”,世称“金台十子”,“十子”者“商丘宋(荦)牧仲,郃阳王(又旦)幼华,安丘曹(贞吉)升六,曲阜颜(光敏)修来,黄冈叶(封)井叔,德州田(雯)子纶、谢(重辉)千仞,晋江丁(炜)雁水,及门人江阴曹(禾)颂嘉、江都汪(懋麟)季甪”[23]卷5,“十子社”诗由王士祯于康熙十六年刻成《十子诗略》。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七月,王又旦、汪懋麟招集陈廷敬、王士祯、徐乾学游祝氏园,其中后三者在当时政坛具有相当影响力,他们所参与的集会颇有影响力。此次集会被画工作《五客话旧图》,汪懋麟为《城南山庄画像记》,曰:“懋麟自顺治末受知于济南王公,及康熙初举于乡试,始通宾客,与海内名贤相结纳,己巳得交郃阳王公,丁未得交昆山徐公,己酉应阁试入京,得交泽州陈公,相与论诗,有合焉。”[25]诸子大都以诗纪其事。在此前后,王又旦与施闰章、毛奇龄、汪楫、曹尔堪、沈荃、李天馥等人有数次集会。通过这些集会,王又旦与王士祯、陈廷敬等人逐渐成为京师文坛的中心人物。考虑政治时势原因,除却明代结社所需的社规、社约外,王又旦和其他京城文坛巨擘的文学活动和明代文社之盛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关中士人已不是文坛的主导者而已。乾隆年间,关中士人在京城有结社记录者更少,仅见于刘绍颁《二南遗音》中所载康绩曾与屈复“倡诗社于京师”[26]。康绩,字方陆,安化人,寄籍泾阳,诗甚富,多散佚。屈复,蒲城人,号晦翁,19岁时童子试第一名,不久出游晋、豫、苏、浙各地,又历经闽、粤等处,并四至京师,乾隆元年(1736)曾被举博学鸿词科,不肯应试,72岁时尚在北京蒲城会馆撰书,终生未归故乡,著有《弱水集》等。
三、明清关中的结社考察
文人结社活动与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流动情况相关。考察明清的文人集会与结社可以发现,京师、江浙一带是文人集会与结社的密集区,而其他一些经济落后、人口流动性较差的地区文人集会与结社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人集会结社在空间分布的不均衡,进而产生了文学实力的地域性差异。
嘉靖前期文人结社出现了一些基本的趋势和特点:首先结社进一步扩展,南方仍为结社的中心,北方的结社也迅速活跃起来,北方如京师、山东章丘、陕西武功、河南祥符等地,都有社团的兴起,特别是山东、陕西结社现象的出现,有着特殊的文学意义[15]250。
康海和王九思致仕后在关中经营着当时全国影响最大、创造水平最高的戏曲中心,选妓征歌、雅集酬唱,演剧观乐而不避声色[15]288。当然在关中很少有京城那样的社事,结社以其他的方式存在,如康海于嘉靖十三年(1534)在武功举行百年会/百岁会。万历中期,长安宝庆寺也有社集的痕迹,据冯从吾《少墟集》卷6《语录·学会约》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冯从吾“与诸君子立会讲学于宝庆寺”,会约规定:“每月三会”,“会期讲论毋及朝廷利害”,“会中一切交际俱当谢绝”,“彼此讲论,务要平心静气,虚己下人”[27]123-124等。继宝庆会之后,冯从吾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复倡关中会。周传诵《关中会语跋》云:“会举于戊戌正月,仲好氏书约,先大夫题辞,不佞以使事过里,与未议焉。”[27]121关中会亦有会约,如有“彼此争构,吾辈无所傥,万一有之,大家务要尽心劝和”[27]120之类的规定。据此可以看出,宝庆会和关中会的文学色彩相对较淡而理学色彩较浓。另外,明中后期关中藩府中也有结社之事,《民国歙县志》载谢陹“尝游秣陵、关中,与诸王孙、名士结社谭艺”[28]。朱敬鎑,字进父,明秦愍王朱樉八世孙,据其《子兴社长睽别三祀,戊子秋会晤浃旬,话言连夜,因论诗各赋一律》《熊左史结社且期眺秦中名胜》等作,至少不晚于万历十三年(1585),他与张致卿、王元锡等人结诗社,选胜吟咏,诗酒跌荡,文学活动十分活跃[15]332。
清初遗民结社,其实也是部分遗民的一种生存方式,正如杨凤苞所言:“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10]10据初步统计,清顺治至康熙初各类文人会社至少有七十余家,其中,明遗民之社超过五十家[29]308。经过考察明清之际文人结社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会社分布的重点在三个区域:京师、江南、岭南,与之相比,关中地区知名的文社则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国家的文化重心在江南,第二是“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30]87。就整体情况而言,清初关中士人在清初的集会与结社相较京师和江浙一带为弱,但集会和结社作为明清士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势必使部分关中士人不能置身其外,如孙枝蔚、王弘撰、李因笃或在关中,或在流寓之地参与各种文社,扩大他们在文坛的影响力,同时也使文学中的“秦风”为外界所了解。
明清关中地区士人集会和结社之风不盛,与明末清初关中地区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黄宗羲从文化史的角度比较东南和西北时说道:“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止,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31]关中地区自中晚唐以来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经济也随之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学发展所需的经济保障,赵翼对此也认为“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32],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明清之际关中因何缺乏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文人雅士。

“青门七子”在王弘撰《山志》中多有记载,屈大均在游华山路过王弘撰斋,也记有“青门七子”事:“诸王孙彬彬作者,以工诗及四体书,相矜尚当时,功令推择,绝迹仕途,而宗才之英,犹以仲宗为最,诗则仲宗有《松学阁集》,子斗有《八斗斋集》,诸王孙有《青门七子集》。”[36]13王弘撰与“青门七子”常有诗歌倡和之事:“余幼随先司马京邸。丙子,咸宁孙嗣履以拔贡应廷试,来见先司马,先司马曰:‘此佳士也。’尝留之书斋,盖余之有友自嗣履始。及归里后,余应童子试,至郡城则主其家。又因嗣履得友青门诸子,一时立文会称盛,为督学岁星汪公所嘉。”[35]224
清初关中遗民结社的还有王化泰在乡里结社讲性命之学,“王省庵先生讳化泰,贤而隐于医,笃志理学,潜心性命,初与本邑单元洲结社讲究,后与同州党两一切砥密旨”[36]265。华州人郭宗昌“辟沚园白崖湖上,地介二华之间,造一舟居之,曰‘斋舫’,自谓‘一水盈盈,与世都绝,沦落崎嵌,任心独往’,又有别业在郑南,即杜子美西溪,与其友王承之、东荫商为‘南玼社’。”[37]东荫商,字云雏,华州人。明崇祯丙子举人,屡上春官不第,与李颙、王士祯、王弘撰、李楷、宋琬等游,有《华山经》一卷。其《东云雏诗》乾隆间列入禁毁书目。王弘撰五兄王弘嘉在易代之后,“立文社,奖率后进,同诸弟子督课之”[38]。
在关中比较偏远的临洮地区有“洮阳诗社”,其历史悠久。吴镇《萝月山房诗序》云:“洮阳诗社,由来最久,兴而废,废而复兴,乘除随时,然倡和者卒未尝绝。忆三十年前余与诸同人重联诗社,一州才俊翕然趋风。”[39]吴镇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按“三十三前余与诸同人重联诗社”的记载,洮阳诗社至少在清初就已经存在,且对洮阳地区文学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李苞《洮阳诗集序》云:“洮阳诗学,自汉唐以来,代不乏人,而本朝称尤盛焉。国初张康侯、牧公提倡于前,约数十年,而又有先师吴松崖先生集其大成,且宏奖士类,善诱后学,故吾洮阳人士,研究声律,著为辞章,往往有可观者。”[40]
四、寓居江南关中士人的结社
明代社事,盛于东南,除了一般的应试举业外,还因吴越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渐渐成为国家库府,其间名士辈出,文人云集,普通士子读书应制也成为风气,民间有“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摛章染墨”[41]。对南人的这一看法,一直延续到清末。南人善文,又有文人雅集的传统,再加上江南富庶的生活,贵游子弟诗酒自娱,便为社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江南在晚明为人文渊薮,历来士子藉科举进身者极多,士大夫聚众讲学、讲论朝政的风气极盛。明朝的士人党社,从早期的东林到应社、复社、几社等有影响力的结社,都首先兴起于江南地区,与此同时流寓江南的关中文人也积极参与到江南的文社之中。
明代流寓江南的关中士人结社最早为孙一元,《国宝新编》载:“太初风仪秀郎,踪迹奇谲,玄巾白袷,混游贵贱。常以铁笛鹤瓢自随,遇所会心,辄一倾倒,盖隐沦之高逸。性好吟诗,初谈道引,人疑其仙。晚婴婚娶,入司空刘公湖南雅社”,“诗辞备极苦心,所乏天才耳”[42]。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弘治间,兰溪方太古“与杨君谦、沈启南、文征仲暨孙太初结诗酒社。正德初,隐于玄英先生之白云源”[19]335,杨循吉、沈周、文征明皆为吴人,故社地当为吴中。方太古、孙一元皆游吴,故与杨循吉等人有结社之举。“(刘麟)晚自称坦上翁,与孙一元、张寰、吴珫、陆昆辈,作湖南雅社。”[19]329金峦,字在衡,号白屿,幼习举子业,长随父宦于金陵,遂家于此,乃弃制又而悉心歌诗,性任侠,慷慨助人于危难;好交游,布衣来往于吴楚淮扬间,所至倒履而迎。嘉靖时,曾执骚坛牛耳;万历初,又以耆宿莅盟青溪社。他与盛时泰交厚,与何良俊、张献翼、王稚登、冯惟敏亦有交往。
清代王士祯的“红桥修褉”为文人社集的佳话。《渔洋诗话》云:“予少时在广陵,每公事暇,辄招宾客泛舟红桥,与袁荆州诸词人赋诗,有‘绿杨城郭是扬州’之句,江淮间取作画图。又与林茂之、张祖望、杜于皇、孙豹人、程穆倩修禊于此。”[20]188康熙三年(1664)的清明节,王士祯约扬州名士林古度、杜浚、张纲孙、孙枝蔚、程邃、孙默、许承宣兄弟等人到红桥一带聚会,饮酒作诗,王士祯赋《冶春绝句》二十首,二十首绝句,或写景,或发思古幽情,写得清丽婉转,神韵渺然,被时人誉为“独步一代”,不少诗人以诗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孙枝蔚作《后冶春,次阮亭韵》二十二首,杜浚作《题王阮亭〈冶春词〉后》,陈维崧作《和阮亭〈冶春〉绝句,同茂之、于皇、祖望、豹人、澹心、椒峰》六首,吴嘉纪作《冶春绝句,和王阮亭先生》八首,宗元鼎作《乙巳春夜,读王阮亭先生红桥冶春诸绝句漫作》三首,一时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空前盛况。在《广陵倡和诗序》中孙枝蔚也描述了甲辰年的一次文人诗会:“甲辰之春,八闽林之茂,鄞县陆古淳、钱退山、杨瀣仙、王正子,宜兴陈其年,钱塘蒋别士,海陵吴宾贤,新安程穆倩、孙无言,上人梵伊皆聚于江都,会海陵陆无文亦适奉两尊人至,寓于天宁兰若之旁,遂招诸君开筵,春夜联句。”[43]
红桥修褉之后,在扬州中文人群体的这种文学活动逐渐形成社集的规模和形势,虽然尚无固定的名称,但其人员构成比较稳定,较活跃的成员有孙枝蔚、汪楫、汪懋麟、汪耀麟、汪士裕、华衮、王宾、夏九叙、黄雨相、鲁紫漪等,而吴嘉纪、杜浚、方文、雷士俊、汪湛若、王正子等人也时而参与,在重要的时令节日(花朝、上巳)、某成员的特殊日期(生辰),抑或在故旧重逢、友人归乡、同志送别等情形下,诗友间往往会举行宴饮集会。尽管这个文学圈子未振臂号召、联席结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却也无碍它表现出一定的群体意识而径以“社集”自称,这从诸人所作诗体可以看出,如孙枝蔚即有《社集赋得早花随处发限七言近体》《九日社集朱纫方半舟斋名》《秋夜社集张与参宅同纪檗子、黄仙裳、范汝爱、畲来仪诸题》。这些社集呈现出清初诗社的典型性特征,但诗酒文宴仅是聚会的一种具体表现方式,文人聚会,就是为了联诗吟唱,为了会朋聚友,为了互诉衷肠,为了排遣苦情。
与孙枝蔚同时代寓居江南的关中文人还有张晋、李楷、张恂、雷士俊、韩诗、东云雏及王弘撰、杜恒灿、张谦等人。孙枝蔚曾经和李楷、韩诗、潘陆等人在镇江结“丁酉诗社”[29]316。雷士俊与王岩、郑廷直等人在扬州建有“直社”,雷士俊“初善举子业,与同里诸子结社,皆一时杰出,制义称雄直社,刊版行世,即慨然念天下古文绝响,久与友人王岩废弃隐处,日夕淬厉,切磨著书。入扬州府学,试高等,督学偿擢第一补廪,屡应乡举不中。崇祯末,天下大乱,遂弃廪贡不仕,有志用世”[44]。“杜恒灿,字苍舒,号杜若,八岁能文,十七补弟子员。值寇乱,家中落,尝走四方,负米养亲”,“先是居京师,与中翰吴炜交,订观文大社以振兴古学为志。及炜使关中,过焦获,复广其社于邑之学古书院。炜去,恒灿主讲席,学者宗之”[45],这些诗社讲论时文,砥砺气节,将秦风古韵带入江南,对江南向为柔弱的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为江南文人认识和理解关中士人及其诗作风格提供了平台。
作为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风尚,士人结社是明清文学繁荣的一个标志,它同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直接相关,体现了明清士人的一种生活与存在方式,对明清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有着直接的影响。明代关中士人的京城结社激发了以李梦阳和康海为代表的关中士人文学革新的意识和激情,最终形成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清代随着统治者对结社的打压及关中士人不再处于政治文化中心,京城结社的文事日趋衰落,关中士人不再是社事的主角,文人的一般聚会代替了结社。
[1] 朱彝尊.静居志诗话[M].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49.
[2]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80.
[3] 舒璘.舒文靖公类稿[M].清同治刻本:卷1.
[4] 陆世仪.复社纪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73.
[5]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21.
[6]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53.
[7] 李季.东林始末[M].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36:171.
[8]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栾保群,吕宗力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61.
[9] 杜登春.社事始末[M].北京:中华书局,1991:1-2.
[10]杨凤苞.秋室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王先谦.十朝东华录[M].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康熙卷69.
[12]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357.
[13]査继佐.罪惟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2034.
[14]李开先.李开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4:603.
[15]何宗美.人文结社与明代文学演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6]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555-1556.
[1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590.
[18]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4872.
[1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0]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张宗柟纂集,戴鸿森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1]朱彝尊.曝书亭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83.
[22]刘壬.戒亭诗草[M].清乾隆刻本:卷首.
[23]王士祯.居易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4]徐世昌.晚晴簃诗汇[M].北京:中华书局,1990:256.
[25]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93.
[26]刘绍颁.二南遗音[M].济南:齐鲁书社,1997:766.
[27]冯从吾.少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8]许承尧.民国歙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86.
[29]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30]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21.
[32]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784.
[33]王弘撰.砥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50.
[34]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40.
[35]王弘撰.山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6]屈大均.屈大均全集[M].欧初,王贵忱主编,李文约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6]李二曲.二曲集[M].陈俊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37]王士祯.陇蜀余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4.
[38]李因笃.受祺堂文集.[M].清道光七年刻本:卷4.
[39]吴镇.松花庵全集[M].宣统二年重梓本.
[40]李苞.洮阳诗集[M].嘉庆四年刻本.
[41]赵宏恩,等.江南通志[M].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1967:418.
[42]顾璘.国宝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
[43]孙枝蔚.溉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036.
[44]雷士俊.艾陵文钞[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4.
[45]焦云龙修,贺瑞麟纂.三原县新志[M].台北:文成出版有限公司,1976:345.
[责任编辑 贾马燕]
The Influence of Guanzhong Scholars’ Literary Societies Activit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ANG Xin
(ResearchInstituteofGuanzhongHistoryandCulture/SchoolofHumanities,XidianUniversity,Xi’an721065,China)
Scholars’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nce it has revealed the downward shift of cultural right and expansion of scholars’ societ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historical fact and the literature since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cholars’ assemblies and societies were complicat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ntaneity, which had extended into th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factors as the imbalance of economy and cultur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scholars’ communities and societie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politically centered capital city and Zhejiang Province where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were relatively developed, and where the Guanzhong scholars were mainly activ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affected by the trend of scholars’ communities and societies, there were also such activities in Guanzhong, which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uanzhong literature, Guanzhong scholar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ir literary work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anzhong scholar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terary societies activities; Guanzhong literature
K24;K825.1
A
1001-0300(2017)02-0058-0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关中士人生存境域与文学生态问题研究”(11ZXW008);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阳明心学关中传播接受史”(2015C003)
2016-11-14
常新,男,甘肃靖远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中历史文化研究所、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关中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