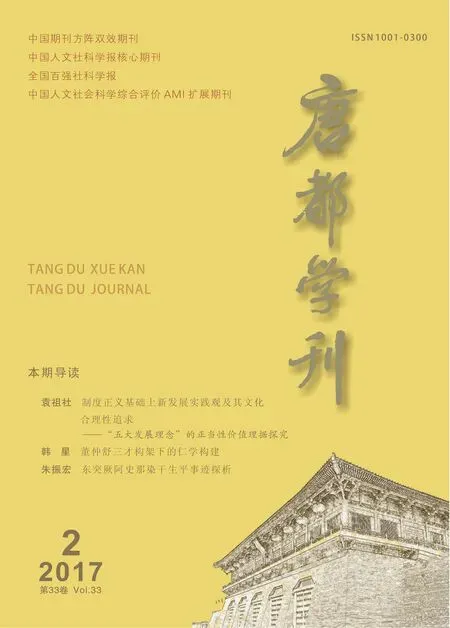汉代的初郡制度
刘 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西安 710054; 中国人民大学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2)
【汉唐研究】
汉代的初郡制度
刘 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西安 710054; 中国人民大学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2)
据文献记载,可以重新确定汉初郡的范围,认为其中不应包括南海郡。随着郡、县等职官的设置,初郡形式上就与汉郡相近。而初郡“以其故俗治”的政策,西汉基本未变,前后承继有着长久的政策连贯性。但进入东汉后,该政策不断遭到破坏。在原初郡内“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及地方官对故俗的主动改造,成为东汉华南郡国叛乱不断的重要原因。而随着东汉时对“以其故俗治”和“毋赋税”等政策的破坏,初郡制度逐渐消失。
汉代;初郡制度;民族治理;变化
秦汉王朝施行郡国并行之制。当统一岭南及西南夷地区后,汉武帝就在新设立的“初郡”地区,采取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统治政策。《史记》载:“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1]《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的记载近同*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2年版。“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又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然兵所过县,县以为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轻赋法矣。”,而其他地区则依然如旧。
长期以来,虽然周振鹤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初郡问题*周振鹤先生曾在《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中对初郡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认为“武帝元鼎年间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南越、西南夷等大片地区归入西汉版图,这时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域已不是零散的点,而是大片的面,设道的办法已不适用。因此元鼎六年后武帝在南越、西南夷地区置初郡17个,以为管理少数民族的特别行政区域。”参见周振鹤《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录入《周振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该文原载于《历史地理研究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此外周振鹤先生在相关专著中也对初郡进行分析,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但在有关汉代民族统治政策的讨论中,对汉武帝灭南越国后设置“初郡”问题所开展的研究一直不多,专门就此问题进行研究者仅胡绍华先生一人*参见胡绍华《汉朝初郡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编《民族史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75~93页;胡绍华《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载于《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10~14页;胡绍华《汉朝开创了中央王朝治理南方民族的基本政策》,见胡绍华《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探索》,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308页。此外,在胡绍华先生所著的《中国南方民族发展史》中对此也有专节论述,见胡绍华《中国南方民族发展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久久无人属意与此。有鉴于此,在阅读相关史籍和资料后,笔者不揣愚陋,想在学界前辈论述的基础上,再对有关问题做一探讨,错漏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初郡”的范围
1.十七初郡
“初郡”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平准书》。而“初郡”所指,《平准书》未有具体郡名,晋灼在《汉书·食货志》注中提出了十七“初郡”的范围:A.越地所开九郡(元鼎六年,前111):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B.西南夷地所开八郡:斨柯、武都、越雟、零陵(元鼎六年,前111)、沈黎、汶山、犍为(建元六年,前135)、益州(元封二年,前109)。
但据文献记载,象郡直至汉昭帝元凤五年(前76)始罢,因此从其位于“番禺以西至蜀南者”间的地理位置看,“初郡”中自当有象郡。而这自然会与晋灼的“十七郡”产生抵牾。分析相关文献,据史汉书例,我想“初郡”中当无南海郡,晋灼之言并不尽确:(1)十七初郡在史汉中有明确的范围,即“番禺以西至蜀南者”。其中“番禺”与“蜀”均不应在十七初郡之列*番禺此处当为代指南海郡,就如今日以北京代指中国。,二者在此处的出现是提供十七郡的两侧范围,为初郡“外界”,并非初郡(蜀郡设置甚早,自不应在初郡之列)。也就是说,初郡是番禺(南海郡)以西至蜀郡之南(即“南海郡<…初郡…>蜀南”),而非从番禺开始至蜀郡南(即并非“南海郡≤…初郡…≥蜀南”)。(2)晋灼“十七郡”首郡即南海郡,以南海郡为十七郡起点,其乃是将界定初郡范围的南海郡包括进去,而未包括蜀郡。他的这种界定,与前引初郡范围的记载有着明显抵牾。简言之,晋灼的初郡范围是“番禺≤…初郡…>蜀郡”。(3)在史汉二书中,“以西至”这样的语例,除此处外,还有不少。如《汉书·匈奴传》:“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若按晋灼分析之例,上谷郡当在“保塞”之列。但从文献看,当时上谷郡已为汉郡,若单于所提“保塞”的范围中有上谷郡在内,则其也就有了向汉索要上谷郡的含义在内。而从接到上书后汉君臣争论中均未提及上谷郡的归属看,单于“保塞”要求中并不含上谷郡。
在文献中,若要将范围两侧的界限均包括在内,一般要以“自”来界定。如《汉书·诸侯王表》:“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共十五郡”,作为起点的“江陵”(为南郡郡治,此处代指南郡)和“云中”(云中郡,郡治云中)就都在十五郡之内。类似记载还有不少,如《汉书·西域传》:“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又如《史记·大宛列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不仅宛是西域诸国之一,乌孙也近匈奴,因此用“自”将其包括在内*此外还有不少记载,如《汉书·翟方进传》“三辅闻翟义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县盗贼并发”,茂陵在二十三县之中,不过此条记载中的“茂陵”明显不如“宛”“乌孙”的性质那样明显可以确定。。而如《汉书·匈奴传》:“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当时云中为汉郡,自然不会在卫青攻打之列。故从史汉书例看,“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的十七初郡中,不应包括作为东侧界限的番禺(南海郡)和西侧界限的蜀郡,因此南海郡并非初郡。而据前文,象郡在空间上位于南海郡之西,因此当在初郡之列,正合“十七”之数。
谭其骧先生曾指出,十七初郡中当进象郡而退零陵,周振鹤先生亦持此说*参见周振鹤《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周振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周振鹤先生指出,谭其骧先生意见原发表于《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0年,第11~12页,笔者查询未见。。从以上分析看,按史汉二书“以西至”等语例看,在十七初郡中当不含南海郡,如是,则零陵郡似尚可保留。即十七初郡当为越地苍梧、合浦、郁林、象郡、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西南夷牂柯、武都、越雟、零陵、沈黎、汶山、犍为、益州等八郡。
2.“初郡”特指十七郡
虽然确定了十七初郡的构成,但是否在此之外还有其他初郡?
首先,从字面看,“初郡”大体是与“往郡”相对的一组词汇。“初郡”首先是“新郡”,是在汉武帝时期在新获之地所设的汉郡。其次,据《汉书·地理志》,在汉武帝及其后帝王在位期间,除上述17郡外,还设立不少新郡,如陈留郡、九江郡、山阳郡、临淮郡、武都郡、金城郡、天水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安定郡、西河郡、朔方郡、玄莬郡、乐浪郡等等。因此,单从这些新郡设立时间和地点看,除陈留、山阳、临淮郡位于内地外,其余大体都分布在西北和东北的新属汉统治的地区。因此对汉王朝而言,其也是“初”郡。第三,如胡绍华先生已指出的,前述各郡均不在“初郡”之列。其原因,不仅是史汉文献对“初郡”的数目有明确记载,而且还有指定的空间(“番禺以西至蜀南”),此外设置“初郡”的时间也有界定(“汉连兵三岁”),即公元前111至前109年间。因此超出此空间、时间范围的汉代新设郡,就都不是“初郡”。第四,当时之所以对“初郡”有如此严格限定和区别,不仅与同一定时期内汉开疆拓土的进程有关,可能更包含了汉在某一时期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模式在内。因此,只有符合了上述两方面的限制,才能称为“初郡”*《史记索隐》提出“初郡,即西南夷初所置之郡”,不确;又认为“谓之“初”者,后背叛而并废之也”,亦非。。
由于“初郡”不仅有着疆域的概念,还包含了汉对这些边疆地区治理制度的内容在内,与特定的统治方式有关,因此笔者将之称为“初郡制度”。
二、初郡制度的内容与变化
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所创的“初郡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据《汉志》《郡国志》,汉在初郡内设置了汉郡所应有的各种职官,如郡级的太守,县道的令、长等职官。这样,随着郡、县等职官的设置,初郡从形式上就与其他汉郡之间没有太多差别。当然,从西南夷地区的记载,许多县级政权的管理者均由当地首领担任,并非汉所派遣而来。在这种情况中,汉对这些民族官员多数只是就既成事实的任命而已。此外,在初郡与中央及其他汉郡之间,还设置了必需的邮传系统*《后汉书·循吏列传》的记载看,邮传系统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可见在此之前,需要民众负担有关劳役。桂阳郡的邮驿设置在东汉卫飒任桂阳太守之时,而之前则未有。。
其二,在初郡地区“以其故俗治”,按当地旧有风俗和制度进行治理,不因其为汉属郡,而施行与汉王朝旧郡一致的汉律和制度。这种“以其故俗治”的政策,西汉时期基本上施行不变。而北方移民在当地的不断进入和繁衍,也只不过使其“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直到东汉之前,初郡依然“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2]卷53。很明显,汉武帝在设立初郡时“以其故俗治”的政策,前后承继,具有长久的政策连贯性。而如《后汉书·马援列传》所载:“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此事发生于光武帝建武十九年(43)。从其记载看,从初郡初设到马援征讨征侧胜利之时,在154年时间里,在九真郡这样的初郡地区,都一直按当地自有法律“越律”治理——尽管“越律”与“汉律”存在不少相悖之处(“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而马援在当地所做的为后世称道并遵循的工作的内容,并不是改变这种政策,而仅是重申政策——“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允许当地继续施行原有越律(“旧制”)不变,对于越律与汉律不同者,则仅“条奏”而未加擅改。此后也遵循不变——“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马将军故事”实质就是延续初郡设置之初的“以其故俗治”政策不变。据文献,在进入东汉之后,“以其故俗治”的政策开始不断遭到破坏。《汉书·南蛮传》载:“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地方官员再也不安于“虽有若无”的“无为”状况,开始进行主动的“教化”,不断改变着当地“故俗”。当然,如锡光、任延等“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的行为,东汉时期并不仅仅限于初郡。在其他非汉武帝所设“初郡”的其他华南郡国内,这种由地方官主导的改变当地习俗的行为也在不断出现。如《后汉书·卫飒传》记载:“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邓禹府。举能案剧,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后汉书·许荆传》:“和帝时,稍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而《后汉书·茨充传》也记载:“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殖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因此,从文献记载看,大体在进入东汉后不久,由地方官出面主导的改变各郡旧有习俗的行动,就在华南逐步展开。很明显,直至东汉和帝(89—105)时,当许荆任桂阳太守后,依然需要在桂阳郡内重复前任如卫飒、茨充所做的改变“故俗”的“工作”。也就是说,在经过多任地方官的主动改变后,这些故俗依然在顽强地延续,而所谓的“邦俗从化”的“教化”结果,大体上并不持久。一旦这些被称为“循吏”的地方官去任,那些“故俗”仍将顽强地“恢复”于当地。此外,如《后汉书·应奉传》载,“永兴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纳,山等皆悉降散。于是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亦是地方官在当地推行“教化”。
其三,汉王朝在初郡地区“毋赋税”,“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3]《循吏列传》,不向当地百姓征收其他汉郡内民众所必须负担的各种赋税。而由于汉在初郡地区不征收赋税,因此为了支持初郡的日常开支和发展,汉王朝规定,“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为何选择南阳、汉中郡对初郡进行财力支持,过去学者未加探究。我考虑之所以选择二郡,除了主要是因为二郡设郡甚早,发展较为成熟,有足够力量支持初郡发展外,从二郡空间位置和统属关系分析,很可能与汉中郡、南阳郡分别位于益州刺史部和荆州刺史部的最北侧,最靠近当时富庶的关中和中原,且二郡向南交通较为便利等原因有关。当时初郡的设置情况是,益州刺史部七郡,荆州刺史部一郡,交趾刺史部有九郡。三刺史部中,益州刺史部最北且富庶者即为汉中郡,荆州刺史部最北且富庶者即为南阳郡,而交趾刺史部则除南海郡外均为初郡。而从南北交通看,汉中郡向南至西南夷的道路较为近捷,而南阳郡向南至交趾刺史部诸郡的交通也较为便利。因此,可能正是从交通便利及在不同刺史部内的统属情况出发,益州刺史部内的初郡就由汉中郡负责,而荆州刺史部、交趾刺史部内的初郡就由南阳郡负责(是否如此,尚需今后更多资料证明)。。于是在“初郡”不征赋税的背景下,另择内地汉郡向初郡提供一郡官员管理和运营所需的财政支持,使其得以运转和正常发展。而这种“毋赋税”的政策,其实也并不仅仅限于初郡之内,在华南的其他一些地区也依然存在。如《后汉书·卫飒传》载:“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而与“以其故俗治”的变化一样。在进入东汉后,“毋赋税”的政策就被不断破坏或放弃。至少到东汉安帝永初七年(113)时,零陵郡中不仅已有租赋,而且租赋还可大量外调。《后汉书·安帝纪》曰:“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汉王朝在零陵郡这种“初郡”内的赋税政策的前后变化,不可谓不小。当然,这种开始或加重赋税的做法,在华南其他郡国也并不罕见。如《后汉书·卫飒传》载,桂阳郡内原本赋税较少的地方,因“流民稍还,渐成聚邑”,而“使输租赋,同之平民”,聚邑中百姓开始缴纳租赋。此外《后汉书·南蛮传》载,“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其征收赋税的范围更不断扩大。“可比汉人,增其租赋”以及各地地方官对当地故俗的主动性改造,事实上成为东汉华南郡国叛乱不断的重要原因(另文详述)。
其四,在“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下,初郡内的军队主要应由归顺的各民族首领掌管。这是因为:(1)各初郡内的民族首领原来都有一定的军队,如《汉书·南粤传》:“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粤已平”,其“夜郎兵”即为当地旧有军队。即使首领归顺,且首领有义务派遣军队跟随汉王朝参加战斗,但“夜郎兵”等各民族首领的旧有军队也不会被纳入到汉王朝整个的军队系统之中。(2)在初郡设立后,在“以其故俗治”政策下,民族首领继续保持旧有军队,因此才发生汉征西南夷参加南越国之战时,“且兰君”拒绝出兵并反叛之事*初郡设立后的记载不多,因此在此处只好采用在初郡设置前不久的文献。但从“以其故俗治”的政策看,在初郡设置后,这种情况当不会改变。。(3)从初郡即使“时时小反,杀吏”,也需“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而无法本郡处理,要近郡调兵镇压的情况看,汉王朝在初郡内应无多少直属兵卒。
因此,从“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政策出发,初郡百姓即使依然需参加军队,所参加的也应是本民族首领的军队,而不需承担汉郡兵役。而这也应是初郡兵卒甚少,在动乱发生后动辄即需他郡兵卒前去镇压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在军事上,初郡内军队由各民族首领掌管,初郡百姓不承担汉郡兵役。汉在初郡地区的军事措施,可能主要是设置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汉书·高帝纪》注“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师古曰:本谓之郡尉,至景帝时乃改曰都尉。”都尉是一地负责军事的直接负责人。,如西南夷地区犍为郡的汉阳、越雟郡的定莋、斨柯郡的夜郎,南越旧地郁林郡的领方、交趾郡的麊泠、合浦郡的朱卢、九真郡的无切,此外在斨柯郡进桑设置南部都尉。汉王朝通过设立都尉,来形成对初郡地区的军事控制。进入东汉后,华南初郡或非初郡地区的郡兵被不断征发。如《后汉书·岑彭传》:“十一年春(笔者注:建武十一年,35年),彭与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吴汉以三郡棹卒多费粮谷,欲罢之”,而这种情况均不见于西汉时期。到东汉晚期,相关情况更为常见。如《后汉书·刘表传》:“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
三、初郡制度的后果与影响
从文献看,从“以其故俗治”和“毋赋税”两项初郡制度核心内容的执行情况看,汉武帝所创初郡制度在西汉时期得以长期维持。但在进入东汉之后,就不断遭到有关郡国地方官的主动“破坏”。大体上,随着这两项核心制度的破坏,在相关郡国内,初郡制度也就随之消失。
西汉初郡制度的施行后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各地风俗长期不变。如据《三国志·吴书·薛综传》,直到东汉早期,华南很多地方依然“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保持着旧有“故俗”不变。此外,在一些非初郡的华南郡国内,如从《后汉书·卫飒传》《后汉书·许荆传》《后汉书·南蛮传》的记载看,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其二,“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西汉在初郡等地设置的官吏,大体上如《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所言的“交阯刺史以镇监之”一样,仅是镇监而已。因此由于其“无为而治”,因此在以记述政治人物活动为主的传世文献中,就未能出现西汉时期的各初郡官员姓名(《后汉书·南蛮传》有珠崖太守孙幸之名),与东汉时期层出不穷的华南各级官吏人名与事迹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其三,除儋耳郡和珠崖郡外,其他初郡内发生反叛的情况甚为少见,华南郡国的社会发展甚为平稳安定。与东汉华南诸郡国此起彼伏的反叛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四,从北方而来的汉人,与当地土著之间虽有一定的文化交流。但如《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所言,“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其是一种潜移默化般的缓慢的文化交融,与东汉时期诸郡官吏强制推行的“教化”完全不同。
从上述四个方面内容看,汉在初郡内设置了与其他汉郡大体一样的各种官吏,建设并维护起连通初郡与汉中央及其他汉郡之间的邮传系统,当是初郡设立后汉王朝在当地所做的最主要工作。设立、委派或派遣官员,建设、完善并维护和其他汉郡一致的、完善的官僚和通讯系统既是汉王朝对初郡进行有效、实质统治的体现,也是对初郡加以管理的根本保证,更是初郡地区归属汉王朝、划入汉王朝版图的直接外在表现。随着初郡的设置,汉王朝版图空前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胡绍华先生认为,东汉王朝官吏在华南推行的“教化”“帮助南方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政策,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客观上逐步缩小了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差距。”但恰如前文所言,不仅这些“教化”与“以其故俗治”的精神完全违背,而且都发生在大量破坏初郡制度的东汉时期,这种主动推行“教化”的行为,与前述在初郡地区征收租税破坏“毋赋税”政策的行为,根本违背了汉武帝所制定的初郡制度。因此,虽在当时的中原和今天看来,这些行为确实推动了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但其却不仅与初郡政策无关,且严重破坏了初郡制度。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1.
[3]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朱伟东]
The Early Prefecture System in the Han Dynasty
LIU Rui
(ArchaeologicalResearch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Xi’an710054,China;CollaborativeInnovationCenterforExcavatedDocuments&AncientChineseCivilization,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The scope of the early prefecture in the Han Dynasty could be reconfirmed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in the document, it was believed that it excluded the Coun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ointment of prefecture and county officials, the early prefecture system was very much similar to the one in the Han Dynasty. The Policy of Rule by Customs remained almost unchange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ith a long-term continuity. Ye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is policy was repeatedly spoiled by constantly increasing taxes and corvee of the minorities until they wer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Han people, and by the local officials’ changing the old customs, as a result, revolts grew intensified in the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the Southern China, eventually, the early prefecture system gradually disappeared due to the changes in the Policy of Rule by Customs and the Policy of Zero Tax.
Han Dynasty; early prefecture system; national governance; change
K691;K928.6
A
1001-0300(2017)02-0013-06
2016-10-06
刘瑞,男,山西晋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历史文化与考古研究。